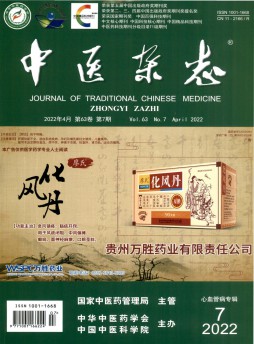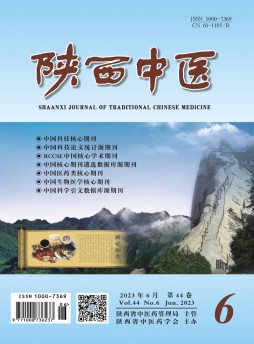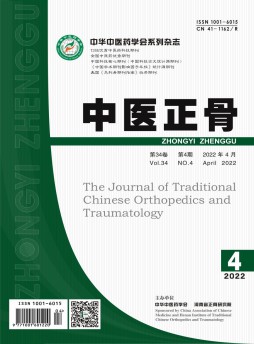中醫哲學及其相關知識內容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中醫哲學及其相關知識內容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中醫學是中國傳統中寶貴的文化形式,是中國科學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國生命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中醫學的進步不但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繁衍有過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堅實的本體論基礎而持久的影響了中國文化發展的理路,“儒必通醫”就是最好的說明。
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的歷程,西方的醫學思想和醫療模式也開始輸入中國。由于西方醫學在治療技術上的方便性,使之國人在醫療實踐中能夠接受西醫的治療方式,但是,正是這種實用主義和“全盤西化”的價值承諾形成了對中醫學和中國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現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數典忘祖、思想淺薄、急功近利成為學術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醫學也成為被否定的內容之一。為了提供否定中國文化的理性基礎,自覺的不自覺的以西方的哲學思想判釋中國文化的方法就成為時代的風氣,以西方的醫學模式判釋中醫學以比較兩者的優劣,成為這個時代中醫學研究的重要特點。如果說以西方醫學技術上的特點做為可接受的標準還帶有實用主義的特點,從而還能在經驗論的層次上證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盤西化”對中國文化及其對中醫學的否定就是對中國文化理性自覺的背叛,而成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時至今日,隨著對西方科學文化產生的一系列誤區的深入認識,中醫學在醫學實踐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療效被肯定,中醫學也日漸受到重視。但是,對中醫學的肯定仍然是在經驗論的層次上,遠沒有在哲學理性上實現自為而自在的統一。尤其對于解決這一已經產生了幾千年的中醫文化的繼續發展的理路問題而言,就更需要哲學的根據和支持。
問題表明,對中醫學的正確認識及其發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醫哲學的研究作為基礎。然而,以我們已經熟悉并習以為常運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學思維進行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結果的。以西方哲學的模式為坐標系進行中醫學的研究,其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正確的方法是,應對中國文化之所以能產生中醫學的哲學思想進行發掘,進而研究中醫學的科學性,以對中醫學的發展方向作出推定。這些是研究中醫學發展應解決的基礎理論問題,應當成為一切關心中醫學發展的學者應投以相當大的精力進行研究的問題。但是,對于中醫學發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對的問題既是中醫哲學帶來的也是以哲學對中醫學提出的本體論承諾出現的。這表現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醫學學科的科學性及其產生的哲學基礎與我們所熟知并運用自如的現代科學和哲學對其進行研究而產生的誤區,另一方面則要求中醫學本身能證明自身的科學性和哲學基礎,即中醫學的學科性在本體論哲學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學形式與哲學方式的統一──中醫學是中國哲學形而中論的自在自為的統一。
就中國哲學的基本原理進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學原理與中醫學有怎樣的相關性以及中醫學表現出怎樣的規律,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哲學和中醫學的關系,表明了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在與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的統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學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義。如果說由于中國文化的哲學基礎生成了中醫學的學科形式,從而表明了中國文化的一以貫之的理論特點,那么,中醫學就在其內容和形式中展現出的基本規律將代表中國文化和哲學的基本形式。因此,應當說,進行中國哲學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國哲學奧秘、并認為中國哲學是不同于西方哲學的、具有獨立的哲學形式,就應在《周易》、《道德經》和《內經》及《論語》等儒家和道學經典的研究上下功夫,這是研究中國哲學的基本方法,同樣,這也是研究中醫哲學的基本方法。
對中醫學的哲學思維進行的研究,以發現其基本規律,這是中醫學的基礎理論問題,這已成為現代以來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全盤西化”、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結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學推定中國哲學的研究一樣,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對中醫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進行西化式的推定。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由于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中國文化對哲學的承諾及其原理的推定,應當認為這些推定的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哲學的本來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學和西醫學對中醫學理論的異化。
如果承認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性,并且承認中國文化的形式具有獨立性──中醫學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醫學的形式,那么,對生成中醫學的哲學思維及其基本規律的研究只能是對中國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學反思──哲學的承諾和推定的統一并進行推定的結果。生成文化的歷史和邏輯只能是歷史和邏輯在文化形式中的統一。所以,對生成文化的哲學基礎進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諾的哲學──哲學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學形式上的統一。哲學在文化母體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諾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來文化所承諾的哲學進行推定。以西方哲學進行的推定,只是一種比較意義上的詮釋,哲學的比較不具有本體論承諾和推定的統一性,本體是自身的邏輯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學在當代的進展產生了分析哲學和解釋學,其理路表明的邏輯和形式對思維的限定,使對西方哲學思維方式的運用產生了嚴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內在結構──被語言和文字及形式邏輯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內部所進行的歷史文本的解釋──以其自在的語言系統和思維方式對文本所進行的解釋,不可能達到本來的意義。既然對自在的文化的解釋呈現出重重困難,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語言本身所進行的解釋都不具備其文本意義,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學原理和學科形式對中國的文化和哲學進行解釋呢?真不理解當代中國學界何以能用西體西用的方法論進行中國文化的研究,并自以為是的認為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規律”。當以中國哲學自在的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與這些“基本規律”(例如辯證法)進行比較后,就會發現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維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簡單的類比和實現哲學思維方式的統一。因此,就中國哲學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諾推定法進行哲學的外化。承諾推定法表明的哲學思維與文化形式的統一性表明,任何一種獨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因此,中國文化的形式和內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國哲學思維產生的結果。
所以,對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以哲學的承諾和推定法進行的研究。由于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只能在中國文化的母體中尋求,所以,這種研究只能是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這一研究還必然包括:中醫學的哲學究竟是什么形式的?與中國哲學的關系是怎樣的?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形成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問題。顯然,在這一研究進路中,將同時構成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中,以《時空統一論》⑴的哲學原理對中國的知識系統進行承諾推定法的研究反思,發現在中國文化的知識形式中,《易經》是中國哲學的基礎,而中醫學是運用中國哲學思維所產生的成熟的科學形式,也可以這樣認為,從中醫學中可以反映出中國哲學的本質性,所謂“醫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國哲學的本質性與中醫學的統一是以怎樣的原理表現出來的?這是研究中醫學的哲學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所以,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的是用哲學的承諾推定法把《易經》的思維方式外化為哲學的形式。我對《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形式的工作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易經》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論⑵的哲學原理進行了對中國哲學的概括,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及思維方式表明,時空對應的認識論原理、對應和中的方法論原理、中和統一的時空本體論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因此,中醫學能否反映出這三個基本規律就成為承諾和推定中醫哲學的基本工作。
從中醫學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維方式并對其進行與中國哲學原理的整合是這一研究工作的組成部分。由于中醫學的思維方式與《易經》統一,所以歷代中醫學者對“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醫章虛谷說:“詩、書、春秋,論世間事跡,褒君子,貶小人,以明治亂之所由,原非論陰陽之理者。《易》象表陰陽進退消長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事之道。……故易為大道之源,醫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辭》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醫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真與易書比哉?醫經與易經,體同而用異,拙集屢申其義矣。即將先天后天打作兩橛,遂有一橛截全體之見,而不識其體用所在也。圣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假年學易,不聞學醫,蓋以此也。圣人為治世之大道,不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達不敢當。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猶先于大道,何故?蓋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醫道也。其理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故體同而用異也。”(《章虛谷:《醫門棒喝·論易理》)顯然,章虛谷對《易經》和醫經的哲學關系的認識是深刻的。由于中國哲學的外化是當代哲學的研究任務,因此,和所有對“醫易相通”有相當深刻認識的古代學者一樣,這一研究是以《易經》自在的哲學思維的承諾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闡釋中醫學的哲學思維的。
筆者以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結果。既然中醫學的哲學基礎是形而中論的統一,那么,中醫學在形而中論哲學思維中生成的基本規律是怎樣的形式、以及這些基本規律對中醫學發展的基本意義之所在就成為中醫哲學研究的重要的價值論承諾。
《周易》和《道德經》及《內經》的哲學思維對當代的哲學發展及對中醫學的繼續進步將有極重要的意義。這已在近年的中國文化熱中顯見端倪。筆者在對人存在的本質性問題的研究中,結合西方哲學中的問題,以哲學的承諾推定法對《周易》的道器之論之承諾,推定出形而中論的哲學。形而中論的哲學認為,人對存在的認識,是以形作為主體認識、并區分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體地位實際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時空的方式建立起對形的認識,因此,形而中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建立在時空的本體論基礎上,并且與中醫學的時空觀統一。所以,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能很好的解決一系列重大的中醫學哲學問題。
二、醫易相通
隨著世界學術界對《周易》研究的關注,“醫易相通”作為中國古代學術史上重要的哲學命題,在當代尤為引起重視。“醫易相通”的承諾表明,其不朽的意義和學術魅力發生于對人類生命本體的哲學思考和推定。“醫易相通”概括了易學的哲學思維作為中醫學理論基礎的基本特點,其不但表現出易學的博大精深,同時也說明了中醫學理論基礎一以貫之的哲學內涵。顯然,從內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醫學理論基礎的易學哲學性質。《周易》的形而中論的哲學制式,表明其哲學思維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學思維。就醫學的作用和價值而言,中醫和西醫這兩種不同的醫學理論和實踐特點表明了其起源于兩種不同的哲學思維,從對存在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及其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諾不同的價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疇和理論體系。對主體存在本質的不同認識,使其對生命形式本體的認同形成不同的醫學觀念,在此基礎上的發展,使我們看到了人類對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歷史形式中和由此產生的現實問題──中醫和西醫展現在歷史中的不同的邏輯理路和學科建構。
然而,對當代人類社會的存在而言,就哲學的層次上推定人類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認為雖然有西方自然科學近三百年來的主導和促進,但是,人類就基本的存在問題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質性問題,還是作為一個亙古常新的課題困擾著人們的理性。近現代表現出所謂的人類進步絕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現在人類生存本質上的進步,可以說,到目前為止,人類是在其自為的異化形式下存在,對人類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為的對自在的超越──自為的達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實現自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顯然,人類的存在現狀表明,人類還遠遠沒有達到這一目標。
因此,當西方科學模式對人們所期望解決的終極關懷問題不但沒有解決,而且又由此產生了嚴重的可持續性發展問題時,人們已經顯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學產生的負面價值引起人們的反思時,后現代主義的哲學和文化思潮應運而生。可以說,后現代主義思潮表明的對理性否定的堅決性已經成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學理性的重大問題。一些思想家把力圖走出誤區的方法寄托于中國文化時,中國的《周易》就不失時機的又一次成為顯學。對中醫哲學的研究而言,面對后現代主義哲學思潮,當企圖再以西方哲學的制式推定中國文化時,無疑是當頭棒喝。在這種形勢下,對于中醫哲學研究而言,許多學者不約而同的想到了“醫易相通”的古老命題。所以“易學熱”也把中醫哲學帶入其中。但是,就其以“醫易相通”為命題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卻令人倍感失望,因為其產生的結論,無不帶有西方哲學的“前見”。問題表明,因為《周易》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中醫學的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統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學的制式不可能正確的推定中醫哲學。中醫哲學由《周易》的哲學制式所推定,這是應當首先明確的問題。
顯然,后現代主義表現出的西方哲學的多元性及其帶來價值取向的多元性對理性的異化是顯而易見的。即使在當代中國,也隨處可見西方文化的哲學、科學和宗教以各自的價值承諾帶給人們存在方式的異化。以《周易》為基礎的中國哲學的一以貫之,不但使“醫易相通”,而且使《周易》與中國古代科學相通、《周易》與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為中國文化的基石。可以說,綜觀人類文明的幾大形式,沒有任何一個文明能像中國文明那樣能夠錦延不絕,持續發展并表現出文化的穩定性。西方哲學表明,就哲學問題及其表現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學家們在近代和當代由于他們內在哲學傳統思維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顯得無能為力,最終以據斥形而上學作為西方哲學的終結。然而,問題卻沒有解決,問題伴隨著其造類存在的異化在當代使人們終于注意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優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學思維巨大的差異性,所以盡管《周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學及科學和宗教是對存在形式化的結果,所以,不能將《周易》與西方文化及哲學作簡單的類比,例如我們看到的把《周易》比附為科學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認定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樣。形而中論表明,《周易》的重要貢獻是其哲學的本體論思想,在這方面,同樣不能與西方哲學的本體論作簡單的比附。對西方哲學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學是內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學作為明確的形式外化出來,是一項歷史性的任務,《周易》哲學的外化將帶來人類哲學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醫學的學科形式表明,其屬于不同的知識形式和結構,之所以稱為“醫易相通”,是指其作為共同的哲學本體而言的,具體講,《周易》的哲學思維是中醫學的基礎,易道廣大使中醫學與《周易》在“道”的層次上相通。因此,對道的理解問題成為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這屬于哲學層次的問題,在中國的學術史中被歷代學者所重視,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經之首的學術地位,但是,在西學倡興的當代,則帶來了更重要的問題,這就是,以《周易》為首的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關系和相互的哲學承諾,成為人類文化交融中的問題,尤其是人類發現其自身歷史的和社會的、群體的和個體的行為方式所引起的價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質作為反思的對象時,以《周易》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就又一次為人類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類存在的問題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發出其他所有問題的都應歸結為一個基本問題──這就是所謂的終極關懷問題,“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表明了其與西方醫學和哲學的截然不同的本體觀──而西方哲學對終極關懷的無能為力在后現代主義哲學中已經充分的暴露無遺。中醫學家、道家及道教學者在對“醫易相通”的基礎上和以自身的醫療及修煉實踐中形成的中國生命科學關于人的本質和應達到的存在方式,解決了終極關懷問題。中國的生命科學表明,“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和推定與《周易》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說卦傳》)終極關懷的價值論承諾的統一,是“醫易相通”的重要表現形式。
關于“醫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醫學的基本理論方面,在中醫學的發展過程中,張介賓的論述簡要而精到的指出了“醫易相通”的基本意義。他說:“賓償聞之孫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醫,每竊疑焉。以為易之為書,在開務成務,知來常往;而醫之為道,則調元贊化,起死回生,其義似殊,其用似異。且醫有內經,何借于易,舍近求遠,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學到知羞,方克漸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陰陽二氣造化萬物;人身之理,以陰陽二氣而長養百駭。易者,易也,具陰陽動靜之妙;醫者,意也,合陰陽消長之機。雖陰陽已備于內經,而變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陰陽也;醫易同原者,同此變化也。豈非醫易相通,理無二致,可以醫而不知易乎?”又說:“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醫,欲賅醫易,理之陰陽。故天下之萬聲,出于一闔一辟;天下之萬數,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萬理,出于一動一靜;天下之萬象,出于一方一圓也。方圓也,動靜也,奇偶也,闔辟也,總不出乎一與二也”、“予故曰:易具醫之理,醫得易之用。學醫不知易,必謂醫學無難,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終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醫,必謂易理深玄,渺茫難用也,又何異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饑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錯過了此生。然則醫不可以無易,易不可以無醫,設能簡而有之,則易之變化出乎天,醫之運用由乎我。”
上論表明,張介賓非常精練的總結了“醫易相通”的基本意義。把醫學和易學在天地萬物存在的基本層次上統一起來,使之形成易體醫用、體用不二的一元論哲學思維,是中國哲學和醫學上的重要思想。
總結前人在“醫易相通”方面的研究,應當認為《周易》對中醫基礎理論的影響是重大的。《周易》是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其具體影響了中醫學的臟腑理論、經絡理論、陰陽氣血理論、病理病機理論、診斷理論、治療理論、方劑學和本草理論。而在當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學領域內的具體運用──“氣功”理論成功的運用易理,可以作為“醫易相通”最好說明。
以當代的哲學觀推定“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必然要求從哲學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層次分析《周易》對中醫學的影響。《周易》的陰陽之論表明,陰陽之道是時間和空間產生的并由主體承諾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體是時空的陰陽變化生成的存在。陰陽之道的推定是主體所能發現本體存在之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體而言,《易傳》認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所以,陰陽能對人體的存在發生生命的本質性作用是因為時空的本體性,而這種本體性作用與主體性方式的正確統一,是在主體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產生的正確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易傳》)的命題承諾和推定。人作為一種存在,本身是屬于《周易》哲學推定的哪一種形式呢?人是什么呢?這些問題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為哲學所關心的也必須給預回答的主體論哲學承諾和形式推定的重要問題。但在《周易》哲學中,是不作為問題的,因為結論已經內化于“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承諾之中。所以。對應于西方哲學的主體論承諾而言,《周易》對這一問題沒有作出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關于人的主體性的中醫學中推定這一與《周易》相關的哲學問題,對今天的人類哲學而言是重要的。我認為,《周易》的哲學模式表明,從“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承諾的主體論作出的形式推定,說明了人的主體形式既不屬于形上之道,也不屬于形下之器,而是屬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謂之人。所以,主體被形而中所承諾──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謂的形而中者,以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時空層次和主體意識時空能力的對應和中,通過主體時空方式所能把握主體自身存在和客體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過主體的形而中實現對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確認識。
“醫易相通”是中國生命科學中的重要命題。“醫易相通”的形而中論哲學推定,使主體的生命存在形式成為中國生命科學研究的內容。形而中者謂之人的主體論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體將通過對時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實現主體的價值。主體能夠適應時空層次,并通過時空陰陽的形而中的自我操作而把握存在,從而超越生命的時空形式。這是形而中論哲學承諾的生命科學原理。形而中者謂之卦──形而中者謂之人的統一,從而解決了認識論的主體性問題。形而中論哲學表明的認識論本質是:人沒有獨立的主體性,客觀實在也沒有獨立的客體性,自為是自在的自為,而自在也是自為的自在,世界的時空統一性要求人類把握的世界要成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對客觀的存在而言,絕沒有獨立性可言,人的主觀存在也絕沒有獨立性,因此,在方法論上的建構,《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統一,形而中論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學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對人類哲學發展作出的重要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及方法論方面的貢獻,其由形而中的主體方式承諾和推定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學將成為人類科學的終極形式。
在“醫易相通”中,以陰陽的概念范疇承諾了哲學認識論。《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陰陽的推定成為中國哲學中的基本概念范疇。在中國文化中,陰陽范疇的具體應用,可謂一以貫之。在中醫哲學中,陰陽承諾了哲學本體論的邏輯推定和主體論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中有陰,陽中有陽”(《素問·金匱真言論篇第四》)等等。張介賓認為:“陰不可以無陽,非氣無以生形也;陽不可以無陰,非形無以載氣也”(《類經附翼·求正錄·真陰論》);石壽棠認為:“陽不能自立,必得陰而后立,故陽以陰為基,而陰為陽之母,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后見,故陰以陽為統,而陽為陰為父”(《醫源·陰陽互根論》);吳謙等認為:“一陰一陽者,天地之道;一開一和者,動靜之機”(《醫宗金鑒·刪補名醫方論》卷二·六味地黃丸集注);鄭壽全認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陽氣乎!陽氣無傷,百病自然不作,陽氣若傷,群陰即起”(《醫理真傳》卷二·陽虛證問答目錄)柯琴認為:“陰陽互為其根,陽中無陰,謂之孤陽;陰中無陽,便是死陰”(《傷寒來蘇集·傷寒論注·卷一·傷寒總論》)等等。從上面眾多的論述中,可以看出陰陽概念在中醫學中的應用是相當廣泛而重要,并且在邏輯上是自恰的。如果陰陽的推定方式對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論哲學的對應和中的推定方式,將使這一自律由主體的自為而實現。這是“醫易相通”承諾的中國生命科學自在性的表現。
三、形而中論與中醫學
如果把《周易》作為群經之首,那么,中國的哲學原理就應當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的形式化,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為哲學形式的──形而中論是對“卦”的時空本質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謂之卦”的命題產生的哲學原理。關于“形而中者謂之卦”,我已多次進行論證⑴,在這里再簡單的作一介紹。“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思維以時空方式生成對存在的認識,中國哲學是以“卦”作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認識論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這就是說,“卦”是存在與思維的統一方式──存在與思維的對應和中,“卦”是“道”、“器”的對應和中者也。因此,筆者認為“形而中者謂之卦”,這是中國哲學的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現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質性而言,因“卦”承諾了主體論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統一,就有形而中者謂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謂之人的哲學推定表明,主體的對應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是由形而中論哲學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及價值論承諾和范疇推定的統一而實現的。
筆者在關于《周易》的研究方面,從認識論的角度把“卦”的哲學內涵歸結為“形而中者謂之卦”,“卦”的形式為陰陽爻表示的“時”和“空”,由此使“卦”無所不包,“卦”作為萬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極”,才能推定“太極”承諾的本體。把“太極”以“太極圖”和“八卦圖”統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論的哲學推定。具體講,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與主體對應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極”或“無”是不能與主體的形式對應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體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體,即本體不能作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體只能以時空進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簡單的討論形而中論的幾個基本問題。新晨
“卦”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形而上者謂之道”《周易》的一個基本承諾是關于人作為主體對客觀事物的推定方式,即主體的形而中性決定了和中為是。和中為是來源于《周易》的本體論承諾。《易傳》中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推定《周易》本體論承諾的依據。一陰一陽者,太極所生之兩儀也,故,兩儀之所統者,乾、坤者也。關于乾,《周易·乾·彖》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關于坤,《周易·坤·彖》說:“至哉坤元,萬物資始,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和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乾坤作為“萬物資始”,太極之生也。所以,“太極”作為本體,是形而中對形上之道的的推定方式。
在《周易》的研究中,把本體論的哲學承諾以太極生八卦的方式進行推定和以“太極圖”方式的推定,進而以“八卦圖”與“太極圖”的復合方式的推定,是以“象數”表達《周易》哲學原理的推定方式。“象數”的推定方式有其直觀的意義,其中表達出《周易》關于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及價值論承諾和范疇推定的統一,這是中國哲學獨具特色的方式之一,這一方式也是西方哲學力圖達到的一種境界,而中國哲學早在幾千年前就已經達到了承諾和推定的統一性。但是,對中國哲學的這種推定方式,卻不能以西方哲學的原理去加以理解,因為西方哲學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及價值論承諾和范疇推定的邏輯形式是與中國哲學不同的,西方哲學的推定是形式化的制式,而中國哲學是方式化的制式。西方哲學史表明,自亞里士多德以后,以形式化的制式推定本體,產生了西方哲學中的不可克服的本體論困難。把“太極圖”和“八卦圖“結合到一起,一般認為這種方式是在朱熹之后才開始的,在此之前即使有太極圖,也沒有人將其與八卦結合在一起。周敦頤的“太極圖說”開創了這一推定的方式。把兩者的結合,即把“太極圖”放到“八卦圖”的中心,使“八卦圖”的推定統一于“太極圖”的邏輯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