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罌粟在古代的醫藥作用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淺析罌粟在古代的醫藥作用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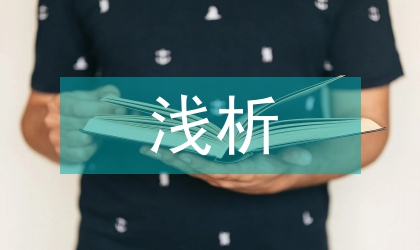
清代雍正、乾隆年間,吸食鴉片煙風氣日漸蔓延開來。尤其是到了嘉慶、道光年間,隨著走私貿易的猖獗進行,鴉片對于中國社會構成了嚴重威脅。許多學者對于當時的鴉片危害和走私輸入情況進行了認真研究,澄清了許多問題。但是,到目前為止,關于罌粟與鴉片傳人中國的早期情況,尤其是二者傳人中國之后對于古代中國人的社會生活究竟產生了哪些重要影響?還很少有人進行深入探討。為了弄清這些基本事實,筆者收集了大量資料,現在予以初步梳理,以期得到對罌粟和鴉片史的正確認識。
一、罌粟種植在唐代傳入中國
在小亞細亞和地中海沿岸,人類種植罌粟和采集鴉片的歷史十分悠久①。一種說法是,在公元七世紀罌粟種植與鴉片生產已經傳人中國。依據的是這樣一條資料:“乾封二年(667),(拂秣國國王)遣使獻底也伽”②。拂襪,舊稱“大秦”,即東羅馬帝國。“底也伽”是neriaka的音譯,是一種治療痢疾的特效藥物,其中含有鴉片的成分。筆者認為這是含有鴉片質的藥丸偶爾的少量輸入,而不是真正鴉片輸入的開端。主要理由有三:第一,“底也伽”與鴉片的概念不同,這正如罌粟不是鴉片,鴉片不是嗎啡,嗎啡不是海洛因一樣,盡管后者都是由前者提取加工制成的;第二,自唐代到明成化年間,史籍浩繁,目前還沒有發現有關鴉片向中國輸入的正式記載,因此,把數百年前的偶爾的零星含有鴉片的藥丸作為鴉片輸入中國的開端是不妥當的;第三,鴉片最初是作為藥物向中國輸入的,應當在醫藥典籍上有應用記載,然而查閱唐、宋、遼、金、元數百年間的重要醫藥書籍,從民間配方到宮廷醫案,并未提及鴉片的臨床應用。筆者認為,依據上述這條孤零零的材料將公元7世紀視為鴉片輸入中國的開端是不妥當的。但并不否定,罌粟種植在中國始于7世紀末或8世紀初,主要是罌粟種植在當時已經成為事實。一首唐詩這樣寫道:“開花空道勝于草,結實何曾濟得民。卻笑野田禾與黍,不聞弦管過青春”④。這是迄今為止,我們查閱到的中國最早的關于罌粟的種植記載。米囊花是罌粟的別名。作者郭震(656~713),字元振,魏州貴鄉(今河北大名東南)人,咸亨四年(673)進士。先后任通泉尉、右武衛鎧曹參軍、奉宸監丞等職位;長安元年(701),任涼州(治所在甘肅武威)都督;神龍二年(706),為安西(唐代方鎮之一,所轄龜茲、疏勒、于闐、焉耆,均在天山以北)大都護;太極元年(712),任朔方(為唐代方鎮之一,又稱靈武,或靈州,治所在今寧夏靈武西南。)大總管;開元元年(713),任饒州(州名,治所在今江西鄱陽)司馬,病死途中,封代國公。由于作者生活在七世紀末或八世紀初,我們斷定,罌粟傳人中國的時間為七世紀末或八世紀初。又由于作者的鎮所均在寧夏、甘肅、新疆境內,我們斷定,罌粟種植在長安以西的絲綢之路上。是時,人們對于罌粟的認識尚局限在庭院花卉觀賞階段。到了九世紀,漢中與成都盆地的田地中已開始種植罌粟。晚唐一位詩人在馬上吟誦道:“行過險棧出褒斜,出盡平川似到家。萬里客愁今日散,馬前初見米囊花”④。詩中的“險棧”,指北棧道,即沿著褒水、斜水所修建的棧道。自陜西鳳縣東北草涼驛入棧,西南至鳳縣折向東南,經留壩,又南至褒城舊治北雞頭關出棧。五代以前,前往四川,通常經褒谷南下蜀中。“褒斜”,乃是古道路名,與終南山之褒水、斜水平行,為古代連接關中平原與漢中盆地之要道。自漢至五代,凡南北兵爭,雙方行軍往往取道于此⑨。作者雍陶,字國鈞,成都人。太和(828—835)間登進士第。大中八年(854),自國子毛詩博士,出任簡州(治所在今四川簡陽)刺史。在上任途中,途經褒斜到達漢中,看到米囊花,異常興奮,立即產生回到家鄉的感覺。是詩證明,詩人家鄉成都地區與漢中的田野里已有罌粟種植。晚唐另一位詩人在《江南雜題三十首》中寫道:“碧抽書帶草,紅節米囊花”@。由此可知,晚唐江南地區已開始種植罌粟。江南詩人李貞白,對于罌粟生長情況業已非常熟悉,否則,對于其蒴果形狀的描寫不會如此逼真:“倒排雙陸子,希插碧牙籌。既似犧牛乳,又如鈴馬兜。鼓捶并瀑箭,直是有來由”回。從上述詩人的吟詠情況來看,罌粟傳人中國的時間大致在7世紀末或8世紀初。唐代屬于罌粟移植中國的初期階段,人們對于罌粟的認識基本局限在花卉觀賞上。《備急千金方》和《銀海精微》是盛唐醫學家孫思邈(581~682)集其大成的醫藥著作,其中沒有一個藥方涉及罌粟。《顱囟經》二卷,則是唐末宋初的醫藥著作,亦無關于罌粟的任何配方。這說明,罌粟的醫藥價值在唐代還沒有被醫家所認識。
二、宋遼金元時期的罌粟醫藥價值
到了北宋時期,罌粟種植范圍進一步擴大。大詩人蘇軾之弟蘇轍閑居潁川,開始向當地農夫學習種植罌粟,留下《種藥苗二首》,其中一首為《種罌粟》:“筑室城西,中有圖書。窗戶之余,松竹扶疏。拔棘開畦,以毓嘉蔬。畦夫告予,罌粟可儲。罌小如罌,粟細如粟。與麥皆種,與棕皆熟。苗堪春菜,實比秋谷。研作牛乳,烹為佛粥。老人氣衰,飲食無幾。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槌石缽,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調養肺胃。三年杜門,莫適往還。幽人衲僧,相對忘言。飲之一杯,失笑欣然。我來潁川,如游廬山。”從這一首詩可以看出,在北宋時期罌粟的功能還很有限,苗可以當成蔬菜食用,籽可以充饑,熬成“佛粥”,可以治病,調肺養胃而已。在引子中蘇轍寫道:“予閑居潁川,家貧不能辦肉。每夏秋之交,菘芥未成,則盤中索然,或教予種罌粟、決明,以補其匱。寓潁川諸家,多未知此,故作種藥苗二詩以告之”㈣。潁川,古郡名,治所在今河南省禹州。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潁川的農家已經有人掌握了罌粟栽培技術,而從外地遷移到潁川的移民大多不了解罌粟的種植技術與食用功能,這說明罌粟種植在當時還不普遍,所以,詩人感到有必要以詩歌方式向朋友傳播罌粟種植技術和食用方法。無獨有偶,另一位詩人也用詩歌詳細記述了自己種植罌粟的情況:“前年陽亢驕,旱日赤如血。萬里隨羽書,揮鞭無留轍。炎毒乘我虛,兩歲苦病喝。遇夏火氣高,煩蒸不可活。飽聞食罌粟,能滌胃中熱。問鄰乞嘉種,欲往愧屑屑。適蒙故人惠,筠篋里山葉。堂下開新畦,布藝自區別。經春甲未坼,邊冷傷晚雪。清初氣忽動,地面龜兆裂。含滋競出土,新綠如短發。常慮蒿莠生,鋤剃不敢缺。時雨近沾足,垂凌爭秀發。開花如芙蓉,紅白兩妍潔。紛紛金蕊落,稍稍青蓮結。玉粒漸滿房,露下期采折。攻疾雖未知,適愿已自悅。呼童問山鼎,芳乳將可設”⑨。是詩作者李復,字履中,先世居住祥符(今河南開封市),因其父官關右,遂移居長安。元豐二年(1079),登進士,官至集賢殿修撰,有《滿水集》。“滴水”,在今長安縣境內。作者種植罌粟的目的是為了獲取罌粟籽,以治療胃病,“能滌胃中熱”。這與蘇轍的上述認識是基本一致的。北宋時期,罌粟的使用范圍基本限于熬制“罌粟湯”和“佛粥”。關于“罌粟湯”,大詩人蘇軾在《歸宜興留題竹西寺》詩中有所提及,“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罌粟湯”凹。江西詩人黃庭堅亦有這樣的詩句,“女奴煮罌粟,石盆瀉機泉”@。江南宜興的“童子能煎罌粟湯”,江西的“女奴煮罌粟”,固然證明罌粟不太罕見,但同時也說明仍然比較珍貴,畢竟是用來招待貴客的物品。正是由于比較珍貴,罌粟成為達官貴人互相饋贈的禮物凹。關于“罌粟湯”的養胃健身的功能當時人比之“丹石”,也有明確記載。“茶粒齊圜剖罌子,作湯和蜜味尤宜,中年強飯卻丹石,安用咄嗟成淖糜”凹。而“佛粥”,又稱“罌粟粥”,配料及熬制、服用方法如下:“白罌粟米二合,人參末三大錢,生山芋五寸長,細切研三物。以水一升二合煮取六合,人生姜汁及鹽花少許,攪勻,分服。不計早晚食之,亦不妨別服湯丸”凹。大致說來,罌粟在醫藥學中具有驅除邪熱,養肺健胃的醫療保健作用,這是北宋時期人們對其醫療功能的基本認識。北宋末年的一本藥物學著作如此總結前人的種植經驗和醫藥效果:“罌子粟,舊不著所出州土,今處處有之。人家因園庭中多蒔以為飾花,有紅白二種,微腥氣。其實作瓶子,似髂,箭頭中有米,極細。種之甚難。圃人隔年糞地,九月布子,涉冬至春始生苗,極繁茂矣。不爾,種之,多不出,出亦不茂。俟其瓶焦黃,則采之。主行風氣,驅逐邪熱,治反胃,胸中疾滯。丹石發動,亦可合竹瀝作粥,大良。然性寒,利大小腸,不宜多食。食過度,則動膀胱氣耳”@。到了南宋、遼、金、元時期,罌粟的種植范圍進一步擴大。著名詩人楊萬里對于罌粟寫下膾炙人口的詩歌。“鉛膏細細點花梢,道是春深雪未消。一斛千囊蒼玉粟,東風吹作米長腰。鳥語蜂喧蝶亦忙,爭傳天詔詔花王。東皇羽衛無供給,探借春風十日糧”∞。關于罌粟的種植、生長情況以及使用功效,周紫芝寫了兩首詩。第一首詩是《種罌粟》@,第二首詩是《罌粟將成》∞,所談醫藥功能與北宋時期相同。與北宋相比,除了詩人在詩歌中繼續吟誦罌粟之外,南宋時期有許多文人在筆記、文集和方志中開始記錄罌粟的種植和使用情況。陳元靚在《歲時廣記》中如此寫道:“重九日,宜種罌粟,早午晚三時種,開花三品。按本草名罌粟子,味甘平,無毒,主丹石發動,不下食者,和竹瀝煮作粥,食之,極美。一名象谷,一名米囊,一名御米花”q9。這一記載反映了南宋時期對于罌粟的不同稱呼。“罌粟”、“米囊”、“象谷”、“御米花”等,都是時人對于罌粟果實形象性的稱呼∞。這里需要注意的是,人們對于罌粟的認識當時還停留在養胃治病水平上,很有局限性。在南宋時期的方志風物記載中,涉及罌粟的地方較為模糊,大抵重復前代詩人的認識。如:《淳熙三山志》日:“罌粟花,有紅白二種。九月布子,春深乃生實,如小罌,子如細粟”@。《重修毗陵志》云:“罌小如罌,粟細如粟,與麥皆種與椽皆熟,斫作牛乳,烹為佛粥”管。《新安志》記載:“有罌子粟,結房如瓶罌,如骨高箭,花艷好,而實細美,非他粟之類”曰。這種記錄,說明罌粟的種植和使用情況,尚不是十分普及。尤其是在遼人、金人控制的北方地區,罌粟種植還是比較困難的事情。正是種植罌粟在北方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金代山西詩人元好問才有“花有如罌粟,能同橘不遷”的感嘆鑼。南宋、遼、金、元時期,罌粟在醫藥學上進一步發揮作用,除了治療肺胃等疾病之外,開始更多地用于治療咳嗽、痢疾等頑癥,并解金石之毒。可以說,這一時期罌粟在醫藥學上得到了積極的應用,有益于中國人的身體健康。
三、明朝的鴉片輸入及其醫藥價值
罌粟在明朝的社會生活中作用越來越大,不僅在日常生活中以罌粟為原料,可以制成各種美味佳肴蟄,而且在治病救人方面也得到了充分利用。李時珍全面總結了前人的經驗,對于罌粟的生長情況和醫療功效作了更精細的記載,指出:“罌粟秋種冬生,嫩苗作蔬食甚佳。葉如白苣,三四月抽薹結青苞,花開則苞脫。花凡四瓣,大如仰盞,罌在花中,須蕊裹之。花開三日即謝,而罌在莖頭,長一二寸,大如馬兜鈴,上有蓋,下有蒂,宛然如酒罌。中有白米極細,可煮粥和飯食。水研濾漿,同綠豆粉作腐,食,尤佳。亦可取油。其殼入藥甚多,而本草不載,乃知古人不用之也”∞。在他看來,罌粟籽,甘平,無毒,可以行風氣,逐邪熱,治反胃和胸中痰滯;罌粟殼,可以止瀉痢,固脫肛,治遺精,斂肺澀腸,治咳嗽,止心腹、筋骨諸痛@,書中記錄了大量處方,限于篇幅,在此恕不一一例舉。現在,我們把注意力轉向鴉片的輸入和使用。查閱中國各類圖書,在元代以前的圖書中沒有發現任何關于鴉片的信息,因此,我們可以斷言,在元代之前不僅外國鴉片尚未輸入中國,而且中國人也沒有掌握鴉片的采集方法。“鴉片”,又寫作“阿片”,是外來詞語opium的音譯。“鴉片”的別名為“阿芙蓉”或“合甫融”,也是一個外來詞語,是阿拉伯語afyun的音譯。由此可見,“鴉片”最初是一種舶來品。那么,鴉片究竟是何時輸入中國呢?在明朝的圖籍中,最早出現記錄鴉片信息的是一本名為《蟬精雋》的書籍。是書分條記載有關史事,作者在其第十卷“合甫融”一條中這樣寫道:“海外諸國并西域產有一藥,名‘合甫融’,中國又名鴉片。壯若沒藥,而深黃,柔韌,若牛膠焉。味辛,大熱,有毒,主興助陽事,壯精益元氣。方士房中御女之術,多用之。又能治遠年久痢,虛損元氣者,往往服不三數分。多服,能發人疔腫、痛疽、惡瘡,并一應熱疾。而其性酷烈,甚于硫磺、丹砂,熱燥猛于蘇合油、附子,自仙靈、脾瑣陽、陽起石、丁香、鹿茸、龍骨、兔絲,而下功皆不及也。成化癸卯,嘗令中貴出海南、閩浙、川陜,近西域諸處收買之。其價與黃金等”國。這一珍貴資料除了說明“合甫融”的藥用價值之外,重要價值在于第一次記錄了鴉片在中國市場上已經成為一種商品,“價同黃金”,可以在廣東、福建、浙江、四川、陜西等地購買;它說明輸入中國的鴉片有兩個來源:“西方諸國并西域”。這里的“西方諸國”,顯然是指將鴉片稱作叩ium的歐洲國家。“西域”,應當是指將鴉片稱作a銣n的阿拉伯國家和地區。鴉片的兩種音譯最早出現在同一條資料中,說明歐洲人和阿拉伯人向中國運送鴉片幾乎是同時進行的。究竟是阿拉伯人還是歐洲人最先向中國運送鴉片?在沒有比較可靠的資料情況下,我們在此無法作出明確判斷。這一資料還是明廷在市場上直接收買外國商人鴉片的最早記載。成化癸卯(1483)年,朝廷派遣太監到邊遠省區大規模收購鴉片,標明鴉片在當時宮廷生活中已有相當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明朝中期關于鴉片的記載還很少見。但是,到了明朝末年,關于鴉片的記載開始多起來。由于鴉片最初是作為藥物進口的,所以,關于鴉片的介紹往往談及其醫藥功能。云南的一位地方官說:“哈芙蓉,夷產也。以鶯粟汁和草烏合成之。其精者為鴉片,價埒兼金,可療泄痢、風蠱諸癥,尤能堅陽不泄,房中之術多用之。然亦有大毒,滇人忿爭者,往往吞之,即斃”固。這里的“哈芙蓉”,也是鴉片的阿拉伯音譯。作者以其精與粗區分鴉片的名稱顯然是不正確的,說“哈芙蓉”系罌粟汁與草烏的合成品也是不精確的。關于鴉片采集方法,方以智(1611~1671)的記載是:“其結青苞時以針刺十數眼,其精液自出,收入瓷器,用紙封口,曝二七日,即成鴉片,最能澀精”凹。“以針刺十數眼”,采集鴉片,這個記載還不夠精確。因為采集鴉片汁液的通常做法是用利器在罌粟蒴果的外面劃傷三五處傷痕,傷痕的深度是不可傷及里面的硬殼,這樣才能保證汁液慢慢津出。醫藥學家繆希雍的記載最為準確。他說:“阿芙蓉,罌粟花之津液也。罌粟結青苞時,午后以大針刺其外面青皮,勿損里面硬皮,或三五處,次早津出,以竹刀刮取人瓷器,陰干,用之。其氣味與罌粟殼相同,而此則止痢之功尤勝。故小兒痘瘡行漿時,泄瀉不止,用五厘至一分,未有不愈,他藥莫逮也”鑼。著名醫藥學家李時珍采納了繆希雍的觀點,并對鴉片的醫藥性能作了比較全面的解釋。“阿芙蓉,前代罕聞,近方有用者,云是罌粟花之津液也。罌粟結青苞時,午后以大針刺其外面青皮,勿損里面硬皮,或三五處,次早津出,以竹刀刮收入瓷器,陰干用之。故今市者猶有苞片在內。……氣味酸,澀,溫,微毒。主治瀉痢、脫肛不止,能澀丈夫精氣”固。大致說來,鴉片作為珍貴的藥物,在明代主要用于治療痢疾、脫肛、小兒痘瘡以及各種頭風、疼痛病癥,同時還用于治療男性疾病,所謂“堅陽不泄”者也。正是由于鴉片在明朝醫藥學上應用廣泛,奇效無比,它才成為外國經常向中國輸入的重要商品之一。明廷為此還制訂了鴉片進口稅率,保存到現在的《陸餉貨物抽稅則例》規定:“阿片每十斤稅銀二錢”∞。這項稅則制訂于萬歷十七年(1589)。一項稅則不可能對偶爾的少量的貨物來制訂。萬歷四十三年(1615),明朝又新訂《貨物抽稅見行則例》,將鴉片人口稅率改為“每十斤稅銀一錢七分三厘”鼬。這項稅則一直維持到明朝滅亡。這些資料足以證明,從16世紀開始,鴉片已經成為中國需要經常進口的貴重物品。向中國輸入鴉片的商販,既有阿拉伯人、爪哇人和泰國人,也有葡萄牙人、荷蘭人等西歐人。尤其是在葡萄牙人占踞澳門(1553),荷蘭人占據臺灣(1624)之后,鴉片成為經常進口的商品。明朝人服食鴉片的方法主要是吞服,即由醫家將其拌合其它藥料,制成中藥丸散,如“一粒金丹”、“鴉片散”、“大金丹”等,主治痢疾、頭風及男子遺精、早泄等癥。鴉片在明朝得到了積極的應用,對于當時中國人的身體健康是有功效的。但由于吞服鴉片或鴉片質的合成藥品極易成癮,一些患者難免受其控制,成為癮君子,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當時鴉片價格極為昂貴,普通百姓無力消費,鴉片流毒限于富貴階層極少數人,“相傳明神宗御極三十年,不召見群臣,即為此物所累”固。1958年,發掘定陵地宮,經過科學化險,發現朱翊鈞尸骨中確實含有較重的嗎啡成分,偶爾服食過鴉片不可能留下這樣的記錄,證明他是一位經常服食鴉片的癮君子。皇帝如此,王公大臣、貴戚閹宦難免互相浸染,宮廷先受其毒,無怪乎成化年間,明廷派出太監到各地收買鴉片。只是由于流毒范圍有限,尚未引起醫家重視而已。通過上述資料分析,我們知道,明朝人對于罌粟的醫藥使用范圍比宋元時期有所擴大,除了繼續用于治療脾虛肺寒,咳嗽多疾,胸滿短氣,飲食減少,痢疾腹痛,妊娠心氣不足等癥外,還用于治療脫肛、遺精、痘瘡和鎮痛等。在日常生活中,罌粟還被做成佛粥、面餅、餛飩和豆腐等食品,得到了相當積極的使用。而鴉片進口發生在明朝中期,成化年問開始留下最初紀錄。鴉片輸入從一開始就留下兩組截然不同的譯稱:“鴉片”或“阿片”,“合甫融”或“阿芙蓉”、“哈芙蓉”。這說明鴉片來源一開始就不同,進口商分別來自歐洲和阿拉伯國家。鴉片作為珍貴的藥物,在明朝主要用于治療痢疾、脫肛、小兒痘瘡以及各種疼痛病癥,同時還用于房中術,醫治男子遺精、早泄等癥。由于鴉片價格昂貴,明朝人對于鴉片的使用是積極的。盡管如此,卻不能完全排除鴉片被濫用的可能性。
四、清代前期鴉片與煙草混合吸食方法的傳入及其危害
鴉片對中國社會造成巨大危害,導因于煙草與鴉片拌合吸食方法的傳人。這個問題以往少有人注意,即是偶爾提及,也未深究,還有嚴重誤解。要想了解鴉片煙的由來,需要追述一下吸食煙草方法的傳人。15世紀末16世紀初地理大發現,原產美洲的煙草被帶回歐洲,美洲土著居民吸食煙草的方法很快經由歐洲人介紹傳播到世界各地。大約在萬歷末年或天啟初也傳到中國。方以智記載:“萬歷末,有攜至漳泉者。……漸傳到九邊,皆銜長管而火點吞吐之,有醉仆者。崇禎時嚴禁之,不止。其本似春不老,而葉大于菜,暴干以火酒炒之,日‘金絲煙’。北人呼為‘淡把姑’,或曰‘擔不歸’。可以去濕發散,然久服則肺焦,諸藥多不效,其癥忽吐黃水而死”圓。姚旅說:“呂宋國出一草,日:‘淡巴菰’,一名日‘醺’。以火燒一頭,以一頭向口,煙氣從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且可避瘴氣。有人攜漳州種之,今反多于呂宋,載入其國售之”回。明末清初,種植吸食煙草風氣迅速從福建向各地傳播。崇禎年間,“北土亦多種之,一畝之收可以敵田十畝,乃至無人不用”∞。“順治初,軍中莫不用煙,一時販者輻輳,種者復廣,獲利亦倍初價”固。上自公卿士大夫,下逮兵役婦女,都有許多人嗜吸煙草。正是由于吸食煙草風氣傳染太快,引起明朝政府的警惕,于崇禎十二年(1639)即詔令禁止,“犯者論死”姻。1643年,再次下令禁種禁吸,然而由于政綱失墜,社會秩序大亂,無法杜絕,“至論死而不能革”鯽。吸食鴉片煙是從吸食煙草的方法中發展而來的。煙草傳入東南亞國家較早,混合吸食鴉片與煙草的方法發明于爪哇,經荷蘭人傳入中國。傳教士艾約瑟說,德國醫生甘伯佛耳在康熙年間著有一書,記載了鴉片與煙草拌合吸食的情況:“咬▲巴黑人吞服之外,復有一以黃煙和鴉片之法,先取水人阿片中攪和勻,以是水拌黃煙,競吸取。其能使頭眩腦熱,志氣昏惰,而多生喜樂也。”夠。這里所說的咬▲巴,一作葛喇巴,系爪哇的一座城市。李圭的《鴉片事略》也說:“明末,蘇門答臘人變生食而吸食,其法先取漿蒸熟,慮去渣滓,復煮煙草葉為丸,置竹管就火吸之”∞。蘇門答臘與爪畦隔海峽相望,應是鴉片水與煙草拌合吸食的早期發源地之一。這一說法與德國醫生甘伯佛耳的記載基本一致。而問題是,鴉片水與煙草拌合吸食的方法何時傳人中國?傳播情況如何?雍正二年(1724),一位參與鎮壓臺灣朱一貴起義的清朝官員,在其治臺方略中要求禁止“鴉片煙”。他說:“鴉片煙不知始自何來,煮以銅鍋,煙筒如短棍,無賴惡少,群聚夜飲,遂成風俗。飲時以蜜糖諸品及鮮果十數碟佐之,誘后來者。初赴飲,不用錢,久則不能自己,傾家赴之矣,能通宵不寐,助淫欲,始以為樂,后遂不可復救。一日輟飲,則面皮頓縮,唇齒敞露,脫神欲斃,復飲乃愈。然二年之后,無不死矣。聞此為狡黠島夷誑傾唐人財命者,愚夫不悟,傳入中國已十余年,廈門多有,而臺灣特甚,殊可哀也”凹。這則資料證明“鴉片煙”于康熙末年已在福建廈門、臺灣流行開來,成為一種風俗。正是由于發現吸食“鴉片煙”的惡習迅速蔓延,出于道德風俗的原因,雍正七年(1729),清廷頒布了中國第一道查禁自己的臣民販賣“鴉片煙”的命令。規定:“凡興販鴉片煙,照收買違禁貨物例,杖一百,枷號一月;再犯,發近邊充軍。私開鴉片煙館,引誘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眾律擬絞監候;為從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戶、地保、鄰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如兵役人等借端需索,計照枉法律治罪;失察地方文武各官并不行監察之海關監督,均交部嚴加議處”∞。雍正時期,清廷禁止的“鴉片煙”究竟是何種物品?“鴉片煙館”是什么場所?當年在福建發生的一起冤獄平反事件,可以說明這些問題。雍正六年(1728),福建漳州一位名叫陳遠的商人,在廣州以桔餅兌換鴉片、木香而歸。次年春天,因清廷要求各地查禁“鴉片煙”,被漳州知府李治國所派密探查獲,收繳鴉片33斤。漳州知府李治國按照興販“鴉片煙”例,擬將陳遠枷號一月,發邊衛充軍。這一案件申報到福建巡撫衙門,巡撫劉世明親自提審,陳遠滿口呼冤,堅稱鴉片是必需的藥材,并不是“鴉片煙”,“鴉片煙”是用鴉片水拌合黃煙煙絲而成,要求檢驗證明。劉世明乃令福州府傳到太和堂藥鋪戶陳書佩當場認驗。陳書佩認驗后說:“驗得此系鴉片,熬膏藥用的,又可做鴉片丸,醫治痢疾,這是并未做成煙的鴉片”。劉世明據此上奏說:“夫鴉片為醫家需用之藥品,惟加入煙草始淫蕩害人,為干犯禁例之物。李治國何得設計誘出陳遠家藏鴉片,便以鴉片煙之例問擬枷號、充軍,錯混施行,甚屬乖謬。法應照依故人人罪,列款題參”∞。在說明這是一樁冤案之后,劉世明考慮到禁止“鴉片煙”令剛剛下達,擔心因題參李治國,引起百姓藐視官府,不利禁令貫徹,建議將錯就錯,將33斤鴉片收歸藩庫。這通奏折送達御案,雍正皇帝非常重視,朱批將33斤鴉片退還陳遠本人。朱批說:“其三十余斤鴉片若系犯法之物,即不應寬釋。既不違禁,何故貯藏藩庫。此皆小民貿易血本,豈可將錯就錯,奪其生計。如欲留為異日證據,數兩幾片足矣,未有全留貯庫之理。雖系細事,殊關輿論。汝等身膺封疆重任,慎勿因其細而漫忽視之。蚩蚩愚氓正于此等處,觀汝之體恤民隱周祥與否也”衄。從這一案件的處理結果來看,當時清廷所禁止的是“鴉片煙”,而不是“鴉片”。“鴉片煙”是煙草與鴉片的混合物,鴉片作為合法的醫治瀉痢等疾病的特效藥材是允許貿易的,不在禁止之列。正是由于二者概念不同,我們才能理解在雍正乾隆時期,為什么清廷既允許海關進口鴉片∞,又在國內查禁“鴉片煙”的政治措施。通過平反陳遠冤案,還可以看出,當時單純吸食鴉片的方法尚未發明,尚未造成嚴重社會危害。從上述情況來看,大致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混合吸食鴉片與煙草的方法大約在清朝康熙末年傳入臺灣、福建,流行于江南地區,隨著這種吸食“鴉片煙”習慣的迅速傳播引起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導致雍正七年(1729)清廷采取嚴厲措施,下令禁止販運和制造“鴉片煙”。然而,有禁而不止。大約在18世紀80年代,也就是乾隆中后期由于單純吸食鴉片方法的發明,混合吸食鴉片與煙草方法才逐漸被取代。混合吸食鴉片與煙草的方法在中國流行了將近一個世紀,待到單純吸食鴉片法發明并流傳后,還直接從中承襲了兩個非常重要的名詞:“鴉片煙”和“鴉片煙館”。不過,它們的含義已發生重要變化,“鴉片煙”成了鴉片的同義詞,“鴉片煙館”不再是炮制鴉片與煙草混合物的場所,而是專供人們消費鴉片膏的毒窟。
五、需要糾正的三個誤解
其一,關于禁止鴉片輸入的時間。雍正時期的“鴉片煙”與“鴉片”的概念是不同的。前者是指鴉片與煙草的混合品,后者是指通過海關正常輸入的鴉片。由于不能正確區別早期“鴉片煙”與“鴉片”的不同,因此許多人便把雍正七年頒布的禁止興販和制造“鴉片煙”的條例,當成是中國禁止鴉片輸入的最早的法令。這顯然是一種誤解。查閱海關檔案可知,雍正時期和乾隆時期鴉片一直是一種合法的商品,從未被禁止輸入。只是到了嘉慶四年(1799),中國才開始明令禁止鴉片輸入。中英文資料均有這方面的證據。道光十四年,兩廣總督盧坤在奏折中指出:“迨嘉慶四年,前督臣以鴉片有害民生,禁止入口,販運者不得入關,而吸食者傳染日廣。夷人隨私帶鴉片煙土在外洋寄泊銷賣”@。此處的“前總督”指的是覺羅吉慶,此人于嘉慶元年至嘉慶七年任兩廣總督,在任期間目睹單純吸食鴉片風氣迅速蔓延,已經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為了從源頭上切斷鴉片流毒,他和廣東巡撫陸有仁向粵海關監督下達了嚴禁鴉片輸入的命令。命令強調說:“目前如不竭力剪除此種禍害,則后患何堪設想!是以余等特頒此令,通告全省各地及各關卡文武官弁一體知照,隨時隨地嚴行查禁。一經發覺此種行為,即予懲處。同時,余等要求海關監督大人亦頒布嚴令,飭諭該管之官吏、家人及各關卡等弁兵,今后必須對引水船只、巡船及漁船等嚴行搜查有無夾帶煙土,如有違犯,即予拿捕,送官究辦,治以應得之罪”∞。粵海關監督接到上述命令后,于當年十一月十一日(1799年12月7日)將其轉發外國商人。聲稱,今后一旦發現任何外國船只運入鴉片,或發現中國行商承銷鴉片,“本官將此事報告總督與撫院,即將該行商嚴查并處罰,決不稍予寬貸”。并要求行商,必須按例回復,“俾知彼等已遵奉此令”。這一通令發出之后,立即在廣州行商和外國商人中激起很大反響,東印度公司的航務長認為,這是“中國初次采取積極步驟制止鴉片貿易”卸。現存的東印度公司檔案保存了這些命令和通告的原件,托馬斯•斯當東將其翻譯成英文。以上的官方文件證明中國官方命令禁止鴉片輸入始于1799年12月7日。所以,中國官方禁止鴉片貿易的時間應當始于1799年,而非1729年。其二,關于“芙蓉”就是“鴉片”的說法。明代戲曲作家湯顯祖(1550一1616)有一首題名為《香山驗香所采香口號》小詩。詩文日:“不絕如絲戲海龍,大魚春漲吐莢蓉。千金一片渾閑事,愿得為云護九重”。徐朔方先生認為湯顯祖詩中的“芙蓉”就是“鴉片”,詩文譏諷明神宗吸食“鴉片煙”曾。進而,又說“湯顯祖的這首小詩帶有敏銳的時代感,可以說不亞于龔自珍在鴉片戰爭前夕所寫的那首同題材的七絕《己亥雜詩•津梁條約遍南東》”。這是一種嚴重誤解。“芙蓉”不是鴉片。“鴉片”是英語Opium的譯音。它在中國又叫“阿芙蓉”,或“合浦融”,是阿拉伯語A』如n的音譯。而“芙蓉”是荷花的別稱,或者是木芙蓉。如前所說,混合吸食鴉片與煙草的方法大約在18世紀初期才傳人中國,而湯顯祖卒于1616年,萬歷皇帝死于1620年,顯然,他們誰也不了解“鴉片煙”是怎么一回事。萬歷皇帝與鴉片有染,如前所說是吞服鴉片。吞服鴉片藥丸在中國由來已久,“吞服”與“吸食”鴉片方法明顯不同,不能混淆。萬歷皇帝不曾吸食“鴉片煙”,湯顯祖更不可能寫詩予以譏諷,徐朔方的有關推論自然是站不住腳的。其三,關于《曾羽王日記》中的記載問題。中國史學會編《鴉片戰爭》第一冊摘選的《曾羽王日記》中的一段話經常引起人們的誤解:“余幼時,聞有鴉片煙之名,然未見有吸之者,止福建人吸之。余年三十六而遭鼎革,始于青村王繼維把總衙內見有人吸此,以為目所親睹也”曰。這段話通常被用來說明中國早期吸食鴉片煙的情況。筆者找到《曾羽王日記》進行核對,結果發現原來日記的這段話并無“鴉片”二字。既然沒有“鴉片”二字,這一資料只能用于說明煙草傳播情況,而不能作為“鴉片煙”傳播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