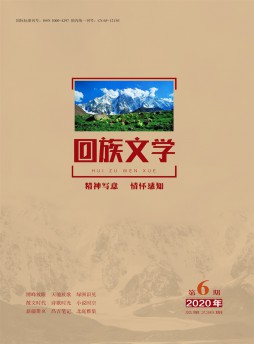文學社會學與小說社會學研討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文學社會學與小說社會學研討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純粹思辨的文學探討,具有理論的深度,看待問題更為透徹和深邃,也可挖掘到文學———社會關(guān)系的深層本質(zhì)。但是,過于沉溺于理論思辨,往往使得問題更為復(fù)雜,太過宏觀的探討,對于實際的文學———社會問題有時并沒有給予現(xiàn)實的幫助,而且這種思辨的方法常常會忽視對具體文本的分析和探討,使這種研究經(jīng)常流于形而上或“大而空”的趨勢,甚至文風晦澀,普通讀者很難看懂,也導致其理論研究的應(yīng)用或者有意義的觀點局限于很小的讀者范圍內(nèi)。馬克思后來已經(jīng)意識到這個問題并回到了經(jīng)驗實證科學上來。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xiàn)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fā)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關(guān)于意識的空話將終止,它們一定會被真正的知識所代替。對現(xiàn)實的描述會使獨立的哲學失去生存環(huán)境,能夠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歷史發(fā)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jié)果的概括。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xiàn)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②另一方面,經(jīng)驗實證主義的文學社會學研究,與馬克思主義文學社會學相比,具有微觀考察的優(yōu)勢,它是在現(xiàn)實經(jīng)驗和占有具體材料的基礎(chǔ)上的一種科學研究,這種研究往往針對的問題也很具體,可操作性也很強,特別對文學———社會研究中一些具體事實或具體因素常常在數(shù)據(jù)材料方面給人以信服的結(jié)論,的確具有科學研究的優(yōu)勢。但是經(jīng)驗實證的文學社會學在其根本上也有難以解決的問題,即這種研究最常受到的詬病就是缺乏理論深度。
這種刻意規(guī)避辯證探討,使經(jīng)驗實證主義的研究停留于簡單的事實陳述和歸納,正如自然科學一樣完全不帶個人的價值判斷和意義考察,最后成為一種毫無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的科學知識的羅列。“過分強調(diào)經(jīng)驗實踐之觀察和證實的維度,實證主義的推進嚴重地縮小了經(jīng)驗分析的范圍。經(jīng)驗概括的努力愈來愈停留在簡單關(guān)聯(lián)陳述的水平上,而且對于卷入‘思辨’的恐懼禁錮了那些本可以幫助平衡在某種程度上不可避免的科學知識原子化傾向的諸連接環(huán)節(jié)的形成”。③意識到經(jīng)驗實證主義研究存在的困境,有些學者就試圖溝通馬克思主義和經(jīng)驗實證主義這兩種文學研究,為這一問題尋找出路。如被稱為馬克思主義藝術(shù)史家的豪澤爾(ArnoldHaus-er),在研究中較為注重對經(jīng)驗事實的考察。戈德曼在發(fā)生結(jié)構(gòu)主義文學社會學方法中也同樣非常注重對經(jīng)驗事實以及歷史事實的查考,也注重具體作品的分析,正是在盧卡奇純思辨的小說發(fā)生學的基礎(chǔ)上,同時借鑒當時法國較為流行的經(jīng)驗實證主義社會學方法以及文學社會學研究的一些優(yōu)秀成果,形成了戈德曼獨特的綜合的文學社會學研究。
當然,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和側(cè)重點。在具有悠久的思辨?zhèn)鹘y(tǒng)的德國,辯證研究或許能得到更多的延續(xù)和發(fā)展,而在處于經(jīng)驗主義傳統(tǒng)氛圍中的英國對待純思辨哲學的態(tài)度則是另一種情形。法國的文學觀念本身就具有文化特征,正如法國學者埃斯卡皮所述,“文學觀念最早是描述一種社會文化事實,而不是一種審美事實”。④其實在比較文學研究方法中,美國學派強調(diào)審美特征的平行研究,與法國學派對強調(diào)不同文化間關(guān)聯(lián)的“歷史社會事實”的影響研究的偏執(zhí),也是出于不同文化傳統(tǒng)對“文學”概念的理解的差異造成的。正如威廉斯對英國經(jīng)驗實證研究與歐陸研究的區(qū)別的解析:“把這些物質(zhì)社會過程從物質(zhì)社會總過程中排除出去同樣是錯誤的,正如把所有的物質(zhì)社會過程簡化為僅僅是其它抽象的‘生活’的技術(shù)手段。”⑤在威廉斯看來,對經(jīng)驗事實及社會過程的關(guān)注之所以區(qū)別于法國和德國,關(guān)鍵在于“科學”這一概念在德語和英語中的不同內(nèi)涵。自19世紀早期以來,德語中的“Wissenschaft”與法語的“sci-ence”一樣,具有“系統(tǒng)的知識”或“有條理的學問”等較為寬泛的含義;而“在英語中,‘science’很大程度上專指那些建立在對‘現(xiàn)實世界’進行觀察基礎(chǔ)上的知識,以及建立在對原來可以互換的‘experience’和‘experiment’兩詞的重要區(qū)分上。在發(fā)展的過程中,后者生發(fā)出‘經(jīng)驗的’(empirical)和‘實證的’(positive)之新的意義。那么,對任何英語讀者來說,很難超脫這種專門含義來理解這些翻譯過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語匯‘真正實證科學’(real,positive,science)”。⑥可見,不同的學術(shù)傳統(tǒng)在概念的理解上表現(xiàn)也很明顯,英國對“科學”的狹義理解使其文學社會學研究往往建立在“經(jīng)驗”和“實證”的基礎(chǔ)上。因此,在德國和法國這些崇尚思辨哲學的學術(shù)氛圍中,辯證法的文學社會學得到了較好的發(fā)展,盧卡奇的《小說理論》正是得益于海德堡學派的新康德主義理論和黑格爾辯證法的理論滋養(yǎng)。而英國經(jīng)驗主義的學術(shù)環(huán)境,造就了經(jīng)驗實證的文學社會學的較好基礎(chǔ),而對辯證法向度的文學社會學研究卻不太感興趣,瓦特的《小說的興起》正是如此。
當前的小說社會學研究
作為近幾百年來文學家族的核心成員,“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相對于其它文類,小說似乎取得了支配權(quán),但是它從來沒有得到經(jīng)典批評層級結(jié)構(gòu)給予的很多關(guān)注和地位”。⑦事實的確如此,小說在創(chuàng)作上取得的成就和贏得的關(guān)注遠遠超過在其理論上的建樹。在今天學科高度分化而又高度綜合的時代,尋求研究方法和事業(yè)的多樣化互補已經(jīng)成為一種大趨勢,小說同樣必然要進入多維的研究視野。如果按照時間維度來劃分的話,小說研究可以大致分為共時研究和歷時研究。在當今國內(nèi)外小說理論界,比較熱門的是對小說的心理學研究和小說本體的語言學研究。很明顯,這些探討當屬共時研究,如小說敘事學、小說形態(tài)學、小說中的時間———空間研究等。但是,任何藝術(shù)作品的美學價值永遠不能同歷史過程相分離,它展示的永遠是發(fā)展方向:來自何處,去向何方。⑧當前的小說研究中,對小說作為一種文類的發(fā)展流變,與其所處外部環(huán)境的關(guān)聯(lián)以及小說生產(chǎn)的具體環(huán)節(jié),如作者、讀者、出版、社會功能、各時期社會文化、社會心理、社會情感、讀者的接受批評等關(guān)注不多。韋勒克在談到文學與社會的關(guān)系時曾指出:“文學是一種社會性的實踐,它以語言這一社會創(chuàng)造物作為自己的媒介,諸如象征和格律等傳統(tǒng)的文學手段,就其本質(zhì)而言,都是社會性的”,“文學具有一定的社會功能或‘效用’,它不單純是個人的事情。因此,文學研究中所提出的大多數(shù)問題是社會問題”。⑨即使是最純粹的文學作品也是語言創(chuàng)造物,而語言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其社會性。事實上,小說這一文類與史詩、戲劇一樣,“本身都與一定的社會命運相聯(lián)系。個人的孤獨感或集體的安全感、社會的樂觀主義或絕望情緒、對心理內(nèi)省的興趣或?qū)r值的客觀標準的堅持……都有助于人們根據(jù)社會情境重新探討文學形式”。⑩
即使是完全的審美活動也具有審美標準的歷史性和社會風尚的傾向。正如洛文塔爾所論,作者的社會地位,文學作品的社會意識的歷史呈現(xiàn),作為文學材料的社會和社會問題,社會關(guān)系對作者和讀者的影響,社會控制領(lǐng)域,科技變化帶來的經(jīng)濟與社會后果等等,對作品及作品的成功都有著這樣那樣的影響。隨著社會學這一學科的發(fā)展,越來越多的人注意到社會學調(diào)查研究的科學方法,當代文學社會學家們在進行文學研究時,把文學作為一種事物,一種現(xiàn)象,或曰研究對象進行考查而基本忽略其文學內(nèi)容,如菲根和西爾伯曼等人的文學社會學研究。小說社會學作為文學社會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小說生產(chǎn)于其中的外部環(huán)境和歷史社會發(fā)展的外部研究。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小說社會學的共時研究,即把小說作為一種產(chǎn)品,注重研究它得以產(chǎn)生的物質(zhì)基礎(chǔ)和生產(chǎn)條件;研究這種商品的制造者,即作者與社會之間的關(guān)系,對傳播媒介(評論家、出版商、書商、圖書館、書展等)也進行積極研究;研究作品的消費,誰消費?消費什么?為什么?這與接受美學頗具相似之處,但較注重消費者的社會心理和社會影響等問題,這也是當代文學社會學研究的主流。毫無疑問,無論是辯證的方法還是經(jīng)驗主義的社會學研究方法在文學研究中的應(yīng)用,在20世紀都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作為文學的一個分支,小說理論在其技巧方法與文本內(nèi)部分析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然而對于小說本身的發(fā)展流變及其特質(zhì)的探討還沒有得到應(yīng)有的重視。已有的小說社會學研究成果中,主要是對小說社會學的橫向研究,即小說各要素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guān)系剖析,如國內(nèi)學者徐啟華的《小說社會學初探》等。但這些理論都沒有追溯小說作為一種文類的發(fā)生原理,缺乏對其在發(fā)展過程中與意識形態(tài)的深層關(guān)系,小說的心靈救贖本質(zhì)以及小說在圖像時代的未來可能路向的歷史流變的整體關(guān)照。西方的小說社會學研究成果已經(jīng)具有相當?shù)囊?guī)模,如有瓦特《小說的興起》的經(jīng)驗實證主義小說社會學的調(diào)查研究,盧卡奇的《小說理論》依托于“精神科學”的哲學探討,戈德曼《隱蔽的上帝》、《論小說的社會學》、《文學社會學方法論》等建立的意識形態(tài)和資本主義經(jīng)濟框架內(nèi)的宏大結(jié)構(gòu),以及薩義德的《東方學》與《文化與帝國主義》等作品,剖析小說經(jīng)典化與帝國主義殖民擴張和維持的關(guān)系等,巴赫金的《小說理論》等也從這方面或那方面對小說社會學進行了分析和探索。
小說社會學研究舉隅
盧卡奇《小說理論》的小說發(fā)生學可作為小說社會學辯證法方向的代表;瓦特的《小說的興起》以社會學方法考察小說興起諸因素的研究,可作為經(jīng)驗主義小說社會學的代表;而戈德曼的發(fā)生結(jié)構(gòu)主義小說社會學可作為綜合兩種路向的代表。盧卡奇的《小說理論》正是在海德堡新康德主義“精神科學”的影響中開始走向黑格爾的思想產(chǎn)品。他從歷史哲學層面考察了小說與史詩興替關(guān)系的根源在于其“總體性”文化的存在與否。盧卡奇繼承了溫克爾曼、歌德、席勒以來崇尚古希臘文化的德意志傳統(tǒng),把古希臘文化看作完整的文化,并以此取代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盧卡奇認為,在史詩的世界中,人類與自然、個人與社會、生活與意義、實然與應(yīng)然、心靈與形式,都是主客一體的“完整”存在。“星光朗照”下的道路是清晰可依的。史詩后時代的人所棲居的世界是一個充滿了未知、無限、陌生的主客兩分的世界。在無神的世界里,小說的出現(xiàn)正是孤獨的、“有問題的”個體對自我的找尋,是一種對“總體性”的想象和建構(gòu)。盧卡奇根據(jù)人的內(nèi)心與外部世界的關(guān)系把小說劃分為抽象的理想主義、幻滅的浪漫主義、綜合二者傾向的教育小說和趨向史詩形式的托爾斯泰小說以及難以命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與盧卡奇的唯心主義的悲觀論調(diào)相對的,是對小說的經(jīng)驗實證研究。瓦特的小說社會學研究的名作《小說的興起》汲取了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基本觀點,并接受了Q.D.利維斯夫人的《小說與讀者大眾》中的社會學調(diào)查方法和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在小說領(lǐng)域運用了這一帶有英國傳統(tǒng)的經(jīng)驗主義方法。瓦特認為正是在18世紀,處于上升階段的資本主義發(fā)展帶來的中產(chǎn)階級的崛起,使小說這一文類開始具有“形式現(xiàn)實主義”的特征。
在批判性的、反傳統(tǒng)的、革新的哲學背景下,區(qū)別于以往對一般性的、普遍性的偏愛,這一時期的“小說(novel)”本身具有“新穎”的內(nèi)涵,它不再以歷史或傳說為基礎(chǔ),轉(zhuǎn)而關(guān)注個人經(jīng)驗、關(guān)注世俗生活,真正開始與之前的“虛構(gòu)故事”(fiction)相區(qū)別。瓦特還分析了與18世紀讀者隊伍有關(guān)的經(jīng)濟、文化普及程度、流通圖書館的成功、經(jīng)濟發(fā)展帶來的閑暇時間以及恩主制度的衰微帶來的出版商與作者、讀者的關(guān)系等因素,都促進了小說的現(xiàn)實主義特征的形成和讀者隊伍的擴大。被稱為“早期盧卡奇門徒”的戈德曼主要生活在法國。與盧卡奇不同的是,他的文學社會學研究實際上帶有更多的經(jīng)驗實證成分。其發(fā)生結(jié)構(gòu)主義方法的核心,指向在大環(huán)境中對一個行為的解釋,即對行為發(fā)生的根源的追溯,要把它置入一個更大的結(jié)構(gòu)背景,從而部分的、獨立的事件或行為在一個整體中得到了說明和闡釋。而對文學作品的認識則存在于作品所透露的“世界觀”,即從“文本”到“世界觀”到“群體的意識和精神生活”以至于再擴展到經(jīng)濟和社會生活的一個層層遞進的解釋過程。
在《隱蔽的上帝》中,戈德曼運用發(fā)生結(jié)構(gòu)主義方法對拉辛和帕斯卡爾之間存在的共同的悲劇世界觀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把他們透露的思想歸入穿袍貴族這一社會集團的思想意識中,進而放進法國歷史,甚至納入整個西方社會,從而實現(xiàn)對拉辛作品或帕斯卡爾思想的理解。在《論小說的社會學》中,他從歷時層面,以小說不同的時期透露出的“集體意識”,對應(yīng)于資本主義不同時期的形態(tài)特征,進一步對其發(fā)生結(jié)構(gòu)主義方法進行實踐。從以上小說社會學的研究內(nèi)容可以看出,無論是辯證的方法、經(jīng)驗主義社會學的方法或者二者的綜合,在小說社會學實踐中都體現(xiàn)出關(guān)注個體與群體的關(guān)系,特別是個體性、個人的重要性、人與物的關(guān)系等,強調(diào)小說的生成與物化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關(guān)系等。值得一提的是,小說作為近幾百年來最重要的一種文學形式,對它的研究經(jīng)歷了從歷史研究走向形式研究,再從形式走向歷史的一個過程。當然,當代的小說社會學研究是在汲取形式主義方法營養(yǎng)的基礎(chǔ)上對小說進行文學———社會關(guān)系的深層探索,一如瓦特的經(jīng)驗主義小說社會學以及戈德曼的發(fā)生結(jié)構(gòu)主義小說社會學研究,都是建立在對作品文本分析的基礎(chǔ)上的歷史研究,而這些研究,不僅豐富了文學研究內(nèi)容,也深化了文學這一事物與社會文化之間的相互促進過程。
作者:陳麗英單位:南陽師范學院文學院
擴展閱讀
推薦期刊
精品推薦
- 1文學批評論文
- 2文學作品分析論文
- 3文學作品鑒賞論文
- 4文學寫作論文
- 5文學鑒賞論文
- 6文學教育論文
- 7文學的藝術(shù)性
- 8文學學術(shù)論文
- 9文學專業(yè)論文
- 10文學敘事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