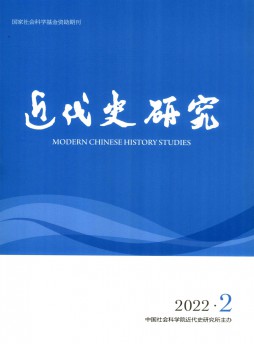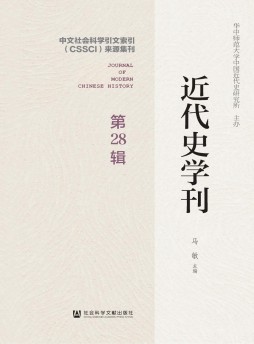近代婦女社會生活缺陷探討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近代婦女社會生活缺陷探討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作者:陳美玲單位:福建師范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2010級碩士研究生
纏足問題
中國婦女纏足之俗,起源于五代十國的南唐,有上千年的歷史,是中國封建社會從精神到肉體對婦女的禁錮。纏足給廣大婦女帶來了沉重的苦難,造成女子終身痛楚。由于身體的局限,中國婦女不能像男子一樣正常勞動,這其實就變相地侵害了婦女的勞動權(quán)、自由權(quán)等人生權(quán)益,因此勸禁纏足對婦女解放具有極其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早在辛亥革命前,維新派人士就已在社會上歷陳纏足之毒,提倡“不纏足”運動,并成立了“不纏足會”等專事廢除纏足惡習(xí)的機(jī)構(gòu)。清末新政時期,更由政府出面,勸止民間纏足。于是,社會上纏足的風(fēng)氣發(fā)生了一些新變化。但是,當(dāng)時的纏足之風(fēng)也僅限于部分知識分子和城市居民之中。真正以法令形式對纏足予以廢棄,取得立竿見影效果的,還是辛亥革命時期。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積極倡導(dǎo)廢除纏足惡習(xí)。孫中山在致內(nèi)務(wù)部關(guān)于勸禁纏足的指令中,歷陳纏足惡習(xí)給社會及婦女帶來的危害,并“為此令仰該部速行通飭全省一體勸禁,其有故為禁令者,予其家屬以相當(dāng)之罰”。據(jù)該命令,南京臨時政府內(nèi)務(wù)部通令各省,要求嚴(yán)禁纏足,“已纏者令其必放,未纏者毋許再纏,倘鄉(xiāng)僻愚民,仍執(zhí)迷不悟,或編為另戶,以激其羞恥之心,或削其公權(quán),以生其向隅之感。”
這是在中國歷史上首次以國家法令的形式,在全國范圍內(nèi)大張旗鼓地宣傳和實施廢除纏足惡習(xí)。民國成立后,中國婦女逐漸擺脫纏足惡習(xí),由于“不纏足”更多地與人們的社會道德及現(xiàn)代生活觀念的變遷有關(guān),故民國后官方在勸禁婦女纏足等惡習(xí)的過程中,沒有因為民初民眾政治心理的滯后,而發(fā)生巨大沖突,其過程基本上是由大城市帶動中小城市,由城市推廣到農(nóng)村,由觀念較新者帶動愚昧無知者,由政府有關(guān)部門因勢利導(dǎo),逐步在全國推廣開來的。于是,“女子裹腳從此解放了。已裹的放掉,已經(jīng)裹小的也放大。”
盡管“民國社會的婦女生活依然有許多舊時的遺留物,婦女解放的道路仍很艱難,但,這是通向婦女解放的決定性一步,由此,婦女才有可能獲得生活的自主、自立,尋找全新的生活環(huán)境,或求學(xué)或做事,甚或參加革命斗爭,爭取其應(yīng)有的社會地位”,放足成為了民初女子爭取自身權(quán)利和解放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婚姻家庭的問題
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和“三綱五常”等封建禮教的統(tǒng)治下,中國婦女一直處于不利的地位,她們沒有表達(dá)自身欲求的權(quán)利,沒有自由選擇的權(quán)利,她們所能做的僅是屈從于家長的權(quán)威和守好相夫教子的本分。因此長期以來,中國婦女的命運是悲慘的,她們別無選擇,無法追求和實現(xiàn)自身的真正價值,而只能淪為封建時代的犧牲品。然而,隨著社會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發(fā)展以及西化的婚姻家庭觀念的逐漸傳入,封建式的婚姻家庭制度越來越難以維持,不斷遭到新興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的抨擊和批判。與此同時,那些飽受封建世俗禮教摧殘的女性也不再安于現(xiàn)狀,她們渴望獲得自由,渴望平等。于是,廢除封建落后的婚姻家庭制度,實現(xiàn)婦女在婚姻生活中的自主與獨立,成為一種向高層文明演進(jìn)的趨勢,銳不可當(dāng)。伴隨著改良運動的發(fā)展,晚清一場聲勢浩大的婚姻家庭變革終于拉開了序幕。新興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在歐風(fēng)美雨的震蕩下,面對風(fēng)云際會的時局,以挽救國家危亡為出發(fā)點,把婚姻家庭作為影響社會變革的重要因素,提出了許多婚姻家庭新觀念。這些觀念在一定程度上與婦女解放運動、實現(xiàn)婚姻自由相聯(lián)系,顯示出相應(yīng)的進(jìn)步性。但是,由于封建守舊勢力的阻撓,這些新觀念只是限于城市中的青年知識分子和士紳階層,并沒有得到眾多女性的積極響應(yīng),因此未能取得過多實效。直到辛亥革命后,關(guān)于婚姻自由、家庭變革的思想觀念開始由知識分子和士紳階層向廣大人民群眾、由城鎮(zhèn)向鄉(xiāng)村逐漸滲透,不斷沖擊落后的封建婚姻制度。廣大婦女也逐漸覺醒,她們發(fā)動“女權(quán)運動”,爭取教育權(quán)、參政權(quán)及其他權(quán)力,改變自己在家庭中從父、從夫、從子的地位,爭取做自尊、自強、自立的新人。
與此同時,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有了極大改善,得以與男子平權(quán)。她們可以擁有自由選擇婚姻的權(quán)利而不再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封建禮教的困擾,如民國政府規(guī)定“親不為其子謀婚嫁”,“欲改良家庭,于子女結(jié)婚宜重視本人之意見”。中華民國家庭改良會主張“男女同有繼承權(quán),成年者有財產(chǎn)獨立權(quán)”,破天荒地實現(xiàn)了女子可以同男子一樣享有財產(chǎn)繼承權(quán)。此外,民國政府還廢除了買賣婚姻,規(guī)定“男子不納妾,女子不置婢”,極大地保障了女性的自主與平等的權(quán)利,使婦女不再遭受封建性禮教的壓迫和凌辱。隨著婦女地位的提升,寡婦這一特殊群體也引起了人們的同情和關(guān)注,于是,不少地區(qū)開始逐步認(rèn)可了寡婦再嫁的事實,寡婦不再為封建禮教的“重操守,滅人欲”所累。這與封建倫理道德強迫婦女守寡的貞潔觀相比,是一個巨大的進(jìn)步。至此,現(xiàn)代式的婚姻家庭關(guān)系在辛亥革命時期逐步形成,女權(quán)運動初顯成效,婦女地位開始穩(wěn)步提升。
婦女自由問題
婦女自由,即婦女思想自由、行動自由。換句話說,婦女擁有自主權(quán)利,她們可以根據(jù)自己的意愿決定自己的思想和行為。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在生產(chǎn)勞動、參與政治、戀愛婚姻、社會交往、人際關(guān)系等方面呈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自由精神。
(一)婦女參政自由
從一定意義上說,辛亥革命可以稱其為一次全民革命。在革命期間,除了男子,不少婦女也“以纖弱女子之身”,抱著“慷慨興師之志”投入到了這場革命中,為革命的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xiàn)。辛亥革命勝利前后,婦女的地位得到了顯著的提高,婦女參政自由問題也日益提上了日程。
1912年1月10日,中華民國女子同盟會在上海成立,它本著“扶助民國、促進(jìn)共和、發(fā)達(dá)女權(quán)、參與政事”的宗旨,主張女性參與國家政事并可對國家事務(wù)提出意見和建議。臨時政府成立后,孫中山把婦女解放和民主權(quán)利的實行聯(lián)系在一起,特別強調(diào)“天賦人權(quán),男女本非懸殊”,提出“女子將來之有參政權(quán),蓋所必至”。臨時參議院隨后通過了承認(rèn)女子參政權(quán)的議案,正式宣布賦予婦女與男士一樣的政治參與權(quán)利。這對千百年來備受歧視的廣大婦女來說,盼得此種徹底之解放,誠屬亙古未有。此后,女子參政自由問題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認(rèn)可。女子參政,一時成為社會關(guān)注的焦點,女性的政治地位逐步上升,越來越多女性開始關(guān)注國家政事,她們活躍在國家政壇上,為國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xiàn)。
(二)交往自由
隨著身份等級的否定和“男女授受不親”、男尊女卑的傳統(tǒng)格局的打破,男女平等的觀念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這種較為普遍的意識,自然使“男女交際不公開”的傳統(tǒng)交往方式成為“中國有許多不良的風(fēng)俗和習(xí)慣,你覺得哪一種應(yīng)當(dāng)首先改良”中普遍視為應(yīng)當(dāng)摒棄或改進(jìn)的一個方面。婦女由此開始步入社會,成為人際交往的重要成員。男女平等,男女同校,一時成為社會關(guān)注的焦點。男女的正常交往由完全緊閉到公開自由,婦女社會生活的開放性和平等參與程度得以提高。
禁婢問題
奴婢制度不僅是丑惡奴隸制的一種遺留,也是中國封建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判斷婦女是否得到解放、地位是否得到提高的一個重要依據(jù)。辛亥革命前,奴婢制度是合法的,奴婢沒有獨立的戶籍,他們或依附于官府,或依附于私家,連命名權(quán)都屬于主人。奴婢等同于主人的資財,沒有人格與自由,奴婢本人和子孫累世都和主人家有依附關(guān)系。婢女若遭受主人的性侵害,法律上也難給予有效的保護(hù)。在該制度下,無論男奴或是女婢,都過著非人的生活。其中,女婢的數(shù)量要遠(yuǎn)遠(yuǎn)多于男奴的數(shù)量。到了民國時期,女婢制度終于失去了其法律依據(jù),然而蓄婢作為一種習(xí)俗卻依然存在,“大概城市中百個女人中,怕至少也有三十或四十個,大城市如北京,怕還不止此數(shù)。”顯然,這是與知識分子所倡導(dǎo)并要建立的新的國民形象相違背的。因此,早在南京臨時政府時期,政府就頒布法令禁止蓄婢,要求“其從前所結(jié)買賣契約,悉與解除,視為雇主雇人關(guān)系,并不得再有主奴名分”
。國民政府成立后,先后頒布并施行了《修正解放奴婢辦法條例》《禁止市民蓄婢辦法》。這些法規(guī)規(guī)定,婢主供給婢女的衣食須和自己的子女同等,不能虐待婢女,并且要將婢女送入學(xué)校就讀。婢女到達(dá)一定年齡后還有婚配的自由。1932年,國民政府又將禁婢的措施具體化,頒布了《禁止蓄奴養(yǎng)婢辦法》,禁止非雇傭關(guān)系的奴婢的存在。
從解決蓄婢問題的結(jié)果來看,由于政府執(zhí)行不力,總體成效并不是很理想。比如在桂林,就曾有人做過這樣的估計,“假定桂林人口為五萬戶,每四十戶有一養(yǎng)女,也有養(yǎng)女一千人”,“約占全女性人口百分之一”,“桂林的婢女?dāng)?shù)量達(dá)到二千五百人以上,占女性人數(shù)的百分之二”。雖然這只是人們的一種估計,沒有很高的精確度,但是它卻足以反映出當(dāng)時存在的婢女人數(shù)之多。不可否認(rèn)的是,民國時期婢女問題已經(jīng)引起了政府與社會的足夠重視。禁止蓄婢、禁止買賣婦女,這對中國婦女無疑是一種極大的解放。從這個意義上說,盡管婢女問題在辛亥革命后未能得到有效的解決,但是它畢竟引起了政府的重視。從此以后,婢女的生活質(zhì)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人格尊嚴(yán)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維護(hù)。中國婦女得到了進(jìn)一步的解放。
婦女服飾問題
服飾是時代的一個重要標(biāo)志,透過服飾,我們可以大致判斷出這個時代的社會文化。清朝的服飾是封建專制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是阻礙中國社會走向現(xiàn)代化的因素之一。辛亥革命后,中國傳統(tǒng)服飾出現(xiàn)了巨大變化,即不再以等級定服飾,而是讓服飾充分體現(xiàn)“自由”、“平等”、“民主”等精神。孫中山曾說:“但凡政治、法律、風(fēng)俗、民智種種之事業(yè),均須改良進(jìn)步,始能與世界各國競爭。”在他看來,風(fēng)俗(其中以服飾尤為重要)的改良進(jìn)步是中國實現(xiàn)與各國競爭并成為佼佼者的必要條件之一。
20世紀(jì)初,與社會大變革相適應(yīng),中國的服飾也發(fā)生了很大變化,中國婦女服飾發(fā)生的巨大變化尤為引人矚目。它以中西交融、滿漢交融為特色,充分展示了這一時期女性服飾大跨度的歷史變革,突顯了人性化、個性化和近代化的時代特征。一方面,中國大地上興起了一股崇洋風(fēng),“大江南北,莫不以洋為尚”。這個時期時興的旗袍款式也在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上廣泛吸取西服的特點,使之成為一種中西合璧式的服裝,且不斷創(chuàng)新,不斷變化。另一方面,中國婦女可以自由著裝,自由討論服制問題了。她們不再飾以厚重的冠失物(其中有很多是象征封建等級與民族壓迫的)。
以往服飾上的那種單調(diào)、古板、等級森嚴(yán)的局面,開始被生動活潑、千變?nèi)f化的景象所取代。據(jù)相關(guān)資料記載,20年代以后中國婦女有了“曲線美”的意識,她們一改傳統(tǒng)習(xí)慣,開始將衣服裁制得稱身適體,服裝上不僅裝有墊肩、硬領(lǐng),而且打有胸裥,故在貯藏時適宜以大櫥懸掛,很少折疊存箱。當(dāng)時的婦女不時興戴手鐲、戒指、耳環(huán),此種服飾由于緊身得體盡顯婦女婀娜體態(tài),風(fēng)格清雅、簡樸。婦女走出家門,參與社會生活,成為一道靚麗的風(fēng)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