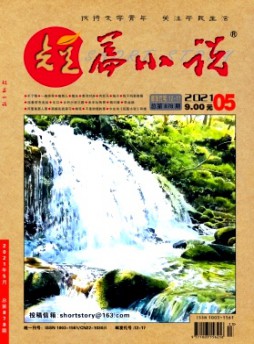小說(shuō)城鄉(xiāng)敘事的審美價(jià)值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小說(shuō)城鄉(xiāng)敘事的審美價(jià)值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xiě)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北京工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雜志》2015年第十一期
文學(xué)有一定的地域特色,江蘇獨(dú)特的地理位置和濃厚的人文傳統(tǒng)深深影響了本地作家的創(chuàng)作心理結(jié)構(gòu)與審美選擇,使江蘇作家群在創(chuàng)作上呈現(xiàn)出一定的地域文化共性。盡管江蘇從地域?qū)用嫔蟿澐钟刑K南與蘇北之別,在文化傳統(tǒng)上存在著吳越文化與楚漢文化的分歧和差異,江蘇作家群在審美取向上表現(xiàn)出細(xì)膩溫婉的江南士風(fēng)與粗獷質(zhì)樸的蘇北民風(fēng)的迥異,但是民間本位的創(chuàng)作立場(chǎng)、凡俗人生中的人性剖析與詩(shī)意文化傳統(tǒng)的自覺(jué)承襲都使江蘇作家群呈現(xiàn)出相似的文學(xué)氣質(zhì)。所以,本文主要立足于新時(shí)期以來(lái)江蘇作家的小說(shuō)創(chuàng)作,試圖從創(chuàng)作視角、敘事結(jié)構(gòu)與地域文化層面來(lái)發(fā)掘江蘇作家在城鄉(xiāng)敘事中共同的文學(xué)表征以及區(qū)別于其他當(dāng)代作家的審美獨(dú)特性。城市與鄉(xiāng)村在文學(xué)中的存在不只是作為兩種不同的地理空間,更承載著獨(dú)特的地域風(fēng)情與豐厚的社會(huì)文化內(nèi)涵。隨著城鄉(xiāng)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現(xiàn)實(shí)變化,作家對(duì)城鄉(xiāng)主題的關(guān)注自然折射了不同的審美意識(shí)與文化心態(tài)。新時(shí)期以來(lái)江蘇作家在進(jìn)行城鄉(xiāng)敘事時(shí),敘事視角的獨(dú)特與城鄉(xiāng)互望結(jié)構(gòu)的建構(gòu),再加上多元地域文化的積淀與影響,這些都使江蘇小說(shuō)呈現(xiàn)出了獨(dú)特的文學(xué)個(gè)性。
一、城鄉(xiāng)敘事的日常化
日常化是對(duì)日常生活的審美化呈現(xiàn)。日常生活,本應(yīng)是文學(xué)植根的土壤,但“五四”以來(lái),啟蒙話語(yǔ)與主義話語(yǔ)的限約都使文學(xué)一直脫離正常的日常生活空間。新時(shí)期以來(lái),隨著物質(zhì)化與實(shí)用化的社會(huì)觀念的發(fā)展,吃飯、穿衣、住房、愛(ài)情、婚姻成為人們主要的生存圖景,也成為了文學(xué)作品普遍的敘事內(nèi)容,于是日常生活逐漸成為文學(xué)敘事的審美準(zhǔn)則。江蘇作家對(duì)日常生活的審美呈現(xiàn),主要是將普通個(gè)體的日常生活鏡像浸潤(rùn)到文學(xué)作品中,從對(duì)個(gè)體日常經(jīng)驗(yàn)的描繪中發(fā)現(xiàn)個(gè)體存在的荒誕或意義,從對(duì)日常生存圖景的描繪與批判中提升個(gè)體存在的精神性,從而展現(xiàn)作家對(duì)個(gè)體及人類精神世界的探尋與理性思考。“日常生活是每個(gè)人的事。”
所以,從江蘇作家的作品中讀到最多的是對(duì)個(gè)體生存困境及人生命運(yùn)的關(guān)注,對(duì)人性深層內(nèi)涵的發(fā)掘。(1)個(gè)體日常生活空間的隱喻透視。在江蘇作家的筆下,小巷、商場(chǎng)、酒吧、公交車、KTV、火車、辦公室等是城市個(gè)體經(jīng)常穿梭的生活空間,而稻田、集市、蔬菜大棚、河邊、船等則是鄉(xiāng)村人的生活空間,這些生活空間已不是單一的物理或地理的空間意義,而是滿溢著城鄉(xiāng)個(gè)體平淡瑣碎的生活,是城鄉(xiāng)普通個(gè)體的思維方式、生存方式、文化方式的具體體現(xiàn),具有了更加深刻的隱喻內(nèi)涵。情感、婚姻、家庭等對(duì)于個(gè)體而言,人生中最重要的構(gòu)成就在這些生活空間中頻繁地上演悲喜劇,并在庸常的瑣碎生活中體現(xiàn)出來(lái)———城市人的生存困境與精神的虛空。諸如《高跟鞋》《戴女士與藍(lán)》《相愛(ài)的日子》《猛虎》等作品,作家將描寫(xiě)視域放置在商場(chǎng)、日本與上海、小區(qū)、房間等尋常空間中,展現(xiàn)城市人的欲望、迷失、孤寂、仇恨等復(fù)雜的精神狀態(tài);鄉(xiāng)村人的淳樸、善良及面對(duì)生活變化的迷茫與期待,諸如《顛倒的時(shí)光》《哺乳期的女人》《風(fēng)月剪》《離歌》等作品,作品在鄉(xiāng)村空間中一般選取種菜農(nóng)民、留守兒童、裁縫等小人物,通過(guò)捕捉生活的細(xì)微變化來(lái)展現(xiàn)鄉(xiāng)民的情感世界;城市邊緣人的生存現(xiàn)狀及精神世界的迷失,如《家里亂了》《這人,像鳥(niǎo)一樣說(shuō)話》《幸福家園》《準(zhǔn)點(diǎn)到達(dá)》等作品,作品中沒(méi)有城鄉(xiāng)對(duì)立的單一體現(xiàn),而是通過(guò)對(duì)城市邊緣人群生活的描繪,展現(xiàn)他們?cè)诟鞣矫媾c城市之間的疏離,揭示他們的心理困惑與價(jià)值迷亂。(2)特定歷史背景下的人性與個(gè)體命運(yùn)關(guān)注。在畢飛宇、葉彌、蘇童等作家的作品中,、知青是經(jīng)常被關(guān)注的歷史,作家并沒(méi)有將重點(diǎn)放置在對(duì)特定歷史的評(píng)判上,歷史只是作為個(gè)體生存的背景,作品更凸顯出特定時(shí)代下人性的幽暗、欲望的膨脹、權(quán)力對(duì)人的禁錮以及個(gè)體無(wú)法掙脫的宿命般的生存境遇等。諸如《平原》《玉米》《玉秀》《河岸》《赤腳醫(yī)生萬(wàn)泉和》等作品,這些作品中躁動(dòng)的情欲、人在欲望中的異化與扭曲以及宿命般的命運(yùn)等成為描述的中心,與凝滯的日常生活糾纏為一體,呈現(xiàn)出歷史與現(xiàn)實(shí)、想象與虛構(gòu)相融的日常敘事。日常生活的審美視角的選取,使江蘇小說(shuō)既有對(duì)世俗生活中生命詩(shī)性的發(fā)掘,又有對(duì)幽暗人性及存在困境的描繪,更有對(duì)世態(tài)人情下精神向度諸多可能的思考。這種從一飲一食中把握現(xiàn)實(shí)的平穩(wěn)與常態(tài),從生活細(xì)節(jié)中承載人文關(guān)懷,正是江蘇小說(shuō)的獨(dú)特體現(xiàn)。不僅如此,城與鄉(xiāng)的互相建構(gòu)也是江蘇作家城鄉(xiāng)敘事時(shí)的另一審美呈現(xiàn)。
二、城鄉(xiāng)互望的敘事建構(gòu)
在城鄉(xiāng)現(xiàn)代化的進(jìn)程中,文學(xué)表現(xiàn)出了對(duì)這一現(xiàn)實(shí)的深切關(guān)注。江蘇作家在關(guān)注城鄉(xiāng)主題時(shí),并沒(méi)有讓城鄉(xiāng)呈現(xiàn)出單一的對(duì)立關(guān)系,而是在城與鄉(xiāng)的相互審視中表達(dá)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切與思考。主要表現(xiàn)有4點(diǎn):(1)鄉(xiāng)村人城市生活的敘述。它以鄉(xiāng)村人為主要紐帶,銜接起城市與鄉(xiāng)村,著重從鄉(xiāng)村人入城后的生存困境、人性的變異、精神的惶惑、自我的迷失以及對(duì)城市的憧憬等方面進(jìn)行敘述,范小青、魯敏、畢飛宇等作家對(duì)此進(jìn)行了充分展現(xiàn)。如《賣胡琴的鄉(xiāng)下人》《城市陷阱》《梅花開(kāi)了》《哥倆好》《字紙》《家里亂了》《唱西皮二簧的一朵》《帶蜥蜴的鑰匙》等作品,主要從鄉(xiāng)村人進(jìn)城后的視角來(lái)展現(xiàn)城鄉(xiāng)流動(dòng)中的城市與鄉(xiāng)村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以及入城后的心理及文化上的不相協(xié)調(diào),展現(xiàn)出作家對(duì)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城鄉(xiāng)差異的某種隱憂以及對(duì)村民、鄉(xiāng)村的深層關(guān)注及情感上的緬懷。(2)城鄉(xiāng)交互的視角,即在同一文本中對(duì)城鄉(xiāng)或生存主體的直接敘述。如《準(zhǔn)點(diǎn)到達(dá)》,敘述城市白領(lǐng)王健林坐火車時(shí)與2個(gè)農(nóng)民工相遇,從對(duì)他們各自的行為與人生態(tài)度中展現(xiàn)2種不同的生活境遇,尤其通過(guò)對(duì)照農(nóng)民工的生活,揭示了城市人生活的單調(diào)與心靈的脆弱,從而對(duì)城市主體生存狀態(tài)進(jìn)行深刻的反思。《城鄉(xiāng)簡(jiǎn)史》以一“賬本”連接起了城市與鄉(xiāng)村,在城鄉(xiāng)穿梭中描繪了現(xiàn)代化過(guò)程中城鄉(xiāng)間巨大的差距以及農(nóng)民對(duì)城市生活的低等期待。《無(wú)土?xí)r代》更是城市化過(guò)程中城鄉(xiāng)一體化的寓言化表達(dá)。這些文本具有很強(qiáng)的現(xiàn)實(shí)感,作家以平靜的筆觸展現(xiàn)了現(xiàn)實(shí)的發(fā)展及城鄉(xiāng)發(fā)展中各自的收獲與失落,從而展現(xiàn)對(duì)現(xiàn)代化自身的思悟。(3)鄉(xiāng)村視角的敘述,主要以鄉(xiāng)村為描寫(xiě)主體來(lái)關(guān)注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鄉(xiāng)村及鄉(xiāng)村主體的變化。如《即將消失的村莊》《顛倒的時(shí)光》《我的名字叫王村》等作品,作家用理性的態(tài)度敘述了現(xiàn)代化背景下鄉(xiāng)村的衰敗與空心化,并對(duì)持續(xù)的城市化對(duì)傳統(tǒng)文明及鄉(xiāng)村文明的影響表現(xiàn)出了某種隱憂。(4)城市與鄉(xiāng)村的各自敘述,即同一作家對(duì)城市與鄉(xiāng)村的分別關(guān)注。如魯敏在進(jìn)行城市敘述的同時(shí),又建構(gòu)了自己的“東壩系列”小說(shuō),從鄉(xiāng)村的淳樸與良善中來(lái)暗示城市隱含的頑疾。畢飛宇觀照的則是特殊歷史境遇下的鄉(xiāng)村人性及其命運(yùn),與其表現(xiàn)城市生活的作品相比,鄉(xiāng)村作品的背后總有種難掩的憂傷。其實(shí),城鄉(xiāng)互望的敘事是在社會(huì)變遷影響下城鄉(xiāng)交互融合的文學(xué)表現(xiàn),與其他作家創(chuàng)作不同的是,江蘇作家將城市與鄉(xiāng)村互為參照,在不割裂城鄉(xiāng)關(guān)系的前提下,將城市與鄉(xiāng)村主體各自的生存境遇作為主要的描繪內(nèi)容,通過(guò)對(duì)個(gè)體命運(yùn)的關(guān)注來(lái)思考城鄉(xiāng)社會(huì)的整體命運(yùn),充分體現(xiàn)出以人為本的寫(xiě)作立場(chǎng)和審美理想。這也是江蘇小說(shuō)的另一審美價(jià)值所在。
三、世俗化與詩(shī)性品質(zhì)的交融
江蘇作家一直就有關(guān)注大時(shí)代里凡人瑣事的文學(xué)傳統(tǒng),如老一輩作家葉圣陶的一些作品,新時(shí)期以來(lái),江蘇作家更是繼承了這一傳統(tǒng),陸文夫、汪曾祺、蘇童、畢飛宇、范小青等作家的作品,以平凡生活狀態(tài)下的普通人的悲歡離合作為他們敘述的內(nèi)容。與其他作家相比較,在江蘇作家的作品中,看不到對(duì)平庸沉滯的日常生活的凸顯,更看不到對(duì)個(gè)體日常體驗(yàn)的情緒化的癡迷,展現(xiàn)更多的是衣食住行里的人性、人情和豐富的精神特征。所以,對(duì)日常生活的理解與選擇往往影響著作家的價(jià)值立場(chǎng)與敘事情感價(jià)值取向。江蘇作家總是力圖從庸常的日常生活中尋找著人生的驚喜,發(fā)掘著生活的詩(shī)性,從而展現(xiàn)一定的意義深度。世俗性與詩(shī)性的交融成為江蘇作家的獨(dú)特體現(xiàn)。世俗性,是指文學(xué)對(duì)俗世生活的美學(xué)呈現(xiàn)。畢竟,每個(gè)個(gè)體的人生都無(wú)法擺脫愛(ài)情婚姻、地域風(fēng)情、休閑娛樂(lè)等日常經(jīng)驗(yàn)世界的羈絆,文學(xué)需要從綿長(zhǎng)、瑣碎的俗世生活狀態(tài)中探尋可能性的存在,所以世俗性充分體現(xiàn)了文學(xué)與現(xiàn)實(shí)生活的緊密聯(lián)系。“日常生活是一個(gè)與人的生存直接相關(guān),人的生存和再生產(chǎn)以及人的消費(fèi)、交往、觀念等活動(dòng)在其間存在并展開(kāi)的人性世界。”[2]在新時(shí)期以來(lái)江蘇作家的作品中,無(wú)論是對(duì)市井生活的描摹,特定歷史背景下的人生展現(xiàn),還是近年來(lái)城鄉(xiāng)遷移背景下的社會(huì)關(guān)注,個(gè)體的生存訴求與生命愿望成為主要的敘事內(nèi)容。在早期的描寫(xiě)農(nóng)民的作品中,諸如《李順大造屋》《陳奐生上城》《石門(mén)二柳》等作品,盡管仍然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卻是以普通農(nóng)民樸素的個(gè)體訴求為基本內(nèi)容,即使后面出現(xiàn)的《平原》《玉米》《我們的戰(zhàn)斗生活像詩(shī)篇》《李小蘭和她的朋友》等以為背景的作品,它們都將社會(huì)、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等融入世俗的生活中,從愛(ài)情、婚姻、家庭等情境中來(lái)展現(xiàn)人間的冷暖,人性的豐厚及心靈的遷徙。“我眼中的歷史是日常的……歷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構(gòu)成的,歷史是日復(fù)一日、點(diǎn)點(diǎn)滴滴的生活的演變,它只承認(rèn)那些貼膚可感的日子。”
正是由于日常生活的浸潤(rùn),這些大歷史下的瑣事與凡人,才顯得格外親近動(dòng)人。一些貼近現(xiàn)實(shí)生活的作品,如《我就是我想象中的那個(gè)人》《即將消失的村莊》《赤腳醫(yī)生萬(wàn)泉和》《水姻緣》《莉莉姨媽的細(xì)小南方》《推拿》《無(wú)土?xí)r代》《我的名字叫王村》等,這些作品中農(nóng)民工、赤腳醫(yī)生、普通小市民、商人、村長(zhǎng)、城市生活的盲人、智障者、保安等成為主要的描寫(xiě)對(duì)象,充分展現(xiàn)國(guó)家的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過(guò)程中普通凡人的生存愿望、困惑、迷失、孤獨(dú)及其種種無(wú)法言說(shuō)的生存?zhèn)础7卜蛩鬃拥纳媾c瑣碎生活的纏繞構(gòu)成了江蘇作家創(chuàng)作的共同底色,其中滿蘊(yùn)的卻是個(gè)體與現(xiàn)實(shí)沖突下的種種不確定性。盡管江蘇作家普遍選取日常的生活視角,但是他們并沒(méi)有陷入庸常生活的淺顯呈現(xiàn),而是力圖從平凡生活的不確定中尋求一種詩(shī)性的支撐,這種詩(shī)性主要體現(xiàn)為地域文化的傳承與彰顯及直面現(xiàn)實(shí)的文學(xué)理想的重建。地處長(zhǎng)江三角洲的江蘇,文化呈現(xiàn)出多元化的特征,這里既有內(nèi)秀儒雅的吳文化,又有瀟灑豪放的楚文化,還有雍容高雅的金陵文化等,所以在不同地域文化的浸染下,江蘇文學(xué)呈現(xiàn)出了與多元地域文化精神相契合的審美風(fēng)貌。陸文夫、朱文穎、范小青等對(duì)蘇州小巷文化的執(zhí)著追求,汪曾祺、葉兆言的民俗風(fēng)情畫(huà)卷,蘇童、畢飛宇、荊歌等江南園林似的人性描摹,還有趙本夫?qū)Υ肢E豪放的楚地風(fēng)情的刻意展現(xiàn)。這些特點(diǎn)共同展現(xiàn)了江蘇文學(xué)的敘事風(fēng)格:溫婉、細(xì)膩、深沉。江蘇作家在堅(jiān)守自身創(chuàng)作價(jià)值觀的同時(shí),都非常自覺(jué)地發(fā)掘著豐厚的傳統(tǒng)資源和民間資源,從普通平實(shí)的自然人生中傳達(dá)出對(duì)生活、生命本質(zhì)的理解與領(lǐng)悟,從民間世界中發(fā)掘著生存的頑強(qiáng)與精神的強(qiáng)大,從而構(gòu)建著文學(xué)的精神向度。無(wú)論是蘇童的香椿樹(shù)街、新歷史主義小說(shuō)以及最新的作品《黃雀記》,魯敏的東壩系列小說(shuō),畢飛宇特定歷史背景下的鄉(xiāng)村小說(shuō)和關(guān)注城市弱勢(shì)群體的小說(shuō),還是范小青、趙本夫的現(xiàn)實(shí)轉(zhuǎn)型背景下的城鄉(xiāng)敘事,都能從中讀出作家從社會(huì)、文化、倫理等角度對(duì)個(gè)體生存本身的思考,其中既有對(duì)存在困境的展示、豐厚人性的描摹,更有對(duì)生命價(jià)值及意義的理性深思。“我一向認(rèn)為,在中國(guó)民間的生存哲學(xué)里,特別有一種自圓其說(shuō)的能力,再糟的生活、再不堪的境地,人們都能夠在‘自嘲’和‘小滿足’中實(shí)現(xiàn)自我安慰、苦中作樂(lè)。中國(guó)人歷代多難,但生命力之頑強(qiáng)、偷生之余歡,實(shí)在罕見(jiàn),常令我感動(dòng)而珍重……”從普通人世中發(fā)現(xiàn)生命的尊嚴(yán)與高貴,從卑微個(gè)體中發(fā)掘人性的豐厚與溫暖,已成為江蘇作家主要的創(chuàng)作姿態(tài)。以凡俗生活為底色的詩(shī)性品質(zhì),正是江蘇小說(shuō)的獨(dú)特審美價(jià)值。
四、結(jié)論
城市與鄉(xiāng)村本是不同的生存之地,在中國(guó)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的大時(shí)代背景下,當(dāng)代作家都依據(jù)自身的書(shū)寫(xiě)立場(chǎng)與姿態(tài)對(duì)其進(jìn)行了多樣的審美表現(xiàn),呈現(xiàn)出了不同的文本。江蘇作家關(guān)注城鄉(xiāng)主題時(shí),并不著眼于展現(xiàn)時(shí)代變遷的宏大敘事,而是從日常生活的瑣碎、城鄉(xiāng)的相互對(duì)照中來(lái)探究生命個(gè)體的存在處境及其命運(yùn)走向,并希望從庸常瑣碎的生活中尋求一種詩(shī)性的價(jià)值支撐,這種注重人的寫(xiě)作立場(chǎng)和姿態(tài)與“文學(xué)是人學(xué)”的價(jià)值取向相契合,也正因?yàn)槿绱耍K小說(shuō)的城鄉(xiāng)敘事呈現(xiàn)出了世俗化與詩(shī)性品質(zhì)相互交融的特色。或許江蘇文學(xué)長(zhǎng)久以來(lái)一直缺少史詩(shī)性的著作,但從衣食住行中來(lái)觸摸人的心理與靈魂,關(guān)注人的精神與生存,是江蘇文學(xué)對(duì)當(dāng)代文學(xué)的獨(dú)特貢獻(xiàn)。
作者:張春歌 楊紅英 單位:江蘇理工學(xué)院 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