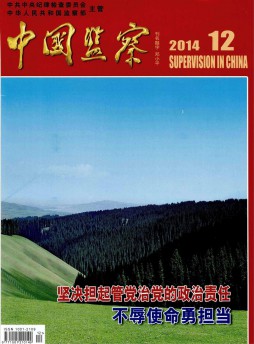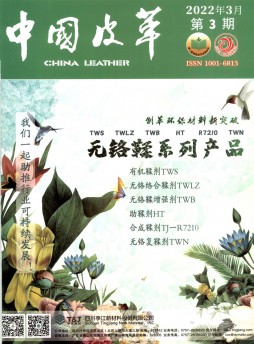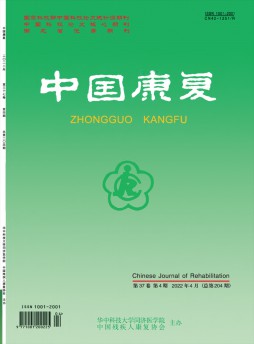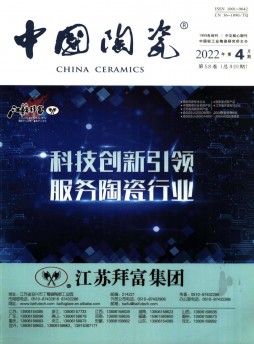中國歷史地理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中國歷史地理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一、關于諸環境要素的歷史變遷
(1)氣候變遷。繼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后,氣候變遷的研究成果斐然。龔高法、張丕遠、張瑾瑢等指出仰韶時期普遍較現今溫暖,相應的氣候帶較現在偏北;歷史時期亞熱帶的北界,在最溫暖時曾達到華北平原,而在最寒冷時期卻移至長江以南(《歷史時期我國氣候帶的變遷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歷史地理》第五輯)。倪根全認為歷史時期氣候變遷造成了我國北方濕潤區和半濕潤區由北向南的退縮,使得我國農業地區不斷南退,這也是我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的重要原因之一(《論氣候變遷對中國古代北方農業經濟的影響》,《農業考古》1988年第1期)。滿志敏《唐代氣候分期及各期氣候冷暖特征的研究》一文以八世紀中葉為轉折點,把唐代氣候分為兩個時期,認為從七世紀初至八世紀中葉,氣候冷暖特征與今相近,而八世紀中葉至十世紀中葉氣候轉寒,氣候帶要比現代南退一個緯度(《歷史地理》第八輯)。吳宏歧從唐長安馴象的史實入手,對滿志敏的上述觀點予以反駁,認為其論斷不足以否定隋唐溫暖期的存在,而傳統的關于隋唐溫暖期的劃分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唐都長安的馴象及其反映的氣候狀況》,《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年第4輯)。滿志敏還就歷史時期黃淮海平原的氣候特征進行了探討(《黃淮海平原仰韶溫暖期的氣候特征探討》、《黃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葉的氣候冷暖狀況》,《歷史地理》第十、十一輯)。鄒逸麟對明清時期北方氣候進行了研究(《明清北部農牧過渡帶的推移和氣候變化》,《復旦學報》1995年第1期)。何業恒分析了近五千年來華南地區的冷暖變化情況(《近五千年來華南氣候冷暖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年第1輯)。王開發、韓昭慶就歷史時期上海西部和太湖流域的氣候狀況進行了探討(《根據孢粉組合推斷上海西部三千年來的植被、氣候變化》,《歷史地理》第六輯;《明清時期太湖流域冬季氣候研究》,《復旦學報》1995年第1期)。藍勇和于希賢則就西南地區的氣候變遷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國西南歷史氣候初步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2輯;《蒼山雪與歷史氣候冷期變遷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年第2期)。
(2)海陸變遷。李元芳分析認為:西漢黃河三角洲范圍以孟村為頂點,自西向東北方向發展,其沉積特征與近代黃河三角洲相似(《西漢古黃河三角洲初探》,《地理學報》1994年第6期)。張忍順指出,近岸沙州并岸是江蘇濱海平原成陸的重要特征,十五世紀末黃河奪淮入海給江蘇岸外沙州田暗沙、明沙、直至并岸造成了巨大影響(《歷史時期的江蘇岸外沙州及其演變》,《歷史地理》第八輯)。張修桂、陳金淵分別分析了上海和南通地區的成陸過程(《上海地區成陸過程概述》,《復旦學報》1997年第1期;《南通地區成陸過程探索》,《歷史地理》第三輯)。景愛探討了科爾沁地的形成過程(《科爾沁地的形成過程及其影響》,《歷史地理》第七輯)。馮季昌等則全面系統地描繪了科爾沁河地經歷的四個變遷階段(《論科爾沁河的歷史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年第3輯)。劉德岑撰文探討了梁山泊的淤平過程(《從大野澤到梁山泊》,《西南師大學報》1990年第2期);鄭寶恒等則就連云港市的水陸變遷進行了研究(《連云港市的水陸變遷》,《歷史地理研究》第二輯)。此外,林汀水、張修桂還探討了海岸線的變遷(《遼東灣海岸線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年第2輯;《金山衛及其附近一帶海岸線的變遷》,《歷史地理》第三輯)。
(3)沙漠與沙漠化。李淼在《對歷史時期烏蘭布和沙漠成因的幾點認識》一文中指出,烏蘭布和沙漠屬于非原生性沙漠,主要是在漢代以后形成和發展的(《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陳育寧考察了鄂爾多斯地區沙漠化形成和發展的過程,認為自秦漢以來的過度開墾是引起沙漠化的主要人為因素(《鄂爾多斯地區沙漠化的形成和發展述論》,《中國社會科學》1996年第2期)。他又探討了寧夏地區沙漠化的情況,認為干旱多風,近百年來氣候干化是土地沙化的重要自然因素(《寧夏地區沙漠化的歷史演進考略》,《寧夏社會科學》1993年第3期);景愛、馬正林也對引起沙漠化的原因進行了探討(《木蘭圍場的破壞與沙漠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年第2輯;《人類活動與中國沙漠地區的擴大》,《陜西師大學報》1984年第3期)。李并成從敦煌文書中發現了古代瓜沙二州間的一塊綠洲,并探討了這塊綠洲的沙漠化過程(《瓜沙二州間一塊消失了的綠州》,《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他還揭示了河西走廊古綠洲沙漠化區域的分布特點和結構特征(《河西走廊漢唐古綠洲沙漠文化的調查研究》,《地理學報》1998年第2期)。
(4)植被的變遷。對于歷史時期植被變遷史的研究,史念海貢獻最大。他認為黃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區在遠古之時森林相當茂密;黃河中上游可以稱道的森林亦不少;長江流域及珠江流域森林相當普遍;東北地區直到清代尚極繁多(《論歷史時期我國植被的分布及其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年第3期;《歷史時期森林變遷的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總第6輯)朱士光《全新世中期中國天然植被分布概況》(《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總第6輯)和《歷史時期我國東北地區的植被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年第4輯)兩文深入分析了歷史時期植被的更替情況。文煥然、周云庵、袁森坡、郭松平等分別探討了歷史時期新疆、秦嶺、塞外承德及凌源的森林變遷(《歷史時期新疆森林的分布及其特點》,《歷史地理》第六輯;《秦嶺森林的歷史變遷及其反思》,《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1輯;《塞外承德森林歷史變遷及其反思》,《河北學刊》1986年第2輯;《凌源森林盛衰和自然災害》,《農業考古》1986年第1期)。王守春《明清時期黃土高原植被與環境》一文指出,明清時期黃土高原天然植被受到人類的破壞比以前任何時期都嚴重(王守春主編:《黃河流域地理環境演變與水沙運行規律研究文集》第五集,海洋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楠木是珍貴樹種,藍勇認為先秦時期楠木的分布比現在要偏北一些;唐宋時以今四川為多;明清時期由于采辦皇木,加之氣候趨冷,楠木資源日漸枯竭(《歷史時期中國楠木地理分布變遷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年第4輯;《明清時期的皇木采辦》,《歷史研究》1994年第6期)。我國古代黃河流域盛產竹子。文煥然指出華北西部歷史上栽培竹林的分布呈面積大小不一,不連續的斑點狀,漢代以前最北分布似在40°N,現今似在36°N(《二千多年來華北西部經濟栽培竹木之北界》,《歷史地理》第十一輯)。
(5)野生動物的變遷。關于歷史時期動物的研究,何業恒成果頗豐。他先后出版了《中國珍稀獸類的歷史變遷》(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中國珍稀鳥類的歷史變遷》(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中國珍稀獸類(Ⅱ)的歷史變遷》(湖南師大出版社1996年版)、《中國珍稀爬行類、兩棲類和鳥類的歷史變遷》(湖南師大出版社1997年版)。他認為我國歷史時期金絲猴的地理分布遠比今天為廣;我國是曾見朱鹮數量最多,分布最廣的國家;而大熊貓的地理分布范圍經歷了一個由小到大又縮小的變化過程;到十八世紀平原地區的華南虎相繼絕跡;歷史時期我國三種麝的分布范圍遠比當今廣;而揚子鱷由于氣候變化、棲息環境的破壞以及人類的亂捕濫獵,分布北界不斷南移(《試論金絲猴的地理分布及其演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年第4輯;《論試朱鹮地理分布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年第3期;《試論大熊貓的地理分布及其演變》,《歷史地理》第十輯;《試論華南虎在長江三角洲的絕跡》,《歷史地理》第十一輯;《中國麝地理分布的變遷和麝香生產的消失》,《史念海八十壽辰學術文集》,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揚子鱷在黃河中下游的地理分布及其南移的原因》,《歷史地理》第十五輯)。裴修碧、文煥然分別探討了歷史時期揚子鱷、野馬野驢的分布變化(《上古時期揚子鱷分布地域考》,《安徽史學》1996年第3期;《歷史時期中國野馬野驢的分布變遷》,《歷史地理》第十輯)。文煥然、王振堂、藍勇對野生犀象的歷史變遷進行了考察(《再探歷史時期的中國犀象分布》,《思想戰線》1990年第5期;《犀牛在中國滅絕與人口壓力關系的初步分析》,《生態學報》1997年第6期;《歷史時期中國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索》,《歷史地理》第十二輯)。此外還有劉洪杰《中國古代獨角動物的類型及其地理分布的歷史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年第4輯)等。
(6)水文的變遷。對黃河的研究依然是水文變遷研究的重點。鄒逸麟的《千古黃河》一書是繼岑仲勉《黃河變遷史》之后的又一研究黃河的力作,是學術界有關黃河研究的最新總結(香港中華書局1990年5月版)。譚其驤等老一輩歷史地理學家認為黃河在東漢以后800余年間長期處于安流狀態。趙淑貞、任伯平對此提出了疑議。他們認為決溢次數的多寡并不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東漢以后黃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的缺失均是導致“安流”局面的因素(《關于黃河東漢以后長期安流問題的再探討》,《地理學報》1998年第5期)。徐海亮《歷史上黃河水沙變化的一些問題》一文推測黃河在歷史上的水沙變化可能存在更為宏觀的環境背景(《歷史地理》第十二輯)。史念海探討了黃土高原主要河流及西安周圍諸河流的流量變化(《黃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年第2輯;《論西安周圍諸河流量的變化》,《陜西師大學報》1992年第3期)。譚其驤、張修桂分別探討了海河水系分合離聚的歷史過程(《海河水系的形成與發展》,《歷史地理》第四輯;《海河流域平原水系演變的過程》,《歷史地理》第十一輯)。此類文章還有鄒逸麟《歷史時期華北大平原湖沼變化變遷述略》(《歷史地理》第五輯);朱玲玲《明清時期滹沱河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9年第1輯);林汀水《遼河水系的變遷與特點》(《廈門大學學報》1992年第4期)。
長江江流的清濁變化引起了周宏偉的關注,他認為歷史時期長江干流出現過九次較為明顯且持續時間較長的清濁變化,而人類活動和氣候變遷可能是造成清濁變化的主因(《歷史時期長江清濁變化的初步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年第4期)。對于河道變遷的研究有助于推動長江研究的開展。中國科學院地理所編寫的《長江中下游河道特性及其演變》一書是一部關于長江中下游河道演變的綜合性論著,該書詳細論述了全新世以來長江中下游河道的變遷情況(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張修桂撰文討論了長江中游河床的演變過程,為三峽工程提供了背景資料(《長江宜昌至城陵磯段河床歷史演變及其影響》,《歷史地理研究》第二輯;《近代長江中游河道演變及其整治》,《復旦學報》1994年第6期)。周風琴對湖北沙市河段河道及荊江的歷史變遷進行了研究(《湖北沙市地區河道變遷與人類活動中心的轉移》,《歷史地理》第十三輯);《荊江歷史變遷的階段性特征》,《歷史地理》第十輯)。張修桂推翻了荊江百里洲于十六世紀由水流切灘形成的說法,認為其演變過程是以漸變為主要形式(《荊江百里洲河段河床的歷史演變》,《歷史地理》第八輯)。滿志敏對黃浦江水系的形成原因進行了分析(《黃浦江水系的形成原因述要》,《復旦學報》1997年第6期)。
(7)災害史。請參見卜鳳賢《中國農業災害史研究綜論》(《中國史研究動態》2001年第2期),此不贅述。
二、關于環境史的綜合研究
(1)對環境的綜合評價。朱士光通過對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分布及目前殘存的植被的考察,對歷史時期農業生態環境變遷作了初步探討(《歷史時期農業生態環境境變遷初探》,《地理學與國土研究》1990年第2期)。王乃昂則分析了歷史時期甘肅的環境變遷(《歷史時期甘肅黃土高原的環境變遷》,《歷史地理》第八輯)。李民《殷墟的生態環境與盤庚遷移》一文指出,殷墟良好的生態環境是盤庚遷殷的重要原因(《歷史研究》1991年第1期)。唐亦功的《金至民國時期京津唐地區的環境變遷研究》(陜西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一書探討了京津唐地區金到民國時期的環境變遷。此類文章還有徐海鵬《北京新石器時代人類活動的地理環境》(《北京大學學報(專刊)》1992年7月)、于希賢《北京市歷史自然環境變遷的初步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年第1輯)、趙永復《歷史時期黃淮平原南部的地理環境變遷》(《歷史地理研究》第二輯)、張寶秀《灤河潮河中上游地區三百年來自然環境的變過(《環境變遷研究》1996年第5輯)、高俊虎《三百年來承德地區地理環境演變趨勢初探》(《干旱區研究》1998年第2期)、張自強《江海平源的自然基礎和先民文化之探討》(《東南文化》1996年第1期)、馬強《蜀道地帶生態環境的歷史變遷》(《成都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等。
(2)人地關系研究。90年代以來,人們在加強對環境諸要素研究的同時,也開始探尋人類活動對歷史環境的影響。鄒逸麟在1998年長江洪災過后撰文呼吁:現在應該靜下心來,實事求是地研究迄今為止的我國全部人地關系發展的歷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關于加強人地關系歷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報》1998年11月6日)。韓茂莉則對歷史時期黃土高原人地關系研究作了總體性回顧(《歷史時期黃土高原人類活動與環境關系研究的總體回顧》,《中國史研究動態》2000年第10期)。朱士光、馬雪芹、王建革、賈毅等也對黃河流域的人地關系進行了探討(《我國黃土高原地區幾個主要區域歷史時期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變遷概況》,《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年第1期;《明清時期黃河流域農業開發和環境變遷述略》,《徐州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馬政與明代華北平原的人地關系》,《中國農史》1998年第1期;《白洋淀環境演變的人為因素分析》,《地理學與國土研究》1992年第4期)。
關于長江流域人地關系的研究也有很大進展。藍勇認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來長江上游地區的水土流失加重了中下游的洪澇災害(《歷史上長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光明日報》1998年9月25日)。劉沛林認為長江流域水災頻率的增強基本上是與歷史上地區開發的進程同步的(《歷史上人類活動對長江流域水災的影響》,《北京大學學報》1998年第6期)。張潤元、張國雄、龔勝生分別就長江流域各重點林區及沿江湖區的人地關系進行了探討(《清代長江流域人口運動與生態環境的惡化》,《學術月刊》1994年第4期;《明清時期兩湖開發與環境變遷初議》,《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年第2期;《清代西湖地區人口壓力下的生態環境惡化及其對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1期)。
此類文章還有祝功武等《廣東水土流失歷史變遷》(《歷史自然地理研究》1995年第2期),戴一峰《近代閩江上游山區的開發和生態環境》(《廈門大學學報》1991年第4期),鄧輝《全新世氣候最宜期燕北地區人地關系研究》(《環境變遷研究》1996年第5期)、《全新世大暖期燕北人地關系的演變》(《地理學報》1997年第1期),韓光輝《清代以來圍場地區人地關系演變過程研究》(《北京大學學報》1998年第3期)等。
(3)環境保護史及古人生態哲學研究。羅桂環等《中國環境保護史稿》(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一書是一部系統論述中國環境保護史的專著。鄒逸麟以先秦兩漢為例,探討了我國古代環境意識產生的歷史地理背景、不合理的環境行為及后果(《我國古代的環境意識與環境行為》,《慶祝楊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論文集》)。劉世芮分析了先秦文化中的生態文明觀念(《先秦文化中的生態文明觀念》,《社科縱橫》2000年第4期)。倪根全《秦漢環境保護初探》(《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探討了秦漢時期存在的環境問題、自然環境的保護措施及污染防治。陳業新則對秦漢時的生態職官進行了考察(《秦漢生態職官考述》,《文獻》2000年第4期)。劉華介紹了唐代環境的保護情況(《我國唐代環境保護情況述論》,《河北師大學報》1993年第2期)。張全明探討了宋代生物資源保護的特點和宋人的生態意識(《論宋代的生物資源保護及其特點》,《求索》1999年第1期;《簡論宋人的生態意識與生物資源保護》,《華中師大學報》1999年第5期)。王風雷分析了元代野生動物保護的法律條款(《論元代野生動物保護條款》,《內蒙古社會科學》1996年第3期)。楊昶考察了明人的生態觀念(《明代的生態觀念和生態農業》,《中國典籍與文化》1998年第4期)。
(4)從文化角度研究生態環境的初步嘗試。生態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狀態,文化則是體現人類思想和實踐的現象。兩者相互影響,而其中生態對文化起著決定作用,這是王玉德、張全明提出的觀點。他們的《中華五千年生態文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10月版)正是基于上述理論展開的。全書共十六章,分上下兩編,從橫、縱兩個方面對五千年來中華生態文化進行了探討。上編七章分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代、清代七個階段探討了中華五千年的生態環境的變遷及其與政治、經濟、民俗、學術的相互作用;下編九章分別分析了古代氣候、土壤、生物資源、水文、礦產、災害等諸生態因素的變遷和文化的相互影響,并探尋了中國古代生態旅游文化的特征及古代人們的生態思想。余論部分則從生態文化的角度分析了當代中國所面臨的決策、土地、人口、水、大氣、森林、廢物處理、噪音、珍稀動物、交通等十大問題并提出了相應的建議。此書作為從文化角度探索我國長時段生態環境的初步嘗試,無疑為我們開闊了視野,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三、關于理論、方法及今后研究的方向
環境史是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出現的以人類與環境相互作用的歷史為對象的一門學科。包茂宏在介紹美國環境史學的發展史的基礎上提出了對環境史概念的新認識。他認為:“環境史就是以建立在環境科學和生態學基礎上的當代環境主義為指導,利用跨學科的方法,研究歷史上人類及其社會與環境之相互作用的關系;通過反對環境決定論,反思人類中心主義文明觀來為瀕臨失衡的地球和人類文明尋找一條新路,即生態中心主義文明觀”。他把環境史分為三個階段:人與環境基本和諧相處的環境與前現代文明期,人類中心主義的現代文明對環境的征服及走向生態中心主義的超越現代文明的新文明觀。提出了建立我國的環境史學派的大膽構想(《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4期)。
第2篇
[關鍵詞]歷史民族地理;區域歷史地理;歷史人文地理
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對歷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十分活躍。而歷史民族地理這一概念的提出,始于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先生,在他的代表性著作《中國歷史地理綱要》一書中,專辟有“歷史民族地理”一章,把歷史民族地理視為與歷史政治地理、歷史城市地理、歷史交通地理、歷史人口地理、歷史文化地理、歷史軍事地理等并列的歷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學科。[1]史先生“歷史民族地理學”概念的提出意義重大,直接引發了以后對歷史民族地理學和民族歷史地理學的重視及對此項研究工作的展開。之后郭聲波先生和安介生先生,進一步探討了歷史民族地理學的基本概念與科學性質、研究現狀、研究方法、研究的地域范圍與內容劃分、研究的基本資料等諸多問題。[2]
在史念海先生提出的“歷史民族地理學”概念的基礎上,黃盛璋先生首先提出了“民族歷史地理學”的概念,并把民族歷史地理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來看待。[3]對于這一觀點,劉錫濤、李并成、朱圣鐘等先生表示贊同,并針對民族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等進行了探討,推動了該學科理論建設體系的不斷完善。[4]
到目前為止,學術界關于歷史民族地理與民族歷史地理的討論方興未艾,其是否能夠成為一門獨立學科也并無定論。筆者認為,不管是歷史民族地理還是民族歷史地理其實質并無區別,徐強在《論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學科屬性》[5]一文中已有論述,故將歷史民族地理另行稱為民族歷史地理沒有必要, 將其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的學科是不妥當的。但按照傳統的學科體系劃分方法,把歷史民族地理作為歷史人文地理的分支也不盡合理,從研究內容來看,歷史民族地理不僅研究人文地理現象,而且研究自然地理現象,所以簡單的把歷史民族地理作為歷史人文地理的分支有失偏頗。事實上,在歷史地理學的學科體系中,除了包括歷史自然地理和歷史人文地理外,區域綜合歷史地理學、歷史地理學理論、歷史地圖學、應用歷史地理學,[6]而把歷史民族地理作為區域綜合歷史地理學的分支更為合理。
所謂歷史民族地理學,就是研究歷史時期少數民族地區的歷史地理狀況的學科。如果說歷史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環境及其演變規律的學科,那么歷史民族地理學就是研究少數民族地區歷史時期地理環境及其演變規律的學科。而從古至今,少數民族的分布都呈現出區域性特點,故將其作為區域綜合歷史地理學的分支。
一、歷史民族地理不應屬于歷史人文地理的分支
在早期的研究中,歷史民族地理主要是研究歷史時期不同地域上民族的起源、發展、分布與變遷的歷史過程以及分析產生這一變化的原因。但隨著近年來研究的深入,研究內容有所擴大,例如朱圣鐘先生《一萬年以來涼山地區氣候變遷》[7]一文,屬于歷史民族地理范疇,卻不屬于歷史人文地理范疇。經初步整理可將目前的研究分為以下幾部分:(1)歷史民族地理民族學的理論與方法,包括學科屬性之討論、研究對象的確定、歷史地理學方法、民族學方法等。(2)民族地區歷史人文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區歷史政區地理、歷史經濟地理、歷史人口地理、歷史交通地理、歷史軍事地理、歷史文化地理、歷史聚落地理等分支。(3)民族地區歷史自然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區歷史氣候變遷、歷史水文地理、歷史動物地理、歷史植物地理、歷史礦藏地理、歷史時期自然災害情況等。(4)民族地區歷史地理文獻研究,包括漢文資料如《蠻書》、《華陽國志》、正史地理志、各類游記、碑刻等,以及少數民族文字資料。
綜上,歷史民族地理學的研究內容相當豐富,既包括理論體系的探討,也包括具體問題的研究。歷史民族地理學既研究民族地區歷史時期的自然地理現象,同時也研究民族地區歷史時期的人文地理現象。故不能將其作為歷史人文地理的分支。
二、將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獨立學科是不合理的
黃盛璋、李并成、劉錫濤、朱圣鐘等先生將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的研究稱為民族歷史地理學, 并主張將其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的學科。但看完幾位先生的論文后,將民族歷史地理學與前面提到的歷史民族地理學對比, 不難發現二者的研究范圍都限于歷史時期, 研究對象都是民族實體, 研究內容都是與民族實體有關的地理問題,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二者是基本一致的, 沒有明顯區別。既然二者沒有明顯區別, 那么將歷史時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稱之為民族歷史地理學就沒有必要了。
某一學科的獨立存在總是建立在與其他學科相區別的前提之下, 黃盛璋先生把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是基于三個方面的原因, 他指出:1. 當前各方的需要, 日益要求提到討論日程上來;2. 重視民族歷史地理記載與研究, 是中國學術傳統;3. 中國具有一定的研究條件和基礎。[8]但僅憑這三點將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 是難以令人信服的。歷史地理學是否是一門獨立的學科,還得從研究對象和內容、研究理論和方法等方面界定。
盡管歷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對象和內容豐富,但其不足以構成獨立的學科體系,歷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對象和內容均屬于歷史地理學的范疇。
再從研究方法來看,歷史民族地理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文獻分析法:這是歷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同時在歷史民族地理學研究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豐富的歷史文獻是獲取民族歷史地理信息的一個重要途徑,雖然歷代正史地方志對民族地區記載較為簡略,但各時期的總志、地方志、筆記、游記等記載了豐富的民族歷史地理信息,是我們進行研究的主要資料來源。
民族調查法(或稱之為實地考察):是進行歷史民族地理研究的方法之一。歷史民族地理雖說是談歷史上的東西, 但歷史是延續的。其次,由于歷史久遠,許多文獻的記載多有出入,這要求從事歷史民族地理學研究的工作人員深入到民族地區,對民族居住地(包括歷史時期的民族居住地和現在民族分布地區)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進行詳細的考察,獲取研究所需的第一手資料,然后進行分析研究。早在建國初期,許多的民族工作者深入到民族地區進行社會歷史考察,撰寫了大量的民族、民俗調查報告,這些民族調查材料也是從事民族歷史地理學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9]
各類圖表法:地理學家巴朗斯基曾說過:“地圖是地理學的第二語言, 并且應該說它永遠是更經濟, 更容易了解的語言。地圖能使人很容易地了解許多在正文里往往必須用很多篇幅來敘述, 但完全得不到充分效果的東西”。可見, 充分利用圖表, 是民族歷史地理學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10]
考古學方法:在歷史民族地理學的研究中,更多的是使用考古資料,進行直接現場挖掘的情況較少。
現代技術手段的運用:隨著社會、科學技術的發展, 在研究民族歷史地理學過程中,除采用傳統的研究方法外, 還應采用經濟論證法、電子計算機、遙感遙測等新技術手段。這些都會使我國的民族歷史地理研究達到一個新的水平。
盡管歷史民族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多樣,但這些都借鑒了歷史地理學甚至是歷史學、民族學的方法,歷史民族地理學自身并無特有的研究方法。
三、歷史民族地理應作為區域歷史地理學的分支
歷史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環境及其演變規律,以及與人類關系的科學。對于歷史地理學的理論體系, 國內外學者多按其研究內容分為兩大類, 即歷史自然地理與歷史人文地理。除此之外, 還有把歷史自然與人文地理各要素綜合起來進行研究的論著, 比如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于希賢主編的《滇池歷史地理》, 則屬于區域歷史地理學研究的范疇。
根據李令福觀點,歷史地理學主要研究歷史自然地理、歷史人文地理、區域綜合歷史地理學、歷史地圖學以及歷史地理學理論等方面的內容。[11]所謂區域歷史地理學是指以特定的地域為對象,揭示該區域環境條件(包括自然環境、人文環境或其總體)的發展與演變。區域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區域歷史自然地理、區域歷史人文地理、區域歷史地理專題研究和區域歷史地理綜合研究。[12]由上可知,歷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內容屬于歷史區域地理的范疇。
四、小結
總之,某一學科的獨立存在總是建立在與其他學科相區別的前提之下,所謂的民族歷史地理學與歷史民族地理學, 無論是在研究范圍、研究對象還是在研究內容上都沒有區別, 因而將歷史時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稱之為民族歷史地理(下轉第26頁)(上接第10頁)學沒有必要,故以歷史民族地理學為基礎,提出民族歷史地理學的概念,并將其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是不太成熟的。
事實說明,歷史民族地理學既研究人文地理現象、也研究自然地理現象,而把歷史民族地理單純的歸為歷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就會不盡全面,綜合各方面因素,將其作為區域歷史地理學的分支較為合理。
參考文獻:
[1]史念海.中國歷史地理綱要(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2]郭聲波.歷史民族地理的多學科研究――以彝族歷史地理為例.南方開發與中外交通――2006年中國歷史地理研討會論文集.西安地圖出版,2007;安介生.略論中國歷史民族地理學.歷史地理第二十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黃盛璋.論民族歷史地理學的基本理論問題.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5(5).
[4]李并成.西北民族歷史地理研究當議.甘肅民族研究,1997(1);劉錫濤.中國民族歷史地理學的幾個理論問題.喀什師范學院學報,2000( 1);朱圣鐘.論民族歷史地理學研究的若干問題.廣西民族研究,2005(1).
[5]徐強.論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學科屬性.貴州民族研究,2008(5).
[6]李令福.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理論體系、學科屬性與研究方法.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0(3).
[7]朱圣鐘.一萬年以來涼山地區氣候變遷.云南地理環境研究,2007(3).
[8]黃盛璋.論民族歷史地理學的基本理論問題.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5(5).
[9]朱圣鐘.論民族歷史地理學研究的若干問題.廣西民族研究,2005(1).
[10]劉錫濤.中國民族歷史地理學的幾個理論問題――兼談新疆民族歷史地理.喀什師范學院學報,2000(3).
第3篇
關鍵詞: 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 研究 困境與契機 主要學術成果展望
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是歷史自然地理學的重要分支領域,其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我國歷史時期動物的分布和變遷,包括自古至今我國野生動物分布地區的變化,珍稀動物數量的減少及其深層原因探究。歷史動物地理研究一些珍稀動物分布地區的歷史變遷,挖掘其變遷規律和變遷原因,對于探討我國歷史時期生態環境的變遷、珍稀動物的保護等,都有著重要的學術和現實意義。[1]
一、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的困境與契機
(一)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的困境
《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一書中對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有所提及。只不過在這樣一本反映至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歷史自然地理學總體水平的成果匯總的書里,對于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是這樣描述的:由于“研究工作還很不夠”,從而“只好暫付缺如”。可見,在文煥然、何業恒等的系列成果問世之前,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并不是一個重要的學術領域。
究其原因,一是資料分散。搜集這方面的資料,真如大海撈針,查索竟日而一無所獲的情況往往有之。這就是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本身的難點,實際上這也是整個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共同難點,不過歷史動物地理學的資料分散尤甚。對資料的收集和整理要求極高,這是由歷史地理學的學科特點所決定的。與地理學和歷史學所不同的是,歷史地理學是一門雙維的學科,它既要復原事物、現象在空間上的分布,又要對應地揭示其在時間上的演替。沒有時間的歷史地理空間研究是沒意義的,對于歷史地理的時間研究來說亦然。這就要求對資料要無限地全面占有,力求作出全面的分析,得出具有精確度數的結論。對于歷史動物地理學來說,資料的極度分散無疑讓高要求的資料收集“雪上加霜”,工作難度可見一斑,以致很多歷史地理工作者“見之則避”,歷史動物地理學的研究少人問津,進展緩慢,遠遠落后于其他分支領域。
再有,在極為分散的史料中,有關動物的記載異常混亂。歷史動物地理學的研究資料大多來自地方志,而舊方志的動物記載不列學名,一不小心就會出錯。對此,陳橋驛先生描述得特別精辟:“在這些志書中查索動物名稱,通名與俗名混用,本名與別名交錯,有時一名為數物所共有,有時數名卻僅系一物。混亂顛倒,不勝其煩,魯魚亥豕,出錯更屬難免。”[2]動物記載使用學名并加列拉丁文二名法,是從上世紀30年代的民國《覲縣通志》開始的。而80年代初,當時新編的方志仍大都沿用舊方志的套路,關于動物的記載不列學名。此后,在一些有識之士的倡導和呼吁下,某些地方的新編方志已經在動物卷中使用了學名,并加列拉丁文二名法,但是大多地方志中的動物記載還是相當混亂的。中國歷代的地方志編寫都是有專人專門負責,新地方志的編寫也不例外,且編寫水平和資金、人力的投入更是以前無法比擬的。在這等情況下,方志中關于動物的記載尚且如此,其他史料就猶有過之了。這就導致了歷史動物地理學的研究難度極高,要進行研究必須破譯出各種古動物在當時中國古籍上的名稱,今天是國際上通用名稱的何種動物種屬。研究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也就成了很多歷史地理工作者手中的“燙手山芋”,棄之可惜,嘗之不能。
當然,當時的歷史地理學科的發展也不夠快,也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很多新的領域、很多分支的研究也沒真正啟動,不是顯學的歷史動物地理學也就難免受到冷遇了。
(二)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的契機
80年代初至今,歷史自然地理學的發展進入了開拓發展的高峰期,歷史動物地理學的研究也隨之受到重視,發展勢頭良好。首先是人們的環境意識加強,對歷史自然地理的重視非往日可比,環保支持者的奔走呼號也讓動物保護走進每個人的潛意識,歷史動物地理的研究日益興旺起來。再有大型綜合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編寫的開展,令到地圖集中對各歷史自然地理要素的研究都迎來了人力、資金異常充沛的一個發展契機,歷史動物地理學也不例外。況且在該地圖集中各歷史自然地理要素的研究都緊密結合當今發展勢頭迅猛的環境變遷研究,其現實意義使得歷史自然地理學的研究全面鋪開,其前期的一些較薄弱的分支領域,特別是歷史動物地理學被擺到了研究前沿,成為雖“老”也“新”的研究熱門。
二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的主要學術成果
在80年代初至今的短短二十多年間,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迎來了黃金時期,成果頗豐,探討的問題很全面、深入,在研究的方法上實現了突破,以文煥然、何業恒為主的一批學者知難而上,文獻整理分析和實地考察相結合,沖破歷史地理學研究本身的難度“瓶頸”,發表了一系列的論文和專著,論述了幾十種國家一級、二級保護動物在地理分布上的變遷,為歷史動物地理學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使得歷史動物地理學躋身歷史地理學的前沿,備受關注。他們的動物地理區域探討方面,偏重于我國東部季風區中南部野生動物種群及其分布區域變化情況;探討時限方面,研究時間上限直抵全新世前期,與地質時期古生物變遷相銜接;在他們的論著中,也深刻體現了生態系統的“大一統”,歷史時期動物地理的研究結合了歷史時期氣候、水文、植被等自然因素的變化和區域開發中人為活動的影響。[3]
對歷史時期動物的類屬進行概括性探究的成果很多,主要集中在珍稀獸類、珍稀鳥類、珍稀爬行類、兩棲類、魚類,代表人物是何業恒,研究成果有何業恒等著的《湖南珍稀鳥類的歷史變遷》、《中國珍稀獸類的歷史變遷》、《中國珍稀獸類(Ⅱ)的歷史變遷》、《中國珍稀鳥類的歷史變遷》和《中國珍稀爬行類兩棲類和魚類的歷史變遷》。
珍稀獸類方面,研究的動物集中在虎、象、熊、熊貓、野生犀牛等。對于虎的研究又側重于華南虎,成果有藍勇先生的《清初四川虎患與環境復原問題》劉正剛的《明清閩粵贛地區虎災考述》和何業恒的《試論華南虎在長江三角洲的絕跡》。對于歷史時期象的研究集中在江河流域一帶,有曾昭璇的《試論珠江三角洲地區象、鱷、孔雀滅絕時期》、何業恒的《黃河下游古代的野象》和文煥然等著的《歷史時期中國野象的初步研究》。至于熊的相關研究,何業恒的成果較多,有《歷史時期湖南有棕熊嗎?》和《中國虎與中國熊的歷史變遷》。歷史時期大熊貓的研究歷來是個熱點,主要的成果有何業恒的《大熊貓的興衰》、《試論大熊貓的地理分布及其演變》和文煥然等著的《近五千年來豫鄂湘川間的大熊貓》。歷史時期野生犀牛的研究較為透徹,成果有文煥然等著的《中國野生犀牛的滅絕》,文煥然、何業恒著的《中國野犀的地理分布及其演變》,劉洪杰的《中國古代獨角動物的類型及其地理分布的歷史變遷》,藍勇的《歷史時期中國野生犀角分布的再探索》。其他獸類的歷史時期分布變遷研究成果也頗豐,有周躍三、何業恒的《試論野生水牛、四不像鹿和中國鼉在黃河中下游的絕跡》,王青等著的《海岱地區的獐與史前環境變遷》等。
歷史時期鱷魚的分布變遷研究主要集中在馬來鱷和揚子鱷上。馬來鱷的分布變遷研究成果有文煥然等著的《歷史時期中國馬來鱷分布的變遷及其原因的初步分析》。相比較而言,揚子鱷的分布變遷研究更為透徹一些,成果較豐,有文煥然等著的《試論揚子鱷的地理變遷》、裴修碧的《上古時期揚子鱷分布地域考》、何業恒的《揚子鱷在黃河中下游的地理分布及其南移的原因》及文榕生的《揚子鱷盛衰與環境變遷》。另外,何業恒等著的《中華鱘達氏鱘和白鱘地理分布的變遷》是中華鱘歷史地理分布研究的重要成果。
三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的展望
對于動物而言,其與植物本是一家,在生物鏈中兩者也是相鄰的鏈節,相互之間的依存程度不言自明。動物是生長在一定的氣候條件,一定的水文、地貌環境中的,氣候和水文地貌與其是時刻在互動的,動物的狀況更是氣候、水文的一面“鏡子”。這樣的規律是具有客觀性和歷史性的,在漫長的生態演變過程中,自然界始終堅持并遵循這樣的一個規律,所以歷史時期動物的變遷的研究不會是孤獨的,更不應該是獨立的。它的發展有賴于歷史時期氣候、水文地貌等主要要素的研究,它的發展是應該站立在氣候、水文地貌等主要要素的歷史時期研究的基礎上的。這樣,歷史時期動物的變遷得出的研究結論才有統治性,才有說服力,才中肯。
對于中國歷史時期動物的變遷研究來說,它是眾多自然要素歷史時期研究中較為薄弱的一個分支研究,在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上都大可借鑒其他先行分支領域的成果,這樣,歷史時期動物的變遷研究才具有更高的研究效率和研究范圍。歷史時期動物變遷的深層次原因和規律分析探討才有更廣泛的理論支持,才有更廣泛的指導意義,才有生物系統、生物環境“大一統”的高度和深度。展望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的研究,合作全面的研究才是可持續發展的道路。為此可采取兩個措施,第一,將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對象之時間下限下延至當今,使之與現代地理學其他分支學科研究之內容在時間上更緊密地相銜接;第二,將歷史動物地理學的研究內容由僅復原過去歷史時期之環境變遷,延伸到對當前環境變遷動態的評估及對今后環境變遷趨勢的預測,并提出防止環境惡化,改善環境質量等方面的對策。[4]
參考文獻:
[1]張全明.中國歷史地理學導論[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104.
[2]陳橋驛.中國珍稀鳥類的歷史變遷[M].1994.7.
[3]華林甫.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成就[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