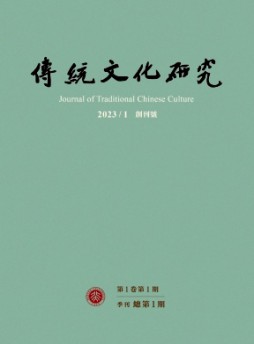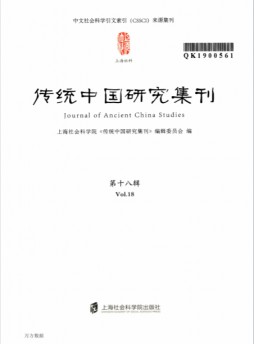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生態覺悟;“力量型”科學;和諧;中國現代科學體系
一西方“力量型”科學范式的理論溯源及其界限
今天我們提到科學,一般指的是近代西方科學,它起源于希臘的理性科學,重視數學的運用與實驗的檢測,因而也稱為數理實驗科學。[1]西方近代科學既有對希臘理性科學的繼承,同時受西方近代文化觀念的影響,它在某種程度上也偏離了希臘理性科學對自由精神的追求,正如吳國盛先生所言,“近代科學不僅是希臘理性精神的正宗傳人和光大者,作為現代工業社會的奠基者,科學還以其‘效用’服務于意欲‘控制’的人類權力意志。這是近代科學的一個嶄新的維度:力量化、控制化、預測化。”[2]這樣,主體維度的價值訴求加上對物質力量的狂熱追求,構成了近代科學精神的核心部分,也就是尼采所說的強力意志。這種強力意志構成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主旋律,也造就了西方“力量型”科學范式。
[3]西方“力量型”科學范式雖然在過去幾百年中獲得了飛躍性的發展,二十世紀的科學與技術卻展示了西方“力量型”科學本身的某種界限。20世紀基礎科學的三大成就相對論、量子論和復雜科學的核心思想和結論分別從宇觀、微觀和宏觀尺度證實了西方“力量型”科學的局限性,且這種片面性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
[4]無論是西方科學自身的發展,還是在處理與社會、自然的關系上,西方“力量型”科學范式都面臨著發展的瓶頸問題。和諧的生態覺悟、科學的前沿發展都呼喚一種新的科學范式,而這種新的科學范式的核心思想與東方文明中的生態智慧不謀而合,作為東方文明代表的中國文化與科學將面臨新的歷史機遇與挑戰。
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天人和諧”思想對“力量型”科學界限的消融
二十世紀以來,以相對論、量子力學和復雜科學為代表的前沿科學,通過深刻的觀念轉變和理念創新,打破了時空對立等二元對立觀念,演繹了自然宇宙和諧一體的更為純正的科學自由精神。這種情況下,強調和諧一體的中國傳統自然觀,在解釋新的科學思想上,較之西方“力量型”科學所依賴的機械自然觀顯得更加優越。[5]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一些人自然地把他們的目光投向了東方文明,投向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以解決人類面臨的全球科技文化困境。
1儒家文化中的生態智慧:“天人合一”思想的發掘
儒家文化具有十分豐富的內容,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主流。儒家文化在中國思想史上曾發揮過重要的作用,對于當代科技的有序發展也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6]第一,儒家整體性的思維方式有助于克服西方近代科學的原子論限度。儒家的“天人合一”觀始終把宇宙看作為一個整體,如孟子認為自然之天產生萬物,人和萬物只有一個來源,萬物和人都是其整體的一個組成部分,且彼此相互倚賴。儒家的整體性思維方式反對把人與自然相分割和對立,這有助于消融西方近代科學中還原論、原子論的錯誤理念,有助于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存、協同發展的關系。第二,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有助于消融近代“力量型”科學范式中的主體外化傾向。在和諧的狀態中求發展,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給予西方“力量型”科學最大的啟迪。如荀子認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各有不同分職,只有充分把握好天與人的分職,才能清楚地認識天與人的發展規律,從而更好地認識與改造世界。[7]第三,儒家“天人合一”觀有助于改變西方“力量型”科學的控制論世界圖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建立在深厚的倫理道德基礎之上,如孟子主張“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即把愛心從家庭擴展到社會,從社會再擴展到自然萬物,進而使仁愛具有了生態道德的含義。這種崇高的境界引導人類理性地控制物質欲望,并把物欲導向精神的追求與創造,塑造人類“贊天地之化育”的偉懷,即理解、贊美和協助自然界之生生不息,并以這樣的方式發揮人性,而成為天地大自然界的一部分。而西方近現代科學思想認為自然界本質上是一種純粹物的結合,是一幅符合機械力學規律的自然圖景,是一個在人類之外跟人類毫不相干的體系,是人類的能源場與垃圾場,從而培養了人對自然的傲慢感、對于其他物種的優越感。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態智慧則對自然有一種熱愛、同情、親近之情,認為一切知識本質上都來源于活生生的自然,而不是來自實驗室中的自然切片,強調對自然本身的直接接近。[8]這樣,儒家文化的生態智慧顯然能夠彌補西方“力量型”科學觀念的不足。它警示人類,應該去除在自然面前的自負和傲慢,應該敬畏自然,停止無止境地向自然索取,保持與自然的和諧,才能使科學技術更好地造福于人類。
2道家文化中的生態覺悟:“道法自然”思想的啟迪
道教文化也是華夏母體上土生土長的血脈文化,道家的核心范疇“道”把人類置于自然世界的大系統中,從自然現象推及人類社會的道德行為準則,以及人類對自然界的態度。其思想路徑和特征,與當代復雜性科學的生態趨向是一致的,從而有助于消融西方“力量型”科學范式的界限。[9]首先,道家的“道法自然”生態思想可以為科學提供新的形而上學基礎。老子認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人來源于自然并統一于自然界,人是天地生成的,人與天地的關系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它們相互依賴、相互作用,構成和諧統一的整體。道家文化中的生態智慧與近代西方主客二分的機械論、二元論以及人類中心主義觀念是根本不同的,從而可以為西方“力量型”科學范式提供新的哲學基礎。其次,道家的循“道”而為的價值原則與當代生態科學的價值目標是一致的。老子的“道”具有生態價值的意蘊,就是要求人們的行為要與“道”一致,要與天地萬物一致,尊“道”貴“德”,順應自然,體現在實踐上就是“無為”。當代生態科學十分推崇老子的這一思想,與老子把天地之“道”作為確立人類道德的根據一樣,生態科學的整體論思想、價值觀原則都是以生態系統的自然性質為根據的,主張要對自然過程作出謙卑的默認,讓自然按照自己的節律運行而不要去破壞它。其三,道家的生態哲學與當代21世紀科學追求的最高境界都是人與自然相和諧的生態整體境界。老子的“道”是一種尊重生命和自然的倫理觀,它要求人們的活動尊重天地自然,尊重一切生命,與自然和諧相處,這與生態科學的生態中心主義觀念是十分吻合的,他們共同指向“天人一體”、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生態境界。總之,在生態整體系統中,人不在自然之外,也不在自然之上,而在自然之中。人應當站在生態系統和地球的角度,成為大自然的神經和良知,關心其他生命,維護生態系統的穩定,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體現并弘揚大自然的“生生之德”,維持自然界的美麗與和諧。這就是道家中所蘊涵的生態智慧對西方“力量型”科學最大的啟迪,今天我們提出科技生態轉向的理論支撐點也在于此。
西方科學的畸形發展而帶來的一些文化困境,為東方文化發揮作用提供了新的歷史機遇,使人類把目光投向了更為廣闊的人類文化圖式,從儒學、道學等東方文化中尋找生態智慧與啟迪。作為東方文明代表的中國文化,能以其特有的生態智慧和覺悟為西方“力量型”科學突破固有的范式提供有益的催化作用,并以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范導科學應有的氣質,現代科學與蘊涵了東方智慧的儒家、道家文化進行跨文化對話,對于人類超越科技文化困境、邁向澄明之境無疑具有積極意義。
三中國傳統文化中和諧生態智慧的發掘與現代科學體系的建立
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許多科學家在“東方神秘主義”與現代物理學之間發現了“驚人的平行之處”,以此為契機展開了東方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之間的跨文化對話。[10]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雖然對于克服和糾正西方“力量型”科學的缺陷能夠起到積極作用,但是能否起到主導作用——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覺悟推進為一種整個人類文明的生態價值觀和生態世界觀,成功地實現中華科學技術的騰飛,這還取決于中國人對于傳統文化的自覺與超越的程度。二十世紀末以來,在世界范圍內掀起一股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強勁聲浪,其原因之一就是西方“力量型”科學的天人分離思維摸式的弊端日益顯露出來,特別是在復雜科學等前沿領域,因而當代西方科學正經歷著從主客二分轉向主客融合的后現代主義的洗禮。而中國傳統文化和后現代主義有許多相似之處:它們都崇尚天與人的和諧一致、思與詩的交融貫通;都鄙視對外在對象作還原性的分析,而注重對人在其中的世界的情感體驗。因此,西方的一些學者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看成是抵御西方科學工具理性的希望。[11]而對今天的中國人而言,一方面要跟西方發達世界站在一起,憂慮“力量型”科學本身的缺陷;另一方面也要跟不發達世界站在一起,憂慮本民族的傳統文化被不知不覺排除在“體”之外而流于“用”的危險。中國人的“現代化之憂思”,既有西方后現代主義者的“現代性批判”的一面,也有發掘傳統文化的一面,既有后現代的一面,也有前現代的一面。[12]因此,為了徹底擺脫現代化的雙重困境,中國人不僅要發掘傳統文化中的生態覺悟以消融西方近現代科學“工具理性”的界限,更為重要的是在西方科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發掘并提煉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蘊涵的生態覺悟,建立起與西方科學平行的中國現代科學體系,進而將這種生態智慧推進為整個人類文明的生態價值方法和生態價值觀,而20世紀基礎科學的三大成就相對論、量子論和復雜科學則為中國現代科學體系的建立提供了歷史性機遇。20世紀前沿科學的核心思想與中國科學和文明的生態智慧不謀而合,這些前沿科學領域將成為中國人大顯身手的場所。因此,建立中國特色的東方科學體系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在系統科學、協同科學、混沌科學以及生態科學等綜合性較強的學科領域。[13]如何將可能訴諸于現實?這還取決于中國傳統科學能否在吸收西方科學精髓的基礎之上,創造性地闡述與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蘊涵的生態智慧,從而使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成為中國現代科學體系的形而上學基礎!
激活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創造性地闡釋中國科學傳統背后所蘊涵的人文理念,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來制約一再跌落的西方科學,是一條十分恢宏而又漫長的道路,但又是一個十分誘惑的思路。一方面對西方而言,他們則有可能獲得突破工具理性這個“座架”的外援——融合中國傳統文化的生態智慧于母文化之中,激活科學自身內在的修復機制;另一方面對于中國而言,提供了民族傳統文化復興與現代科學體系建立的絕佳機會。當中國人真正超越自己文化中的舊傳統之時,就是中國科學技術走向騰飛之日。
參考文獻:
[1][4]姜巖東方科學與文明的復興[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3.8
[2][12]吳國盛科學與人文[J]中國社會科學,2001.4
[3]吳國盛.何為科學精神[J]百科知識,1998.2
[5]吳國盛20世紀的科技展示了科學本身的某種界限——回顧百年科技
[J]國際經濟評論,1999.Z2
[6][11]陶渝蘇論作為科學精神生長點的西方思維模式[J]貴州大學學報,1998.1
[7]梅薩羅維,等人類處于轉折點[M]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1987.148
[8]吳國盛.反思科學[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23-24
[9]李承宗,謝翠蓉.試論道教文化對科學技術的影響與啟示[J]廣東行政學院學報,2003.6
第2篇
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 北京精神 意義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直以來都是我們改革和發展的重要思想寶庫。認真總結、分析并有選擇性的吸收古代先賢為我們留下的歷史財富,對于我們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推進改革開放,實現中國夢有著十分重要的歷史借鑒作用,生態文明建設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部分當然也不例外。在生態環境破壞日益嚴重的今天,我們需要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生態文明建設的智慧。
一、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思想內涵
(一)“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思想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關于“天人合一”,季羨林先生的解釋是: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類;天人合一,就是互相理解,結成友誼。“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于周易,傳說中伏羲氏作八卦,八卦中的各卦都是不同的卦體,每個卦體由三個線段組成,每個線段有一個象征意義:上象征天,下象征地,中間象征人,稱為天、地、人“三才”。“天人合一”思想被我國古代多數思想家所推崇和發展,是我國傳統生態思想的重要內容。
儒家“仁”的思想就包含著“天人合一”的內涵。孔子提出了著名的“仁”的思想,以至后來有人把孔子的思想概括為“仁學”。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1]那么什么是仁呢?孔子對仁的解釋在其著作中出現過多次,他在《論語?雍也》中解釋說“仁者先難而后獲,可謂仁矣。” [2]教育人們要勇挑重擔,而不計較收獲的多少,這樣才能算作是有仁心的人。也就是說要敢于進行自我犧牲,要帶著責任感主動承擔利他行為,勇于擔任道德主體的角色。孔子還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3]有仁德的人待人接物都會恭謹慎重,不會把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施加給別人,對于國事也好,家事也好,都不會怨天尤人。總之,有仁德的人要有大愛,要嚴于律己寬以待人。并且,孔子將這種仁愛之心由對人擴展到了對自然界,他說:“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4],體現了孔子對動物的仁愛之心。
孟子的思想更加強調民本和責任感,他一再勸誡君王實施仁政,使社會內部形成相互關愛,相互幫助的和諧、溫馨氛圍。他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 [5]要求人們在養育自己的孩子和贍養自己的老人的同時也要關愛到別人的孩子和老人,這樣才能實現國泰民安。孟子更進一步把這種博愛精神擴展到自然領域,他指出“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闖兀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6]可見,在幾千年前,孟子就已經告誡人們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要適度,要順應其生長規律,根據具體的節氣時令耕種、捕撈、砍伐,這樣百姓就不會對自己的生活有什么不滿了。
儒家學派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的觀點也飽含“仁”與“天人合一”的融合。荀子認為[7],草木開花長大的時候,斧頭不進山林砍伐,這是為了不讓植物的生命夭折。黿鼉、魚鱉、鰍@懷孕、生育的時候,漁網、毒藥不入湖澤,這是不斷絕它們的生長。春天耕種,夏天除草,秋天收割,冬天儲藏,一年四季不耽誤時節,百姓就有多余的糧食了。池塘、水潭、河流、湖泊,嚴格遵守每個季節的禁令,百姓就有多余的資財了。樹木的砍伐、培育養護不耽誤時節,百姓就有了多余的木材。所以還是要順應自然,以愛護的角度適當索取,才能實現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平衡發展。
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包含著循環觀點,老子認為萬物都有一個循環發展的過程,而人們就應該遵從規律,順應自然,而不要輕舉妄動,就可以達到與自然的統一了。“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夫物蕓蕓,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兇。” [8]老子通過觀察指出,世間萬物都會經歷周而復始的循環運動,然后回歸它們的根本,從而達到永恒,能認識到這一點的人就會成功,不懂得循環規律的人就會有災禍。老子又說,“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故從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 [9]刮風刮不了一早晨,大雨下不了一整天,這都是由自然規律決定的,連自然現象都不能長久更何況是人呢?所以老子認為,遵循自然循環規律的人就能順應自然,從而實現自身,所以人們要修養德行,尊重自然。
(二)“天人相分”思想
荀子是“天人相分”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所謂“天人相分”并不是把人與自然對立起來,而是說人可以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來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從而達到發展自身的目的。荀子在《王制》[10]中指出,水火雖然有氣但沒有生命,草木雖然有生命但沒有知覺,動物雖然有知覺,但不懂禮義。而人跟某些動物相比雖然看起來沒有那么強健,但可以集群并相互協調,從而合理利用四季節氣,使天下收益,所以人才是世界上最珍貴的東西。荀子在繼承前輩們“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而后又具體解釋了發揮主觀能動性的依據是要以人們自身的需要為尺度,而對自然資源的利用也正是自然界賦予人類的權利。他說:“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 [11]是說人們要會利用人以外的其他事物來供養自己,順應人的需要去做就是福,違背人的需要去做就是禍。這樣人們就可以實現“天地官而萬物役”恰到好處地役使萬物了。
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也在自己的作品中肯定過科技的重要性,他說“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國可得而食也。” [12]在遇到自然災害的時候,正是勞動人民用自己的勤勞和智慧探索出自然的奧秘,從而產生了科學,人們進而創造出了技術來應對災難,讓自己擺脫困境,這些依靠的都是人類對能動性的合理發揮。
道家學說雖一直強調自然的先在性和人類對自然的依附和順應,但并不是否定人的主觀能動性,而是要人們適可而止,審時度勢地合理發揮能動性,控制自己的行為,避免走極端,以實現長久發展。“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靜勝躁,寒勝熱…” [13]偉大的成就好像有缺陷,但它的作用永不凋敝;盈滿的杯子好像中間有虛空,但它的作用無窮無盡。最剛直的東西仿佛是彎曲的,最靈巧的人仿佛笨手笨腳,最雄辯的人好像不善言辭。所以老子的本意只是告誡人們擁有了這些技能也應謙虛謹慎,保持一顆平常心,切不可驕傲自滿,目中無人。
(三)尊重自然界內在價值
生態學家奈斯指出:“地球上的非人類生命的美擁有自在的價值。這種價值獨立于它對人類的有限目的的工具意義上的有用性。” [14]
我國古代思想家們也都在自己的著作中表達過尊重自然內在價值的思想。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15]意思是說自然界雖不言不語,一年四季卻運行不息,世間萬物也生生不已,這種默然的存在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子貢在反駁叔孫武叔對仲尼的詆毀時也以日月為例說:“人雖欲自絕,其何傷于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16]在子貢看來,人類自身的損益對自然界來講是沒有任何影響的,日月星辰的運行不會因為人們的極端行為而有任何變化,人類在自然面前是看似微小的。荀子作為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更是在《天論》中明確指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 [17]自然界的運行有其自身內在的規律,即使是世間再偉大的英雄也無從改變,如果順應其規律,人類就會有所發展,如果違背規律,就會遭殃。而后他又進一步具體說明:“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18]既然天地不會因人的喜好而改變自身規律,那么人也應依照自己的原則來做事。
道家學說以中庸、無為、善柔為特點,更是強調自然界的獨立性和先在性。老子把[19]自然法則的玄妙程度視作高于人類語言表達能力的范疇,認為世間萬物都源于規律,源于自然,都有一個產生、強大、衰落、此消彼長的過程,而事物運行的具體規律是人類難以參透的。他進而又說:“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20]意思是說世間偉大的東西有四種,而君王僅排第四,人取法與地,地取法于天,天取法于自然,自然才是萬事萬物的根本尺度。道家的另一代表人物莊子更是以其“萬物一齊”的思想為核心要求人們尊重世間萬物。莊子認為,那些試圖把一己成見假托給客觀事物而不愿順應規律的人最終只是在做無用功;而真正有智慧的人會廣博、豁達地生活在均衡而又自然的境界里,不強求、不急躁,從容地接受和應對身邊的事物,因為他們早已領悟到萬物終將歸為一體,以平和的心態應對生活才最有益自己身心的健康。他在《齊物論》中對天籟的描述是“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 [21]天籟雖然有萬般不同,但使它們發生和停息的都是自身,沒有任何事物可以操控。所以世界是渾然一體的,萬物終將殊途同歸。
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生態文明思想的當代啟示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文明思想,是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古代社會中孕育產生的,是根植于農業文明基礎上的一種前科學主義思維方式,對于當代人類社會工業文明及后工業文明而言,缺乏時代性和前瞻性的要素。放眼世界歷史,文明古國創造的偉大文明幾近衰落、消失,唯有中華文明獨存,究其原因,不難發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生態文明思想的智慧,是使中華文明得以延續下來的重要原因,古人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分”、“尊重自然”等生態文明思想值得我們今天牢固地樹立生態文明觀念,建設生態文明的“美麗中國”所吸收和借鑒。
中國古代傳統生態文明思想要求人們把從自然中獲得的平常心、安全感應用到人際關系中去,以關愛、誠懇、謙虛、信任的態度來對待其他社會成員,從而實現人類社會自身的協調。在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今天,這一思想對我國當今生態文明建設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對豐富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轉變社會風氣,轉變人們價值觀也會起到重要作用。
隨著我國生態環境的逐年惡化,很多人把環境破壞歸咎于經濟和科技的發展。實際上,問題不在于經濟和科技本身,而在于人們對科學技術應用的方法和目的,古代先哲們告誡我們,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對自然資源的利用本身是自然賦予人類的能力,我們應該充分應用我們的能力來了解自然、研究自然,從而找到在順應自然的前提下滿足自身發展需要的方法。但對改造自然方面能力的發揮要堅持適度原則,不能因在對抗自然中的短暫勝利或對自然開發過程中所得到的短期利益而忘乎所以地對自然界進行無限度的索取。
隨著科技的發展,為滿足工業化社會發展的需要,人們對自然的敬畏早已遠不及農業文明時期強烈,對自然規律的重視程度也在日益消減,以致污染、浪費、過度開發等現象甚囂塵上。因此,傳統思想中對自然環境內在價值的高度認同對生態文明建設有著頗具時效性的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黃克劍.《論語》解讀[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62
[2]黃克劍.《論語》解讀[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118
[3]黃克劍.《論語》解讀[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247
[4]黃克劍.《論語》解讀[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144
[5]孟子.孟子[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26
[6]孟子.孟子[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10
[7]荀況.荀子[M].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7:47
[8]老聃.老子[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38
[9]老聃.老子[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52
[10]荀況.荀子[M].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7:46
[11]荀況.荀子[M].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7:110
[12]孟子.孟子[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124
[13]老聃.老子[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98
[14]Arne Naess, “A Defence of the Deep Ecology Movement”, Environmental Ethics (Fall 1984)
[15]黃克劍.《論語》解讀[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386
[16]黃克劍.《論語》解讀[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423
[17]荀況.荀子[M].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7:109
[18]荀況.荀子[M].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7:111
[19]老聃.老子[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8
[20]老聃.老子[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57
第3篇
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生態覺悟;“力量型”科學;和諧;中國現代科學體系
一西方“力量型”科學范式的理論溯源及其界限
今天我們提到科學,一般指的是近代西方科學,它起源于希臘的理性科學,重視數學的運用與實驗的檢測,因而也稱為數理實驗科學。[1]西方近代科學既有對希臘理性科學的繼承,同時受西方近代文化觀念的影響,它在某種程度上也偏離了希臘理性科學對自由精神的追求,正如吳國盛先生所言,“近代科學不僅是希臘理性精神的正宗傳人和光大者,作為現代工業社會的奠基者,科學還以其‘效用’服務于意欲‘控制’的人類權力意志。這是近代科學的一個嶄新的維度:力量化、控制化、預測化。”[2]這樣,主體維度的價值訴求加上對物質力量的狂熱追求,構成了近代科學精神的核心部分,也就是尼采所說的強力意志。這種強力意志構成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主旋律,也造就了西方“力量型”科學范式。
[3]西方“力量型”科學范式雖然在過去幾百年中獲得了飛躍性的發展,二十世紀的科學與技術卻展示了西方“力量型”科學本身的某種界限。20世紀基礎科學的三大成就相對論、量子論和復雜科學的核心思想和結論分別從宇觀、微觀和宏觀尺度證實了西方“力量型”科學的局限性,且這種片面性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
[4]無論是西方科學自身的發展,還是在處理與社會、自然的關系上,西方“力量型”科學范式都面臨著發展的瓶頸問題。和諧的生態覺悟、科學的前沿發展都呼喚一種新的科學范式,而這種新的科學范式的核心思想與東方文明中的生態智慧不謀而合,作為東方文明代表的中國文化與科學將面臨新的歷史機遇與挑戰。
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天人和諧”思想對“力量型”科學界限的消融
二十世紀以來,以相對論、量子力學和復雜科學為代表的前沿科學,通過深刻的觀念轉變和理念創新,打破了時空對立等二元對立觀念,演繹了自然宇宙和諧一體的更為純正的科學自由精神。這種情況下,強調和諧一體的中國傳統自然觀,在解釋新的科學思想上,較之西方“力量型”科學所依賴的機械自然觀顯得更加優越。[5]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一些人自然地把他們的目光投向了東方文明,投向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以解決人類面臨的全球科技文化困境。
1儒家文化中的生態智慧:“天人合一”思想的發掘
儒家文化具有十分豐富的內容,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主流。儒家文化在中國思想史上曾發揮過重要的作用,對于當代科技的有序發展也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6]第一,儒家整體性的思維方式有助于克服西方近代科學的原子論限度。儒家的“天人合一”觀始終把宇宙看作為一個整體,如孟子認為自然之天產生萬物,人和萬物只有一個來源,萬物和人都是其整體的一個組成部分,且彼此相互倚賴。儒家的整體性思維方式反對把人與自然相分割和對立,這有助于消融西方近代科學中還原論、原子論的錯誤理念,有助于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存、協同發展的關系。第二,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有助于消融近代“力量型”科學范式中的主體外化傾向。在和諧的狀態中求發展,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給予西方“力量型”科學最大的啟迪。如荀子認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各有不同分職,只有充分把握好天與人的分職,才能清楚地認識天與人的發展規律,從而更好地認識與改造世界。[7]第三,儒家“天人合一”觀有助于改變西方“力量型”科學的控制論世界圖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建立在深厚的倫理道德基礎之上,如孟子主張“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即把愛心從家庭擴展到社會,從社會再擴展到自然萬物,進而使仁愛具有了生態道德的含義。這種崇高的境界引導人類理性地控制物質欲望,并把物欲導向精神的追求與創造,塑造人類“贊天地之化育”的偉懷,即理解、贊美和協助自然界之生生不息,并以這樣的方式發揮人性,而成為天地大自然界的一部分。而西方近現代科學思想認為自然界本質上是一種純粹物的結合,是一幅符合機械力學規律的自然圖景,是一個在人類之外跟人類毫不相干的體系,是人類的能源場與垃圾場,從而培養了人對自然的傲慢感、對于其他物種的優越感。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態智慧則對自然有一種熱愛、同情、親近之情,認為一切知識本質上都來源于活生生的自然,而不是來自實驗室中的自然切片,強調對自然本身的直接接近。[8]這樣,儒家文化的生態智慧顯然能夠彌補西方“力量型”科學觀念的不足。它警示人類,應該去除在自然面前的自負和傲慢,應該敬畏自然,停止無止境地向自然索取,保持與自然的和諧,才能使科學技術更好地造福于人類。
2道家文化中的生態覺悟:“道法自然”思想的啟迪
道教文化也是華夏母體上土生土長的血脈文化,道家的核心范疇“道”把人類置于自然世界的大系統中,從自然現象推及人類社會的道德行為準則,以及人類對自然界的態度。其思想路徑和特征,與當代復雜性科學的生態趨向是一致的,從而有助于消融西方“力量型”科學范式的界限。[9]首先,道家的“道法自然”生態思想可以為科學提供新的形而上學基礎。老子認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人來源于自然并統一于自然界,人是天地生成的,人與天地的關系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它們相互依賴、相互作用,構成和諧統一的整體。道家文化中的生態智慧與近代西方主客二分的機械論、二元論以及人類中心主義觀念是根本不同的,從而可以為西方“力量型”科學范式提供新的哲學基礎。其次,道家的循“道”而為的價值原則與當代生態科學的價值目標是一致的。老子的“道”具有生態價值的意蘊,就是要求人們的行為要與“道”一致,要與天地萬物一致,尊“道”貴“德”,順應自然,體現在實踐上就是“無為”。當代生態科學十分推崇老子的這一思想,與老子把天地之“道”作為確立人類道德的根據一樣,生態科學的整體論思想、價值觀原則都是以生態系統的自然性質為根據的,主張要對自然過程作出謙卑的默認,讓自然按照自己的節律運行而不要去破壞它。其三,道家的生態哲學與當代21世紀科學追求的最高境界都是人與自然相和諧的生態整體境界。老子的“道”是一種尊重生命和自然的倫理觀,它要求人們的活動尊重天地自然,尊重一切生命,與自然和諧相處,這與生態科學的生態中心主義觀念是十分吻合的,他們共同指向“天人一體”、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生態境界。總之,在生態整體系統中,人不在自然之外,也不在自然之上,而在自然之中。人應當站在生態系統和地球的角度,成為大自然的神經和良知,關心其他生命,維護生態系統的穩定,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體現并弘揚大自然的“生生之德”,維持自然界的美麗與和諧。這就是道家中所蘊涵的生態智慧對西方“力量型”科學最大的啟迪,今天我們提出科技生態轉向的理論支撐點也在于此。
西方科學的畸形發展而帶來的一些文化困境,為東方文化發揮作用提供了新的歷史機遇,使人類把目光投向了更為廣闊的人類文化圖式,從儒學、道學等東方文化中尋找生態智慧與啟迪。作為東方文明代表的中國文化,能以其特有的生態智慧和覺悟為西方“力量型”科學突破固有的范式提供有益的催化作用,并以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范導科學應有的氣質,現代科學與蘊涵了東方智慧的儒家、道家文化進行跨文化對話,對于人類超越科技文化困境、邁向澄明之境無疑具有積極意義。
三中國傳統文化中和諧生態智慧的發掘與現代科學體系的建立
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許多科學家在“東方神秘主義”與現代物理學之間發現了“驚人的平行之處”,以此為契機展開了東方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之間的跨文化對話。[10]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雖然對于克服和糾正西方“力量型”科學的缺陷能夠起到積極作用,但是能否起到主導作用——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覺悟推進為一種整個人類文明的生態價值觀和生態世界觀,成功地實現中華科學技術的騰飛,這還取決于中國人對于傳統文化的自覺與超越的程度。二十世紀末以來,在世界范圍內掀起一股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強勁聲浪,其原因之一就是西方“力量型”科學的天人分離思維摸式的弊端日益顯露出來,特別是在復雜科學等前沿領域,因而當代西方科學正經歷著從主客二分轉向主客融合的后現代主義的洗禮。而中國傳統文化和后現代主義有許多相似之處:它們都崇尚天與人的和諧一致、思與詩的交融貫通;都鄙視對外在對象作還原性的分析,而注重對人在其中的世界的情感體驗。因此,西方的一些學者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看成是抵御西方科學工具理性的希望。[11]而對今天的中國人而言,一方面要跟西方發達世界站在一起,憂慮“力量型”科學本身的缺陷;另一方面也要跟不發達世界站在一起,憂慮本民族的傳統文化被不知不覺排除在“體”之外而流于“用”的危險。中國人的“現代化之憂思”,既有西方后現代主義者的“現代性批判”的一面,也有發掘傳統文化的一面,既有后現代的一面,也有前現代的一面。[12]因此,為了徹底擺脫現代化的雙重困境,中國人不僅要發掘傳統文化中的生態覺悟以消融西方近現代科學“工具理性”的界限,更為重要的是在西方科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發掘并提煉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蘊涵的生態覺悟,建立起與西方科學平行的中國現代科學體系,進而將這種生態智慧推進為整個人類文明的生態價值方法和生態價值觀,而20世紀基礎科學的三大成就相對論、量子論和復雜科學則為中國現代科學體系的建立提供了歷史性機遇。20世紀前沿科學的核心思想與中國科學和文明的生態智慧不謀而合,這些前沿科學領域將成為中國人大顯身手的場所。因此,建立中國特色的東方科學體系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在系統科學、協同科學、混沌科學以及生態科學等綜合性較強的學科領域。[13]如何將可能訴諸于現實?這還取決于中國傳統科學能否在吸收西方科學精髓的基礎之上,創造性地闡述與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蘊涵的生態智慧,從而使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成為中國現代科學體系的形而上學基礎!
激活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創造性地闡釋中國科學傳統背后所蘊涵的人文理念,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來制約一再跌落的西方科學,是一條十分恢宏而又漫長的道路,但又是一個十分誘惑的思路。一方面對西方而言,他們則有可能獲得突破工具理性這個“座架”的外援——融合中國傳統文化的生態智慧于母文化之中,激活科學自身內在的修復機制;另一方面對于中國而言,提供了民族傳統文化復興與現代科學體系建立的絕佳機會。當中國人真正超越自己文化中的舊傳統之時,就是中國科學技術走向騰飛之日。
參考文獻:
[1][4]姜巖東方科學與文明的復興[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3.8
[2][12]吳國盛科學與人文[J]中國社會科學,2001.4
[3]吳國盛.何為科學精神[J]百科知識,1998.2
[5]吳國盛20世紀的科技展示了科學本身的某種界限——回顧百年科技
[J]國際經濟評論,1999.Z2
[6][11]陶渝蘇論作為科學精神生長點的西方思維模式[J]貴州大學學報,1998.1
[7]梅薩羅維,等人類處于轉折點[M]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1987.148
[8]吳國盛.反思科學[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23-24
[9]李承宗,謝翠蓉.試論道教文化對科學技術的影響與啟示[J]廣東行政學院學報,2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