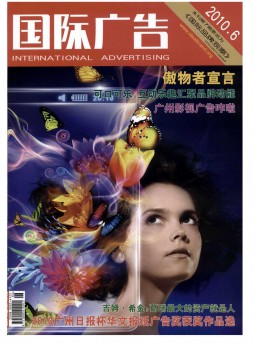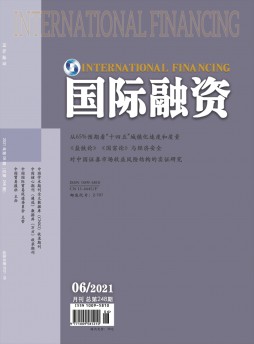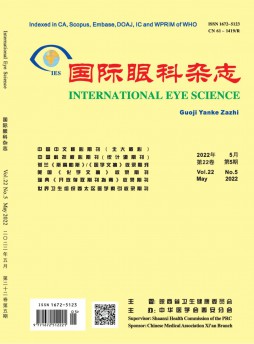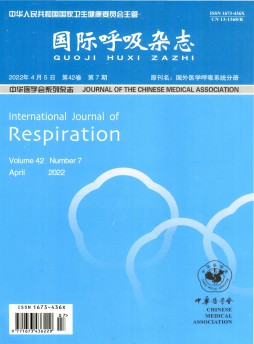國際刑法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國際刑法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國際刑法是一門邊緣學科。它在國際法方面,含有國際人道法、國際人權法的基本原則,以及國際法下的國際罪行部分,如侵略罪、反人道罪、戰爭罪和種族滅絕罪,等等;在刑法方面,它除了刑法上的實體法和訴訟法以外,還有比較法,如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的比較,以及各國的司法制度的比較,等等。此外,國際刑法在其實踐的過程中還時時刻刻涉及到國際關系中最重要、也是最為敏感的問題,即國家問題。比如:國際刑庭為了索取證據和查清案子而向有關國家或政府官員送達傳票或命令;國際刑庭要求有關國家提供線索合作,以鎖定和抓獲被法庭的嫌疑犯,并在將其抓獲了以后押送到法庭;為了審理案子的需要,國際刑庭必然要求將出庭證人所在地的國家當局同意他(她)出來、又要求法庭所在地國家同意他(她)入境;以及當被告被定有罪后,國際刑庭又需要有國家自愿同意、將其關押在該國的監獄里服刑,等等。
聯合國成立了國際刑事法庭
1993年,聯合國安理會成立了前南斯拉夫刑事法庭,第一次在聯合國的范圍內將有關國際刑法的原則和理論付諸實施。
第二年11月,又成立了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盧旺達是一個有著800萬左右人口的國家,1994年4月和7月,占全國人口總數80%的胡圖族對占人口總數14%的圖西族進行了大屠殺。被屠殺的盧旺達人總共達到了80萬左右,連德國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屠殺猶太人也沒有那么快。這一事件在國際社會上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動。盧旺達政府自己要求成立國際刑事法庭,以通過懲治罪犯來達到民族和解的目的。這樣,聯合國安理會先后成立了兩個國際刑事法庭。以后,聯合國又成立了東帝汶國際刑事法庭、塞拉里昂特別刑事法庭等。去年,聯合國還就成立柬埔寨刑事法庭問題與柬埔寨政府簽定了備忘錄。
人們可能會聯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成立的紐倫堡軍事法庭和東京軍事法庭。這兩個軍事法庭在性質上雖然也是國際法庭,但它們與聯合國的前南法庭和盧旺達法庭有很大的不一樣。主要的區別在于它們成立的機制不同。紐倫堡軍事法庭和東京軍事法庭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成立的,審判的對象是二次大戰中的德國和日本的反和平罪、戰爭罪和反人道罪的嫌疑犯,或者叫戰爭罪犯。檢察官在狀中都采用“代表某國政府對某某的”的措辭,因此在學術界和國際法上時常被稱為“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審判”。而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以及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不是這樣。它們是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成立的,不是一個戰勝國的法庭。所以,聯合國前南國際刑事法庭和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是代表整個國際社會的。
除了聯合國成立的刑庭以外,近年來與國際刑法發展有關的,還有英國法庭對皮諾切特引渡一案的審理,以及安排在荷蘭審理的洛克比案等等。
“普遍管轄原則”在歷史上的第一次運用
談到國際刑法的新發展,值得一提的是比利時在2001年6月18日作的一個判決,這是國際法歷史上、或國際關系史上第一次適用“普遍管轄原則”。這個案例在國內幾乎不為人所知,但它在國外傳得很歷害,其在國際法和國際關系上的意義也很深遠。
普遍管轄權,是指每個國家都有權根據國際法,對違反國際法的罪行,特別是對構成危害人類共同利益的少數特定的國際犯罪,行使管轄權和予以懲罰。所以,普遍管轄權與刑法上傳統的領土管轄、保護管轄或國籍管轄原則,在性質上有很大的區別。由于普遍管轄權突破了地域、利益保護和國籍這三種傳統管轄的因素,在國際法上歷來受到嚴格的限制。
“普遍管轄原則”在國際法和國際關系領域中,很長一段時間里只是一種理論,這個從來沒有的歷史,在去年6月被打破了-6月18日,比利時由其國內刑事法庭下了一個判決,裁定被的4個盧旺達人犯了戰爭罪。
事情的背景是這樣的:1993年,比利時國內立法機構通過了一個法律,授權比利時國內司法機構可以對違反1949年關于國際人道法四個公約的事件進行。盧旺達種族滅絕事件正發生在1994年。事發后,很多盧旺達人逃亡國外。比利時以前是盧旺達的殖民國家,逃亡到比利時就有這個案子里的4個被告。他們是教父和修女。盧旺達是一個很濃厚的國家,教堂被公認為庇護所。但1994年大屠殺發生時,人們往往對教堂也實施進攻。這4個被告把那些被追殺的圖西族人引進教堂里,然后馬上又去報告當地的武裝部隊和胡圖族的人,把教堂包圍了起來,并往里面扔手榴彈等,結果里面避難的人死得非常慘。當時,我作為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的檢察官,到盧旺達當地去調查過。只見教堂里的尸體是一堆堆堆起來,真是慘不忍睹。這4個人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被,其中兩人被判有罪。
比利時的判決打破了國際刑法上一貫采用的屬地管轄權和屬人管轄權原則-這個罪行發生地在盧旺達,被的四個人國籍又是盧旺達,被他們殺害的是盧旺達人,與比利時一點關系也沒有。但比利時的法庭實踐普遍管轄權的原則,用本國的法律審理與自己國家或國民沒有任何聯系的案子,這在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史上還是第一次。
前南國際刑事法庭是聯合國安理會成立的,聯合國安理會的權力又是從《聯合國》來的。《聯合國》可以說是現代國際社會的根本大法。當然,聯合國安理會作為一個機構,本身也不能凌駕法律之上。聯合國安理會要成立國際刑事法庭或采取其他措施,也必須遵守《聯合國》的規定。實事求是地說,《聯合國》里并沒有明確授權安理會可以成立國際刑事法庭。但是,國際刑事法庭對此的解釋是,雖然聯合國里沒有明確規定,但是它在第41條規定了聯合國安理會為恢復世界和平與安全可以采取的一些制裁措施。雖然這些措施中沒有成立國際刑事法庭一條。然而,規定中用了“包括”(including)這個詞,表示這里的措施沒有詳盡的意思,因此,從邏輯上分析,在必要的時候,聯合國安理會可以采用“包括”中沒有列舉到的措施。這沒有明確的措施也可以理解為包括成立國際刑事法庭。
《聯合國》第25條還賦予聯合國安理會一個很大的權力,即對于聯合國安理會在《聯合國》第七章下通過的決議,所有聯合國成員國必須接受并履行。這一條很厲害。由于前南國際刑事法庭和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是聯合國安理會根據《聯合國》第七章成立的,所有聯合國的成員國都必須予以合作。這為國際刑事法庭的運作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條件。
關于常設國際刑事法院的建立
成立國際刑事法院最初是1989年由兩個國家在聯合國大會提出來的。當時的初衷是為了禁毒。但提出以后,聯合國接了過去,準備成立一個對違反國際人道法罪行的自然人進行審判的常設國際刑事法院。1994年,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提出草案,交給聯合國第六委員會進行審議。同年的聯大會議上討論并成立了關于“成立國際刑事法院預備委員會”機構。以后,在1998年7月,在意大利羅馬召開了關于成立國際刑事法院外交會議。我作為前南國際刑事法庭和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的正式代表,作為國際刑法的專家,參加在美國紐約和意大利羅馬的會議,從法律技術的角度(不是政策的角度考慮)幫助各國代表團起草國際刑事法院的《規約》。
根據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的規定,有60個國家批準這些規約,它就能生效。經過國際上的一些非政府組織、西方國家紛紛做工作,到去年底今年初,有57個國家批準了。以后的幾個月,就一直停留在57個國家這個數字上。但到了今年4月11日這一天,一下子就有9個國家批準,因此,7月1日這天,世界上出現一個新的國際組織,即國際刑事法院。該法院的屬事管轄權方面,和前南國際刑事法庭和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幾乎一樣,涉及戰爭罪、反人道罪和種族滅絕罪。成立以后,如果絕大多數締約國同意,還會加上侵略罪。但在某些方面,國際刑事法院和聯合國目前的兩個國際刑事法庭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聯合國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和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在性質上屬于臨時性的。它們的成立就是為了分別審理與前南斯拉夫和盧旺達有關的案子,審完以后它就解散了。而今年7月1日開始運作的國際刑事法院是一個常設的機構。一旦設立,它就將一直存在下去。
另外,在它們有關屬地、屬時管轄權方面,也有很大的區別。前南國際刑事法庭和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在管轄權方面,是都有一定的限制的。這從它們的名稱就可看出來。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的全稱很長,叫“聯合國1991以來在前南斯拉夫國家領土內犯下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行為的嫌疑人的刑事法庭”。它把法庭的管轄權限定得清清楚楚。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也一樣,它的全稱叫做“聯合國1994年以內在盧旺達境內所發生的或者由盧旺達國民在鄰國境內所發生的有關嚴重違反種族滅絕罪行以及其他國際人道法罪行的刑事法庭”。所以,盧旺達國際刑庭的管轄權,也僅限于1994年之內,在1994年1月1日以前或1994年12月31日以后發生的,法庭管不了;罪行發生地被局限在盧旺達和鄰國以內;犯罪的自然人,只能是在盧旺達領土內的或鄰國的盧旺達公民;而所審理的罪行,則和前南國際刑事法庭一樣,被限制在國際人道法的范疇內。
所以,國際刑事法院與現有的兩個國際刑事法庭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普遍性。它一旦成立,對全世界范圍內的罪行都有管轄權。另外,它是永久性的。
1998年7月份,國際刑事法院的《規約》在意大利羅馬被通過后,開始開放給各國簽字、批準。規約通過以后,簽署的就有130多個國家。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簽了字。以色列也簽了字。我們中國從維護自己國家利益的考慮出發,暫時還沒有批準《規約》,也沒有簽字。
從理論上講,通過懲治來制止國際犯罪,是世界所有國家義不容辭的責任。然而,一個國家是否加入國際刑事法院的《規約》,則要根據自己國家的具體情況來定。各國的法律文化也不盡相同。在有關重要的問題達成共識之前,每個國家自然都有選擇是否加入、或在什么時候加入《規約》的權利。我在前南國際刑事法庭工作中經常切切實實地感受到,西方對我國抱有偏見。所以,在環境不合適時,我們不一定非要急著進去。
第2篇
冷戰結束后,國際人權法獲得了較為廣闊的生長空間,國際刑法也進入復興和快速發展的階段。以下就是由求學網為您提供的淺論國際人權法對國際刑法的影響。
國際人權法對國際刑法各個領域的影響都十分明顯,從基本原則到具體規則,從實體法到程序法,從刑罰制度設計到刑罰的執行,并努力在保護被害人與保障被告人權利兩者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透過國際人權法推動國際刑法發展的帷幔,不難發現其背后人權和主權之間的緊張博弈:為保護人權,國際人權法引領著國際刑法試圖突破國家領土的藩籬進而穿透國家主權的堅硬鎧甲國家則奮力祭起主權大旗并訴諸司法獨立的堅固盾牌,抵御某些外部政治實體利用國際刑事司法機構干涉其內政、侵蝕其司法獨立,以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利益。
雖然通過國際刑事審判來懲治國際罪行的設想由來已久,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進行的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一般被視為國際刑法的真正起點,其基本文件《歐洲國際軍事法庭》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已經成為國際刑法的具體淵源。{1}在此后的半個世紀中,國際刑法基本上處于休眠狀態。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初起,國際刑事司法機構開始勃興,數量增加,地位上升,國際刑法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成為國際法領域中一個頗為引人注目的焦點。從迄今為止近20年的特設及常設國際刑事司法機構的理論與實踐來看,至少已經呈現出這樣一種明顯的趨勢:國際人權法借助國際刑法的長矛利刃,企圖刺穿國家主權的堅硬鎧甲,突破傳統意義上國家領土的界限,消解特權與豁免的庇護,以實現保護人權的宗旨;另一方面則是主權國家力圖以維護國家主權之名,借助于現行國際法的原則和規則最大限度地維護自己的利益,而這其間的矛盾與沖突共同成就了國際刑法的光榮與夢想,同時也彰顯了其遭遇挫折和反復時的無奈與彷徨。
在國際人權法與國際刑法的關系問題上,多年來中外學者進行了不少研究并發表了一大批專著和論文[1]。國內有學者認為尊重基本人權原則已經成為國際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2}還有的學者認為國際刑事法院的建立極大地強化了國際人權監督機制,使得人權的國際保護制度帶有強制力,這是國際社會在通向普遍的人權和法制進程中邁出的巨大一步。{3}從總體上看,在研究視角和思路方面,國外學者更傾向于從具體問題入手,研究國際人權法與國際刑法基礎及原則之間的關系問題[2],例如國際法是如何與國際人權法一道共同推進國際刑法具體規則變化發展的,這三者之間是如何形成互相補充關系的,等等。{4}然而,迄今為止,國內外學者從人權與主權關系視角對國際人權法影響國際刑法的方式和結果進行專門研究的著述并不多見。為了厘清討論的對象與范圍,劃定討論問題的合理邊界,在本文中,國際人權法指國際社會促成其成員保障基本人權和自由的國際法原則、規則和制度的總稱{5}而國際刑法則指國際社會中調整國際刑事關系的法律原則、規則和制度的總稱,{2}是包含國際刑事實體法、國際刑事程序法、國家間刑事合作和國際刑法實施機制的一個綜合的法律體系和法律學科。
編輯老師為大家整理了淺論國際人權法對國際刑法的影響,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第3篇
一、中國現行刑法典在體現國際刑法方面存在的問題
從目前的現狀來看,中國刑法在與國際刑法的協調與銜接方面還存在不少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中國刑法與國際刑法規范之間的關系不明確。對于中國加入的國際刑事法律規范,是直接適用,還是通過轉化的方式將國際刑事法律規范轉化為國內法再適用?當中國刑法與中國所加入的國際刑法規范相矛盾時,是優先適用國內法還是優先適用國際刑法規范?“政治犯”的范圍包括哪些?這些問題在中國刑法中尚未予以明確。同時,中國刑法中的死刑制度也還與死刑適用的國際標準相差較大。
第二,中國刑法典第9條規定:“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罪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所承擔條約義務的范圍內行使刑事管轄權的,適用本法。”根據這一規定,應當在中國刑法典分則中規定相應的國際罪行。但遺憾的是,中國刑法典分則規定的國際犯罪屈指可數。而對于尚未明文規定的國際犯罪,根據刑法典第3條確定的罪刑法定基本原則,就不得定罪處刑,因而中國刑法典第9條規定的“適用本法”就等于紙上談兵,既不能承擔有關條約義務,也不能真正行使對國際犯罪的刑事管轄權。
第三,中國已加入的國際條約中規定了侵略罪、反和平罪、滅種罪、反人道罪、種族歧視罪、海盜罪、扣留人質罪等國際犯罪,但中國刑法對于發生在中國境內的上述犯罪行為,沒有專門加以規定,雖然可以將上述有些行為視為殺人、放火、決水、販毒、爆炸、傷害、搶劫、劫機、綁架等犯罪適用中國刑法進行追究,但上述國際罪行的內涵遠非是這些國內刑法中的罪名所能涵蓋的。而且也有些行為也無法歸入這些犯罪中,因而成為“法無明文規定”的情形,如滅絕種族罪、種族歧視罪、種族隔離罪等,因沒有專門的法條規定,而難以予以追究懲處,即使將之勉強歸入現有罪名中處罰(如將種族滅絕罪作為故意殺人罪來處罰,將奴役罪納入非法拘禁罪或者強迫職工勞動罪中處罰),亦顯然有罰不當罪之虞,與這些犯罪之嚴重危害性遠不相稱。
二、加強中國刑法與國際刑法協調與銜接的措施
國際刑法的理論與實踐充分表明,國際刑法規范作用的發揮,在一定范圍內,在相當程度上,要依賴國內刑法的配合。有關國際犯罪的公約一般都要求各締約國依照本國憲法制定必要的法律對國際犯罪采取相應的、有效的懲罰措施,并按照其國內法律的規定防止和懲治國際犯罪。目前,對絕大多數國際犯罪分子的懲罰還只能由具體國家的司法機關來進行。在國際社會還沒有完善的直接執行機制的現實條件下,對大部分國際犯罪分子的懲罰仍需要依靠有關國家的司法機制進行。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在處理國際犯罪案件時,首先是要從其國內法中去尋找依據,而不可能僅僅依據國際條約。離開了有關國家國內刑法關于刑罰及其具體適用的規定,單純依照國際刑法規范,是難以切實有效地追究國際犯罪的刑事責任的。而我國刑法在與國際刑法的協調與銜接方面又存在著上述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足以使我國承擔的懲治國際犯罪的義務無法得到切實的貫徹落實。所以,我認為,現階段亟需對我國刑法加以完善,使之與國際刑法能有效地協調與銜接,具體說來,可以從刑法總則和分則兩個方面予以完善。
(一)完善中國刑法總則的有關規定
1、理順并明確中國刑法和國際刑法規范之間的關系
當國內法規定與中國所承擔的條約義務發生沖突時,應如何處理?關于國內法同國際法之間的關系,中國《憲法》沒有明確規定。1990年4月27日,中國代表在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上回答問題時聲明《禁止酷刑公約》的適用是基于國際法優于國內法的原則,條約直接對中國有效,若違反其規定,同樣視為中國國內法所規定之犯罪,公約的規定可直接適用于中國。據此,我們可以主張,中國在處理國內刑法同國際刑法規范沖突時,也應實行國際刑法規范優先的原則。這一原則應當貫徹到所有中國已經簽署或者加入的國際條約,亦即中國已正式承諾遵守的國際刑事法律規范可以直接適用于中國。
2、堅持普通刑法與特別刑法相結合的原則
國內刑法生效后,國際社會基于現實的需要而確認了一些新的國際犯罪行為,國家為了保證法律的相對穩定性而不能隨時修訂其國內刑法,但國家應履行的國際義務不能因此而免除。我們認為,較為及時、有效的辦法是,一方面,國家應在其普遍刑法中宣布凡該國締結或加入的國際條約中規定的國際犯罪,在國內法中尚未規定的,應參照國際條約的有關規定來處理;另一方面,制定具有針對性的特別刑法來打擊新的國際犯罪。
3、限定“政治犯”的范圍
由于“政治犯罪”的概念模糊不清,很多犯罪分子利用各國的政治觀點不同,在實施犯罪后逃往他國,給自己的犯罪行為披上“政治犯罪”的外衣,尋求庇護,這使得許多犯罪得不到應有的懲罰。為了有效打擊國際犯罪,一些國際性文件確立了“政治犯罪例外”的原則。中國并不否認“政治犯罪”的存在,并承認“政治犯不引渡原則”。但是,在中國的《憲法》、《刑法》以及其他刑事立法中均沒有使用“政治犯罪”這一術語,更未提供辨別此類犯罪的標準。所以,我們認為,在中國刑法中應當盡可能明確“政治犯罪”的范圍,特別是應當將國際公約中“政治犯罪例外”的內容在國內刑法典中加以明確體現。
4、完善中國的死刑制度
迄今為止,一些國際規范性文件樹立生命權的特殊保護觀念,確立嚴格限制并逐步廢除死刑的目標,并確立了一系列死刑適用的國際標準,如死刑適用的范圍為最嚴重的犯罪;任何人只要其在犯罪時未滿18歲,便不得被判處死刑;對孕婦或新生嬰兒的母親、精神病患者不得執行死刑等等。中國刑法典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完善:(1)較大幅度地減少適用死刑的罪名,在中國尚不具備廢除死刑條件的現階段,應將可以判處死刑的犯罪加以嚴格控制,只對特別嚴重的危害國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軍職罪和侵犯公民生命權利的犯罪適用死刑,而對經濟犯罪、職務犯罪等的死刑可以廢除;(2)嚴格而合理地限制適用死刑的對象,中國刑法典第49條規定:“犯罪時候不滿十八周歲的人和審判的時侯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由于“懷孕的婦女”前加上了“審判的時候”這一限制,使得在司法實踐中對這一規定產生了認識上的分歧,對此需要從立法上進一步加以明確;(3)完善死刑的減刑制度,中國刑法應當加大對死刑減刑的力度,除實行死緩制度外,還應規定對死刑可直接減為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以充分體現中國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懲治與教育相結合的刑事政策;(4)增設死刑的赦免制度,這不僅能體現中國的“慎刑”政策,而且還能進一步限制死刑的適用。
(二)完善中國刑法分則的有關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