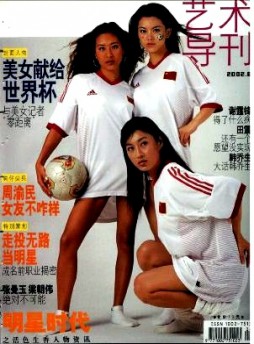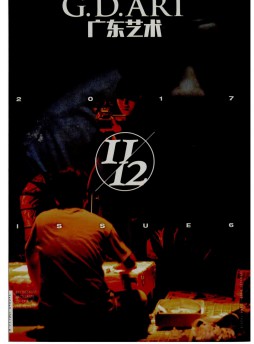藝術特質下中國抒情傳統論探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藝術特質下中國抒情傳統論探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安陽師范學院學報》2016年第3期
摘要:
“中國抒情傳統”研究者經過將近半個世紀的持續建構實際上為“中國抒情傳統”建立了一個屬于創作層面的“感興”論述。這一論述不但沒有認真對待中國抒情詩藝物我情境互動中的“物”,而且忽略了中國詩學傳統建構后的廣闊文化背景。“感興”論述屬于中國抒情傳統藝術特質層面的建構,而不應該歸屬于藝術本質范疇。抒情傳統只是“平行研究”視域下中國文學的一個“異質性”層面。中國抒情傳統要在藝術特質層面盡量呈現其多面向的變遷,否則容易造成虛假的“超概括”。藝術特質是反思“中國抒情傳統論”的有效憑借。
關鍵詞:
中國抒情傳統;藝術特質;自洽
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一些域外華人學者在中西比較文學“平行研究”框架下將中國古代文學的藝術傳統確立為一種“抒情傳統”,并在對此傳統的闡釋中逐漸形成了一個前后相續的學術傳統。“中國抒情傳統”論述,從蘊生到顯題,已經綿延近半個世紀。作為一個歷史時期,在特定社會文化情境制約下產生的知識產物,一定有屬于那個歷史時期的詮釋語境。正如陳國球所指出,中國抒情傳統論述“是中國文學研究者在‘現代狀況’下對研究對象的文化歸屬及其意義的省思”。[1](P31)時過境遷,其詮釋視域的遮蔽無疑已昭彰。基于此,本文擬從自己拈出的“藝術特質”這一藝術范疇出發,接續當下學界對“中國抒情傳統”的反思,探究“抒情傳統論”的指涉范圍,從而希望在對“抒情傳統論”的轉拓及其理論自洽有所裨益的同時,為中國詩學體系的建構以及中國古典詩學“異質性”的甄別貢獻一些具體意見。
一、中國文學“抒情傳統論”省思
20世紀70年代,留美學者陳世驤首先標舉中國文學是有別于西方以戲劇、史詩為主的“抒情傳統”。陳世驤于1971年發表《中國的抒情傳統》一文,在中西比較文學“平行研究”的框架下,正式提出“中國的抒情傳統”這個論題:中國文學的特質即在于“抒情”。此一特質普遍涵蓋詩歌、散文、小說、戲曲各種文類,并形成源遠流長的傳統,故稱為“抒情傳統”;它恰與西方以希臘史詩、戲劇為主的“敘事傳統”形成對比。這一觀點見于他的幾篇論文:《中國的抒情傳統》、《中國詩字之原始觀念試論》、《原興:兼論中國文學特質》等。繼而,同在美國的高友工做出進一步的擴展,構建起涵蓋多個藝術門類的“中國美典”架構。嗣后,孫康宜、林順夫分別從斷代史的角度,蔡英俊、呂正惠以及余寶琳從傳統詩學的概念發展,刻畫了中國抒情傳統的形成與演變;張淑香則對此一傳統之本體作了思辨。[2]于是,再加上柯慶明、鄭毓瑜、蕭馳、宇文所安以及浦安迪等人對此研究領域的廣泛拓展,中國抒情傳統研究逐步形成了一個有所承襲的學術傳統,“抒情傳統”成為理解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維度。不僅如此,由于“抒情精神”的求索恰是現代西方文學的一種重要傾向,在“現代主義”的“前衛”中占有一席,是故,陳世驤等現代學人,通過與西方文學傳統比較對照而建構的“中國抒情傳統”,又為中國在文學的世界地圖中找到了一個值得尊重的位置。[1](P25)然而,時過境遷,其詮釋視域的遮蔽已昭彰。
關于“中國抒情傳統”的歷史起點,陳世驤認為“始于《詩經》”。“《詩經》之后,在中國文學上是動人心魄的《楚辭》,或稱楚的悼亡詩。……以字的音樂做組織和內心自白做意旨是抒情詩的兩大要素。中國抒情道統的發源,《楚辭》和《詩經》把那兩大要素結合起來,時而以形式見長,時而以內容顯現。此后,中國文學創作的主流便在這個大道統的拓展中定形。”[3]1986年,蔡英俊出版《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一書。在書中“‘抒情自我’的發現與情景要素的確立”一節中,蔡英俊接受陳世驤“中國抒情傳統”的基本觀點,但又從“古詩十九首”的個人抒情特質、魏晉的時代環境與文人的生命存在意識以及“詩言志”與“詩緣情”的辨析出發,將“中國抒情傳統”的歷史起點修改為“起于古詩十九首”。蔡英俊認為:兩漢時期“本于政治教化的社會群體的共同情志”,根本無法彰顯“‘詩三百篇’中原有的情感性質以及借助自然景物以起情的表現手法”,“《詩經》和《楚辭》的傳統在漢代基本中斷了,而《古詩十九首》的傳統卻延續了一千又七、八百年。”[4]繼而經過呂正惠、張淑香等人的建構,大抵形成這樣一種共識:“中國抒情傳統在漢、魏、晉的發展,是趨向以‘嘆逝’的角度去觀察大自然,‘從而賦予大自然以一種變動不居、凄涼、蕭索而感傷的色澤’。尤其古詩十九首幾乎成為‘悲觀主義之祖’,也是后來魏晉詩的基調,更進一步說,悲哀的詩人所看到的悲哀的自然,就是中國抒情傳統的主流。”[5](P36)因為陳世驤“中國抒情傳統”的論述目的是為了凸顯中國文學的特質及價值,進而與希臘史詩、戲劇進行“平行比較”,其后的論述雖然轉入了中國文學的內部,但中西架構下的“中國抒情傳統”的基本視角卻沒有變,所以,這種“中國抒情傳統”論述就比較著重詩人主觀與自我情感的發抒,于是就有了蔡英俊等人“悲哀的詩人所看到的悲哀的自然,就是中國抒情傳統的主流”這一看法,進而衍生了“中國抒情傳統”真正歷史起點是《古詩十九首》這一論斷。綜觀陳世驤以降有關“中國抒情傳統”的論述,他們大多強調內在主觀心靈的優位性,相對將外在于人的“物”,僅視為詩人情感的寄托,“‘物’是為了‘情’而存在,并且是在情志的聚焦范圍下被選擇、被呈現”。[5](P37)但問題是,難道中國抒情傳統除了“情往似贈,興來如答”,通過借助自然景物以起情,彰顯個體自我的發展過程這一線索之外,就沒有其它的理論與實踐嗎?漢儒針對《詩三百》極盡“法度”性的解釋,在今天看來似乎有點像天方夜譚,但是,這一批評系統對于中國抒情傳統的塑成難道一點作用都沒起嗎?在兩漢,經學大部分時間屬于國家學說,是意識形態,而且在以后的封建王朝中繼續扮演著這一角色。那么,演進在這一文化系統的中國抒情傳統難道不受到它的選擇和建構嗎?我們以為,陳世驤以降蔡英俊等中國抒情傳統論者的闡釋忽略了中國詩學傳統建構后的廣闊文化背景,不但將中國抒情傳統的演進單線索化了,而且還忽略了兩漢這一所謂表現社會群體意志的時期對于建構中國抒情傳統的重要性。
在《從反思中國文學“抒情傳統”之建構以論“詩美典”的多面向變遷與叢聚狀結構》一文中,顏昆陽認為“抒情傳統論”的根本“負面”問題在于“這種論述是建立在‘特殊性’與‘普遍性’兩個相對的基本概念上,即設定了中國文學的某一范型以與西方文學的某一范型加以比觀,而指認彼此的差異;此一差異就是它的‘特殊性’。而這一‘特殊性’回到中國文學的本身來看,卻可由《詩經》推擴為全體中國文學的‘普遍性’”。[6](P738)正是這一“覆蓋性大論述”單線化了中國文學史的多元詮釋。基于此,顏昆陽提出“中國‘詩美典’的變遷與結構,不能僅由一個‘抒情傳統’獲致完全的詮釋。它所呈現的是‘多面向變遷’和‘叢聚狀結構’”。[6](P771)進而在此基礎上,他認為應該“從‘布體’的典律性文本開始,尊存各種不同文學體類的歷史他在性,而逆溯地進行詮釋其發生、構成因素、美感特質、社會文化功能及各自相對性的價值等議題”,[7]對此,顏先生稱之為“完境文學史”。筆者認為,顏昆陽的論析確實是觸及了“抒情傳統論”負面價值之根本。但問題是,包括顏昆陽在內的開創者、繼踵呼應者、反思者都在有意無意之間遮蔽了這樣一個問題:抒情精神或者是抒情傳統只是“平行研究”視域下的中國文學的一個“異質性”層面。借用顏昆陽先生的說法,“抒情傳統”對于中國文學而言應該只是“相對普遍的物性本質”,[6](P756)而不歸屬于“藝術本質”范疇。然而,許多論者在有意無意之間,將此一論述上升到了絕對普遍本質層面,這樣,該論斷自然也就產生了問題。因此,在筆者看來,“抒情傳統論”不能理論自洽是因為對它的指涉范圍認識混亂所致。
二、藝術特質
藝術特質,是筆者基于中外抒情傳統,兼及內在感情活動與抒情活動機制嘗試提出的一個藝術范疇。我們認為,在本質與特點之間還有一個層面,這個層面即為特質。本質力圖把握所有,而特質則未必時時顯現,但卻又在一般層面參與構建,從而比特點高一級別。基于此,我們認為,在藝術本質層面把握所有與藝術特點的一般性顯現之間的那個層面即為藝術特質。
藝術特質是建基于一系列連續進行的同時性描述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首先,藝術特質是某一國家或某一民族某一時段藝術顯現特點的“同時性”概括。我們不妨設想一下,是否會有一位具有“創造性”的詩人往桌前一坐,拿起筆和白紙,憑其特殊的創造本領,一下就寫出一首詩來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詩歌只能從其它詩歌中產生。約而言之,作家創作的“視域融合”要受三重結構性關系限定。首先,社會結構中的作家,不可避免要隸屬于某一整體性的歷史文化與社會情境。李白不能提筆寫出“十四行詩”,莎士比亞不會創作律詩和絕句,這是不可逃避的“地域民族”限定。正如布魯克斯所說:“當一個詞在一首詩里,它應當是在特殊語境中被具體化了的全部有關歷史的總結。”[8]例如在中國古典詩歌里,“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江淹《別賦》)中的“南浦”一詞已不是具體的地名,而是表達離愁別緒的常規用語;“章臺”不再是漢長安的街名,而成為“柳”的別稱;“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王粲《七哀詩》),“灞岸”是表達“折柳送別”、“喟然傷心”的慣用語;而“香草美人”則是屈原以來用以表達“志潔行芳”的個人情志而形成的一種特殊文學表現,等等。潛藏著“歷史痕跡”的語詞不斷地填充著中國詩歌結構中的空項,于是,創作才成為可能,當然,創造也就不會漫無邊際。其次,作家都從屬于某一社會階層,他只能在階層限定的“視域”中,選擇、認定某些由“文化傳統”和“社會階層”所形塑的價值觀。魯迅先生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中說:“饑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9]可見,只有那些承受著相同文化遺產的階層,才會一致認同“符碼”背后所指涉的價值體系。作家的創作展演,遞衍的正是所屬階層的文化精神、價值理念。換言之,作家所屬的“社會階層”要“如影隨形”地限定著進入其意義視界的“符碼”或符號系統。最后,從選擇性角度而言,作家由于文學觀念及活動所自主選擇、承受的“文學傳統”與“社會交往”的不同而相應地歸屬于他認同的“文學社群”。盡管“傳統”一詞,往往具有“規范性”,隱含了允許、要求、建議、期望同樣行動的信念,但是,由于文學傳統是大時代里多種聲音的匯集,塑成的“美典”是多面向的變遷,所以,投注自己的感懷或目的于其中的文學家會基于“同理心”的共鳴,選擇與己相默契的“符碼”系統展演主體生命的起伏悸動。正是基于上述這三重“結構性關系限定”的彼此疊合、混融、交涉、衍變,文學傳統才得以綿延,多樣化文學史景觀才得以構建。由于作家創作的“視域融合”要受“地域民族”、“社會階層”以及“文學社群”這三重結構性關系的限定,所以,作家的創作一定會打上前后相繼的形式特征。由是,藝術特質能夠讓我們看到同種形式的歷時共繼,看到某一階段積極保留下的或被動保留下的那部分文學傳統。與此同時,藝術特質又不是消極被動的藝術結構,而是能夠自我調節,起藝術構成作用的。文學生產中,藝術特質能及時“轉換”以對新的經驗做出反應,不斷地整理加工新的材料。藝術特質不是靜態的,它是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調節者。藝術特質的轉換、構筑使得彼此均無其獨立存在的質料與形式形成新的結構,從而形成既是經驗的又是理智的實體———作品。由是,藝術特質也能夠讓我們看到形式的創新性,亦即它也有一個前后相續的“歷時”發展問題。要言之,藝術特質絕不是一種靜態的描述,它是建立于連續進行基礎上的一系列“同時性描述”。談到“傳統”,米歇爾•福柯在《知識考古學》中有過這樣一種意見:“傳統這個概念,它是指賦予那些既是連續的又是同一的(或者至少是相似的)現象的總體以一個特殊的時間狀況;它使人們重新思考在同種形式中的歷史的播撒;它使人們縮小一切起始特有的差異,以使毫不間斷地回溯到對起源模糊的確定中去;有了傳統,就能把新事物從常態中區分出來,并能把新事物的長處移交給獨特性、天才、個人的決策。”[10]揆之以福柯對“傳統”的界定,不難發現,藝術特質是文學傳統得以塑成的最重要因素。藝術特質的參與建構,使過去和現在得以中介,使得民族文學呈現出連續樣態,彰顯出自己的特點,從而讓我們得以在剝落差異性的時候把握其“同一性”。與此同時,藝術特質又并不抹殺創新,阻遏藝術的發展。藝術特質的圖譜是多重的,它能夠因應時代,及時“轉換”,對新的生態會做出積極的反應。是故,藝術特質不但不會遮蔽個體的光芒,而且會讓個體天才的光芒成為時代、民族藝術的一部分。
三、藝術特質視域下的中國抒情傳統多面向變遷
藝術特質的參與建構,使得某種范式歷時共繼,成為“有意味的形式”。這一“有意味”的范式使過去和現在得以中介,使當下行為得以發生,于是,在歷史的遞延中民族文學傳統得以塑成。在中國古典詩學中,“興象”就具有詩學質素意義,是顯現于抒情實踐的具有“同時性”的詩性之特質。“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可情感本身不具有抒發性,所以,中外詩藝都是借助于外在的“象”來抒發主體的內在情思。但是,天人合一的悟覺思維模式卻使中國詩藝當中的用“象”行為呈現為興中取象,象中有興。“象”于詩情的抒發,在與情感聯系的背后不是出之以邏輯思維下的推理過程,而是呈現為一種“景←→情”似的遷就關系,于是,“象”便具有了一種當下的情境性。“象”沒有像西方詩歌那樣,被從直接與可感的背景中抽取出來,而是挪位到心里去充當一個被沉思的對象,“象”的背景,出現在中國詩中是含有“情”的“景”,而在西方,“象”卻被塑成“得意忘象”的述情手段而被普遍地使用。于是,我們詩藝當中的“象”,并沒有止于借意象以述情,而是在觸物感興的基礎上導向了一種意味不盡的“興象”境界———情境互動,“象中有興”,由象生意,由意轉情,“物色盡而情有余”,“情有余而味不盡”,“象”生發出了一種余味不盡的境象之美。[11]抒情文學的本質乃是一種物我情境互動之下的主觀抒發。揭橥“興象”的美學特質和藝術精神,不難發現,“興象”這一詩學范疇能夠引領我們把握中國抒情詩藝物我情境互動中主觀情感發抒層面的藝術特質。因此,在中國古典詩學中,“興象”具有詩學質素意義,是顯現于抒情實踐的具有“同時性”的詩性之特質。但是,有一點我們必須明確,“興象”只是詩之為詩的基本質素,而不是在本質層面限定了所有。因為就本質而言,它應該顯現于整個中國抒情傳統,但很顯然,這一點并非此范疇所能有。是故,“興象”只是一個層面元素,在中國抒情傳統中它扮演的是詩學基本質素角色。
陳世驤以降的“中國抒情傳統”研究者經過將近半個世紀的持續建構實際上為“中國抒情傳統”建立了一個屬于創作層面的“感興”論述。這種論述“強調創作者與自然萬物、人物事件彼此的觸然相遭、同情共感”。[12]揆之以“興象”這一藝術特質,我們認為,“中國抒情傳統論”中的“感興”論述確實把握到了中國抒情詩藝物我情境互動中主觀情感發抒層面的藝術特質。但是,中國抒情論者以此為基準認為從“嘆逝”的角度去觀察大自然表現大自然是中國抒情傳統的主流,兩漢時期“本于政治教化的社會群體的共同情志”,根本無法彰顯“‘詩三百篇’中原有的情感性質以及借助自然景物以起情的表現手法”,“《詩經》和《楚辭》的傳統在漢代基本中斷了”,則是把中國抒情傳統單線索化了。
首先,這一論述忽略了中國抒情傳統建構后的廣闊文化背景。對于一個群體或民族來說,文化是一種結構,一個系統,它往往在“在”的地方以“不在”的形式規范著群體成員的思維與行為,同時迫使個體接受一些經過不斷詮釋賦予而被視為客觀范疇的觀念框架、有效規則以及模式。是故,藝術特質的塑成,離不開文化與理論話語的共謀。就中國抒情傳統來說,早在《詩經》時代,禮樂文化即塑成了“和合”這一藝術特質參與詩人情感的發抒。殷周革鼎,周代精英認識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于是,周公“制禮作樂”,把這種尋繹于歷史變動的文化思考攝入傳統禮樂,從而使傳統禮樂涅槃升華,有周一代,“郁郁乎文”。禮樂文明一方面用“禮”來制約和規范“樂”,另一方面也用“樂”來輔佐和推廣“禮”。周人的禮樂文化既要恰如其分地宣揚“禮”,又要愉悅和陶冶人的情操,從而通過“樂者敦和”與“禮者別宜”的相互配合,達到“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的理想狀態———“和合”。這樣,周人便在演禮奏樂當中,實踐著自己的德行,演繹著自己的德行。因此說,周朝的社會在本質上其實就是一“道德性團體”。《詩經》三百篇,首先所抒發的情感即是立足于這一“尚德”思想背景下的,人作為宗法社會成員,以倫理情感為旨歸的情感言述。這一特征主要顯現在大雅和頌詩之中,作為正風、正雅的周召二南也部分地物化了這一情感特質,而“變風變雅”則在悖離中昭示了一種新的言情機制的轉變。“變風變雅”時代,抒情主體開始覺醒,詩人們直接介入外在情境,直接抒瀉著自身的喜怒哀樂。周人開始擺脫群體歌唱和歌唱群體,他們逐步走出自己的宗法位置。“變風變雅”昭示的是一場抒情詩人群體“私人化言說”的開始。不過,他們悲憤,他們哀怨,他們迷狂———雖然說他們已經走向了個體人性的光輝演繹,但是,“變風變雅”當中的周人依舊徘徊在宗法倫理社會的位置之中。兩漢時期的詩學建構,“政治的要求,也即是如何使三百篇成為維系社會秩序以達到鞏固漢家統治的目的,一直是一個被關心的問題。可以說兩漢御用的詩經博士們,最焦灼的無過于如何在三百篇中幻化出一個切合漢天子意志的‘法度’來。”[13]職是之故,兩漢詩學的生成,內蘊著意識形態的共謀,“文化性”的默契。從我們對《詩經》情感言述的揭示來看,《詩經》首先言述的是立足于“尚德”思想背景下的,人作為宗法社會成員,以倫理情感為旨歸的群體志意感受。這樣說來,兩漢閱讀視域下“本于政治教化的社會群體的共同情志”歸約,并非是對三百篇的完全背離,它應該是新的歷史條件下,兩漢士人在《詩》藝基礎上的一種積極建構。換言之,兩漢閱讀視域下的這一建構應該是《詩經》詩學傳統構建的一部分。與此同時,透過兩漢抒情實踐的考索,我們發現,從“變風變雅”揚起的這場“私人化言說”,個體情志之關注,一方面在兩漢解詩中并沒有完全缺失,而且,兩漢士人,以賦這種文體,進而是賦與詩的互動中來尋繹人生個體價值之安放,更是對“騷人”以“詩”“言一己窮通”的一種接續。
從“和合”圖譜中的言志詩藝來看,兩漢“本于政治教化的社會群體的共同情志”,也并沒有導致個體情感在詩學詩藝中的缺席。先秦時期的言志詩藝可約化為兩個主體中心,一是以創作主體為中心,從群體普遍感受之志演進為私人專有內在之志;一是以閱讀主體為中心,從偏向于現實運用的情境意義演進為對普遍義理的建構。兩漢士人接續這兩個中心,就處理自我與他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繼續展開思考。彼時,崛起于先秦時期,“高置位置”的士人階層與皇權博弈后達成共謀。于是,兩漢社會實踐主體———士人,接續原始儒家詩學的道德化訴求,并將之系統化,為鞏固漢家的統治機制服務。總體而言,兩漢閱讀視域下的言志要求是,“志”之傾瀉要“發乎情,止乎禮義”。因為這一和合導向,既符合統治者的利益,是漢家統治所亟需,而兩漢士子群體之意志與要求又由此得到棲居與滿足。所以,這一詩藝訴求在兩漢得到了極大發展,成了詩學主流。不過,政教視域下的義理關懷并未完全淹沒主體心靈的躍動。閱讀體認中,毛派詩學的《詩大序》將文學功能當中的政教訴求推向了極致,但它所闡發的言志詩藝卻并未因此就完全皈依了政治而罔顧“志”的情感性。實踐創作中,漢人接續屈、宋將生命歷程呈露于辭的言志訴求,在賦與詩的互動中,繼續追問著人生價值的皈依,個體情感的安放。最終,兩漢言志詩藝就在實踐創作與閱讀體認的相互交蕩下,將文化結構中的人文境界躍升為藝術境界,生成了一種不假乎外求,只關注著內心情意的自適,自言自語,自彰自明的言志詩藝。不僅如此,將“興象”詩藝放到先秦兩漢的抒情實踐中尋繹,我們發現,《詩經》《楚辭》以來,景情互動,興會取象,借助自然景物“感發”以起情的這一“興象”詩藝在有主名的漢詩、無主名的樂府以及古詩中均得到了繼承,并在以《古詩十九首》為代表的古詩中塑成了“泣鬼神,動天地”的藝術表現力。而就理論建構而言,兩漢時期,“毛公述傳,獨標興體”,首次將“興”從用詩領域擴展到詩的創作,將“興”移用至詩學領域。就批評視域移易而言,先秦時期“詩可以興”的用詩方法在毛公追問所謂“作者本意”的語境中生成了“興也”這一作詩方法而將“興”的立論發言位置轉向了“作者”。總體說來,《毛傳》對“興”的理解是比較寬泛的,但是,“超概括”的習慣性心理使得以喻釋興成了漢人的普遍做法。而政教視域下的義理關懷又是兩漢詩學的“前理解”。于是,“興”在兩漢興義論述集大成者鄭玄的語境中便具有了政治寄托、道德寓意的內容。鄭玄的興義論述視域完成了“讀者”向“作者”的移易,興在鄭玄的箋注語境中是一種特殊的表達方式———興喻。進入六朝,隨著儒家思想影響的弱化,普遍的道德理性主體轉為個殊的審美才性主體。原來統攝在道德主體價值觀念世界中的自然萬物,也從兩漢的譬喻世界得以釋放出本來面目,由自然景物所引起的情意經驗得到強調。換言之,被漢人有意無意地遮蔽了的情意與自然物象間純為美感經驗的“感發”獲致了論者的注意。于是,六朝時期的“興”義也就由先秦時讀者對作品的“感發”轉向了“作者”對自然景物的“起情”、“感發”。這時候的“興”不再是一種譬喻的語言工具,而是“興中取象”的一種表現方式。依藉著這種表現方式具現為作品后,作品語言便獨立為一個可以喚起讀者直覺感性經驗的美學意象。于是,“興”又獲致了“文已盡而意有余”這一美學內涵。將蔡英俊等人的“感興”論述放到這一理論背景下來尋繹,不難發現,兩漢的“興喻”論述顯然應該是“中國抒情傳統論”中的重要一環。
“中國抒情傳統論”中的“感興”論述確實把握到了中國抒情詩藝物我情境互動中主觀情感發抒層面的藝術特質。但是,這一傳統中的另一個重要維度———“物”卻沒有得到認真對待。實際上,中國抒情美學物我情境互動中的“物”除了“在情志的聚焦范圍下被選擇、被呈現”外,還有一個窮形盡相,曲盡物貌,“情貌無遺”,“求物之妙”的傳統。“體物”最初是由魏晉時期的著名文論家陸機在《文賦》中拈出的。他在《文賦》中提出了“詩緣情”和“賦體物”這兩個范疇。按一般性的理解,“詩緣情”和“賦體物”分別指的是詩與賦的不同文體特征。而當超越“賦體物”這一單純文體自覺的層面來理解“體物”,我們發現,中國的詩歌創作實踐和詩學批評中實際上也存在一個“體物”問題。隨物婉轉,曲盡物貌,求情感、情景、情事之妙的“體物”詩藝不同于“言志”“緣情”主導下的“感興”論述,它是在“物”的層面來回答“物”的準確描摹、傳達問題。是故,中國抒情傳統除了“情往似贈,興來如答”,通過借助自然景物以起情,彰顯個體自我發展過程這一線索之外,還有一個“物”之準確再現描摹,“求物之妙”的詩學詩藝傳統。《詩經》時代詩人即以“賦”法開始了“體物”。《詩經》以后,“體物”詩藝不斷在實踐中得到發展。建安以下,直到齊梁,“體物”詩藝已經塑成為一種詩風并見之于詩評,其具體表現就是鐘嶸、劉勰、顏之推等人筆下“尚巧似”、“形似”等這些論斷。而鐘嶸的賦之界定,注解著五言詩“尚巧似”的創作實際,綰合著情、物兩端,以“稱物”為終極旨歸,更是使得“賦體物”完成了向“體物”詩藝的過渡。漢魏六朝,“體物”詩藝力圖“巧言切狀”,曲盡物貌,以使“情貌無遺”。而當這一詩藝傳統經過詩人的努力取得卓越的藝術效果后,杜甫以降,詩人們又開始擺脫“尚巧似”的傳統,力圖在“道藝不二”的指導下“求物之妙”,亦即由“體物”走向了“禁體物”。“禁體物”,既非禁止“體物”,亦非不作體物語,而是禁用世人熟知的“體物”語言。而將歐陽修、蘇軾的這一“禁體物”的倡導放到兩宋追求詩歌創新、語言創新的時代背景下考索的時候,可以發現,這一求新求變是“宋調”形塑中的重要一環。對此,宋人已有自覺的理論認識。朱弁的“體物”詩論就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以一種更高的藝術境界進一步豐富了中國詩學詩藝傳統中的“體物”詩論。兩宋以降,將“體物”作為一種詩藝手法來研究,元人陳繹曾的“體物七法”最為詳備。而明清時期的“體物”詩藝,沿著兩宋的“求物之妙”,一直強調體物之妙,貴得神似。要之,隨物婉轉,曲盡物貌,求情感、情景、情事之妙的“體物”詩藝是中國詩學傳統中的一個重要維度。中國詩學詩藝中的“體物”傳統,對“言志”“緣情”主導下的中國抒情傳統“感興”論述來說是一個重要補充。我們要在藝術特質層面來闡釋中國詩學中的“體物”傳統。
四、結論
綜上所述,藝術特質是反思“中國抒情傳統論”的有效憑藉。中國抒情傳統論不應該成為一個單線索的“超概括”,它不能以一個面向概括中國抒情美學的多面向變遷。就藝術特質在中國抒情實踐的呈現來看,蔡英俊等人構建的“感興”論述屬于中國抒情傳統的“相對普遍的物性本質”,而不應該歸屬于“藝術本質”范疇。進一步言之,“抒情傳統”對于中國文學而言也應該只是藝術特質,而不應該歸屬于“藝術本質”范疇。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在本質與特點之間來盡量呈現中國抒情傳統的多面向變遷,否則,將之納入“一般和普遍”的本質視域,極易造成虛假的“超概括”,從而影響“中國抒情傳統論”的理論自洽及其概括力。
參考文獻:
[1]陳國球,王德威.抒情之現代性:“抒情傳統”論述與中國文學研究[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31.
[2]蕭馳.中國抒情傳統[M].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1.
[3]陳世驤.陳世驤文存[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2.
[4]蔡英俊.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M].臺北:大安出版社,1986:24-27.
[5]鄭毓瑜.替代與類推———“感知模式”與上古文學傳統[J].漢學研究,2010,(1).
[6]柯慶明,蕭馳.中國抒情傳統的再發現[M].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
[7]顏昆陽.混融、交涉、衍變到別用、分流、布體———“抒情文學史”的反思與“完境文學史”的構想[J].清華中文學報,2009,(3):145.
[8]趙毅衡.新批評[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12.
[9]魯迅.魯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208.
[10]米歇爾•福柯著,謝強、馬月譯.知識考古學[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20.
[11]任樹民.“興象”的詩學質素意義闡釋[J].黃河科技大學學報,2012,(3):91-93.
[12]鄭毓瑜.抒情、身體與空間———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一個反思[J].淡江中文學報,2006,(15):262.
[13]施淑.漢代社會與漢代詩學[J].中外文學,1982,(10),80.
作者:任樹民 單位:北華大學文學院
- 上一篇:尼采關于同情的批判范文
- 下一篇:機械自動化技術探究(7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