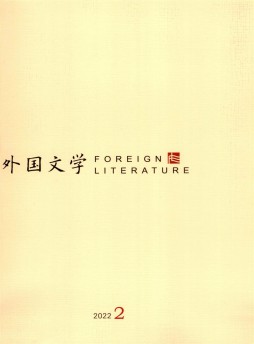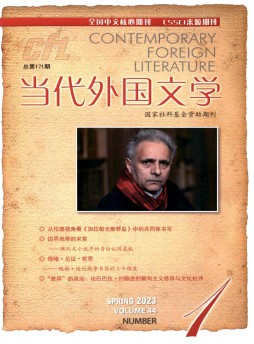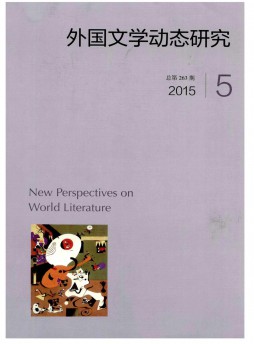外國文學中的人性之惡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外國文學中的人性之惡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外國語言文學雜志》2014年第二期
1對作品主題的爭議
很久以來,《貝尼托•塞萊諾》(以下簡稱《貝》)被認為表現了善與惡的斗爭,其中巴波代表邪惡,德拉諾代表天真,而飽受折磨的塞萊諾代表邪惡對人們的沖擊。塞萊諾在得救后,仍然郁郁寡歡,德拉諾勸慰他:“你已得救了,還有什么陰影籠罩著你呢?”,塞萊諾答道:“黑人。”②這被引用來解釋黑人的叛亂在他身上投下陰影,即意味著黑人是邪惡的象征。但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特別是90年代以來,這種善惡論的觀點遭到挑戰,人們認為麥爾維爾并未將黑人視為邪惡的象征,相反,他在故事中贊揚黑人為了自由而抗爭所表現出的勇氣和精神,巴波不僅不是一個邪惡的兇手,還是一名充滿智慧的領袖。評論家舉出各種例子說明黑人在船上殺害白人都是為了自衛和自由。很多評論家還指出故事表現了麥爾維爾對蓄奴制的批判,并以微妙的方式批判和諷刺了蓄奴制背后的主導意識形態,批判了白人潛在的種族優越感。在國內,韓敏中教授洋洋灑灑幾萬字的論文可以說是對《貝》做的最細致的研究。她批評了當前對該作品過于政治化的解讀。通過對比麥爾維爾的作品與阿瑪薩•德拉諾的《南北半球的航行與旅游記》以及另一個對作品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底本”,即《查理五世皇帝的隱修生活》(TheCloisterLifeoftheEmper-orCharlesoftheFifth),她解釋了作品中的內在矛盾,并將小說納入了麥爾維爾對形而上的“惡”的一貫關注中。
這種種解讀為我們提供了審視作品的不同視角,令人受益非淺,但這些解讀似乎都沒有解答這個問題:為什么麥爾維爾在作品中會對黑人白人都有種種暴行的描寫。在傳統解讀中,作為邪惡象征的叛亂首領巴波帶領其他黑奴們殺害了許多白人船員,甚至在他們完全控制船只后,還殘忍地殺害了一些已無反抗能力的白人。然而,如果說黑人是邪惡的代表,為什么這部發表于內戰爆發四年前的作品仍有大量對白人暴力的描寫?尤其是德拉諾在叛亂暴露后對黑人的追殺。面對作品中白人與黑人都實施的暴力,簡單地斷定巴波象征著惡、而白人代表著善似乎有失偏頗。在對《貝》進行政治化的解讀中,德拉諾被視為當時美國白人大眾的代表。他之所以不能對“圣多明尼”號上的種種跡象做出正確判斷,之所以無法預想黑奴可能叛亂,不是因為他的善良天性和單純性格,而是因為他的種族優越感使他根本無法想象黑人居然有能力組織起來進行判亂。他自視甚高,既沒有將黑人視為平等的人,也瞧不起沒落的西班牙人。他在無意識中顯示了美國人以理性自居、以新大陸精神為自豪的傾向。巴波正是利用了德拉諾的這種優越感,才成功地迫使塞萊諾演出了一場大戲。巴波因而被視為黑人智慧和勇氣的象征,德拉諾也成為麥爾維爾含蓄諷刺的對象。然而,如果說麥爾維爾在作品中表現了對黑人的同情,對白人和蓄奴制進行了批判,為什么他還會描寫黑人的一些不必要的殘忍行為?除了叛亂黑奴將阿蘭達的尸骨高懸、巴波在為塞萊諾剃須時顯示了他的奸詐與兇狠等例證外,研究者還例舉了巴波最后跟隨塞萊諾跳入小艇,企圖刺殺他的細節。③在對《貝》的研究中,研究者常將德拉諾的歷史敘述與麥爾維爾的虛構作品進行對比。評論家費爾騰斯坦(Feltenstein)指出,在德拉諾的歷史敘述中,是塞萊諾想用暗藏的短劍刺殺被俘的黑人,被德拉諾憤怒地制止。而在作品中,麥爾維爾卻描寫“如蛇般的”(2321)巴波拿著兩把匕首,來刺殺塞萊諾。費爾騰斯坦認為這最有力地說明了麥爾維爾是將巴波“變成純粹的惡的表征”(韓敏中2005:98)。
上述兩種解讀似乎都難以解釋為什么麥爾維爾會對黑人白人均有種種暴行的描寫。我們認為,上述的兩種解讀并非完全矛盾,實際上還起到了相互映證的作用。麥爾維爾在作品中的確表現了他對“惡”的一貫關注,但黑人并非“惡”的象征。作品顯示,惡并非一成不變,而是人一旦掌握有某種權力便會顯露出來的一種劣根。奴隸主和販奴者原本代表著惡,奴隸們為了反抗這種惡,運用了暴力。在他們獲得船上的控制權后,又不自覺地濫用了這種權力,表現了惡。同時,麥爾維爾也批判了古道心腸、樂善好施的美國船長德拉諾代表的另一種惡,因為他的“天真”,他不僅對自己的“惡”毫無意識,甚至還為自己的天真之惡沾沾自喜,為蓄奴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2人性之惡
反對對《貝》進行政治化解讀的評論家提出的一個重要論點是,在麥爾維爾的創作筆記、書信和日記中,難以找到他對蓄奴制和黑人的評論,僅憑《貝》一部作品就斷定他在批判蓄奴制有武斷之嫌。當然,這意味著,從中也難以找到麥爾維爾在為蓄奴制辯護的證據。因而,要對作品做出客觀判斷,只能從文本入手了。故事發表在美國內戰爆發的四年前,與麥爾維爾同時代的梭羅、惠特曼等作家都對蓄奴制作出了種種評論,生活在新英格蘭的麥爾維爾不可能對那時的廢奴運動毫無耳聞。作品中的一些細節也表明他對蓄奴制并非完全漠然置之。如前文所述,麥爾維爾在創作中對歷史上真實的德拉諾的敘述進行了一些修改。在德拉諾的歷史敘述中,這次奴隸起義發生在1804年12月。而在麥爾維爾的作品中,時間提前到了1799年。麥爾維爾還將塞萊諾的“磨煉”號販奴船改為了“圣多明尼”號。這些改動讓人不由自主地聯想到1799年在圣多明尼島發生的一次有名的奴隸起義。《貝》中時間與船名與該次奴隸起義的直接聯系最有力地說明了麥爾維爾對蓄奴制和黑人暴力反抗的思考。另外,故事最初在《普特納姆月刊》上連載,據評論家凱瑟琳•亞當斯稱,該雜志是一份廢奴主義雜志,麥爾維爾最初設想的讀者群與哈里艾特•比徹爾•斯托(HarrietBee-cherStowe)風靡一時的《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Tom’sCabin)是一致的(Adams2004:373)。這些似乎都說明麥爾維爾創作此故事是旨在批判蓄奴制。
然而,僅憑這一點,就判斷說麥爾維爾就是在批判蓄奴制似乎有些草率。雖然沒有明確文本表明麥爾維爾對蓄奴制的態度,但他本人的經歷可能會影響他的看法。他年輕時,曾在捕鯨船上擔任水手,1841年在南太平洋上的一條捕鯨船上時,因種種原因在馬克薩斯群島的努卡希瓦棄船上岸,不慎進入素有食人生番之名的泰皮人部落。兩周后才設法搭上另一條捕鯨船逃離該島,但又因參與該船水手的叛亂而被捕入獄。翌年,他又在夏威夷的檀香山親眼目睹了號稱文明的白人對當地土著居民的剝削與欺壓。這些經歷讓麥爾維爾深刻感受到被奴役、失去自由的痛苦,或許影響了他對黑人受奴役的狀態表示同情。然而,在此期間,他還目睹了這些“原始”部落種種血腥、殘酷、尚武的儀式和行為,這或許影響了他對包括黑人在內的“野蠻人”的看法。因此,麥爾維爾的親身經歷或許能從一個角度說明《貝》中黑人形象的復雜性:這些值得同情的受奴役者在掌握權力之后,也成為血腥暴力的實施者。困繞麥爾維爾研究者的一個問題是《貝》中哪個人物是道德的代表?麥爾維爾在創作中喜愛運用大量意象和象征,使得讀者難以做出簡單明了的闡釋,《貝》也不例外。讀者很難判定麥爾維爾究竟是在批判奴隸制的不正義,還是在描述一場殘酷、非正義的奴隸起義。一方面,白人對黑人的奴役很難被視為正義、道德的行為,而奴隸們叛亂成功后的殘暴和血腥也似乎難以用正義來描述。這種被很多評論家稱為介于黑與白之間的“灰色”地帶正表明了麥爾維爾對惡的思考。正如很多評論家所注意到的,作品中的意象和色彩耐人尋味(Richards2010)。故事開篇的色彩描寫奠定了全文的基調,“一切都是灰蒙蒙”:鉛色的大海,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水鳥,“到處都是陰影,預示著即將到來的更深的陰影”(2272)。這一灰色似乎寓示著故事的復雜性和惡的復雜性:惡并不是非黑即白。
在作品中所表現的惡里,蓄奴制可能是惡的源頭。蓄奴制使得白人成為主人,黑人淪為奴隸,這就賦予了白人為所欲為的權力和絕對的話語權。在黑人面前,當他們的權力無限大時,白人就會不自覺地顯露出人性深處的惡。大量黑人被抓捕和販賣,滿足了白人對金錢的貪欲;黑奴在販運途中被無故鞭打和折磨,滿足了白人的權力欲和控制欲;黑奴在被制服后殺害,則滿足了白人的報復欲。黑人最初是惡的受害者。由于白人的欲望和惡,許多黑人被迫只身遠離故土,來到異鄉淪為奴隸。他們必須得忍受販運途中惡劣的條件,很多黑奴會在途中悲慘死去,葬身魚腹。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販運途中黑奴叛亂事件頻發。正是白人的惡和殘酷迫使黑奴為了自由奮而反抗。在《貝》中,黑人在控制船只后,巴波要求塞萊諾將他們帶到附近海域的黑人國家,當得知沒有時,又要求塞萊諾將船駛到塞內加爾,希望能回到非洲的家鄉。在叛亂暴露后,德拉諾率領水手攻下叛亂船只,黑人們在沒有領袖、沒有勝利可能之時,仍然“對和平與停戰嗤之以鼻”,拒絕投降。(2324)顯然,這些叛亂的黑人之所以發生叛亂,是因為他們對自由的渴望,希望能回到黑人之家。如果說為了確保叛亂成功而不得已殺人能證明黑人的勇氣和對自由的向往,但在叛亂成功后,黑人顯示的殘暴就難以解釋了。完全控制船只后,黑人顯示了與白人同樣的專制和殘暴。他們用棍棒和斧子殺死了很多沒有表示絲毫反抗的白人,還把一些人綁住扔到海里活活淹死。當塞萊諾懇求巴波不要再濫殺時,他們卻當著他的面,把三個活著的白人綁住扔到船外。后來,巴波決定殺死奴隸主阿蘭達,一是為了“確保他們的自由”,二是“為了給其他水手一個警示,告誡他們如果試圖反對他,將會面臨什么樣的一條路”。盡管塞萊諾不斷哀求,但巴波卻很堅決:“所有西班牙人如果試圖在這件事、或別的任何事上阻撓他,都只有死路一條。”(2328)遍體鱗傷、奄奄一息的阿蘭達被拉到甲板上,巴波卻不讓其他黑人將他扔到海里,而是當著塞萊諾的面將他殘忍殺死。四天后,巴波將阿蘭達的白骨放在船上做船頭雕像,并在下面寫上“追隨你的領袖”的字樣,以警示其他白人船員,如果他們企圖反抗,就會遭受與阿蘭達同樣的命運。巴波不僅顯示了他充滿智慧和勇氣一面,還表現出殘酷、專制的一面,有著強烈的權力欲、控制欲和報復欲。
但在巴波被捕后,白人表現出的殘暴和惡與黑人其實并無不同。在塞萊諾縱身跳到德拉諾的小艇,黑人叛亂暴露,其他黑奴駕駛船只試圖逃跑時,德拉諾仍然命令他的水手前往追趕,并殺害了很多為自由抗爭的黑奴。在巴波被捕處決后,他的尸體被焚燒,首級被懸掛在廣場的柱子上,“泰然自若地面對白人的注視”(2338)。一邊是白人阿蘭達被懸掛的尸骸,直指黑人的殘忍;一邊是黑人巴波被示眾的首級,同樣彰顯著白人的血腥。如果說敘述者德拉諾深刻意識到了黑人將阿蘭達白骨作為船頭雕像時的殘酷,但他卻似乎沒有意識到白人把巴波首級示眾時的血腥。作品中這兩個突出意象之間的張力表明,《貝》既表現了蓄奴制的惡,也表現了人性之惡。
3天真之惡
故事中敘述者美國人德拉諾船長還表現了另一種惡,即天真之惡。在黑人叛亂最終暴露后,盡管塞萊諾堅決反對,德拉諾仍然決意奪取叛亂船只。歷史上真實的德拉諾并非像他自己所標榜的那樣“純粹出于人道動機”(Delano2010),也不像麥爾維爾筆下那樣俠膽義肝,古道熱腸,而是一名精明的商人。歷史上的德拉諾與塞萊諾之間有一些交易。因為塞萊諾的“磨煉”號上有大量金錢和貨物,塞萊諾許諾如果德拉諾幫助他奪回船只,他將會給德拉諾一定的經濟回報。這說明德拉諾幫助奪取叛亂船只的行為并不只是他的熱心和義憤,他同樣有著經濟上的考慮。為了獲取經濟上的最大利益,他甚至不惜犧牲其他人的生命,也要奪回叛亂船只。麥爾維爾作品中的德拉諾天真善良,樂善好施、英勇無畏,沒有表現出對金錢的渴望。韓敏中教授認為,麥爾維爾在作品中“剔除了他們(德拉諾和塞萊諾)身上猥陋的一面”,是為了突出他們天真的特點:“麥爾維爾在創作和修改中不斷降低德拉諾預期得到回報的數字。過濾掉利益權衡后的白人形象表現出一種哲理意義上的單純……根本不懂得何為‘黑暗’。”(韓敏中2005:90)從這個角度上說,德拉諾可以被視為一個“天真的亞當”。在1955年發表的《美國亞當:19世紀的天真、悲劇和傳統》一書中,R.W.B.劉易斯認為19世紀的美國人剛來到新大陸,擺脫了傳統和歷史的束縛,自立自強,樂觀向上,能勇敢地面對一切困難。這一“新的英雄可以說是墮落前的亞當。……他的新體現在他本質上的天真。”(Lewis1955:5)德拉諾充分表現出了美國亞當的這些令人自豪的品質。看到塞萊諾的船只有難,主動伸出了慷慨援助之手。在叛亂被暴露后,他顯示了充分的勇氣、鎮靜和指揮能力,一舉攻下了叛亂船只。
如同美國亞當,德拉諾最突出的特點是他的天真。他的天真使他不相信身邊有大惡。雖然他曾懷疑過塞萊諾可能居心叵測,但這些念頭只是一閃而過,很快就被他拋到腦后。他的這種天真和率直是許多美國人感到自豪的一個特點。然而,也正是這種天真,使他全面低估了黑人的能力和智慧。當他感到塞萊諾行為乖張、遮遮掩掩時,他首先想到的是塞萊諾可能在陰謀奪取他的船:“如果塞萊諾有秘密的話,他可能與黑人合謀嗎?但他們太愚蠢了,而且,誰聽說過哪個白人會背棄自己的種族,而與黑人合謀呢。”對他而言,“白人天生就是更精明的種族。”(2299)他完全沒有將黑人視為平等之人。巴波正是充分認識到了德拉諾的種族優越感,才在他設計導演的大戲中,充分滿足了德拉諾的期待,使他對船上的叛亂毫不知曉。德拉諾的種族優越感使他變得“天真”,不僅不恨黑人,還對他們充滿了同情和好感,根本猜想不到黑人們的陰謀。德拉諾對塞萊諾大贊巴波是一個優秀的奴隸,甚至開玩笑地說要買下他,他卻沒有意識到看似畢恭畢敬、溫順體貼的巴波實則是叛亂的組織者和實施者。德拉諾饒有興致地觀看巴波嫻熟地為塞萊諾理發,感嘆“大多數黑人都天生適合當貼身男仆和理發師”(2307),卻絲毫沒有意識到巴波正在利用剃須的時機,對塞萊諾進行威脅和恐嚇。在德拉諾的眼中,黑人婦女如同“大多數未開化的婦女,她們似乎既有溫柔之心,也有強壯的體魄,準備為孩子們死去,或為他們戰斗。如母豹般單純,如鴿子般可愛”,宛如“在樹林巖石上的樹蔭下歇息的母鹿”(2297),他卻不知這些“單純、可愛”的黑人婦女為了自由,隨時可能拼死奮力抗爭。德拉諾登上“圣多明尼”號后,身材魁梧的黑人阿圖福爾扮演了一個高貴的野蠻人形象,寧愿戴著鐐銬,每兩個小時來見塞萊諾,也不愿低頭認錯。德拉諾不僅沒有看出其中破綻,還責怪塞萊諾對阿圖福爾如此地不諒解是可恥的。麥爾維爾寫道:“實際上,像大多數心地善良、性情樂觀的人一樣,德拉諾船長喜歡黑人不是因其博愛之心,而是因其隨和親切的態度,就像其他人會喜愛紐芬蘭狗那樣。”(2308)顯然,麥爾維爾此處表明德拉諾對黑人屈尊俯就的態度并非特例,他只是大多數“心地善良、性情樂觀的”美國人的代表。
如果說德拉諾對黑人的印象是因為他的天真,那么,以德拉諾為代表的美國人的這種“天真”成為對蓄奴制的最好辯護。在19世紀的美國,白人將黑人常描述為兩種形象,一種是孩子形象,黑人如孩子般天真、無知、任性,因而需要奴隸主(猶如父母和監管者)的指導和約束。一種是野獸形象,黑人如野獸和動物般野蠻、兇殘,因而更需要奴隸主的管教。④無論將黑人視為孩子還是野獸,結論都是相同的,即奴隸制是必須的,甚至也是人道的,因為正是有了奴隸主的管教,黑人們才會壓抑野獸般的沖動和孩子的任性,才會摒棄自身的惡習,成為對社會無害的、甚至有益的一部分,當然,這里顯然指白人社會;正是有了奴隸主的“慷慨”和“仁慈”,黑人才得以有一個棲身之所。在德拉諾對黑人的單純、溫順贊許的同時,是他對蓄奴制的認同。這時,他的天真轉化成了一種惡,實質上為蓄奴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可以說是一種天真之惡。在德拉諾等美國亞當的天真背后,讀者還能看到他們其實并不天真。奴隸主阿蘭達在販運途中,沒有像其他奴隸主那樣給黑奴套上枷鎖和腳鏈,而是允許他們在甲板上自由行走,因為他認為黑奴們“溫順馴良”。(2326)然而,他對黑人的這種“友好”并沒有妨礙他將幾百名黑人從其家鄉抓捕,漂洋過海,販賣到美洲。雖然阿蘭達給予他的奴隸一些自由,但黑人們并沒有感到高興和滿足,甘愿作一個“快樂的奴隸”。而阿蘭達也絕對不會天真到釋放價格不菲的奴隸、給予他們真正自由的地步。他的這種寬容和天真與其說是對黑人的,不如說是為了讓他自己不受良心和道德譴責的一種策略。同樣,正是因為德拉諾并不單純的“天真”,他才在大力褒獎黑人的高貴和溫順之時,對黑人的叛亂進行了無情鎮壓,對白人的權益給予了堅決維護,并將之視為自己的天然職責。此時,他的天真已經以正義和責任的名義,毫無遮掩地轉化成了暴力、殺戮和惡。德拉諾的天真還體現在他不能從“圣多明尼”號的事件中吸取教訓。正如很多評論家所指出,德拉諾是一個扁平人物,自始至終,他都一成不變。在叛亂被平息后,德拉諾試圖勸慰塞萊諾:“過去已過去了,為什么還要對之賦予道德上的意義呢?忘記吧。你看,那邊燦爛的太陽已全部忘了,碧海、藍天,也都忘了。這些都已掀開了新的一頁。”(2337)對德拉諾而言,“圣多明尼”號上的叛亂只是他的一次冒險而已。黑人的命運沒有對他造成任何沖擊,他沒有在事后對這一事件進行再思考,沒有糾正和反省他對黑人的誤解,沒有對自己重新進行審視,也沒有對自我與世界獲得新的認識。更為可嘆的是,無數像他這樣的天真的美國亞當們,一邊因自己的“天真”沾沾自喜,一邊卻完全無視黑人遭受的痛苦。
阿蘭•莫爾•埃米瑞(AllanMooreEmery)將《貝》與美國的天定命運論相聯系。他認為德拉諾對“圣多米尼號”船上的描寫與19世紀50年代美國媒體對古巴的描寫極為相似,即美國是一個“文明進步的種族、強大富有的國家”,西班牙卻“衰敗委靡、正走向末落”,古巴作為西班牙在新大陸的惟一屬國正處于“專制殘暴的統治之下”。當時傳言因其大量的奴隸人口和西班牙人政府的昏庸無能,古巴要解放黑奴,使古巴“非洲化”。因而有人呼吁美國應該介入古巴的“混亂”局面,制止古巴當局解放黑奴,他們認為“兼并古巴會讓熱愛自由的美國人‘維護島上的政治、宗教和商業自由’”。(Emery2010)《貝》中的黑奴叛亂和西班牙人塞萊諾的軟弱無能似乎就是對古巴時政的生動寫照,同時似乎也說明了美國人應當介入古巴事務。⑤因而,《貝》“是一個雙重寓言,將美國蓄奴制被壓制的現實與美國公眾當時不斷高漲的幻想———即美國帝國應該擴張到新世界———并置起來”。(Adams2004:376)評論家埃瑞克•桑德魁斯特(EricSundq-uist)指出,這一并置正好表現了天定命運說中一個“令人痛苦的悖論”(Sundquist2004:626),即它是會促進自由,還是會加深蓄奴制?天定命運論是19世紀中葉為了宣揚美國的擴張而提出的一種說法,即上帝注定美國要在北美大陸上擴張,從大西洋海岸直到太平洋海岸,有時甚至包括加拿大、古巴和中美洲。德拉諾既代表了浪漫的種族主義,也象征了美國新興的帝國主義,他在故事中幫助塞萊諾平息黑奴叛亂的事實說明,所謂的天定命運說不會幫助奴隸們得到自由,而只是會加深蓄奴制。鄧恩•巴卡(DaneBarca)也認為,“《貝》揭示了麥爾維爾就內戰前種族主義審視模式的前景表現出的宿命論態度,和他對這一問題的反帝國主義的思路。”(Barca2010:30)美國擴張到古巴,“對古巴的奴隸們只會意味著主人的更替”,他們仍然得不到渴望的自由。美國人可能對他們表現得彬彬有禮,甚至會對他們的某些才能交口稱贊,但這些黑人卻是“資本主義和基督教的原始資料,是美國人實現帝國夢想的工具”。(Adams2004:376)從這一意義上說,德拉諾的天真只是一個漂亮的幌子。像他這樣“天真”的美國亞當們,雖然表面上對黑人表現出溫情、友好和贊許,實則在繼續維護剝奪黑人自由與人性的蓄奴制。他們舉著“天真”的幌子,繼續為美國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惡”服務。《貝》是麥爾維爾一部非常受歡迎的中篇小說,它在發表后的一個半世紀里引發的各種解讀和爭議說明了作品寓意的豐富性。麥爾維爾既關注哲學意義上的“惡”,也對當時美國的蓄奴制和擴張主義有諸多思考。他不僅揭示了人性之惡,還對白人“仁慈的”種族主義和種族優越感進行了含蓄的批評,表明蓄奴制下美國人的天真和仁慈是一種更有隱蔽性的惡,實則起到了為蓄奴制和美國的天定命運說推波助瀾的作用。
作者:胡亞敏單位:解放軍外國語學院英語系
- 上一篇:受害者的倫理意識范文
- 下一篇:外國文學中的女性成長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