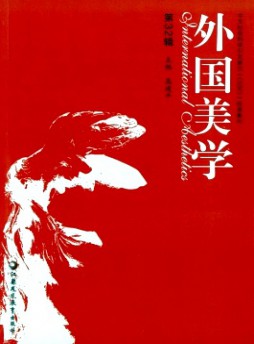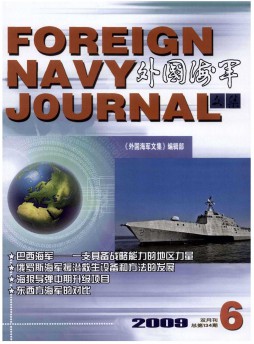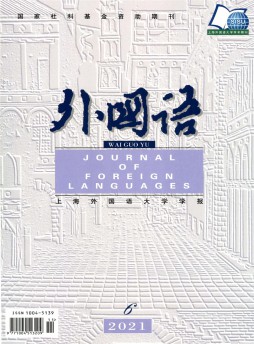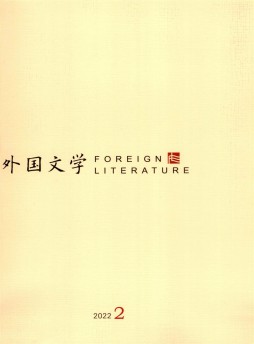外國直接投資的經濟影響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外國直接投資的經濟影響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中國的實際GDP與FDI之間的互動關系
我們用時間序列資料來分析中國的實際GDP與FDI之間的互動關系。我們假定有下列循環式結構:y1t=c1+a1(L)y1,t-1+a2(L)y2t+μ1t(2•1)y2t=c2+b1(L)y1,t-1+b2(L)y2,t-1+μ2t(2•2)式中y1t和y2t分別是對數轉換過的實際GDP和實際FDI;c1和c2是截矩項;L是滯后處理器;Lyt=yt-1;對于i=1,2,ai(L)與bi(L)分別是行為ai(L)=a1+a2L+…+apiLPi和bi(L)=b1+b2L+…+bqiLqi的自回歸處理器;μ1和μ2是白噪音殘差項。滯后次數pi和qi要依實際情況而定。我們之所以假定本期FDI影響本期GDP是因為投資支出顯然是GDP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由于投資的決定一般是基于長期的考慮,所以我們假定FDI受前期GDP的影響①,而不受本期GDP的影響。表1列出了用三階段最小二乘法(GLS)估計得到的結果,其中模型的最終設定是由實際資料決定的。在該模型中,FDI增加了GDP,而GDP的增加也吸引了FDI的流入。就短期彈性而言,FDI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將使GDP年增加0•048個百分點;而GDP年增加一個百分點會使FDI增加2•117個百分點。就直接的長期影響而論,FDI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可使GDP增加0•2959個百分點;GDP增加一個百分點會使FDI增加3•148個百分點。但是,如果考慮到GDP的增長對FDI增加的非直接效果,那么,FDI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最終將使GDP增加5•4479個百分點;同樣,GDP增加一個百分點,10年后也將使FDI增加34•4497個百分點②。比如,中國1999年的GDP為9915億美元,FDI為404億美元,根據上述計算,如果FDI增加4•04億美元,當年可使GDP增加約4•8億美元,最終將使GDP增加498億美元左右。同樣地,如果GDP當年增加99•15億美元,將在第二年使FDI增加約8•6億美元,并在10年后使FDI增加約139•2億美元。有23個發展中國家1976—1997年實際GDP和FDI的的時間序列分析。結果支持了我們對中國資料分析的結論,也就是說,GDP增長促進了FDI的增加,而FDI的增加也促進了GDP的增長。
二、有關FDI的理論以及組織機構和城市化的重要性
FDI的流動由獲利動機所驅使。影響FDI的因素可以分為比較優勢因素和內在化因素。比較優勢因素包括起始地和目的地的特點及優勢等;而內在化因素是指企業能更有效地在本企業內管理其獨有的動產(如技術、知識、營銷技能、商標、品牌和革新能力等),而不必將其租于其他公司。實證研究表明,按照價值最大化原則,跨國公司選擇直接投資地點時,受生產和運輸成本、規模經濟、關稅和需求面如增大市場等因素的影響(Caves,1996;Salvatore,1991)。在這里,除了強調上述因素外,我們還要指出,組織機構的選擇和城市的發展也是吸引FDI的渠道。市場經濟是變化多端的。技術進步使企業的更新換代成為必然。每日每時都會有新企業的誕生,同時也會有舊企業的消亡。公司和個人都要對各種各樣的經濟沖擊做出反應。他們必須重新考慮的不僅僅是做生意的方式,還要考慮如何充分地利用資本和勞動力。我們怎樣才能創造出合適的環境,使革新和有效利用新技術的方法得以發揚,從而產生經濟繁榮呢?組織機構可以發揮轉換作用———幫助資源變成產出———或是分散作用———將資源轉移到非生產者手中(Jordon,2000)。為了使人們能對他們面對的沖擊有最優的反應,從而使每個人的狀況變得更好,組織機構就必須提倡個人在簽訂合同上的自主性。同時,我們相信與我們打交道的機構能實現承諾,他們的行為不會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這一點也很關鍵。經濟交換離不開需要消耗實際資源的信息和交易成本。這些成本影響著貿易的范圍、勞動專業化分工的程度和從商品中獲得的經濟利益。市場經濟要求以可實施的產權、通用的會計準則、完善的金融機構和穩定的貨幣為根基。如果合同,不管是公家的還是私人的,不能夠兌現,市場將受到損害;如果產權不確定,銀行業就不能正常運行;如果財務報告不可信,投資機會就會模糊不清。
為了建立一個可以推動投資和繁榮的經濟基礎,明晰的國家法律、公正廣泛的法律實施、有效的官僚體制以及杜絕腐敗等,都是政府應納入其組織機構的必要構件。否則,資源會被浪費在高成本的信息收集上,或是浪費在生產和消費錯誤的產品上。盡管政府可以為良好的環境奠定基礎,增長卻是由資本(包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存量的擴張來驅動的。但是,資本是流動的,如果一個地區有獲利的地理優勢,高質量FDI就會迅速流進。城市,以其營銷、運輸系統和信息傳播方式,通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外部效應的范圍等,為FDI提供了較好的地利條件,在吸引FDI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過去人們認為的城市先由農村發展成小城鎮,進而發展成城市的序列,只能用來解釋早期城市的形成。如今,城市本身就是重要的文化和經濟機構(Jacobs,1984)。新的商品,新的服務,首先是在城市里產生的。如果不結合城市里的商品和服務,或者不采用來自城市的化肥、機械、電力、冷凍裝置、關于改良動植物的研究成果等,農業就不會豐產。農業隨著城市的成長而興起。最農業化的國家往往農業最不發達。另一方面,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其農產品也最豐富。以日本為例,19世紀末,日本的城市開始工業化和商業化增長,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已經是高度城市化的國家。在此期間,盡管日本的農民勤勞節儉,但是,農民和城市居民的糧食并不寬裕。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農村開始接受大量來自城市的商品和服務,雖然日本人口比戰前增加了25%,日本的農場還是能夠生產出足夠全體日本居民食用的大米。從經濟角度看,城市就像原子核。這不僅僅是因為人們喜歡住在離商店近的地方,因而商店必須座落在離顧客近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城市提供了“群體相互作用”的可能性,而這對個人生產率的提高是至關重要的(Lucas,1988)。我們大部分的知識都是從別人那里學來的。Jacobs(1969)記載的許多事例說明了經濟生活中的“創造性”與“藝術”和“科學”的異曲同工———為了學習和交流思想,我們需要和他人打交道。這就是為什么紐約會有成衣區、金融區、鉆石區、廣告區等,或者為什么高科技公司要集中在硅谷的原因。上述每一個案例中都有一群人干著大致相同的事,他們相互學習,啟發別人又被別人啟發,同時又保留自己的創見和獨特性。單從城市外的土地遠比市內便宜,但資本和人力并沒有搬出城市以降低運作成本的事實,就證明城市所產生的信息和知識優勢遠遠超過因城市外便宜的土地所帶來的短期利潤。
三、決定FDI因素的板塊資料分析
我們現在用23個發展中國家1976—1997年的板塊資料實證地分析影響FDI的因素。盡管很多因素被認為是很重要的,但我們分析依據的是更易于反映地點和比較優勢因素的數量資料,而不是企業特定的因素如技術、知識、營銷技能、商標和品牌等。表3有數據來源的詳細描述。舍去在解釋FDI—GDP比例時yit(對國家i,時間t)變動中統計上不顯著的變量后。1•X1it:經濟增長率,作為比較在不同國家投資回報率的代表性變量。一般認為,當經濟增長加速時,實際的經風險調整后的資本回報率應增加,所以凈FDI會增加。2•X2it:用來衡量開放程度的指數。范圍由0(限制高)到10(限制低或沒有限制)。3•X3it:用來衡量腐敗程度的指數。范圍由0(最腐敗)到10(最不腐敗)。X2it和X3it可被視為衡量政府機構實現承諾的程度和可信度的代用量。我們預期它們對FDI—GDP比例的影響是正向的。4•X4it:公司稅,它是衡量在一國做生意成本的代用量。我們預計其對FDI—GDP的比例有負面效果。運用一般最小二乘法,我們得到:Yit=1•4646+0•2909Yi,t-1+0•0322X1it(1•2143)(4•6716)(1•713)+0•13495X2it+0•319X3it-0•062X4it(3•445)(1•714)(4•282)+αt+uit其中,括號里的數字為t值,αi表示國家i的特定因素,uit為殘差。我們假定國家i的特定因素和殘差與解釋變量不相關。結果表明,我們前述的結論得到了支持。首先,經濟增長率對FDI—GDP的比例有正面、顯著的影響;其次,機構因素的影響也是正面的和顯著的,這揭示了政府機構行為的可預測性、可信賴程度以及實現承諾程度的重要性;第三、高公司稅不利于吸引FDI。
四、影響FDI在中國分布的因素
我們考慮下列因素對于FDI在中國的分布有較大的影響。
1•城市的發展和基礎設施的建設。根據Jacobs(1984)的觀點,城市在經濟生活中是以主要的發展者和推進者的身份出現的。城市工程和城市間的貿易激活了農村的生產和貿易。隨著貿易的擴張,城市帶動更多的鄉鎮(主要處于物產區和供給區)加入經濟生活,并使它們進入多變的城市貿易網絡中。所以,我們用各地區城鎮人均居民年收入(Urit)和城市燈盞數量(Cit,以1000為單位)為代表來反映城市發展的動態。城市燈盞數量是一個表現一省或一市的基本建設投資水平的變量,它影響著一個地區的生產和運輸成本。所以我們認為,上述兩個因素對吸引FDI有正面作用。
2•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提高了物質資本和勞動力的生產率。人力資本的積累既有內部效應(個人人力資本對他本人生產率的影響),也有外部效應(通過提高勞動技能或人力資本的平均水平,對提高所有生產要素的生產率所作出的貢獻),對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高公共支出是東亞異乎尋常表現的主要公共政策因素(Lucas,1988)。我們用文盲率(Lit)來大致反映一個省或直轄市人力資本的積累。我們預期高文盲率不利于吸引FDI。
3•進入市場的容易程度。決定FDI地點的一個主要因素是進入市場的容易程度。中國西部地區屬內陸型經濟。雖然沿海地區土地和其他成本可能會增加,但內陸落后的基礎建設、交通和通訊等可能使西部的生產成本高于沿海地區,因為,產品成本=生產成本+運輸成本。內陸的高運輸成本會使產品成本明顯高于沿海地區。我們用一個地區的啞變量(Dit)來近似地表示距離市場的遠近程度。如果一個省或市在中國東部或中部,我們就讓Dit=1,在西部地區則為0。我們預期啞變量對FDI有正面影響。
4•存貨增加。存貨增加可被視為現有的行業和服務已經過時,它是行業和企業的創造力受到限制的標志。這些變動使得原來發展、擴張的經濟走向一成不變和落后。在這里,該變量(Init,每年用億元人民幣衡量的存貨數量)反映的是Jacobs(1984)所謂的“下降的交易”(TransactionofDe-cline);或者是城市的不景氣。運用中國1996—1998年各省市的資料,我們以上述要素為解釋變量對FDI—GDP的比例作回歸分析,結果為:Yit=16•6+1•21Dit-3•46Lit+1•96Urit(-5•41)(4•94)(-1•96)(5•16)-0•35Init+0•47Cit+uit(-2•67)(2•41)t=1,2,3;i=1,2,3,……31。其中括號里的數字為t值。所有變量都顯著,符號也都符合預期。這些結果支持了我們前述的論點,即城市的發展和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進入市場的容易程度是跨國公司選擇投資地點決策的主要因素。事實上,上述靜態模型僅用了5個變量就可以解釋中國31個省、直轄市的FDI在1996—1998年超過65%的變動情況(R平方為0•6787),而這一結果是引人注目的。
五、結論
本文我們對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作了統計分析,我們也分析了影響FDI流動的因素。我們發現,FDI和GDP之間存在著互動關系。一般而言,FDI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會使GDP在當年增加0•0485個百分點,但從長期看,最終將導致GDP增長5•4479個百分點。相應的,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會使FDI短期增加2•117個百分點,10年后將使FDI增長34•4497個百分點。利用23個發展中國家1976—1997年的板塊資料進行分析,結果表明,經濟增長、低公司稅、政府機構行為的可預測性和可信賴程度以及承諾兌現程度是吸引FDI的主要因素。根據中國1996—1998年資料對FDI分布的分析進一步說明了人力資本積累和城市發展對吸引外資的重要性。然而,作為經濟生活的發展者和推進者,城市需要兩種形式能量的源源不斷地輸入:創新(說到底是人們創新發展力的輸入)和對輸入物的充分替代,就本質而言,這體現著人力漸進模仿能力的輸入。城市的用途在于能提供這樣的環境,讓輸入———創新力和適應性變化———成功地注入每天的經濟生活(Ja-cobs,1984)。步調一致和千篇一律不能生成和發展經濟上有活力的城市。要讓人們的創造性得以發揮,就必須允許現狀被改變、被打亂。必須讓一些由來已久的活動被更新換代,并降低其他一些慣性活動的相對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