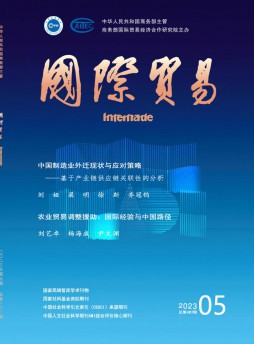國際貿易便利化研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國際貿易便利化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上世紀下半葉,在貿易自由化與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貿易便利化進入主要發達國家的視野,同時貿易便利化也符合一些工業新興國家的利益。這些國家代表著本國貿易商、生產商的利益,高擎著貿易便利化的大旗,以一個個“現代化”的名詞與理念,不斷突破他國貿易門檻。在發達國家的話語權主導下,貿易便利化的關注國際主體與主題范圍不斷擴大。目前,貿易便利化的問題已經并不僅僅局限于WTO或WCO的范疇內,而是在全球的每一個角落全面鋪開,并表現出如下10項新特征:
一、貿易便利化規則制定主體分散化
目前,貿易便利化規則的制定主體分散化具體表現是“一極與多元并存”。至2010年3月,WTO貿易便利化談判組雖已形成整合的貿易便利化談判文本草案的修訂版。[1]多哈回合貿易便利化談判進展與其他議題相較也是最為讓人滿意。[2]但其最終成果如何,還需看拉米2010年5月4日所提出的雞尾酒療法(cocktailapproach)[3]的實際效果。
世界對WTO貿易便利化規則最終出爐的等待是漫長的,但對貿易便利化真實需求卻是迫切的。因此,世界各相關組織、區域等都開始急迫并積極地參與到貿易便利化規則的制定進程中,制定主體開始擴展,其表現為:從“全球—區域—雙邊”的不斷深入到地區層面。方向之一。這主要體現于關稅同盟及多邊自由貿易區的協定中。如歐共體《海關行動綱要》(customs2013)①及《海關方案》[4]中都十分關注貿易便利化;APEC也已在貿易便利化領域取得了較大的成就。在多邊自貿協定方面,如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CAFTA-DR),②東盟自由貿易區(ASEANFreeTradeArea,“AFTA”)③等的目標之一就是貿易便利化以及和諧的貿易規則與標準。
第二,在雙邊貿易協定中也日漸重視貿易便利化問題。由于對WTO談判前景的悲觀預測,各國從上世紀末開始紛紛尋求貿易便利化的雙邊解決途徑。截至2010年上半年,通知WTO的雙邊貨物自由貿易協議共有一百四十多個。[5]這些協議中一般都列有“Customsadministration”或/和“tradefacilitation”的章節。以APEC的成員之間的雙邊協議為例,由APECSOM(SeniorOfficial’smeeting)Chair所提交的一份報告④顯示,至2008年11月,成員間28項雙邊自由貿易協議中24項協議中包含海關程序與貿易便利化。⑤一般包括海關法律法規政策的透明度,通關便利化,快速放行,預裁定制度,轉運與暫準進出口等。這些規則對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成員方國內法有著直接的、明顯的約束力。
二、貿易便利化發展的專業化
貿易便利化規則在專業性國際組織的參與下,日漸從“綜合性”向“專業性”發展。眾多的專業性國際組織都開始從各自的角度關注貿易便利化的不同方面。如國際海運組織關注與海運、集裝箱等的海運供應鏈關鍵因素的安全;萬國郵政聯盟更注重于快件的通關;國際民航組織與WCO之間合作更關注航空運輸與旅客通關的便利。因此,產生了眾多專業貿易便利化規則與工具。
三、國際組織對貿易便利化建設的合作與分工不斷深化
由于各國際組織關注貿易便利化的角度與深度不同,很多組織之間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關系。
第一,國際組織間在貿易便利化建設方面的合作不斷深化。最主要的組織合作是WCO與其他組織之間的合作。WCO將與WTO的關系定位于:一致諧調互補。WTO重于較高原則,WCO通過制定標準和工具為WTO規則的具體實施提供技術支持。WCO與聯合國歐洲委員會也以簽訂諒解備忘錄的形式,將兩者的合作形式與內容進行了約定。[7]
第二,區域性組織和/或專業組織相互間的合作不可忽視。其成果表現有多種形式。如: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機制(GMS)中最重要的貿易便利化倡議是《便利客貨跨境運輸協定》(CBTA),這就是亞洲開發銀行(ADB)的一項技術援助項目成果(1996年);[8]亞太經社會與GMS之間的合作與援助;以及更緊密經濟關系的太平洋協議(thePacificAgreementonCloserEconomicRelations,PACER)所資助的theRegionalTradeFacilitationProgramme(RTFP)等。
第三,國際組織參與貿易便利化建設的分工層次化。國際組織參與貿易便利化建設的分工分為3個層次:第一層次是WTO、WCO進行貿易便利化基本規則的制定;第二層次是以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UNECE)為代表的專業性國際組織對貿易便利化基礎規則的細化,而產生的技術性規范、指南、工具類的貿易便利化文件;第三層次是有全球性區域性開發組織與金融組織,為貿易便利化建設綜合能力的提高提供項目、政策研究與資金、技術援助。例如世界銀行注重于海關現代化、貿易便利化的技術援助問題。IMF也向成員國開展提供相應的支持。不同于世界銀行開展的全面改革項目,其所開展的項目專注于貿易便利化的具體領域,如打擊商業瞞騙,提高稅收能力,實施風險管理等。
四、貿易便利化進程的巴爾干化⑦
第一,不同關境區/國家的貿易便利化進程巴爾干化。貿易便利化規則的區域化與雙邊化,[9]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所持貿易便利化主張的差異化,使得國際貿易便利化進程日漸巴爾干化(進程碎片化,參差不齊)。例如北美洲地區的國家,由于美國與NAFTA的影響,其對于貿易安全的傾向十分明顯,這是一種與貿易便利化的發展產生明顯制約作用的逆向原則。歐洲(特別是西歐),大洋洲等地區的國家比較注重貿易安全與便利的平衡。亞洲、非洲地區的國家比較在意貿易的便利。全球的貿易便利化觀點差異明顯,貿易便利化進程處于發展不均勻的狀態。
第二,區域性/雙邊自由貿易區內貿易便利化進程的巴爾干化。自20世紀初至2010年初,在計入WTO統計的自由貿易協定共462個,其中271個協議現行有效。[10]這些自由貿易協定所形成的雙邊或多邊自由貿易區的便利化進程大不相同。甚至在成員基本相同的自由區內,便利化程度也是不同的。例如:從多邊視角看,ASEAN設定在2020年建立一個有效、協調、專業的通關程序,共包括15個方面的海關程序的便利化,這是一個長期但標準較高的便利化發展進程。中國—東盟自貿區則沒有建立具體的海關程序便利化方面的要求。從雙邊視角看,以新加坡為例,新加坡—新西蘭協議中注重風險管理為基礎的通關便利化;新加坡—澳大利亞協議則同意遵守現有的WTO貿易便利化規則,并主要著重于電子通關與違反海關行為的信息合作與協助調查;新加坡—美國協議的便利化標準較高,是以NAFTA為基礎的,并十分注重貿易安全。[11]
第三,國際組織間貿易便利化主張的巴爾干化。不同的區域經濟組織由于地緣經濟特點,必然有不同的貿易主張。同時,由于有不同的專業性組織對貿易便利化各自提出了具有明顯專業性特點的要求與主張,這些具體主張與規則之間有時也是不能兼得的。例如,代表商界的國際商會(ICC)在其2003年海關能力建設的聲明[12]中明確提出從保護商業利益的角度支持海關為了貿易便利化的目標進行能力建設(ICCsupportforcapacitybuildingintradefacilitation)以及在海關指南《ICCcustomsguidelines》(2003)中所采取立場與措辭中都可以看出其明顯的貿易便利化主張,這一立場在經過9·11之后,身處金融危機的2009年仍然沒有改變。⑧與代表政府的組織所提出的安全主張有時是沖突的。
五、國際貿易便利化規則的境內化⑨
出于多邊或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約束,也為了提升本國的貿易競爭力,各單獨/統一關境區開始通過制定關境內的法律與規則整合對外貿易資源。一幅以貿易便利化為直接目標的涉外貿易制度改革的宏大畫卷因此在全球展開,具體包括單一窗口改革,邊境整合,AEO(authorizedeconomicoperator)制度⑩的產生,通關程序簡化等。
第一,區域性單獨關境區的貿易便利化立法。2008年4月23日歐共體制定了《現代化海關法典》(是對《歐共體海關法典》的現代化)。該法典訂明適用于進出共同體關稅地區貨物的一般規則和程序,旨在簡化海關程序,以及為電子報關和有關審理程序提供法律框架。該法典規定了分階段生效的方式。待有關該法典的實施細則獲得通過后,構成現代化海關法典框架的主要條文將于2013年6月24日前分階段生效。
該法典對《歐共體海關法典》的重大改變涉及以下方面:(1)電子報關和審理:貿易經營者和海關當局之間所有數據、附帶文件、決議和通知的往來,均須利用電子資料處理技術進行。只有在附加措施內明確指定的若干情況下(例如海關當局或貿易經營者的電腦系統暫時出現故障),才可采用紙張的方式處理。(2)集中通關:不論有關貨物經由哪個成員國進出歐盟關稅地區,或在哪個成員國內使用,認可商號將可在其業務登記注冊的地方,以電子方式為貨物報關和繳付關稅。當地的海關辦事處須就該項申報進行核實手續,以及征收關稅。(3)AEO制度,包括:可享受簡化通關的經授權經營者與可享受海關安全控制下的便利措施的經授權經營者,及兩者的結合。
第二,國別性單獨關境區的貿易便利化立法。日本海關AEO制度自2001年開始,至2009年7月1日,其對象擴大到進口商、出口商、報關企業、物流營運商、生產商、特定的保稅經營人等。[13]
至此,日本已經構建起全面涉及供應鏈各環節的日本版AEO制度。我國自1998年開始建立現代海關制度,特別是2004~2010年現代海關制度第二步發展戰略規劃以來,進行的一系列通關便利化改革(包括:集中申報,分類通關,提前報關、實貨放行的簡化通關措施,大通關工程等)。
六、貿易便利化規則主旨差異化
當前世界上對貿易便利與安全的取舍或兼顧存在著多種選擇:
第一類取舍是完全著重于貿易安全。這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國家,以及美國能夠主導話語權的國際組織的做法。這些國家或組織自9·11事件之后,幾乎是對一貫倡導的貿易便利化進程來了一個急剎車。此后多年來對貿易安全問題的關注與憂慮有增無減。其憑借著本身強大的經濟與政治實力的影響,實施“擴張性”的貿易安全措施。在措施的對象上,不僅包括本國的公司,還包括其他國家的公司,例如,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制造商就是C-TPAT中商界的成員。在措施實施的方式上,它一定程度地介入了外國政府執法的過程。措施實施的范圍上,它遠遠超出了本國領土范圍。在措施的效果上,它已經影響到處于外國主權管轄范圍之內的公司。此類國家或組織考慮安全與便利的平衡時,在法律上基本上考慮的都是貿易安全性的立法,對貿易便利問題完全是在采用先進的信息技術與管理技術的層面上操作的。
第二類取舍是從法律與技術上都注重貿易安全與便利的平衡。這是以歐盟等次于美國發展程度的國家或區域所采用的。這是因為他們一方面需要充分重視國家與貿易的安全,另一面出于與美國、其他發達國家以及工業新興國家競爭的需要,他們也必須保證本國進出口貿易環境具有充分的競爭力與吸引力。因此這些國家一方面以立法、技術規則等保證本國的貿易安全,一方面也通過立法整合邊境管理機關,調整邊境管理結構,將邊境管理環境現代化,并借助先進的信息技術,和先進的海關能力來實現安全與貿易的平衡。
第三類取舍是更注重貿易便利化的發展。采取該主張的國家主要有兩種。一種,主要是出口型國家所特別主張的做法。這些國家出于外貿依存度、經濟發展模式等方面的原因,其他的國家的貿易安全規則無疑是一種貿易壁壘,極大地增加了其貿易成本與產品競爭力。但由于其本身在國際上的話語權與影響力有限,不能影響國際上的貿易安全規則的形成,卻深受貿易安全規則的負面影響;同時又不能保證或彰示自身邊境環境的便利化與管理的科學性。因此,這一種國家或以此類國家為主的組織,從內外雙重考慮都十分重視貿易便利化的發展。另一種,主要是在國際經濟中被邊緣化的國家,出于多種原因,如接受了援助,比較基于創造有吸引力的環境,融入國際社會等,更愿意采用貿易便利化的規則。
七、貿易便利化規則的自身異化
貿易便利化規則在自身進展的同時,或可發展到自身的反面——貿易壁壘。典型體現之一就是AEO制度。該制度設定的初衷是為了在保證貿易安全的基礎上,給予經營者以實質性的貿易便利。但在該制度的發展過程中,卻出現了異化的趨勢:
第一,AEO制度實質上是一種設定嚴格條件的便利化待遇。其本身就意味著企業必須跨越高門檻后才能享有便利化,該制度將貿易鏈中各環節的貿易商都分為一般經營者和經認證/授權的經營者。對于經過認證的經營者(符合AEO制度所設定的嚴格條件的經營者),是海關可信任的伙伴,從而享有減少通關成本與費用的優惠簡化通關程序的待遇。所以這種貿易便利化待遇不是一種普適待遇,是一種有條件的便利化待遇。一般經營者只能通過個案的申請,而個案享有。AEO制度因此成為執行國內貿易政策的工具,也成為一種新型的貿易壁壘。WCO中AEO的原則被國內法化以后,各國海關立法對AEO申請人的身份、行業、條件等設定相當高的準入門檻和高標準的安全性守法性義務。有些單獨關境區將ISO/PAS-28001或其他相關的認證標準整合進入獲得AEO認證的標準,意味著更高的安全標準。
第二,各國間AEO制度的差異與認證構成國家間的貿易壁壘。各國間AEO的分類與標準存在著較大的區別,這種差別本身就造成了國家間貿易的障礙。為了消除這種障礙,發達國家間開始尋求AEO相互認證協議(MutualRecognitionArrangements)(例如日本已經與美國、新西蘭簽訂AEO認證協議;韓國已經與美國、日本、歐盟、新加坡、新西蘭簽訂了AEO認證協議[14]),在一些認證雙邊/多邊條約簽署之后,如果沒有進入該協議群的國家的外貿經營者也會面臨著貿易便利化的壁壘。
八、貿易便利化外延的擴張化
對于貿易便利化的狹義理解限于有形貨物跨境流動的便利化。如WTO在2001年多哈舉行的WTO第四屆部長級會議決定,授權WTO貨物貿易理事會“審議并適當澄清和完善GATT1994第5、8、10條的相關內容。當前其貿易便利化談判的最新文本草案所關注的仍然集中在有形貨物貿易的海關和跨境制度上。OECD在2001年對貿易便利化的表述是:國際貨物從賣方流動到買方并向另一方支付所需要的程序及相關信息流動的簡化和標準化。[15]這仍然是貨物貿易跨境流動手續便利化的觀點。
但隨著貿易便利化規則的發展,一些組織與國家對貿易便利化的理解逐漸向著廣義的商務便利化發展,其中可以包括:單一窗口的建立,電子商務的便利化,商務人員流動的便利化,服務貿易便利化,投資便利化,公共管理整體環境便利化,外匯制度便利化,進出境整體規則流程化等。如APEC在完成其第一個貿易便利化行動計劃(APEC’sfirstTradeFacilitationActionPlan)后,在第二個貿易便利化行動計劃中開始尋求更廣泛的商業便利化(包括商務流動,電子商務便利化等)。[16]
九、貿易便利化規則表現形式的技術化、軟法化
第一,從國際層面上看的軟法化。由于不同參與主體對國際貿易利益、主張的加大差異,貿易便利化規則除了一些基本的國際條約,如修訂的《京都公約》等外,大多數都是以指南、建議、參考、計劃、項目等等命名的。這些規則對成員都是沒有約束力的,由各成員作為自主選擇適用。軟法的價值在于“進退自如”,[17]即便不遵守也不會造成法律上的負面效果。在國家利益與國際規則產生沖突時的一種妥協。但是由于軟法可以產生“震懾”的效力,甚至可以產生實際效果。這是國際規則硬化的路徑之一。因此,部分貿易便利化規則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如WCO《貿易安全與便利標準框架》存在廣泛的影響力,至2010年5月有161個成員承諾實施,[18]并得到了WCO能力建設的組織保證。
第二,從國內層間上看的技術化。目前,各國都在進行各自的貿易便利化或貿易安全化的海關制度改革,這些改革往往涉及到時間、國別、路線、運輸工具或容器、港口、貨物等技術的指標與參數,往往需要運用技術的方式或信息技術的手段進行傳輸和分析,這些方式都還處于試行或實驗的階段,還經常要借助信息系統的運用。因此這些系統、流程、參數、手段、工具的運用都處于不甚穩定的狀態,也并不成熟,甚至是不成功的。因此,各國的貿易便利化規則在其國內高層級的立法中多數只能找到只言片語的原則。多數分布在較低層級的規則、裁定、條例中,甚至沒有法律支撐。因此表現出貿易便利化規則的低層級化、技術化。
十、貿易便利化帶動公共管理現代化
國際社會在注重便利化的制度建設的同時開始關注執法機構的能力建設,使得制度建設的益處真正得以實現。
第一,貿易便利化能力建設的初期階段主要在各國海關系統中展開。WCO從2006年開始在全球推行海關能力建設的“哥倫比亞計劃”(ColumbusProgram),幾乎絕大多數的WCO的發展中成員方的海關都卷入了不同階段的貿易便利化能力建設中。目前,除了7個成員處于診斷前階段外,38個單獨關境區是第一階段的受益成員,包括中國在內的60多個成員成為第二階段的受益成員。[19]
第二,貿易便利化能力建設進程逐漸推廣至外貿環節的各個公共機構。由于貿易便利化對整體貿易環境的要求,貿易便利化已從關注海關機構,向著全面公共管理便利化發展。其中,外匯兌換、簽證管理、檢驗建議、稅收管理、港口管理等問題如果不加以改進,僅通關便利是無法實現貿易便利化的,因此對國家外貿的整體公共管理能力提升與便利化水平的改革也提上了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