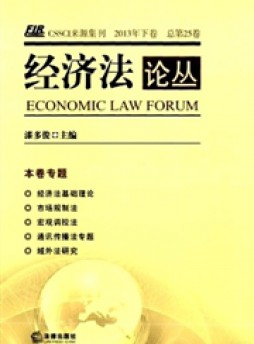經(jīng)濟(jì)法功能研究進(jìn)展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經(jīng)濟(jì)法功能研究進(jìn)展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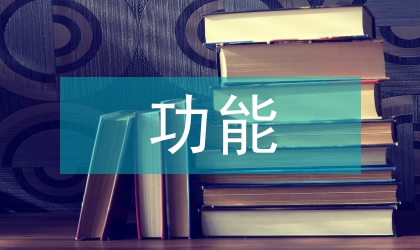
社會制度欲實現(xiàn)內(nèi)蘊的價值和特定的目的都有其預(yù)設(shè)的功能,法律作為社會制度的重要一環(huán)也概莫能外。法律的基本功能只是法律共性的表征之一,而作為龐大法律體系下的各部門法,其個性的彰顯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其具體功能的實施。部門法功能的差異充分反映和體現(xiàn)了各部門法本質(zhì)的區(qū)別和內(nèi)涵的迥異,因此決定了法功能的理論在法律理論體系中的不可或缺性及對認(rèn)識法的本質(zhì)的重要性。經(jīng)濟(jì)法作為需要國家干預(yù)經(jīng)濟(jì)的基本法律制度,研究其功能的構(gòu)成、與其他部門法功能的互補與互動等一系列相關(guān)問題,無論是對經(jīng)濟(jì)法理論研究的深入還是對現(xiàn)實中國家立法部門制定相關(guān)經(jīng)濟(jì)干預(yù)與調(diào)整的法律法規(guī)都大有裨益。
然而與學(xué)者們研究經(jīng)濟(jì)法的價值、原則、理念和本位等表現(xiàn)的熱火朝天相比,對經(jīng)濟(jì)法功能的研究似乎關(guān)注不夠,離闡述經(jīng)濟(jì)法基礎(chǔ)理論中其他術(shù)語與概念出現(xiàn)的著作汗牛充棟的景象也相去甚遠(yuǎn)。由此對經(jīng)濟(jì)法功能的研究似乎成為經(jīng)濟(jì)法基礎(chǔ)理論研究中一塊寂寥的領(lǐng)域。①雖然學(xué)術(shù)成果數(shù)量的多寡與成就的高低不一定存在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與實踐可操作性和指導(dǎo)性也未必協(xié)調(diào)發(fā)展,但畢竟對于經(jīng)濟(jì)法功能這種重要的基礎(chǔ)概念缺乏充分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經(jīng)濟(jì)法基礎(chǔ)理論研究中的某些薄弱之處。所以筆者擬通過此文以期拋磚引玉,促使諸位學(xué)者對經(jīng)濟(jì)法功能的研究產(chǎn)生更大的興趣和投入更多的精力。本文結(jié)構(gòu)安排如下:首先探尋法律功能的內(nèi)涵,然后在對學(xué)界有關(guān)經(jīng)濟(jì)法功能的諸多觀點進(jìn)行全方位的梳理的基礎(chǔ)上評析經(jīng)濟(jì)法功能研究現(xiàn)狀的特點,最后指出筆者所認(rèn)為的經(jīng)濟(jì)法功能研究應(yīng)注意的立足點或切入點。
一、對法律功能研究現(xiàn)狀的預(yù)先考察
在對經(jīng)濟(jì)法功能研究現(xiàn)狀進(jìn)行梳理之前,筆者想占用一些篇幅對學(xué)界(主要是法理學(xué)的學(xué)者)關(guān)于法律功能的研究狀況給予關(guān)注,這主要是緣于深入了解經(jīng)濟(jì)法的功能將不可避免地涉及對法律功能的探尋。①法的功能中的“功能”之詞意源于社會學(xué)中“功能”之意,這不僅表現(xiàn)在對法的功能的研究,是法社會學(xué)或社會法學(xué)派關(guān)注的主要論題及根本方法,而且當(dāng)代西方著名的功能學(xué)派的社會學(xué)家中大多亦論及到法的功能。[1](P25)社會學(xué)的學(xué)者往往從系統(tǒng)論和結(jié)構(gòu)主義的視角出發(fā),認(rèn)為對功能的理解應(yīng)當(dāng)從系統(tǒng)與構(gòu)成要素或整體與部分的關(guān)系中來理解,并強調(diào)部分對整體產(chǎn)生的后果。
目前現(xiàn)代西方法學(xué)家對法律的功能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幾種代表性觀點:一是龐德提出的法的社會控制功能;[2](P31)二是拉茲提出的法律的規(guī)范功能和社會功能;[3](P101)三是StevenVago認(rèn)為法律的功能為社會控制、沖突解決和社會工程;[4](P176)五是魏德士提出的法的八個功能:創(chuàng)建和調(diào)整功能、形式上的調(diào)整功能、保持功能(物質(zhì)的調(diào)整功能)、賦予功能和法律保障功能、裁判糾紛的功能、滿足功能、融合功能、創(chuàng)造與教育功能。[5](P38—43)我國的一些學(xué)者也從自己的角度闡釋了法律功能的意蘊。付子堂認(rèn)為:“法律功能是指法律作為體系或部分,在一定的立法目的指引下,基于其內(nèi)在結(jié)構(gòu)而與社會單位所發(fā)生的,能夠通過自己的活動(運行)造成一定客觀后果,從而體現(xiàn)自身在社會中的實際特殊地位的關(guān)系,其體現(xiàn)一種法———社會關(guān)系。”具體來說,法律的功能包括:規(guī)范功能(指引、評價、預(yù)測、教育、強制等功能)和社會功能(法律的社會導(dǎo)向功能、法律的社會整合功能和法律的文化傳遞功能)、顯性功能(法律的客觀后果合乎立法者的本來意圖,或者說是由立法者有意安排出來的)與隱性功能(法律對社會的影響后果是看不見的或是在立法者無意中所產(chǎn)生的)、正反功能與非功能。[6](P234—251)張文顯認(rèn)為,法的作用指法對人的行為以及最終對社會關(guān)系和社會生活所產(chǎn)生的影響。法的作用常見分類有:一般作用與具體作用、整體作用與局部作用、預(yù)期作用與實際作用、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直接作用和間接作用、規(guī)范作用和社會作用。[7](P126—137)
二、對經(jīng)濟(jì)法功能研究現(xiàn)狀的文獻(xiàn)梳理
從對于經(jīng)濟(jì)法具體功能的研究的現(xiàn)有文獻(xiàn)來看,研究的角度和路徑各有不同,闡釋時的背景和語境差別較大,得出的結(jié)論也形形色色,但是通過歸納性的思考,筆者將這些紛繁復(fù)雜的研究成果初步分為以下幾類并簡要地進(jìn)行了總結(jié)。
(一)從經(jīng)濟(jì)法應(yīng)實現(xiàn)的特有價值取向和在特定政治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時期的背景中對其功能進(jìn)行研究
1.依照經(jīng)濟(jì)法的特有價值取向和法益目標(biāo)研究經(jīng)濟(jì)法功能。岳彩申和袁林從法與利益的關(guān)系出發(fā),提出經(jīng)濟(jì)法有兩種最基本的功能即分配利益的功能與維護(hù)利益的功能。經(jīng)濟(jì)法利益分配的核心在于對集團(tuán)利益的分配,利益分配的對象是集團(tuán)利益而不是社會公共利益與個體利益。如果說經(jīng)濟(jì)法利益分配的傳統(tǒng)目標(biāo)是公平與效率的話,那么平衡正是經(jīng)濟(jì)利益分配的新價值目標(biāo)。[8](P85—89)范海玉也同樣認(rèn)為,經(jīng)濟(jì)法的利益分配功能主要是通過對介于傳統(tǒng)利益和社會利益之間的集團(tuán)利益的分配來實現(xiàn)的。這種分配是以影響經(jīng)濟(jì)的宏觀運行為目的,而不是具體分配個體間的利益。政府作為強制性分配主體具有干預(yù)的有限理性、干預(yù)成本高昂和自身的利益追求和偏好的能力局限。[9](P54-59)陳恭建和蔣進(jìn)認(rèn)為,經(jīng)濟(jì)法的功能是經(jīng)濟(jì)法對社會經(jīng)濟(jì)生活的機(jī)制效能,由經(jīng)濟(jì)法的本質(zhì)決定。經(jīng)濟(jì)法首先具有平衡協(xié)調(diào)社會整體利益與社會個體利益的平衡協(xié)調(diào)功能,其次具有綜合系統(tǒng)調(diào)整功能,即以全局觀念對社會經(jīng)濟(jì)生活進(jìn)行調(diào)整,并實現(xiàn)“微觀規(guī)制”與“宏觀調(diào)控”兩種手段的有機(jī)結(jié)合。[10](P31-36)李劍提出經(jīng)濟(jì)法追求起點公平的作用主要體現(xiàn)在確認(rèn)市場經(jīng)濟(jì)主體的資格、打破市場進(jìn)入與退出的壁壘和反不正當(dāng)競爭。[11](P107-111)關(guān)于經(jīng)濟(jì)法在可持續(xù)發(fā)展中的作用,金玄武提出主要有四項:培育有利于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活躍的市場主體、有助于形成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市場新秩序、保障國家對市場經(jīng)濟(jì)的宏觀調(diào)控實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順利進(jìn)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通過上述作用的綜合協(xié)調(diào)發(fā)揮以營造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良好社會環(huán)境。[12](P97-99)
2.研究經(jīng)濟(jì)法在特定政治、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和時期的功能。焦海濤認(rèn)為經(jīng)濟(jì)法應(yīng)定位于“促進(jìn)型經(jīng)濟(jì)法”,即以促進(jìn)或鼓勵為目的,并采取相對溫和的運作方式的經(jīng)濟(jì)法規(guī)范的總稱。從形式上看“促進(jìn)型”經(jīng)濟(jì)法中的促進(jìn)手段可以分為直接促進(jìn)與間接促進(jìn)、個別促進(jìn)與整體促進(jìn)等。對于某類個體、行業(yè)、區(qū)域的促進(jìn),一般可以視為直接的、個別的促進(jìn)。而對于宏觀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促進(jìn),則往往是在直接的、個別的促進(jìn)的基礎(chǔ)上實現(xiàn)的。[13](P77-83)馬洪雨以市場經(jīng)濟(jì)下應(yīng)建立強化市場型政府為目標(biāo),從“強化市場型政府”的角度重新定位政府干預(yù)的目標(biāo)、干預(yù)的方式和干預(yù)的條件,尋求政府干預(yù)與市場之間新的均衡。[14](P180-182)侯懷霞和李虎分析經(jīng)濟(jì)法的價值取向和政府權(quán)力后,得出在權(quán)力經(jīng)濟(jì)向法治經(jīng)濟(jì)轉(zhuǎn)軌的過程中,控制政府調(diào)節(jié)市場的權(quán)力是轉(zhuǎn)型時期我國經(jīng)濟(jì)法的主要作用的結(jié)論。[15](P17-19)
(二)從經(jīng)濟(jì)法與其他部門法的關(guān)系出發(fā)對經(jīng)濟(jì)法的功能與其他部門法的功能異同進(jìn)行辨析
1.對經(jīng)濟(jì)法與社會法的功能異同進(jìn)行辨析。單飛躍認(rèn)為,經(jīng)濟(jì)法的最大功能為社會整合,但此功能應(yīng)與社會法積極配合。經(jīng)濟(jì)法承擔(dān)著發(fā)展性社會整合功能,社會法承擔(dān)著保障性社會整合功能。在實現(xiàn)社會實質(zhì)公平方面,經(jīng)濟(jì)法的積極公平觀與社會法的消極公平觀相互協(xié)調(diào)。在社會總體性法益目標(biāo)中,經(jīng)濟(jì)法的經(jīng)濟(jì)效益目標(biāo)與社會法的社會效益目標(biāo)共同并舉。[16](P13-15)劉曉農(nóng)和葉萍也認(rèn)為,經(jīng)濟(jì)法和社會法都具有對整體社會調(diào)節(jié)的一般功能,并且各有所側(cè)重性:經(jīng)濟(jì)法的功能以經(jīng)濟(jì)功能為主,社會功能為輔;社會法的功能以社會功能為主,經(jīng)濟(jì)功能為輔。兩法是兼有經(jīng)濟(jì)功能和社會功能的主要法律部門,對斷裂社會的修復(fù),需要對兩法的經(jīng)濟(jì)功能和社會功能進(jìn)行有機(jī)組合與運用,共同擔(dān)負(fù)著社會整合的法律功能。綜觀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史,兩法功能組合呈現(xiàn)出的是一種“交替、逐次的互補”模式,而我國兩法功能組合的模式仍停留在“被動、臨時的補充模式”的初級階段。最后他們提出經(jīng)濟(jì)法與社會法功能組合的實現(xiàn)表現(xiàn)在共生的組合理念、耦合的組合手段和積極適應(yīng)的組合機(jī)制。[17](P92-97)甘強指出,經(jīng)濟(jì)法功能以經(jīng)濟(jì)功能為主,社會功能為輔,是直接的通過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內(nèi)部發(fā)揮作用的功能。經(jīng)濟(jì)法的主功能是克服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的內(nèi)在弊端,保證市場體制內(nèi)部的良性運行,促進(jìn)經(jīng)濟(jì)的快速、安全、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具體而言有六個分功能:綜合調(diào)控功能、分化整合功能、分配功能、克服信息失靈功能、降低交易成本功能和激勵功能。就一般意義而言,經(jīng)濟(jì)法與社會法具有共同促進(jìn)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的功能;就經(jīng)濟(jì)法和社會法對于經(jīng)濟(jì)、社會系統(tǒng)而言,兩者功能具有互補性。[18](P132-134)
2.對經(jīng)濟(jì)法彌補民商法的功能缺陷進(jìn)行研究。陳旭鋒認(rèn)為,隨著人類經(jīng)濟(jì)生活中產(chǎn)生經(jīng)濟(jì)主體的平等性喪失、所有權(quán)絕對受到限制、契約從自由到相對自由和組織關(guān)系的出現(xiàn)的變化,民法的傳統(tǒng)調(diào)節(jié)功能出現(xiàn)缺陷,需要社會本位的經(jīng)濟(jì)法來彌補。[19](P72-74)廖勇將經(jīng)濟(jì)法的功能與民商法比較后指出,經(jīng)濟(jì)法主要是在民商法作用發(fā)揮不到的地方發(fā)揮其功能,為民商法發(fā)揮必要功能而創(chuàng)造相應(yīng)條件。經(jīng)濟(jì)法的功能是規(guī)范政府組織經(jīng)濟(jì),民商法的功能是規(guī)范個人組織經(jīng)濟(jì),二者的價值取向是不一樣的。經(jīng)濟(jì)法功能的發(fā)揮必須結(jié)合和利用民商法。[20](P83-86)鄭艷馨也認(rèn)為,經(jīng)濟(jì)法國家調(diào)節(jié)的本質(zhì)決定了經(jīng)濟(jì)法具有再分配功能,是國家調(diào)節(jié)本質(zhì)在功能上的反映。與民商法對社會經(jīng)濟(jì)利益的初次分配不同,經(jīng)濟(jì)法的再分配主要是指對社會利益資源和權(quán)利的調(diào)節(jié)和再分配,界定和確認(rèn)國家在調(diào)節(jié)社會經(jīng)濟(jì)過程中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同民眾之間的利益分配關(guān)系。其目的主要是維護(hù)和促進(jìn)社會總體效率與社會公平,保障分配的實質(zhì)正義與公平。
[21](P107-109)
3.對經(jīng)濟(jì)法與行政法的功能異同進(jìn)行辨析。陳燕和孫鐵峰從功能角度切入分析經(jīng)濟(jì)法與行政法的關(guān)系,認(rèn)為經(jīng)濟(jì)法的主要功能是控制市場競爭、保障經(jīng)濟(jì)秩序,而行政法的主要功能是控制行政權(quán)力、保障經(jīng)濟(jì)自由,兩者功能不是截然分開,而是相互滲透,有機(jī)運行的。所以經(jīng)濟(jì)法與行政法的關(guān)系是實體(經(jīng)濟(jì)法)與程序(行政法)的分工。[22](P39-45)
(三)以其他學(xué)科的視角運用其社會科學(xué)術(shù)語和概念建構(gòu)經(jīng)濟(jì)法功能
1.借用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理論或術(shù)語研究經(jīng)濟(jì)法的功能。劉水林和雷興虎認(rèn)為,經(jīng)濟(jì)法的功能是立法者為了社會經(jīng)濟(jì)高速、可持續(xù)發(fā)展而預(yù)設(shè)于經(jīng)濟(jì)法規(guī)范中,并期望通過其實施而造成一種積極的客觀經(jīng)濟(jì)后果。他們主要依據(jù)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和產(chǎn)權(quán)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理論認(rèn)為,經(jīng)濟(jì)法必須具備以下五種社會功能:分配功能、信息傳遞功能、激勵功能、節(jié)約交易費用功能、整合經(jīng)濟(jì)功能。它們之間的關(guān)系表現(xiàn)為同一性、層次性、有序性與主次性。在經(jīng)濟(jì)法的五種功能中,分配功能是價值性、目的性的功能,因而處于主要的、決定性地位,而信息傳遞功能、激勵功能、節(jié)約交易費用功能,是手段性功能,處于輔助性地位。最后整合功能是集大成者,使前四種功能相互補充,真正達(dá)到功能互補。[23](P36-42)陳治從福利國供給模式、市場導(dǎo)向型供給模式和促導(dǎo)型利益分配供給模式的變遷路徑中,推導(dǎo)出經(jīng)濟(jì)法應(yīng)有利益配置和社會整合兩大功能形態(tài),并對福利供給變遷中經(jīng)濟(jì)法功能的限度和實現(xiàn)做出積極的考察。[24]應(yīng)飛虎從信息的視角以經(jīng)濟(jì)學(xué)的范疇與概念對經(jīng)濟(jì)法的功能進(jìn)行了分析,提出經(jīng)濟(jì)法在戰(zhàn)勝信息失靈方面的基本功能為克服信息不足、信息不對稱和信息錯誤。[25](P58—66)
2.以社會學(xué)視角或社會學(xué)相關(guān)理論闡述經(jīng)濟(jì)法功能。祖章瓊從社會結(jié)構(gòu)的角度來審視經(jīng)濟(jì)法,認(rèn)為經(jīng)濟(jì)法在社會經(jīng)濟(jì)系統(tǒng)中的作用主要有四個:一是對政府以及其他主體在經(jīng)濟(jì)運行中的角色進(jìn)行分配與界定;二是社會控制及社會整合;三是對資源、權(quán)力、信息和文化價值等社會資源配置;四是實現(xiàn)社會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的均衡和建構(gòu)社會經(jīng)濟(jì)秩序。[26](P132-134)王紅霞以實證社會學(xué)的視角切入,提出市場分配機(jī)制的缺陷應(yīng)是研究經(jīng)濟(jì)法功能的起點。它催生了經(jīng)濟(jì)法的產(chǎn)生,使經(jīng)濟(jì)法的獨特功能表現(xiàn)為通過規(guī)范和保障國家調(diào)節(jié),確保國家調(diào)節(jié)依法作用于社會經(jīng)濟(jì),在市場分配基礎(chǔ)上彌補其缺陷,對國民收入進(jìn)行必要的再分配,以促進(jìn)社會經(jīng)濟(jì)的協(xié)調(diào)穩(wěn)定發(fā)展。[27](P114-116)
3.依據(jù)現(xiàn)代哲學(xué)和政治學(xué)理論闡釋經(jīng)濟(jì)法功能。肖偉志根據(jù)哈貝馬斯的公共領(lǐng)域理論和交往行動理論主張的“外在和內(nèi)在的雙重視角”來解釋經(jīng)濟(jì)法面臨的事實性和有效性之間的緊張,從而認(rèn)為經(jīng)濟(jì)法是作為政治權(quán)威的國家與經(jīng)濟(jì)活動系統(tǒng)之間的交往媒介。與憲法和民商法分別局限于政治權(quán)威系統(tǒng)和市場經(jīng)濟(jì)系統(tǒng)的內(nèi)部整合不同,經(jīng)濟(jì)法的功能是進(jìn)行政治權(quán)威系統(tǒng)和市場經(jīng)濟(jì)系統(tǒng)之間的整合,表現(xiàn)為系統(tǒng)間的語言整合和價值整合功能。他還認(rèn)為哈貝馬斯在超越了自由主義法律范式和福利國家法律范式的基礎(chǔ)上提出的程序主義法律范式,對于理解經(jīng)濟(jì)法系統(tǒng)間整合功能的實現(xiàn)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28](P66-74)
三、對經(jīng)濟(jì)法功能研究現(xiàn)狀的評析
囿于學(xué)識和精力所限,筆者整理的觀點沒有反映學(xué)者的所有研究現(xiàn)狀,無法避免掛一漏萬。但我們可以管中窺豹,一葉知秋,從中大致可以對當(dāng)今經(jīng)濟(jì)法功能的研究現(xiàn)狀做出初步和不成熟的總結(jié)與分析。
(一)經(jīng)濟(jì)法功能研究的觀點趨同之處日漸浮現(xiàn)
盡管學(xué)者的不同知識背景導(dǎo)致分析問題的“前見”及對制度考察的側(cè)重點有所不同,但是還是有不少學(xué)者在某些觀點上出現(xiàn)了不謀而合之處。
一些學(xué)者共通地提出經(jīng)濟(jì)法的功能應(yīng)至少包括控制或者調(diào)控、整合和分配這三大功能。他們的觀點出現(xiàn)一致之處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第一,根據(jù)社會學(xué)和法理學(xué)的基礎(chǔ)理論,法律主要有規(guī)范功能和社會功能,兩者在微觀抑或宏觀上側(cè)重點有所不同。經(jīng)濟(jì)法作為國家干預(yù)執(zhí)法,更多地要從較為宏觀的角度對社會進(jìn)行一定程度的干預(yù),因此沿襲社會作用中的控制性和調(diào)控性乃理所當(dāng)然;第二,經(jīng)濟(jì)法是國家有限度的干預(yù)經(jīng)濟(jì)之法,面對社會經(jīng)濟(jì)生活的劇烈變化、社會階層的急速分化和貧富差距的迅速拉大,為了調(diào)和矛盾和保障社會和諧發(fā)展,需要經(jīng)濟(jì)法發(fā)揮整合功能克服市場經(jīng)濟(jì)內(nèi)生局限和政府謀求私利的行為,調(diào)和利益集團(tuán)間的歧見,拉近各階層之間裂變后的距離,將各類矛盾化解于無形之中;第三,許多學(xué)者都將利益分配功能作為經(jīng)濟(jì)法最基本的功能。經(jīng)濟(jì)法是為了彌補民商法和行政法之不足而產(chǎn)生的,其功能定位理應(yīng)有所不同,體現(xiàn)在經(jīng)濟(jì)法在均衡發(fā)展的理念和追求可持續(xù)發(fā)展、實質(zhì)公平和經(jīng)濟(jì)安全的價值的驅(qū)使下,其主要功能不可避免地要為整個社會的科學(xué)發(fā)展而服務(wù)。因此通過國家的介入將利益在國家、集團(tuán)和個人之間做出公平的分配,整合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沖突,以促使社會和諧、有序地發(fā)展,這將成為經(jīng)濟(jì)法功能發(fā)揮與彰顯的獨特之處。
還有一批學(xué)者對經(jīng)濟(jì)法與民商法、社會法功能的異同與互補給予了不懈的研究。他們對經(jīng)濟(jì)法與社會法功能的不同,強調(diào)重點是在經(jīng)濟(jì)性上還是社會性上;對于經(jīng)濟(jì)法與民商法功能的不同,提出主要體現(xiàn)在個人本位和社會本位指導(dǎo)下的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維護(hù)個體利益和整體利益上。同時,學(xué)者們普遍看到了經(jīng)濟(jì)法與民商法、社會法在功能上不僅是異同的關(guān)系,更是互補的關(guān)系,單靠其中任何一個部門法都無法勝任保障社會發(fā)展和人民富裕的艱巨任務(wù),需要各部門法共同發(fā)揮合力參與到我國法治化建設(shè)的進(jìn)程中來。
(二)經(jīng)濟(jì)法功能研究界限的模糊性
某些觀點對經(jīng)濟(jì)法功能、價值、目的等詞語的真正區(qū)別認(rèn)識不夠,沒有意識到這些概念之間主觀與客觀、實然與應(yīng)然、內(nèi)化與外化的邏輯辯證關(guān)系,導(dǎo)致在具體闡述時沒有找準(zhǔn)經(jīng)濟(jì)法的科學(xué)功能定位,出現(xiàn)了語義的偏差和理論的含混。
1.對經(jīng)濟(jì)法功能與作用區(qū)分不夠精細(xì)化引發(fā)經(jīng)濟(jì)法功能詞性的考量不周。在與“法律的功能”相關(guān)聯(lián)的概念中,“法律的作用”是聯(lián)系度最緊密但也是最難以區(qū)分的。關(guān)于此二者的關(guān)系,學(xué)界歷來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方面,大部分法理學(xué)者認(rèn)為,雖然“作用”與“功能”在嚴(yán)格的語義上確有某些細(xì)微差別———功能比較強調(diào)活動本身,作用則強調(diào)活動的效用,但由于其基本意義是無差別的,所以在大多數(shù)學(xué)術(shù)著作中二者是通用的,一般也不將“作用”與“功能”嚴(yán)格區(qū)別。[7](P45-46)現(xiàn)今的法理學(xué)著作中絕大多數(shù)都是將“功能”與“作用”混用,且采用“作用”一詞者居多。與之相反,部分學(xué)者堅持認(rèn)為,法律的功能與法律的作用有一定甚至是較大差別,不能完全等同起來。周旺生教授認(rèn)為,法的功能和法的作用是形式上相似而實質(zhì)上有別的兩個事物。法的功能主要是描述性的,法的作用主要是規(guī)定性的。法的功能是法的作用的前提和基礎(chǔ),法的作用則是法的功能的外化和表現(xiàn)。[29](P112-116)國外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作用”概念僅僅在一事物對他事物影響的一般意義上使用,而“功能”概念則離不開要素與系統(tǒng)、系統(tǒng)與環(huán)境等關(guān)鍵范疇。[30](P231)
對于經(jīng)濟(jì)法的功能與作用,經(jīng)濟(jì)法學(xué)者也沒有過多糾纏于其語境和詞義上的差別,實際上是將二者混用。在筆者查閱的文獻(xiàn)中,用“功能”和“作用”者都不乏其人,且基本沒有在文中開宗明義地辨析二者之不同。不過依然有學(xué)者認(rèn)為,功能不能等同于作用。功能可以被理解為作用,但功能不是作用的全部,它只是有利的作用(或者稱“積極作用”)。[31](P5)可見,對于經(jīng)濟(jì)法“功能”和“作用”之間有無區(qū)別,絕大多數(shù)學(xué)者要不持否定態(tài)度,要不也是基本忽略了某些可能存在的差異。
筆者認(rèn)為,“功能”與“作用”有沒有大的區(qū)別、能否互替不是問題的根本,關(guān)鍵是要厘清“功能”一詞究竟是褒義的還是中性的。實際上,即使有學(xué)者就認(rèn)為功能與作用等同,但作用又分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以此推斷法律功能自然也有積極與消極之分。也有學(xué)者指出:“嚴(yán)格說來,‘功能’一詞體現(xiàn)了某一事物通過其運行而對其他事物發(fā)生影響的客觀能力,是中性的,即其本身無所謂是積極的或消極的。只是在功能發(fā)揮的過程中,即事物影響外在環(huán)境時,才從主體(人)的角度觀察分出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6](P267)法的功能既然如此,作為部門法的經(jīng)濟(jì)法其功能自然也概莫能外地應(yīng)體現(xiàn)出中性。一些經(jīng)濟(jì)法學(xué)者們在研究經(jīng)濟(jì)法功能時大多沒有首先準(zhǔn)確定義“功能”一詞的明確含義,缺乏對“功能”是否含有消極作用的解釋與說明,往往導(dǎo)致先入為主地將“功能”等同于積極或有利的作用,而忽略了經(jīng)濟(jì)法功能可能具有的無效甚至反向作用。筆者希望今后的相關(guān)研究中能夠更精細(xì)化和準(zhǔn)確化,可以從多個側(cè)面和角度對經(jīng)濟(jì)法功能進(jìn)行評判。
2.經(jīng)濟(jì)法功能與價值、目的之辨異。有些學(xué)者將經(jīng)濟(jì)法功能與價值甚至目的沒有截然分開,含混地將幾種概念溶于一文之中或彼此在不同語境下互相代替。誠然,經(jīng)濟(jì)法有其功能價值和目的價值的提法有一定可取之處,但畢竟功能與目的、價值有著較大的差異,它們之間的離散性大于趨同性,因此對三者做出精確的界分仍是有意義的。經(jīng)濟(jì)法價值與功能屬于不同層次的法律范疇,經(jīng)濟(jì)法功能和價值在含義和內(nèi)容上均有所不同:首先,經(jīng)濟(jì)法的價值是經(jīng)濟(jì)法具有的對人有積極意義的屬性,而經(jīng)濟(jì)法功能是經(jīng)濟(jì)法作用于人而產(chǎn)生的或積極或消極的后果,具有工具性的特點;其次,經(jīng)濟(jì)法價值體現(xiàn)了經(jīng)濟(jì)法的取向,說明經(jīng)濟(jì)法“應(yīng)該是什么”的問題,而經(jīng)濟(jì)法功能則體現(xiàn)了經(jīng)濟(jì)法的狀態(tài),說明經(jīng)濟(jì)法“是什么”的問題,兩者是應(yīng)然與實然的辯證關(guān)系。此外,按照學(xué)者所言:“功能與目的也是兩個不同的范疇,法律目的即立法者的主觀意向,法律功能并非是指這些主觀的意向,而是指可見的客觀后果。”[6](P269)由此可見,經(jīng)濟(jì)法功能與經(jīng)濟(jì)法目的也是客觀后果與主觀意向的關(guān)系,其效用函數(shù)并不一定一致化。
(三)經(jīng)濟(jì)法功能概括具有一定的封閉性
首先,學(xué)界對經(jīng)濟(jì)法的功能研究沒有相對統(tǒng)一的觀點,這也與經(jīng)濟(jì)法基礎(chǔ)理論中的重大問題均沒有共同一致的理論來統(tǒng)領(lǐng)的研究現(xiàn)狀十分契合。進(jìn)一步說,從較為宏觀的角度高屋建瓴地建構(gòu)整個經(jīng)濟(jì)法體系的功能的著作和文章較少,絕大多數(shù)學(xué)者都是從較為微觀的某一個視角出發(fā),結(jié)合經(jīng)濟(jì)法的本質(zhì)、理念或者某一項價值來具體論述經(jīng)濟(jì)法或者經(jīng)濟(jì)法子部門法的功能。誠然,經(jīng)濟(jì)法功能理論的研究進(jìn)路和理論升華與經(jīng)濟(jì)法的其他相關(guān)范疇有著天然和不可分割的有機(jī)聯(lián)系,探討經(jīng)濟(jì)法功能也必不可少地要與經(jīng)濟(jì)法其他相關(guān)范疇的研究建立聯(lián)系。但是如果我們不從法理學(xué)已有的豐富成果中汲取寶貴的營養(yǎng),沒有從法律的基本功能出發(fā),結(jié)合經(jīng)濟(jì)法的邏輯起點、理念、價值、原則對經(jīng)濟(jì)法功能進(jìn)行有針對性和目的性的研究,而是封閉地引用經(jīng)濟(jì)法理論的其他基本范疇研究的一些成果作為經(jīng)濟(jì)法功能研究的理論支撐,可能導(dǎo)致理論的說服力與解釋力不足。有些學(xué)者甚至沒有對經(jīng)濟(jì)法功能做任何界定就迅速進(jìn)入下一主題,使經(jīng)濟(jì)法功能研究與法功能研究在某種程度上出現(xiàn)了“兩張皮”的現(xiàn)象;其次,與經(jīng)濟(jì)法理念、原則的研究相比,對經(jīng)濟(jì)法功能的研究似乎缺乏對當(dāng)代中國時代精神的探索和對熱點問題的回應(yīng)。除了有學(xué)者對經(jīng)濟(jì)法在“可持續(xù)發(fā)展”中的功能有所論及外,涉及到“科學(xué)發(fā)展觀”、“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知識經(jīng)濟(jì)”等具有鮮明特色、體現(xiàn)國家立法和制定政策方向的術(shù)語的經(jīng)濟(jì)法功能研究成果可謂寥寥無幾,表明對經(jīng)濟(jì)法功能的研究仍沒有走出學(xué)術(shù)研究固有的抽象思維的空中樓閣。
(四)經(jīng)濟(jì)法功能研究缺乏科學(xué)的自身學(xué)術(shù)范式
經(jīng)濟(jì)法基礎(chǔ)理論研究過多借用其他學(xué)科的知識和術(shù)語,缺乏自己的統(tǒng)一范疇和學(xué)術(shù)名詞,導(dǎo)致諸多學(xué)者含辛茹苦做出的很多理論成果被其他學(xué)科的學(xué)者認(rèn)為是缺乏自主創(chuàng)新的“嫁接型產(chǎn)品”,對現(xiàn)實的指導(dǎo)力較弱。這個頑疾已是老生常談,它同樣也充分體現(xiàn)在經(jīng)濟(jì)法功能的研究現(xiàn)狀上。“信息失靈”、“社會結(jié)構(gòu)”、“激勵”、“交易費用”、“福利變遷”這些非原生于法學(xué)的經(jīng)濟(jì)學(xué)、社會學(xué)的詞匯往往構(gòu)成了經(jīng)濟(jì)法學(xué)者研究經(jīng)濟(jì)法功能文章的關(guān)鍵詞或主題詞。我們可以說,我國經(jīng)濟(jì)法的研究歷史尚短,自身理論積累和邏輯架構(gòu)尚未成熟,借用和吸收其他學(xué)科的素材是一種捷徑,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時,知識的交流是無界限的,多學(xué)科的理論交叉研究往往更容易產(chǎn)生火花。但是,過多地借鑒其他學(xué)科的基本理論,頻密地使用其他學(xué)科的特定術(shù)語往往一方面暴露了經(jīng)濟(jì)法基礎(chǔ)理論研究自身的不足與短板,一定程度上驗證了某些非經(jīng)濟(jì)法學(xué)科學(xué)者“部分經(jīng)濟(jì)法學(xué)者在研究市場經(jīng)濟(jì)法律本質(zhì)及其功能時,只是簡單地借鑒運用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相關(guān)知識和邏輯,而沒有形成自己的概念工具和理論原理”的判斷,[32](P175)另一方面也阻礙了經(jīng)濟(jì)法基礎(chǔ)理論研究的內(nèi)生性成長,導(dǎo)致不少理論是建立在其他學(xué)科的地基之上,缺乏理論的自洽性。
四、經(jīng)濟(jì)法功能研究的立足點
追溯經(jīng)濟(jì)法的邏輯起點,探尋經(jīng)濟(jì)法的價值和理念,比較經(jīng)濟(jì)法和民商法、行政法及社會法孕育和產(chǎn)生背景之異同,展望經(jīng)濟(jì)法功能研究的未來,筆者認(rèn)為今后可以嘗試將研究的方向立足于以下幾點:
(一)立足于法理學(xué)既有理論
部門法的理論研究無法完全脫離法理學(xué)的相關(guān)研究而自成體系,它需要從法理學(xué)大量地借鑒、引用和嫁接有指導(dǎo)意義的理論或者范疇,這樣才能保證自己的研究不會偏離法學(xué)研究的正常軌道。如果我們沒有參考法理學(xué)對法律功能研究的已有寶貴成果,而是畫地為牢地從事局限于部門法學(xué)科內(nèi)部的研究,對經(jīng)濟(jì)法功能的研究可能會成為無本之木、沙灘上的堡壘,缺乏理論上堅實的根基和實踐中令人服膺的解釋力。因此,經(jīng)濟(jì)法功能研究也不能漠視法理學(xué)關(guān)于法律功能的基本理論和經(jīng)典學(xué)說,尤其是關(guān)于“功能”與“作用”、“價值”、“目的”等相關(guān)概念的界分,更需要我們靈活借鑒國內(nèi)外法理學(xué)界的已有理論成果。通過吸收和消化法理學(xué)界留下的豐富“養(yǎng)分”,我們應(yīng)運用法學(xué)理論中關(guān)于法律功能的基本原理,以其為藍(lán)本結(jié)合經(jīng)濟(jì)法的特有元素和素材,從法律所固有的規(guī)范功能和社會功能入手,在我國建設(shè)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和推行科學(xué)發(fā)展觀的前提下、在我國經(jīng)濟(jì)法承載的特殊使命和立法目的下系統(tǒng)地闡釋經(jīng)濟(jì)法的獨特功能。
(二)立足于經(jīng)濟(jì)法文本自身
借用其他社會科學(xué)領(lǐng)域的理論與術(shù)語研究經(jīng)濟(jì)法功能固然可以開闊視野、起到事半功倍之效,但是畢竟沒有植根于經(jīng)濟(jì)法文本自身,也沒有充分體現(xiàn)出法學(xué)的韻味,而是再次體現(xiàn)了“經(jīng)濟(jì)學(xué)帝國主義”對法學(xué)領(lǐng)域的入侵。誠然,功能理論本源自社會學(xué),經(jīng)濟(jì)法也要體現(xiàn)國家干預(yù)經(jīng)濟(jì)的特色,一定程度上使用社會學(xué)和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理論建構(gòu)自己的學(xué)說無可厚非。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從經(jīng)濟(jì)法的自身規(guī)定性出發(fā),把握經(jīng)濟(jì)法的社會本位,通過考察經(jīng)濟(jì)法的價值、理念、原則、立法目的等重點范疇,運用法學(xué)的范式與思維來建構(gòu)經(jīng)濟(jì)法功能體系,那么即使研究的成果數(shù)量再豐富也只是為其他學(xué)科的理論與知識在經(jīng)濟(jì)法學(xué)科內(nèi)生根發(fā)芽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基礎(chǔ)。當(dāng)然,筆者強調(diào)考察經(jīng)濟(jì)法其他重要范疇,只是希望學(xué)界能夠在挖掘經(jīng)濟(jì)法功能之前恰好的領(lǐng)會經(jīng)濟(jì)法的真諦,而不主張被這些范疇本身迷惑和俘虜,將它們不加區(qū)分地混為一談。同時,我們還要將研究的視角下探到反壟斷法、財稅法等最能彰顯經(jīng)濟(jì)法獨特魅力的法律制度中,使用微觀化和制度化的視角來審視它們內(nèi)蘊的體現(xiàn)經(jīng)濟(jì)法功能的特殊之處,從中提煉與總結(jié)出契合經(jīng)濟(jì)法功能研究的片段。
(三)立足于經(jīng)濟(jì)法與其他部門法的互動
經(jīng)濟(jì)法與其他部門法,特別是民商法、行政法的關(guān)系是我們探討經(jīng)濟(jì)法功能的一個重要立足點。經(jīng)濟(jì)法作為20世紀(jì)勃興之法,既與主要維護(hù)私權(quán)的民商法相差甚大,也與保障和約束公權(quán)力實施的行政法涇渭分明,甚至與同為第三法域的社會法在法益目標(biāo)等方面也有明顯的不同,因此經(jīng)濟(jì)法功能自然與其他部門法有著不小的區(qū)別。我們要正視經(jīng)濟(jì)法對于保障宏觀經(jīng)濟(jì)的良性發(fā)展與科學(xué)調(diào)控有著不可替代的功能,這種功能是較為開放的經(jīng)濟(jì)法的自身使命所承載的,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相對封閉的民商法、行政法功能較為微觀的不足。對經(jīng)濟(jì)法功能考察的視角首先一定要凝聚于這種差異與區(qū)別上,否則沒有比較的話就無法清晰地界定經(jīng)濟(jì)法功能的邊界。其次,對經(jīng)濟(jì)法功能的研究不是為區(qū)分部門法而提供理論上的彈藥和互相攻訐的素材,而是尋求經(jīng)濟(jì)法與其他部門法在功能上互補的途徑,冀求使它們能夠在功能發(fā)揮上找到共同的均衡點。因此,如何使經(jīng)濟(jì)法與其他部門法達(dá)致功能上的良性互動、和諧共處乃是我們研究的終極目標(biāo)。可喜的是,已有不少學(xué)者從以上的視角出發(fā)對經(jīng)濟(jì)法與其他部門法的功能的互動展開了研究,也取得了不俗的成果。稍感遺憾的是學(xué)界往往將注意力投向經(jīng)濟(jì)法與民商法、社會法的功能區(qū)分上,而似乎較少關(guān)注經(jīng)濟(jì)法與行政法的功能平衡問題,希望以后的研究可以補上這塊“短板”。筆者認(rèn)為今后在研究經(jīng)濟(jì)法功能乃至于經(jīng)濟(jì)法基礎(chǔ)理論的其他重要問題時,我們可以嘗試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抽象性思維的固有思考方式而引入類型化的思考方式。類型化的思考方式充分考慮到了不同部門法之間的銜接與過渡、穩(wěn)定與流變、交叉與重疊的情況。它不涉及部門法的優(yōu)劣之分與研究領(lǐng)域之爭,能夠節(jié)省認(rèn)知成本,提高研究效率。[33](P120)這也許是突破現(xiàn)有經(jīng)濟(jì)法與其他部門法功能研究局限的一條蹊徑。
(四)立足于經(jīng)濟(jì)法的本土性和民族性
經(jīng)濟(jì)法功能研究不僅要借鑒國外經(jīng)典理論,考察國外經(jīng)濟(jì)法發(fā)展的歷程,更要從我國建設(shè)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的大前提下出發(fā),將理論研究與現(xiàn)實國情有機(jī)地結(jié)合起來,這樣的研究才能收獲甜美的果實。法學(xué)界的崇洋之風(fēng)早已有之,經(jīng)濟(jì)法學(xué)界雖然此風(fēng)不甚但也不能完全免俗。雖然西方的理論或經(jīng)驗?zāi)転槲覀兲峁┐罅控S富的資料和實踐上的指導(dǎo),但是如果我們沒有考慮到中國經(jīng)濟(jì)法當(dāng)前應(yīng)發(fā)揮的功能與傳統(tǒng)西方經(jīng)濟(jì)法可能有所不同,如果我們沒有以中國意識為中心意識,以中國問題為中心問題,在中國歷史、文化和現(xiàn)實的時空語境下進(jìn)行發(fā)現(xiàn)和闡釋,那么“桔逾淮而北為枳”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必不可免。借用學(xué)者的話:“中國經(jīng)濟(jì)法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生存經(jīng)驗與生活知識的積累和總結(jié)。重組和創(chuàng)建經(jīng)濟(jì)法規(guī)則和秩序,必須將傳統(tǒng)資源與當(dāng)下社會的普遍價值理念兩相接引,同時也注重中國文化與他域文化的良性互動和溝通回應(yīng)。”[34](P9)同理,經(jīng)濟(jì)法學(xué)者也應(yīng)走出書齋,從社會經(jīng)濟(jì)生活中獲取經(jīng)濟(jì)法的“本土資源”,從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中挖掘經(jīng)濟(jì)法的“民族精神”,從國家治國理念與方略中尋求經(jīng)濟(jì)法的“時代特色”,這樣經(jīng)濟(jì)法功能研究才會逐漸“嵌入”到現(xiàn)今我國特定的文化、社會與更廣泛的制度之中。可以說當(dāng)下中國處于轉(zhuǎn)軌經(jīng)濟(jì)的階段為經(jīng)濟(jì)法功能的發(fā)揮提供了廣闊的舞臺,經(jīng)濟(jì)法學(xué)者們?nèi)缒芾蒙鐣{(diào)查等多種實證方法,對經(jīng)濟(jì)法功能在此特定時期如何更好地發(fā)揮進(jìn)行更有針對性的研究,必將為經(jīng)濟(jì)法基礎(chǔ)理論研究抹上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