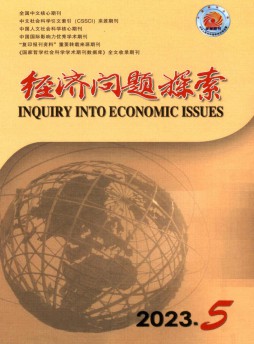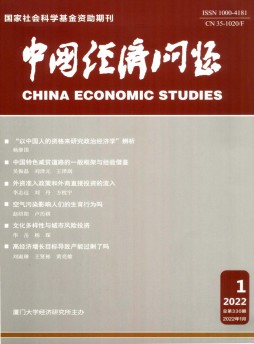經濟問題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經濟問題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問題的提出
近期以來,郎咸平教授一直在指責中國的改革,說它已經演變成一場錢權勾結侵吞國有資產的盛宴,并警告中央政府應該立即停止正在把中國引入權貴資本主義深淵的企業產權改革.郎的判斷是正確的,中央政府也從行動上上認可了這一點.郎咸平也必將因此而載入中國改革的史冊.之后,郎又進一步指出,中國當前經濟的問題關鍵出在中國缺乏"信托責任"上,也就是說,中國人不守信用,那么信用應該從哪里來呢?郎教授說是從嚴格紀律約束中來,而非從自由放任的市場中來.所以,他開出的藥方,是中國應該建立一個強大的政府,制定嚴格的法律,強迫人們去建立"信托責任".
二、郎引發中國對改革的反思和混亂
郎咸平的吶喊,引發了中國自改革以來對改革的空前的大反思和大辯論.實務界和理論界正陷入這場辯論的混亂局面之中.在這場混亂中,舊有的以"主流經濟學家"的理論和建議為支撐的改革秩序和格局被打碎,而新的理論和建議支撐格局尚未來得及建立."主流經濟學家"在當前的中國語境下似乎成了一個貶義詞,他們的理論、他們的建議、甚至他們的“良心”正在遭受公眾的普遍質疑和譴責,而面對這些質疑和譴責他們只能無奈無力地選擇“集體沉默”。“非主流經濟學家”卻似乎在郎咸平的吶喊聲中看到踏入“主流”的曙光,而開始在郎的背影下活躍起來,不遺余力地和大眾一道展開對昔日主流的激烈批判。但,作為整個事件的始作俑者的郎咸平,因為其特殊身份和地位,卻企圖超然于大陸的這場“主流”和“非主流”的爭論之上。他不屑于大陸的“主流”經濟學家,也同樣不屑于大陸的“非主流經濟”學家。
三、中國面臨大抉擇
理論界的混亂必然地導致實務界的迷茫,中央政府的關于改革的下一步的決策顯得舉步維艱。是的,中國的改革面臨著一個另人心驚膽戰、如履薄冰的重大抉擇關口。我們的高層決策者也正站在一個或者彪炳青史,或者遺臭萬年的十字路口。此時的決策你們一定要慎而又慎,思而又思。因為此時的決策,不僅關乎你們個人的歷史聲譽,更關乎的是中國十幾億人的以后相當一段時期的福祉!
四、大陸經濟學家的失敗
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得以揚名立萬的工具是西方的主流經濟理論,而以往指導中國改革政策制定的理論基礎便是新古典和新制度理論了。這些理論都是在一些基本假設以上而展開的。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也是知道的,但是,他們忽略的是,這些基本假設的成立是需要相應的社會環境的,也就是說這些假設的背后還有假設。他們理解了西方經濟理論,也理解了這些理論的前提假設,但卻沒有理解這些假設的假設。譬如,經濟人是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的最基礎的假設。但是,這個假設的成立是需要一定的社會環境的,也就是說是需要假設的。這個假設的假設就是承認和保護個人”私欲“和"產權"的道德、價值觀念和法律制度,而這一切中國都是沒有的。這個假設的假設才是現代社會的基石,才是市場經濟的基石。但是,因為西方經濟理論誕生伊始,這個假設的假設在歷經文藝復興和正在啟蒙運動的英國已經基本具備了,所以,根本未能進入亞當斯密的研究視野,而是被他沒有意識到地當成隱含假設了。即使,后來的科斯意識到”產權“的重要,但是,在這個假設的假設的掩蓋之下,他的對產權的描述也只是產權所有含義的冰山之水面上的一角,主體卻隱藏在這個假設的假設下面。所以,這導致了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失敗。
如果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是現在才被證明失敗,那么中國的非主流經濟學家是二十多年前就已經被證明失敗了,因為他們更多的是訴求于蘇聯和中國獨有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借以凝聚政治實力的理論基礎,這種局面決定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更是一個服務于政治斗爭的政治工具,而非以解釋現實經濟問題為導向的經濟學術理論。這也是郎咸平對中國的非主流經濟學家的盛情并不理睬的根本原因。如果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不是經濟學家,中國的非主流經濟學家就更不是經濟學家了。
五、郎咸平的誤診
也就是說中國的主流和非主流經濟學家目前被無情的事實證明都是失敗的,都是不可以信賴的。那么,企圖超越中國主流和非主流之上的郎咸平教授是否是否可以信賴呢?下面我們就來分析一下本文開頭提及的郎教授為中國經濟所開的藥方。
準確地說,郎的建議包括兩部分,一個是病因,一個是處方。郎對中國改革病因的診斷結果是中國缺乏“信托責任”。
從不同側面對資本主義的起源有很多解釋,其中馬克斯.韋伯就從“精神特質”角度闡釋了資本主義。他認為資本主義起源于“理性地和系統地追逐利潤的非人格化的態度”,而加爾文的新教倫理有助于塑造這種系統的理性,換句話說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精神特質產生于宗教紀律。郎咸平似乎想站在韋伯的肩上,企圖從精神特質的角度診斷中國的改革,所以他的判斷是中國缺乏“信托責任”。
那么資本主義精神真的是象韋伯所說的起源于新教倫理的非人格化的系統理性嗎?明確回答這個問題似乎不太容易,需要一本專著才行。但,本文嘗試在這里簡單地給一個回答。答案就是不是。韋伯的注意力過多地,放在了精神氣質的演變上,卻忽略了社會其他維度的重大變化。譬如,文藝復興的努力擺脫宗教紀律約束的非人道生活,倡導過自然的人性的世俗生活。文藝復興的意義就在于打碎宗教紀律對個人自由生活的約束。從這個意義上,本人認為文藝復興開始的標志就是《君主論》的發表。馬基雅維里在這本書中間接但卻明確地,向基督教道德宣戰,盡管他的真正意圖是為了維護意大利的君主專制,但一個客觀的效果是破壞了基督教權威。文藝復興后,尤其在經過啟蒙運動,人們的道德價值觀念發生了質的變化,就是從否定個人“私欲”的基督教道德價值觀念到承認個人“私欲”的現代社會觀念。幸福就是個人“私欲”的滿足,滿足個人“私欲”的東西就是財富,而追求財富的權力就是產權。所以,承認個人“私欲”的一個必然結果,就是承認個人產權。西方社會也為個人產權的承認展開種種斗爭甚至戰爭。在承認“私欲”和“產權”后,剩下的事情就是渴望幸福的人們使用自己的產權在現有的社會知識和財富積累拼命地掘取財富了、賺錢了。這就是資本主義。為了解釋這一過程,本人提出了“制度核理論”,該理論試圖建立一個嶄新的有邏輯支持的人類制度演進框架。所謂的制度核就是,支撐支持人類具體社會制度的深層道德價值觀念。該理論認為,在人類制度的產生和演進歷史中,存在兩個制度核,第一個制度核產生于西方的古希臘到古羅馬帝國成立這短時期,也即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第一個制度核,是在意識到個人“私欲“的存在卻又無力滿足的的背景下產生的,為規避痛苦,第一個制度核否定了個人”私欲“進而否定了個人產權。在第一個制度的支撐下,演化出了種種的非人道的具體的社會制度。譬如西方基督教的禁欲主義,中國的三綱五常。同樣,人類也正是在基于第一個制度核的制度的約束下,緩慢地進行了社會知識和財富的積累。隨著社會知識和財富的積累,人類逐漸意識到,自己有能力滿足在第一個制度核期就意識到的“私欲”,能夠為自己創造幸福。于是開始否定第一個制度核,建立第二個制度核,這就是剛才所說的承認個人“私欲”和“產權”。也就是說第二個制度核形成于西方的文藝復興以及啟蒙運動時期。
也就是說宗教是屬于第一個制度核范疇的東西,是否定個人“私欲”的,是否定“產權”的,那么源于宗教倫理的所謂的系統理性也是暗含這些道德價值觀念的,是反“資本主義”的。退一萬步講,也只能說這些系統理性在承認個人“私欲”和“產權”的環境下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僅僅是促進而已。人是需要這些理性的紀律約束的,因為這些紀律可以促進人們的良好合作,有助于人們獲取財富活動的展開。但是,人們并不是機械地單純地遵守這些紀律,人們只所以遵守這些理性的紀律約束,是因為這些約束可以幫助其更好地行使自己的“產權”去獲取能夠滿足自己“私欲”的財富。并非這些理性的紀律促使了資本主義的產生,而是“私欲”和“產權”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產生。即使,以前沒有理性的紀律,人們也會為更好的行使自己的產權,更好地滿足自己的私欲而創造出理性的紀律來。所以關鍵是承認人性的個人“私欲”和“產權”,而非莫須有的理性的紀律。
所以,郎教授對中國經濟的診斷是誤診。中國的確缺乏“信托責任”,但這并不是中國經濟問題的關鍵所在。中國的經濟問題的關鍵所在是個人“私欲”和“產權”沒有得到承認和保護。郎提出問題的能力是一流的,但解決問題的能力是鱉足的.正是是他混亂的解決思路使中國的非主流經濟學家感到了可乘之機,早已被證明失敗了說法和觀點有活躍起來.作為正宗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家,他同樣沒有意識到那些主流西方經濟理論假設的假設.
六、中國改革的正確軌道
中國缺乏誠信意識和法律意識的根源不是中國人天生的就不守信用,天生的就不遵守法律規則。而是在于中國的個人產權沒有得到明確和保護。中國缺乏權力意識。真正的誠信和法律意識只能在充分的個人產權的基礎上建立起來。
所以以后的中央政府決策的應該是以承認個人“私欲”和“產權”為基本原則。促進保護個人私欲和產權的道德價值觀念的形成和法律環境的形成。也就是說產權改革的方向不能變,要變的是產權的觀念。所有的產權從本質上只是屬于個人范疇的,不存在企業的、集體的、國家的產權。所謂的“企業的產權”“集體產權”“國家的產權”是衍生于個人產權的,要么是個人產權的集合,要么為保護個人產權。
企業改革要服務于明確和保護個人產權,我認為關于國有資產的可行方案,應該是國家出售應該推出的國有企業,然后把出售后的所得用于支援建設一些基礎設施,如教育、社會保障、醫療,轉移支付于一些落后地區和弱勢群體。這里需要中央政府的強力監督,保證交易的公正和出售所得額的使用不產生貪污腐敗。所以,我同意郎咸平的“需要強化中央政府”的觀點。以后的改革政策的制定和落實需要一個強力的中央政府。中國改革以后的操作更是體現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地方政府代表著既得利益集團,以后的改革就是中央為保護個人的權力而不得不和地方政府進行的激烈的斗爭過程。需要強調的是,我贊成強力的中央政府,并不代表我贊成集權,恰恰相反,我是想用強力的中央政府打碎當前的地方政府對個人進行集權的局面。
表面上,中國是,鐵板一塊。但,實際上,地方是不服從中央的,在地方上已經形成數不清的“多元化”的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是借共產黨的名義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對于黨中央的政策,他們是堅持兩個“凡是”的:凡是能維護自己經濟利益的,堅決執行,強化;凡是損害自己經濟利益的,堅決不執行,弱化。表面上中國是,而實際上,中國已經陷入了一個“經濟上”的諸侯割據時代,形成了很多的經濟壟斷番王!這些經濟諸侯和番王,企圖借助特權,壟斷地方經濟,在經濟上魚肉基層人民,破壞個人產權,嚴重地阻礙經濟的發展!要消除這些“多元化”的經濟諸侯和番王,必須要靠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