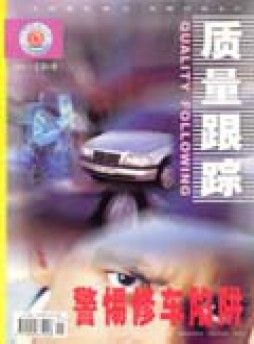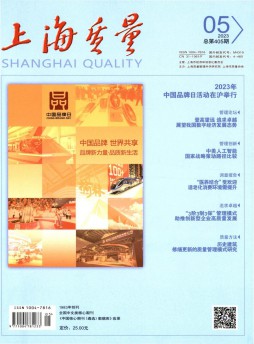質量測度經濟增長論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質量測度經濟增長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對2000—2012年度安徽省經濟增長質量的評價分析,借助統計分析SPSS軟件,根據時間序列指標體系運用時序因子分析法進行經濟增長質量指數測度,并與浙江省、全國進行比較。
(一)數據來源及處理數據樣本為安徽省、浙江省、全國,樣本時序長度為2000—2012年共13期;用于分析的客觀基礎數據從國家統計出版社出版的安徽省、浙江省和中國相關樣本年份的統計年鑒、統計信息網和國家統計局網站獲取,部分數據來源于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其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的估算中,關于資本存量的估算采用張軍的方法[17];全要素生產率的測定采用非參數的DEA-MALMQUIST指數法在Deap2.1軟件中實現。潛在產出根據平減后的真實GDP數據采用HP濾波方法,取λ=100得到。由于數據的不統一,有關人均受教育年限主要根據有關省和國家的統計年鑒數據按照達到相應文化程度需要經歷的受教育年數(小學為6年、初中為9年、高中為12年、大學為16年)和相應人口比例通過加權平均測算所得。對指標體系中的逆向指標運用極大值與指標的差值使其正向化;指標體系中的所有指標統一為同一正向指標后,為了消除量綱差異,同時又不改變指標數值的分布規律,采用均值化處理方法。
(二)時序因子分析法測度時序因子分析法是將時間維度與傳統因子分析結合起來的一種多元統計分析方法。在綜合評價的各類方法中,由于因子分析法具有變量降維、直接源于數據本身的結構而具有客觀性的因子得分權重以及計算方法簡明實用、比較規范等優點,因而在評價實踐中應用普遍。具體分析步驟如下:1.前提條件的判斷利用均值化處理后的變量數據相關矩陣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經反復比較統一抽取前2個主因子,坐標軸旋轉方法采用方差最大化法,得到安徽、浙江、全國的經濟增長質量的穩定性、協調性、持續性、潛力和福利性等五個維度的KMO值均在0.5~1.0之間,在1%顯著性水平下Bartlett球形檢驗皆拒絕原假設,表明選取的2000—2012年安徽、浙江、全國的經濟增長質量的基礎指標數據適宜在各維度進行因子分析。2.計算因子綜合得分利用滿足因子分析前提條件所得的前期結果,分別得到經濟增長質量五個維度的2個主因。根據式(1)并利用2個主因子線性得分函數可以求出經濟增長質量各維度的基礎指標系數向量,并對系數向量作規范歸一化處理得到相應權重(結果見表2);運用式(1)計算各維度指數(結果見表3)。對上述五個維度指數F1t,F2t,…,F5t(t=2000,2001,…,2012)是否適合作因子分析進行判斷:通過抽取2個主因子(k1,k2),安徽省、浙江省、全國的變量共同度均高于80%、累計方差貢獻率也都在85%以上;KMO值都在0.70以上、Bartlett球形檢驗均拒絕原假設。因此,各維度指數滿足因子分析前提條件。進一步計算頂層的因子得分值(經濟增長質量指數)Ft(t=2000,2001,…,2012):以2個主因子的方差貢獻率作為權重分別對其線性得分函數值(k1t,k2t)進行線性加權求和。同樣,根據式(2)并利用2個主因子線性得分函數可以求出各維度指數的系數向量,對系數向量作規范歸一化處理而得到其相應權重(見表4);運用式(1)計算得到經濟增長質量指數(見表5)。
(三)二次加權評價法測度為反映評價對象在樣本期間總體上的經濟增長質量水平以及便于評價對象之間的直觀比較,本文運用二次加權評價法[19]將評價對象在多個時間上的綜合評價值通過時序集結算子轉換為一個點值,形成對原有評價信息的轉換,即將時序動態綜合評價轉化為靜態綜合評價。這里采用時序加權平均(TOWA)算子,其時間權重通過時間權重向量熵的非線性規劃求解得到。根據時序因子分析結果(見表3和表5)運用TOWA算子,測算出靜態綜合評價值(結果見表6)。
二、測度結果的解釋和分析
(一)從經濟增長質量指數來看時間跨度為2000—2012年的13年間歷經“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的前兩年,安徽省經濟增長質量指數表現出小幅波動并呈上升趨勢的動態變化特征,由2000年的-0.56經歷短暫波動后,穩定地上升到2012年的1.053。與浙江省和全國的經濟增長質量指數的變化軌跡相比較,后二者具有周期性波動的特點(見表5)。其中,安徽省經濟增長質量水平高于浙江省的有7年(2000—2002年、2008年、2010—2012年),而好于全國的有9年(2000—2002年、2004年、2008—2009年、2010—2012年)。從近期看出(見表6),安徽省經濟增長質量總體水平(0.915)優于全國(0.824)、浙江省(0.768)。在安徽省經濟增長質量指數中,通過各維度指數的權重(見表4)可知,正向影響的維度指數有穩定性指數、協調性指數、潛力指數和福利性指數,其中福利性指數影響最大,為0.6095,其次是穩定性指數0.4961和潛力指數0.3664,只有持續性指數為負向影響,且對經濟增長質量影響也較大,為-0.4033。而浙江省和全國對經濟增長質量水平有負向影響的也是持續性指數,影響幅度大致接近;其他正向影響的四個維度指數中,浙江省最大的是潛力指數,為0.5321,全國最大的是穩定性指數,為0.5873。由此,可以說明安徽省經濟增長質量在持續、穩定地上升,近期總體上要好于全國、浙江省,而且經濟增長的福利性、穩定性和潛力的貢獻較大,特別是在“十二五”開局的兩年內,比全國、浙江省的經濟增長質量水平有明顯增進,這與安徽省一系列的規劃、政策的實施(如《經濟強省建設實施綱要》的著力推進、合蕪蚌自主創新綜合試驗區和國家技術創新工程試點省建設、推進皖江城市帶、合肥經濟圈、皖北振興等)和經濟發展環境的改善、居民福利水平的增進有著密切的關系,但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值得關注。
(二)從經濟增長質量各維度指數來看1.經濟增長的穩定性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是經濟健康運行的重要基礎,良好的穩定性反映經濟增長過程中資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的改善。安徽省的穩定性指數呈明顯頻繁波動的特征,動態路徑大致與浙江省、全國基本一致,只有2004年、2008年呈現偶然性劇烈波動(見表3),這與經濟系統之外的沖擊如“SARS”病毒傳播、世界性金融危機爆發有關。由表4可知,影響安徽省穩定性的基礎指標均為正向貢獻,其中,經濟增長率波動系數(X1)的貢獻最大,權重為0.6862,其次為通貨膨脹率(X2),其系數和權重分別為0.2584和0.5381,但浙江省的經濟增長質量穩定性受通貨膨脹率(X2)影響最大,其次為失業率(X3),全國的經濟增長質量穩定性受失業率(X3)影響最大,其次為通貨膨脹率(X2)。安徽省穩定性指數優于浙江省的只有6年(2000—2002年、2008年、2010—2011年),超過全國的也只有6年(2001—2003年、2005年、2008—2009年),但從2009年高峰下滑之后在2012年穩定性有所好轉。表明安徽省經濟增長過程中要素配置效率有所提高,價格水平相對穩定使得經濟運行的潛在風險較小,經濟增長拉動就業,尤其是城鎮化的推進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效應得到改觀。但是,在總體上,在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方面(見表6),安徽省經濟增長質量水平(0.109)要低于全國(0.118)和浙江省的水平(0.249)。2.經濟增長的協調性經濟增長的協調性體現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經濟結構包括城鄉結構、產業結構、收入結構、出口結構等的優化程度。安徽省的協調性指數具有與浙江省、全國類似的共變特征:具有顯著的平穩上升趨勢(表3),好于浙江省的僅有5年(2000年、2006—2009年),而高于全國的只有7年(2000—2002年、2008—2009年、2011—2012年),表明安徽省經濟增長質量的協調性與浙江省、全國相比仍存在差距。但是,從安徽省自身觀察,經濟增長的協調性除個別年份(2009年)外表現出較快的上升態勢,由2000年的-0.89升至2012年的0.72;通過表2發現,影響安徽省協調性的基礎指標中,影響最為顯著的是投資消費比例(X8),其系數和權重分別為0.1451和0.4831,其次為城鎮化率(X6)、工業化率(X5),其系數和權重分別為0.1419和0.4725、0.1347和0.4485,這與全國的基本相同,而影響最小的指標為對外貿易依存度(X9),其系數和權重僅為0.0957和0.3186,這與安徽省所處中部腹地,且外向型經濟占比不高(2012年安徽省對外貿易依存度僅為14.76%,而浙江省和全國分別為58.89%和47.00%)、對其他成分經濟的外溢效應較小有關,但6個基礎指標對協調性的影響均為正向的貢獻。影響浙江省經濟增長協調性的基礎指標中,最為顯著的是城鎮化率(X6),其系數和權重分別為0.5888和0.5452,其次為對外貿易依存度(X9)、投資消費比例(X8),它們的系數和權重分別是0.4586和0.4247、0.4563和0.4225,而經濟增長均衡率(X4)和工業化率(X5)卻對協調性有負向的影響,其系數和權重分別為-0.4047和-0.3772、-0.1803和-0.1670。對全國經濟增長的協調性有負向影響的是經濟增長均衡率(X4),其系數和權重分別-0.1529和-0.3992。由數據分析可以認為,安徽省經濟增長過程中結構性調整和轉換所產生的經濟增長效率在多數年份有所改善,但對安徽經濟增長質量的貢獻率(表4)不高,僅為0.2925,低于浙江的0.3953,比全國的0.2921略大,而從總體上看也確實如此(表6),安徽省經濟增長的協調性水平(0.609)低于浙江省(0.635)而高于全國(0.498)。3.經濟增長的持續性經濟增長的持續性體現了經濟增長的成本代價,較高的經濟增長質量應是以較小的資源環境和生態代價而取得經濟增長的。安徽省經濟增長的持續性指數表現長期下降的趨勢(表3),由2000年的0.84降至2011年的最低點-1.24,中間年份雖然在2003年、2005年、2008年有所回升,但均在一年后又繼續下滑;盡管在2012年升至-0.39,但仍然在平均值0以下。這與浙江省、全國的波動趨勢基本相似,只是后二者的變動幅度更大一些。安徽省經濟增長的持續性水平超過浙江省的只有5年(2005—2008年、2012年),高于全國的也只有6年(2003年、2005—2008年、2012年),所以,在多數年份安徽省的經濟增長持續性水平低于浙江省、全國的水平,而總體上也顯示出這一結果(見表8):安徽省經濟增長持續性水平(-0.642)比浙江省(-0.634)、全國(-0.507)低。由各維度的基礎指標系數向量及相應權重(表2)可以看出,影響安徽省經濟增長持續性的基礎指標中,工業固體廢物生產量(X15)影響最大,其系數和權重分別為0.1505和0.4565,其次為工業廢氣排放量(X14)、工業廢水排放量(X13),其系數和權重分別為0.1466和0.4447、0.1273和0.3861,與浙江省受此三個指標的影響方向相同,但全國的持續性水平受工業廢水排放量(X13)影響最為顯著,其次是工業廢氣排放量(X14)、工業固體廢物生產量(X15);安徽省資源配置率(X12)影響程度最低,但對安徽省持續性的影響要高于浙江省、全國水平,系數和權重分別達到0.0840和0.2548。而經濟增長持續度(X10)和綜合能耗產出率(X11)對安徽省和全國的持續性均產生較大的負向影響,浙江省只有綜合能耗產出率(X11)對其持續性有著負向影響。這表明安徽省經濟增長過程同浙江省、全國一樣對生態環境的傷害、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依然存在;特別地,安徽省、浙江省和全國的持續性指數對經濟增長質量均表現為負向影響,因而,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實現綠色增長,實現向可持續的集約性增長方式轉變依然任重道遠。4.經濟增長的潛力經濟增長的潛力意味著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動力的強弱。安徽省經濟增長的潛力指數呈波動上升的趨勢(表3),由2000年的低點-1.31幾經升降,在2010年達到峰點0.81后至2012年降至0.59,其變化軌跡與浙江省、全國相近。安徽省經濟增長的潛力水平超過浙江省的有8年(2001—2004年、2007年、2009—2011年),高于全國的有7年(2001—2002年、2004年、2008年、2009—2011年),在2003年與全國相同。總體上看,安徽省與浙江省、全國比較起來(見表8),經濟增長的潛力(0.628)略高于浙江省(0.623)而低于全國水平(0.649)。由各維度的基礎指標系數向量及相應權重(表2)可知,安徽省經濟增長的潛力指數均受到基礎指標的正向影響,其中人均受教育年限(X18)表現最為突出,其系數和權重分別達到0.5990和0.6011,其次是研發經費支出占GDP比重(X19)、經濟潛在增長接近度(X16),其系數和權重分別為0.5776和0.5796、0.4951和0.4968,表明安徽省區域創新尤其是合蕪蚌自主創新實驗區的建設、研究與開發和教育投入對人力資本的積累及技術創新有著明顯的正向激勵,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X17)對經濟增長潛力的貢獻最低,而高于浙江省,低于全國。浙江省的經濟潛在增長接近度(X16)、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X17)均對其經濟增長潛力有著負向影響,人均受教育年限(X18)和研發經費支出占GDP比重(X19)產生正向影響,較顯著的是研發經費支出占GDP比重(X19);全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受經濟潛在增長接近度(X16)的負向影響,其余基礎指標中正向影響最大的是人均受教育年限(X18),與安徽省一致,其次是研發經費支出占GDP比重(X19)、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X17)。在影響經濟增長質量指數(表4)中,安徽省的潛力指數具有正向影響,其系數和權重分別為0.1697和0.3664,但低于浙江省和全國。因此,安徽省要提高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需要繼續改善教育投入結構、引進民間投資,注重科研經費的投入產出效率,加強基礎研究,實現科研成果的產業化轉移,積極為區域產業承接升級服務,同時促進模仿創新向自主創新和協同創新轉移。5.經濟增長的福利性經濟增長的福利性反映了經濟增長成果的分享性,體現了經濟增長的最終目的在于居民福利水平最大程度的改善。安徽省經濟增長的福利性指數總體上表現出較快上升的態勢(表3),由2000年的-0.40快速升至2002年的-0.15,自2006年-0.66開始快而平穩地提高到2012年的峰點1.43,運動路徑與浙江省、全國較為接近,但后兩者在2004年和2008年均降至低點,特別是浙江省自2011年開始出現下滑趨勢。安徽省經濟增長的福利性水平好于浙江省和全國的均只有6年(2000—2002年、2010—2012年),前期和后期的水平較高,但其間連續7年(2003—2008年)均劣于浙江省和全國的水平。從總體上看(表6),安徽省經濟增長的福利性水平(1.037)反而優于浙江省(0.433)和全國(0.710)。由各維度的基礎指標系數向量及相應權重(表2)可看出,安徽省的福利性指數均受其基礎指標的正向影響,其中最為顯著的是人均GDP(X20),其系數和權重分別為0.6758和0.6388,其次為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X23)、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X22),它們的系數和權重分別為0.6020和0.5686、0.5040和0.4765,而城鄉收入比(X21)影響最小,其系數和權重分別是0.2175和0.2054。與浙江省和全國比較,城鄉收入比(X21)對二者的福利水平均產生了負向影響,而在正向影響的基礎指標中,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X22)對二者的福利水平皆貢獻最高。在影響經濟增長質量指數中,安徽省的福利性指數對經濟增長貢獻較高,其系數和權重分別為0.2823和0.6095,高于浙江省和全國對經濟增長質量的貢獻。通過數據可以判斷安徽省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改善收入分配、縮小城鄉差距,進而提高經濟增長成果的分享性方面有著較好的表現。
三、結論和啟示
在明確經濟增長質量的內涵和外延的基礎上,將經濟增長質量劃分為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協調性、持續性、潛力和福利性等五個維度,從而由規范性判斷轉化為定量分析,并在各維度內建立了衡量的基礎指標體系,運用采集和加工的時序數據和因子分析相結合,即運用時序因子分析方法,比較豐富地展現了安徽省經濟增長質量水平的動態變化;與浙江省、全國水平的比較可以客觀地判斷安徽省經濟增長質量的差距與不足。基于所構建指標體系的數據和測度分析的結果,我們發現在2000—2012年間安徽省經濟增長質量在波動中穩定提升,與浙江省、全國的變化態勢大致相近,近期的數據顯示出經濟增長質量總體上要優于后兩者。各維度水平對安徽省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差異明顯,福利性水平和穩定性表現出顯著的正向影響,持續性卻有著較大的負向效應;浙江省和全國的經濟增長質量受潛力和穩定性水平正向影響均較大,不過浙江省受正向影響最大的是潛力水平,而全國是穩定性水平;同時,由于度量的基礎指標不同,以及經濟增長過程中受復雜因素的影響所形成的時序觀測值水平差異,也使得各維度測度出的經濟增長質量水平存在著差異:安徽省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水平、持續性水平總體上都不同程度地低于浙江省和全國的水平,協調性水平低于浙江省而高于全國水平,經濟增長的潛力水平總體上高于浙江省而低于全國水平,但經濟增長的福利性水平優于浙江省和全國。實證分析結果可以啟示我們:在“十二五”時期的后續經濟發展中,安徽省需要進一步提升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持續性水平,優化資源配置,減少經濟增長對資源生態環境的依賴,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向可持續集約式、高質量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尤其是在承接世界和東部沿海產業轉移過程中,需要慎重選擇承接產業以更好地與承接地的產業實現有效對接,防止高污染、高能耗、低產出的產業移入;在福利性水平上,繼續推進城鄉統籌發展,加強農村剩余勞動力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就業引導和培訓,以及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創業服務,縮小收入分配的絕對差距;增強經濟增長的協調性和潛力水平,深化經濟結構調整,積極推進《經濟強省建設實施綱要》的“十大專項行動”“十項重大工程”“五大保障措施”的落實,優化投資主體結構和制度設計,同時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完善自主創新和協同創新的機制。
作者:李榮富傅懿兵王萍單位:池州學院經濟貿易系煙臺職業學院會計系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 上一篇:高等教育貢獻率的經濟增長論文范文
- 下一篇:市場化進程經濟增長論文范文
擴展閱讀
- 1房屋質量合同
- 2質量興市強化質量安監意見
- 3工程質量體系質量預控
- 4化學復習質量
- 5會計信息質量特征
- 6甘草苷質量標準
- 7婦產科醫療質量
- 8混凝土生產質量
- 9稅收質量審計
- 10會計政策信息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