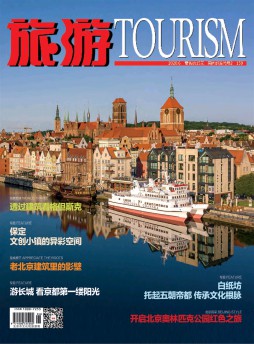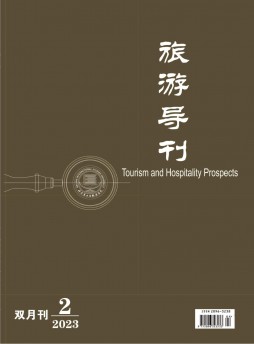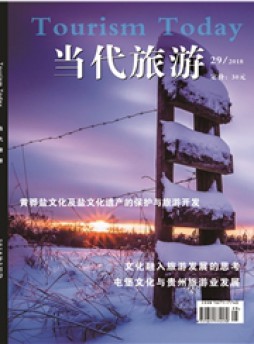旅游經濟發展格局研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旅游經濟發展格局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經歷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西藏旅游業憑借自然與人文旅游資源(歷史文化、雪域高原風光、藏民俗和藏傳佛教景觀)和我國各時期扶持政策實現了跨越式發展,產生了可觀的經濟社會效益。
西藏現有8個4A景區,3個2A景區,2個A級景區,6個國家自然保護區,2個國家地質公園,1個國家優秀旅游城市(截至2008年底),正建設世界級旅游目的地。全區已形成以拉薩為中心、輻射全區的旅游發展空間格局[1]。
一、西藏旅游業發展概述
(一)發展階段
1.1980-1990年:起步和成長期(0-25萬人次)。1980年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的召開是西藏旅游起步的標志。當年接待境外旅客1059人次。1984年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后,中央加大了對西藏的投資力度,繼續推動西藏旅游業的發展。限于當時“先國際、后國內”的政策,西藏旅游發展初期主要針對境外市場。1987年接待量達6萬人次[1]。
2.1991-2005年:快速發展期(25-200萬人次)。第三、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將旅游業作為工作重點,西藏旅游進入快速發展期。我國以項目援藏和導游援藏相結合,極大提升了西藏旅游發展速度和服務質量。2004年接待量突破100萬。2005年中央強調大力發展旅游業,以旅游業帶動農牧民增收和相關產業發展。西藏旅游進一步受到重視,被提升到促進西藏穩定的高度。2000-2005年,西藏接待游客數平均每年增長23.7%,旅游總收入平均每年增長22.9%,都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
3.2006年-現在:井噴式發展期(200-600萬人次)。2006年青藏鐵路和林芝機場相繼開通,西藏旅游的出入性和舒適性大大提高;加上“一產上水平、二產抓重點、三產大發展”產業發展政策和旅游業龍頭產業地位的確立,西藏旅游發展速度明顯加快。當年接待量突破200萬人次,同比增長了39.5%,旅游收入同比增長了43.2%,旅游業開始成為全區支柱產業。2007年,西藏提出“大旅游、大產業、大發展”,旅游業提質增效、呈現井噴式發展,當年接待量突破400萬人次,旅游總收入近50億元,比1980年分別增長800和2200倍。西藏旅游進入飛速發展期。
(二)經濟社會效益
西藏旅游業發展的經濟社會效益突出。截至2007年,西藏全區有各類旅游企業1212家,擁有固定資產達46.8億元。旅游直接從業人員2.84萬人。全區8700戶農牧民參與旅游經營,創造非農就業崗位3.48萬個,年收入達2.2億元,人均增收6383元。
西藏旅游總收入占GDP的比重逐步提高。2006年、2007年、2009年分別為9.6%、14.2%、12.7%。拉薩2009年的相關比重超過20%。2009年全區農牧民純收入比2000年增長1.85倍,旅游富民效應初顯。
二、西藏旅游業發展格局的實證研究
接待量、旅游收入、人均旅游消費是區域旅游發展的重要指標。旅游收入、人均旅游消費是接待量的因變量,易受游客自身條件(經濟條件、職業、年齡等)、主觀選擇(消費偏好、性格等)和不同旅游地實際情況(旅游業成熟度、物件水平等)的影響,波動范圍較大,統計分析的穩定性較差,適用于某一區域的旅游收入縱向上的比較(考慮CPI變化),不適合同一時段不同區域之間的橫向比較。鑒于此,選擇變化相對穩定的游客接待量為基礎數據。
(一)西藏及下轄7地市2000-2009年旅游接
待量分析
從旅游接待量上看,拉薩旅游發展遙遙領先于其它地區,運行軌跡幾乎與西藏旅游接待總量完全一致,對西藏整體旅游業發展起到主要支撐作用。
(二)拉薩對西藏旅游業貢獻度的檢驗
首先采用SPSSV11.5軟件進行相關分析加以驗證。相關分析表明,拉薩與西藏的年旅游接待量在0.01水平上相關性顯著,達到0.989。足見拉薩對西藏全區旅游業的貢獻率之高。
再用聚類分析檢驗,西藏下轄7地市的旅游發展被分為三個檔次:第一檔為拉薩,第二檔為林芝、日喀則、山南;第三檔為昌都、那曲、阿里(見圖3)。聚類分析驗證了拉薩旅游業具備區域旅游增長極的特征。西藏旅游業發展因此呈現出“拉薩為中心、周邊的林芝、日喀則、山南和昌都、那曲、阿里等6個地區受其輻射和帶動”的“核心-邊緣”發展格局。
三、西藏旅游業發展空間格局的“核心-邊緣”結構
弗里德曼(Friedmann.J.R,1966)在其著作《區域發展政策》中試圖通過“核心-邊緣”理論闡明一個區域由孤立到發展不平衡、再由極不平衡發展成互相關聯、平衡發展的區域系統,之后又將該理論從空間經濟擴展至社會生活各個層面[4]。“核心-邊緣”理論主要被用來解釋經濟空間結構演變模式核心-邊緣理論[5-6],也適用于區域旅游經濟發展的研究。
無論從經濟總量、旅游資源豐度、服務設施數量及檔次、與周邊地區通達性和通勤頻率,還是與周邊6地區基于行政和經濟聯系的人流、信息流、物流、資金流等因素看,拉薩都具備強大的經濟外溢功能。鑒于目前進藏游客在拉薩市的旅游消費量和在周邊6地區的消費量相差較大,仍以拉薩市和周邊6地區2000-2009年旅游接待量為基礎數據進行拉薩對周邊地區旅游輻射效應的分析和驗證。
相關分析結果顯示:拉薩與周邊的林芝、日喀則、山南、昌都、那曲、阿里等6地區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985,0.985,0.988,0.935,0.918,0.727(在0.01水平上相關性顯著;拉薩與阿里相關性在0.05水平上顯著)。表明西藏旅游業的“核心-邊緣”效應開始出現。拉薩與周邊地區表現為總體較顯著的旅游輻射效應,但這種聯動性并不均衡。其中山南、日喀則、林芝較好,昌都和那曲稍差,阿里不明顯。周邊6地區在旅游發展總量上與拉薩的差距較大,且從2003年以來呈逐漸擴大的態勢(見圖2)。
拉薩對周邊6地區的旅游經濟輻射效應的空間差異明顯,大致以拉薩為界分為藏西北和藏東南兩大片區。西北片區的阿里、那曲、昌都受拉薩旅游經濟拉動相對較弱,而東南片區的日喀則、山南、林芝受到旅游經濟拉動相對較強。這與各地區的旅游資源品位、自然環境、區位條件和行政區縱深固然有關,但目前藏東南片區與拉薩相對便捷的交通成為影響核心-邊緣效應的主要因素。相對便捷的交通加之良好的生態環境和精品旅游資源,藏東南旅游經濟走廊正在形成和發展。
四、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經過30年發展,西藏旅游業的“核心-邊緣”空間格局已經形成,表現出一定的“核心-邊緣”效應———以拉薩為中心,輻射和帶動周邊6個地區旅游經濟發展。然而,定性定量分析表明西藏旅游業的地域發展極不均衡,拉薩旅游接待量占西藏全區比例高達60%左右(見圖4)。拉薩作為西藏的旅游經濟中心,在發揮極化效應和輻射效應的同時,也呈現出嚴重的單極化發展態勢。單極化為主的發展方式在客觀上造成“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的不經濟后果,從而大幅降低了西藏旅游業整體抵御風險的能力。
2003年“非典”和2008年“3.14”事件讓西藏旅游業的這種缺乏抵御旅游安全風險的弱項暴露無遺。圖2和圖4均顯示:2003年西藏和拉薩旅游業明顯減速,接待量幾乎與2002年持平;2008年西藏和拉薩旅游接待量銳減近50%。在旅游危機事件影響下,西藏整體旅游業發展和拉薩旅游業表現出異常顯著的“旅游共振”現象。“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發展特征讓西藏旅游業繁榮發展的背后隱藏著嚴重的“蝴蝶效應”危機。
此外,單極化發展在形成“核心區域”旅游經濟呈極化效應的同時,也讓“邊緣地區”旅游發展呈邊緣化,旅游經濟發展不足或滯后。以西藏2006年以來旅游發展增速最快的林芝地區為例,其區域知名性景區僅有3處,其余中小景點“空間分布極為不均,密集分布于八一鎮和拉薩之間的318國道兩側,‘拉薩-林芝旅游廊道’初步形成”[7]。雖然林芝地區受拉薩市輻射效應相對明顯,但與豐富多樣的旅游資源和全藏最佳的生態環境相比,林芝旅游發展總量和旅游經濟發展水平仍顯不足,尚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二)西藏旅游業發展建議
參照弗里德曼所持的“核心-邊緣”理論觀點,西藏旅游業同樣要經歷“孤立—不均衡—嚴重不均衡—互相關聯、平衡發展”等階段,目前正處于互相關聯的不均衡的過渡階段。為此,提出相關建議:
1.分時段、分地域對拉薩市旅游客流進行適度控制,緩解拉薩的旅游承載壓力,最大限度地緩和全球各地涌入的大量游客與拉薩市的旅游承載力之間的矛盾;強化拉薩市與周圍6地區的旅游合作機制,量入為出地做好相關基礎和服務設施建設,更好地承接拉薩市旅游經濟的溢出效應。
2.從西藏旅游業發展全局的視角和高度,注重拉薩旅游經濟“核心-邊緣”效應的綜合發揮,使周邊六地區不僅能共享西藏旅游業發展帶來的經濟社會效益,更能借鑒拉薩的成功經驗,規避旅游業發展的教訓和誤區,少走和不走彎路,更好地實現本地區旅游業的跨越式發展,從而以西藏全區旅游業的協調發展提升其產業發展安全度。
3.對目前受拉薩旅游經濟中心拉動效應顯著的藏東南片區(日喀則、山南、林芝)進行重點產業培育,打造生態旅游和民族特色旅游精品,發展自身旅游經濟的同時,做好承接拉薩旅游分流的準備,未來與拉薩市形成優勢互補、合作共贏的局面;對藏西北片區旅游經濟采取選擇性發展措施。為西藏旅游拓展和創造更為寬廣的緩沖空間和發展空間,實現整體、科學、持續發展。
4.基于前三點建議制定西藏旅游業科學發展的決策和政策,改變全區旅游業發展過度依靠拉薩的現狀,增強西藏旅游業發展的產業安全系數。以旅游產業的穩健發展及其產業聯帶效應的發揮,促進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的穩定和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