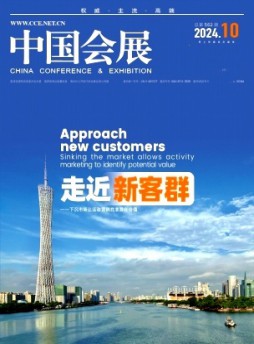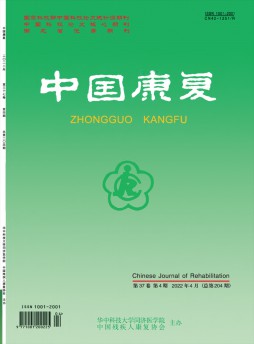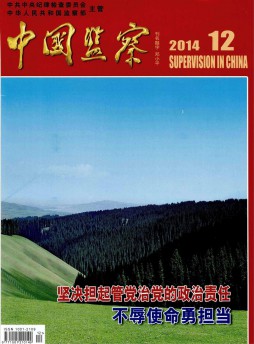中國地區經濟收入差距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中國地區經濟收入差距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自生能力問題以及趕超戰略對中國地區差距的不利影響
中國政府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的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是典型的違背比較優勢的戰略,該戰略下建立的大量國有企業是沒有自生能力的(林毅夫,2002a)。自生能力問題以及為克服這個問題而形成的“三位一體”的經濟體制,在區域經濟發展方面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拉大地區發展差距。其作用機制如下:第一,在中西部地區建立許多資本密集項目需要大量的初始投資。單單從統計數據看,這種投資分配模式意在(或者說有可能)縮小相對發達的沿海地區和相對落后的內陸地區的發展水平差距。但是這些投資真正形成的生產性資本量卻是有限的,而且這些投資形成的資本品專用性極強,對當地經濟活動幾乎產生不了什么顯著的正向外部效應。①第二,大部分趕超項目需要投入大量自然資源、初級原礦產品和初級制成品,而這些投入品大部分出自中西部地區。為補貼趕超項目,政府出面人為壓低這些商品的價格。由此導致的結果是,中西部地區事實上在補貼這些趕超項目。所以,在中西部地區建立的許多趕超項目不但不會促進這些地方的經濟發展,相反還會在一定程度上起負面作用。第三,盡管政府為趕超項目投入了大量的資本,但是這些項目只能夠為來自發達的沿海地區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創造有限的就業機會,而當地勞動力則被局限于生產率低下的農業部門。因而,本地的勞動力收入水平難以提高。
改革以來為補貼沒有自生能力的國有企業,政府繼續壓低原材料和初級產品的價格。而這些資源和產品的產地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改革以來沿海省區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從中西部地區輸入越多的原材料和初級產品。因此,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向經濟相對發達的東部地區的經濟增長不斷提供補貼,導致地區差距進一步擴大。另外,中西部地區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所背負的政策性負擔,內生地導致了這些企業的軟預算約束問題(LinandTan,1999),所以,即使承擔趕超任務的中西部地區企業能夠獲得政策性補貼,但是其經濟績效也不高。大量國有企業沒有自生能力,這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問題(林毅夫,2002b)。
二、對中國地區差距的實證分析
1·實證分析的基本框架
為了深入說明發展戰略對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我們在這里進行嚴格的計量分析。按照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Solow,1956;BarroandSala-I-Martin,1991,1992),由于資本邊際報酬遞減,初始人均收入較低的經濟體在未來經濟增長的潛在速度比初始人均收入較高的經濟體快,這是經濟增長內在的收斂機制。但是,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沒有考慮到發展戰略特征決定的經濟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正如前文闡明的那樣,如果一個欠發達的經濟體推行違背比較優勢的趕超戰略,那么其經濟增長步伐將被延緩,從而使得其實際經濟增長速度低于潛在速度。
林毅夫(2002a)定義了實際的技術選擇指數(TCI)以及最優的技術選擇指數(TCI*)來度量發展戰略的特征。基于此,我們這里采取如下方式間接度量政府推行的發展戰略對于比較優勢戰略的偏離:DS=TCI-TCI*(1)如果一個國家(地區)推行順應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則DS=0。如果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度超越于所處發展階段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則這種趕超戰略之下DS>0。DS的實際取值越是大于0,則表明趕超力度越大,或者趕超的特征越強。進而,我們構造如下的計量方程:Gi=α0+α1·Ln(GDPPL0,i)+α2·DSi+ψX+ui(2)(2)式中,被解釋變量是1978—2000年期間各省區市的勞均GDP年增長率。Ln(GDPPL0,i)是各省區市在1978年的初始勞均GDP,代表初始的發展水平。按照前述分析,如果收斂機制存在,則α1的符號預期應該為負;同時,如果我們的假說和經驗事實相容,則α2符號預期也應該為負。由于TCI*是不可觀察的,所以我們無法直接計算出DSi的取值。但是,注意到TCI*是一個正的常數,在回歸分析時,就可以將(2)式展開為(2′)式:Gi=C′k+α1·Ln(GDPPL0,i)+α2·TCIi+ψX+ui(2′)在方程(2′)當中,C′k=α0-α2TCI*。預期TCIi的系數α2的符號應該為負。在方程(2)和(2′)當中,X代表其他解釋變量,對此我們在后文將給出詳細的介紹。
2·變量和數據來源
關于TCIi的具體測算辦法,請參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發展戰略研究組(2002)的報告。①TCIi實際上是刻畫各個省區的產業、產品和技術結構特征的變量。我們得到的原始TCIi數據是各個省區市1978—1999年期間的年度時間序列數據。為了刻畫整個分析時期里各省區市發展戰略特征,首先引入1978—1999年各個年份TCIi指數的算術平均值作為解釋變量,記為TCI7899。我們還引入了另外一種定義的發展戰略指標:TCI7885,含義是1978—1985年各省區TCI的算術平均值,以便分析改革初始階段各個省區的發展戰略特征。(2′)式涉及到的其他解釋變量X,視具體情況而不同。按照新古典增長理論,儲蓄傾向越高的經濟體,其穩態勞均產出就越高。這樣,如果各個經濟體之間儲蓄傾向不同就會影響到收斂速度。具體來講,儲蓄傾向越高的經濟體,經濟增長速度就越高。因為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高儲蓄傾向導致高穩態收入水平,進而意味著給定的初始人均收入和穩態收入之間存在更大的差距,從而就有更快的勞均收入增長速度。所以,我們引入了儲蓄傾向(以SAVi代表)指標。按照理論預期,這個解釋變量的系數符號應該為正。在具體進行計量估計時,我們沿用Mankiw等(Mankiwetal.,1992)的做法,定義各個省區儲蓄傾向為:SAVi=∑2000t=1978IiGDPi。其中分子代表固定資本和存貨資本投資之和,①分母代表當年的GDP。兩者均為當年價格。另外,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勞動力平均增長率越高的經濟體,穩態人均收入就越低。按照和上述儲蓄傾向大致類似的理論原理,我們引入了各個省區勞動力平均增長率(以LABGi來代表)作為解釋變量。這個解釋變量的系數符號應該為負。
大量的經濟增長收斂回歸都將人力資本作為一個解釋變量。不過各個研究者實際使用的定義不一樣。我們在這里也將各個省區起點時刻的人力資本存量作為解釋變量(以HUMK82i代表)。具體定義是各個省區1982年具有小學文化程度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這個指標的系數符號預期為正。有文獻強調外商直接投資對地區差距的影響(Lee,1994;Dayal-GulatiandHusain,2000)。外資流入,尤其是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往往能夠帶來新的技術訣竅和管理經驗。所以外國直接投資(以FDIi表示)越多的省區,技術進步方面的優勢就越大。我們在計量分析中實際使用的外國直接投資指標的定義是:1978—2000年期間外國直接投資累計額的自然對數。我們預期外國直接投資變量的系數符號應該為正。另外,大量的經驗研究文獻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俱樂部收斂”現象(如蔡和都陽,2000;Tsui,1991,1993)。中國地域廣闊,各地自然條件和市場容量的確相差懸殊。為了控制這些因素,我們也引入中部和西部兩個虛擬變量。②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模型沒有考慮經濟的結構方面。Barro等意識到新古典增長理論本身忽視經濟結構帶來的不利后果,試圖在對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進行實證檢驗時進行彌補。他們關于美國地區收斂的計量回歸中引入了一個結構沖擊變量,該變量是一個加權和,權數是各州中各產業的產出份額,被加權的因子是各產業在全國水平上的增長率(BarroandSala-I-Martin,1991,1992)。從理論層面講,Barro等理解的經濟結構沖擊變量基本上是側重需求方面的。考慮需求沖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本來無可厚非。但Barro等關于經濟結構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理解,違背了一個基本的經濟學道理。舉例來說,如果全國水平上工業增長快,而某個省區的比較優勢卻恰恰在農業,那么,這個省區里工業所占比重較小不見得就是壞事,并不見得不利于經濟增長。當然,在美國那樣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在較長的時期內,各個州之間的產業分工格局已經很好地順應了各自的動態比較優勢。這樣一來,Barro等理解的結構沖擊基本上就是相對短的時期里需求沖擊的影響。換言之,這個指標用在美國還能夠刻畫較短時期里的需求沖擊,但用來理解中國經濟結構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則力有不逮。這是因為中國各省區的經濟結構和其比較優勢吻合得不太好。
魏后凱(1997)的經驗研究中使用了完全按照Barro等定義的結構變量。③為了比較前述定義的發展戰略結構變量和Barro定義的結構變量,我們也根據Barro等的定義計算了1978—2000年期間中國29省區的結構變量,并將之納入回歸分析。①Cheng(2002)的研究認為,中國地區收斂的檢驗結果對于樣本選取比較敏感。具體而言,對京、津、滬三個直轄市的不同處理辦法將導致不同的結論。比如,Tusi(1996)將三大直轄市包含到臨近的省份之后,就會得到中國地區收入水平在改革之后趨異的結論。其他研究得到收斂的結論,是把三大直轄市作為獨立的經濟體來處理的。我們在后面將分別按照包含和不包含京、津、滬三大直轄市的情形進行計量分析。(2′)式中的隨機擾動項假定存在異方差問題,即:E(u)=0,Var(u)=σ2ζi。為此在計量分析結果中,我們報告WhiteRobustness方差協方差矩陣的估計結果。
3·計量分析結果
報告了計量分析結果。模型Ⅰ是新古典無條件收斂的框架。這個模型的估計結果似乎不支持新古典無條件收斂的假說。而且這個模型的擬合精度也比較差。模型Ⅱ和模型Ⅲ分別用TCI7885和TCI7899控制住改革開放初期和整個改革期間各省區市的發展戰略特征。從這兩個模型的估計結果來看,發展戰略越體現出趕超的特征,則勞均GDP增長率就越低;而且初始條件變量Ln(GDPPL0)的符號也符合理論預期。模型Ⅳ-模型Ⅷ的基礎是條件收斂框架。在這些模型中涉及到的發展戰略特征變量系數的符號均顯著為負。不過,盡管初始條件變量Ln(GDPPL0)的系數符號均符合預期,但是在一些情形下不顯著。其他的解釋變量中,儲蓄率、勞動力增長率和外商直接投資的系數符號均符合理論預期。不過這些系數符號的顯著性卻不穩定。而初始人力資本變量的系數符號卻相悖于理論預期,而且在有些場合之下系數的顯著性水平還比較高。當然,從中難以導出人力資本對勞均GDP增長的影響為負的一般結論來。
在報告的8個模型基礎上加入中部和西部兩個虛擬變量之后,所有模型的擬合精度均有比較大的改善。而且加入地區虛擬量之后,初始條件變量Ln(GDPPL0)的系數符號均顯著為負,說明新古典收斂機制仍然成立。而且計量結果表明,中部省份勞均GDP增長率顯著低于東部省區市;而西部省區又低于中部省份。這表明自然條件以及其他不可觀察的區域特征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過即使在加入地區虛擬變量之后,發展戰略特征變量的影響也仍然符合理論預期,從而充分說明發展戰略特征對勞均GDP增長的反面影響。在報告的模型基礎上再引入按照Barro等定義的結構變量進行回歸,得到的結果表明,這些結構變量的統計性質非常不理想。而與Barro等定義的結構變量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發展戰略特征變量。所有涉及到發展戰略特征變量的模型中,發展戰略特征變量的系數符號均顯著為負。不包含京津滬三大直轄市數據集的估計結果與上述包含三大直轄市的數據集的估計結果相類似,在此不再贅述。①
回歸結果有力地支持了我們歸納的理論假說,即如果一個經濟體推行違背比較優勢的戰略,以至于其TCI偏離TCI*,那么該經濟體的勞均GDP增長率將被顯著降低。不妨做一個簡單的匡算。本文的各個模型的估計結果表明,TCI7899的系數的估計值處于-0·0028和-0·0084之間,其中大部分估計值處于-0·003周圍。如果我們以-0·003作為TCI7899的系數的估計值,那就意味著,一個省區市的TCI對TCI*有一單位的偏離,將使其勞均GDP在1978—1999年期間每年的增長率降低0·3%。1978—2000年期間中國大陸省區市當中江蘇省的勞均GDP增長速度最快。如果我們以江蘇的TCI7899(其取值為2·9713)作為TCI*,則可以發現發展戰略對每個省區市經濟增長的影響。舉例來說,貴州的TCI7899為7·7422,所以該省的DS為4·7709。那么,貴州的勞均GDP在1978—1999年期間每年的增長率被降低了1·43%。
三、結論性評論
本文中我們研究了中國的地區差距問題。研究發現,一個省區市如果在發展其工業時推行違背比較優勢的戰略,那么其整體的GDP增長將受到負面的影響。中西部省區市的發展戰略較之東部省區市而言,更加接近于違背比較優勢的戰略,這是導致觀察到的1978年以來逐漸擴大的地區差距的重要原因。為了在國民經濟整體增長的同時縮小地區差距,對各省區市而言,尤其是對那些中西部省區市而言,亟需根據其各自的比較優勢優化其增量投資,以便調整其產業結構。一個地區要違背自身比較優勢而發展經濟,那么其企業就要選擇超越其要素稟賦結構的產業、產品和技術結構,進而這些企業就沒有自生能力,需要政府的保護和補貼。加入WTO之后中國政府保護和補貼企業的可能性大為降低。正是出于這個考慮,中國政府在“十五計劃”中正式全面確立了“比較優勢”原則在農業、制造業、服務業以及在經濟結構調整當中的地位。由于地區之間自然條件差異的作用,地區差距難以徹底消除。但是加入WTO之后的新條件下,地區差距拉大的趨勢將得到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