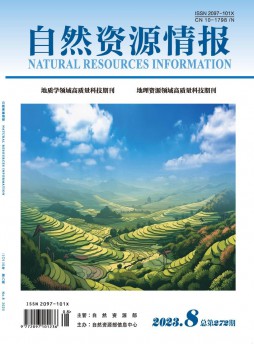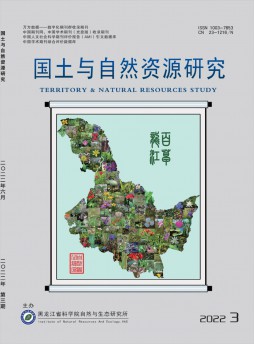自然資源與經濟增長的聯系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自然資源與經濟增長的聯系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荷蘭病”研究范式
這些經典模型完整地解釋了資源繁榮對傳統出口部門(農業)和進口競爭部門(制造業)的“擠出”效應。但是,早期“荷蘭病”研究范式主要傾向于對資源繁榮“為什么”、“是如何”、“是怎樣”引起經濟結構變化這類“實證性”問題進行理論描述和模型解釋。這種研究主要存在兩個理論“缺口”:一是這種資源繁榮引起的結構變化是一種“好”的變化,還是“壞的”變化;二是為什么這種短期的經濟結構變化會導致長期經濟增長能力的喪失。最早對此進行分析并試圖進行回答的學者是范•斯維德爾(1984),他較早地基于“干中學”原理構建了一個兩部門跨期“荷蘭病”效應模型,分析結果表明:制造業部門比非貿易部門具有更加明顯的“干中學”效應,如果這種“干中學”能夠誘發技術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那么資源繁榮對制造業的擠出必將顯著影響經濟長期增長能力。在范•斯維德爾的直接影響下,保羅•克魯格曼(1987)基于“干中學”和內生性技術進步建立了一個“動態比較優勢模型”。根據這個模型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很重要的結論:自然資源的發現可能導致另一些可貿易部門的永久損失,并在長期中降低社會福利水平。“資源繁榮—短期經濟結構變遷—長期經濟增長能力喪失”完整的“荷蘭病”效應理論解釋鏈條已經鑄成。薩克斯和沃勒(2001)進一步把這種“荷蘭病”理論解釋數理化、模型化,構建了一個基于主流范式的標準“荷蘭病”實證解釋模型。
二、“資源詛咒”研究范式
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荷蘭病”研究范式漸微,“資源詛咒”研究范式逐漸興起。飽受爭議的“資源詛咒”激起了學術界的廣泛研究興趣,特別是得到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的普遍認可。“資源詛咒”研究范式占據了發展經濟學的主流地位,并深深影響著眾多資源豐裕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政策與經濟實踐。“資源詛咒”研究范式以“資源詛咒”為核心范疇、以回歸分析為主要研究方法,形成了“資源詛咒”研究范式的基本或標準模型,即“S-W模型”。
(一)“資源詛咒”命題的提出及實證檢驗1988年,學者吉爾伯提出了一個經典命題:“自然橫財:是祝福還是詛咒?”1990年,學者理查德•M•奧蒂對世界范圍內普遍存在的自然資源豐裕而經濟表現不佳這種現象給予了較早的關注。1993年,奧蒂首次提出“資源詛咒”概念。1994年,奧蒂正式提出了“資源詛咒”假說,為后來相關的大量研究奠定了實證檢驗的基礎。其標志性研究成果是形成了“資源詛咒”標準實證檢驗模型。“資源詛咒”假說一經提出即引起廣泛的爭議,吸引了大量學者對相關問題進行深入研究。“資源詛咒”命題是否存在?這是頗有爭議的。1995年,美國學者杰弗里•D•薩克斯和安德魯•M•沃勒采用初級產品出品份額作為解釋變量對“資源詛咒”假說進行了開創性的實證檢驗研究,不僅首次驗證了“資源詛咒”命題的存在性,也為驗證這一命題提出標準模型和分析方法。根據這項研究,1970~1989年,97個樣本發展中國家中,只有兩個資源豐裕型國家(馬來西亞和毛里塔尼亞)年增長速度超過2%;其余95個樣本發展中國家的回歸檢驗表明,自然資源豐裕與經濟增長之間有顯著的負相關性,資源型產品(農產品、礦產品和燃料)出口占GDP的比重每提高16%,經濟增長速度下降1%(見表2)。2001年,薩克斯和沃勒[9]進一步把“S-W模型”發展成為標準的實證解釋模型,為揭示“資源詛咒”的作用渠道和傳導機制做出奠基性貢獻。其核心邏輯是:在回歸分析中引進一種解釋變量X因素,X因素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如果資源繁榮“擠出”X因素,則可以利用這種“擠出”機理來解釋“資源詛咒”。“擠出效應”是“荷蘭病”研究范式的核心結論,借鑒了“荷蘭病”“擠出”邏輯的“S-W模型”確實更加富有創新性、包容性、延展性,也更加具有解釋力。
(二)對“S-W模型”的拓展和完善大量學者主要從兩個方面對“S-W模型”進行了拓展和完善。第一,引進更多的解釋變量,應用實證檢驗模型對這種負相關關系作了更為廣泛而深入的研究(Le-ite,Weidmann,1999;Gylfason,2001;Sala-i-MartinX,1997;Sala-i-Martin,Subramanian,2003)。TobiasKronenberg(2004)[14]應用“S-W模型”對20個轉型國家的“資源詛咒”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這些轉型國家存在顯著的“資源詛咒”現象。多數學者肯定“資源詛咒”,但也有不少人對“資源詛咒”命題提出了質疑。例如,斯汀杰斯(2001)指出,根據“S-W模型”本身,如果采用資源儲量或者資源產品產量來替代“S-W模型”的初級產品出口與出口總額的相對比例來作為解釋變量,則“S-W模型”回歸分析結論并不是很強,即1970~1989年間資源豐裕與經濟增長之間并沒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而如果采用1970年以前的數據,即使像薩克斯和沃勒一樣采用初級產品出口份額作為解釋變量,也能得到相反的回歸分析結果:資源豐裕國家的經濟增長率都要高于資源貧瘠國家,換言之,資源豐裕與經濟增長之間呈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再如,默爾魯姆、莫安妮和托維克等(2002)則用一個精美的模型令人信服地證明:資源豐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關系依賴于政府制度的質量。第二,引進更多的X因素,例如物質資本(GWright,JCzelusta,2002)、人力資本(EPapyrakis,RGerlagh,2004)、基礎教育(Gylfason,2001)、制度質量(Leite,Weidmann,1999)等,應用實證解釋模型對“資源詛咒”作用機制(或傳導機制)進行各種不同的“解釋”。這些解釋大致可以歸結為兩類:一是經濟層面的“荷蘭病”經濟學解釋,即“荷蘭病”機制;二是制度層面的政治經濟學解釋。荷蘭病”效應被當作不言而喻的傳導機制被置于“資源詛咒”范式研究框架之內,并成為“資源詛咒”研究范式的核心傳導機制之一。薩克斯和沃勒(2001)完美地把這兩類解釋統一納入實證解釋模型之中。
三、兩種研究范式的比較
盡管“資源詛咒”命題備受爭議,但“資源詛咒”研究范式卻已形成,無論是贊成者還是反對者,大多采用相同的研究范式。目前來看,“資源詛咒”研究范式已經基本確立并處于不斷擴展和發展中,將“資源詛咒”研究范式與“荷蘭病”研究范式作一簡單對比,有助于理解未來研究演進趨勢。
(一)研究對象上的差異“荷蘭病”研究范式主要研究資源快速繁榮給產業帶來的“結構變化”,這很可能受到當時流行的結構主義思想的影響;“資源詛咒”研究范式主要研究資源豐裕國家的總體經濟發展表現。
(二)研究內容的差異“荷蘭病”研究范式主要研究資源快速繁榮導致的產業“擠出效應”。“資源詛咒”范式的研究內容則由產業“結構變化”不斷向產業、社會、制度等方面擴展;不僅研究資源繁榮導致的“擠出效應”(包括產業擠出、資本擠出、創新擠出等),而且研究資源豐裕導致的各種政治、經濟、社會效應,如“租金攫取”、“尋租活動”、“腐蝕效應”、戰亂、暴力沖突、制度弱化等。
(三)研究方法的差異“荷蘭病”研究范式主要采用局部均衡模型或一般均衡模型進行分析。“資源詛咒”研究范式主要采用變量相關回歸分析與政治經濟學分析。
(四)研究范圍的差異“荷蘭病”研究范式主要研究范圍局限于一國,或者給定國外因素,著力分析資源繁榮導致的國內產業結構變遷,即一國內部不同產業的非對稱增長。“資源詛咒”范式研究從一國轉向跨國研究,從一國內部不同產業的非對稱增長轉向資源依賴不同國家的相對增長,從對一國內部產業結構變化的“解剖”轉向對不同國家之間相對經濟表現的“解釋”。
(五)研究價值取向的差異“荷蘭病”范式主要進行理論實證研究,較少進行規范性研究,研究目標主要是揭示資源快速繁榮對經濟結構的作用機制。“資源詛咒”范式不斷從理論實證研究轉向政策規范研究;由發達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從科學性走向辯護性。例如,過去20年來國際上日益流行的“資源詛咒”實證研究,“有意”或者“無意”地把廣大發展中國家差強人意的經濟發展歸因于其自身的資源豐裕。或許,這是一個錯誤的理論研究取向,一個只有“上蒼”才能“負責”的結論。言下之意是:你們之所以貧困和發展落后,只是因為上蒼過于眷顧你們,賜予你們過多的自然資源財富,終究受到懲罰從而遭受“資源詛咒”。或許,這是一個“人為”或者“故意”的錯誤,是一種用于掩蓋事實真相的“陰謀”。這種“錯誤”的表現之一,就是國際學者僅僅選取人類歷史發展長河中的“一小段”,即20世紀60年以來的發展片斷作為對“經濟增長與資源豐裕”之間進行回歸分析的數據樣本,從而得出了二者之間具有普遍的“相當顯著的負相關關系”的著名結論。其中,最典型、最著名的Sachs-Warner回歸分析采用的是97個發展中國家1970~1989年的數據樣本。但是,有些學者顯然也已經意識到了這一不足(TobiasKronenberg,2004)。
四、“資源詛咒”研究范式替代“荷蘭病”研究范式的演進趨勢
近20年來,國際上主要流行“資源詛咒”研究范式,并占據了發展經濟學的主流地位。“資源詛咒”研究范式就像一股“潮流”,似乎大有取代“荷蘭病”研究范式之勢。但是,我們認為,“資源研究”范式不可能真正替代“荷蘭病”研究方式,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兩種研究范式的本質區別決定了不可能簡單地進行研究范式替代這兩種研究范式不僅在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研究范圍、研究價值取向方面存在較大的差異,而且僅就研究科學性而言,二者也是不相上下。“荷蘭病”研究范式仔細考量一國內部經濟結構變化,在一定假設條件下構建精巧的理論模型,進行不偏不倚的實證研究分析,得出了富有真知灼見的道理。盡管“資源詛咒”范式研究采用的“S-W模型”本身無懈可擊,但是在具體應用“S-W模型”進行實證研究時,卻可以隨心所欲地“擇取”相關數據,“裁剪”歷史時間剖面,以便得到符合某種“胃口”或研究價值取向的“回歸分析結果”。這或許可以很好地解釋為什么“荷蘭病”研究范式一經提出便得到學術界的共鳴,備受推崇;而“資源詛咒”研究命題一經提出卻引起學術界的分歧,飽受爭議。“資源詛咒”范式研究結論把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差異的原因引向其“內部”因素,例如自身的尋租、腐敗、教育和人力資本投資不足;而“荷蘭病”效應具有明顯的“外部”性特征,如資源品的出口和貿易品的進口、匯率變動等。任何國家和民族經濟社會的發展都是自然歷史過程,如果都像“資源詛咒”研究范式那樣,不顧經濟發展的歷史聯系,隨心所欲地“擇取”相關數據,“裁剪”歷史時間剖面,以便得到符合某種“胃口”或研究價值取向的所謂“回歸分析結果”,則無論采用的解釋模型怎么完善,回歸分析方法再怎么科學,回歸分析再怎么精確,都只不過是把“騙人的把戲”演得好看一些。
(二)兩種研究范式的研究結論和價值取向難以相互替代“荷蘭病”范式主要進行理論實證研究,較少進行規范性研究,研究目標是揭示(主要是發達國家如荷蘭、英國、澳大利亞、挪威等,也涉及發展中國家如尼日利亞、馬來西亞等)資源快速繁榮對經濟結構的作用機制,很少帶有偏見,得出的結論具有更多的科學性;而“資源詛咒”范式也許是出于為“全球化”或某種傾向辯護的研究取向,隨心所欲地“擇取”相關數據,“裁剪”歷史時間剖面,所得出的結論表面似乎“科學”,但實際上卻帶有相當的誤導性、欺騙性和辯護性。換言之,穿著科學分析手段外衣的“S-W”模型被“操縱”或者被“御用”了。斯汀杰斯(2001)[15]曾經指出,如果采用1970年以前的數據,即使采用初級產品出口份額作為解釋變量,根據“S-W模型”只能得到相反的回歸分析結果:資源豐裕國家的經濟增長率都要高于資源貧瘠國家,換言之,資源豐裕與經濟增長之間呈明顯的正相關關系,而不是負相關關系。基爾菲森(2001)也不得不承認:“S-W模型幾乎沒有將長期因素包含在內,從50年的經濟發展周期來看,資源富集國家的自然資源對經濟的影響是正向的,我們不能從中間截取20年的數據來證明自然資源是經濟增長的阻礙因素。”[11]實際上,許多發達經濟體自身根本就沒有能源資源,全部依賴外部供應。交通運輸成本大幅度下降和經濟全球化發展使得發達國家全部依靠進口發展中國家的石油、天然氣、煤炭等能源資源變得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可行。
(三)從廣大發展中國家發展實踐和研究現狀上看也不能簡單地進行研究替代誠然,“資源詛咒”研究范式一方面公正地指出了自然資源相對豐裕的發展中國家其內部存在的諸如產業擠出、人力資本擠出、制度弱化、產權模糊、浪費、腐敗、尋租、沖突等問題,并針對性地提出了治理對策措施和建議,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另一方面卻又主觀地(或帶有偏見地)把發展中國家落后表現簡單地(就像“S-W”模型回歸分析結論、結果歸因分析所指向的那樣)歸咎于“上蒼”或者歸咎于其自身,從而非常巧妙地“繞開”或者“閃躲”最近半個世紀以來由發達國家主導、新自由主義鼓吹的“全球化”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種種不利影響(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為之,結果都一樣),這些是值得商榷的。特別是從廣大發展中國家切身利益的視角來看,至少發展中國家的學者是不會簡單地接受這樣的理論評判的。更進一步說,要真正解釋、理解廣大發展中國家過去50年的發展經驗、目前的發展困境并提出相應的解救措施,不得不從其經濟內部結構變遷的視角進行深入的研究,這就不得不采用“荷蘭病”研究范式。總之,“荷蘭病”研究不會簡單地被“資源詛咒”研究替代,至少從發展中國家視角來看仍然還有重要的理論研究價值和經濟實踐意義。
作者:郝玉柱敖華單位:北京物資學院經濟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教學與研究》編輯部
- 上一篇:淺析生態建筑設計(共2篇)范文
- 下一篇:自然資源優先用益權思考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