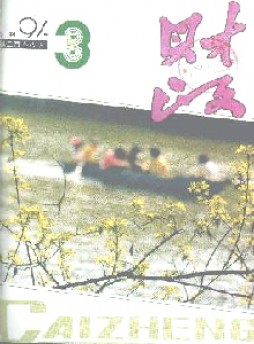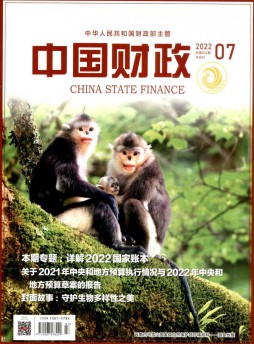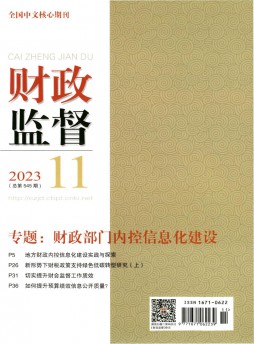財政分權下環境污染問題研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財政分權下環境污染問題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模型構建與變量選取
(一)基準模型的設定和變量選取基于省級面板數據,財政分權變量對廢水、廢氣、固體廢棄物環境影響的分析,本文主要從以下三個計量模型展開。首先,按照Keenet.al(1997)、李猛(2009)、鄧玉萍(2013)等文獻的回歸思路,借鑒其關于財政分權、地方政府競爭等與環境污染的分析機制。其中,是第i個省在第t年的污染程度,分別用工業“三廢”來表示。是第i個省在第t年的財政分權程度。交叉項是財政分權與外商直接投資人均值的乘積,表示財政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競爭,用來刻畫地方政府競爭水平。其中表示不可觀測的省或直轄市的特質,是隨機擾動項,假設與解釋變量無關。其中,本文衡量環境質量的因變量指標有三個:各省歷年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廢氣排放量和工業固體廢棄物排放量,變量水平越低則該區域的環境污染水平越低。對于財政分權程度的測度,本文以各地區財政收入/中央政府財政收入的百分比全面反映我國財政分權趨勢及其影響。在控制變量設置中,對于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構建,本文選取了省級人均實際GDP,通過采用以2003年為基期,利用平減指數獲得各省實際GDP變量指標。此外,在總體樣本數據中,本文以外商直接投資人均值來構建fdi指標,其中在區域引資水平的衡量上,以區域實際利用外資額為標準,估計原則與方法參考王立文(2007)的方法,同時依據當年的匯率水平轉換為人民幣單位,并以上述的GDP平減指數來消減價格影響。同樣,本文借鑒徐現祥等(2007)、沈坤榮等(2006)、馬曉鈺等(2013)等文獻,用工業生產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來衡量區域產業結構。對于城市化水平會影響環境質量的問題,本文采用馬曉鈺等(2013)的研究,用各省非農人口占總人口比值衡量城市化水平。
(二)地方政府行為模型的構建1.地方政府的節能環保支出行為通過上述文獻的研究,借鑒Dewatripom和Maskin(1995)等文獻的思路,本文基于省級面板數據,引入地方政府節能環保支出這一變量,分析地方政府的節能環保支出行為對環境污染的影響。相對于基準模型(3),模型中加入變量inv,表示各類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即以ln_water、ln_air以及ln_solid分別代表廢水污染治理支出、廢氣污染治理支出以及固體廢棄物污染治理支出等。如果系數是顯著的,則說明財政分權通過地方政府節能環保支出行為對環境污染發揮作用。X為其他解釋變量。2.財政轉移支付行為基于Boadwaye等(2009)等面板模型,本文采用省級面板數據,并構建中央政府轉移支付變量,以及中央政府轉移支付變量與財政分權變量的交叉項,以分析財政分權下中央政府轉移支付行為對環境污染的影響。相對于基準模型(3),模型中加入變量,表示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占該省財政總收入的比重,交叉項刻畫中央轉移支付對fd的邊際影響。如果回歸結果發現和是顯著的,則說明財政分權通過中央轉移支付發揮作用。X為模型中的其他解釋變量。3.污染產業發展行為在高污染產業的確定上,本文參考沈洪濤和李余曉璐(2010)的做法,以采掘、金屬非金屬、石化塑膠、生物醫藥、水電煤氣、紡織服裝皮毛、食品飲料和造紙印刷作為重污染行業。基于省級面板數據,引入各地高污染產業增加值比重這一變量,分析高污染產業發展行為對環境污染的影響。相對于基準模型(3),模型中加入變量1,主要衡量高污染產業增加值對環境污染的影響。如果系數顯著為正,說明財政分權通過地方政府吸引高污染產業來發展經濟的行為加劇了環境污染。
(三)估計方法的選取本文主要選取系統廣義矩估計(SystemGMM)的模型估計方法,對上述三個面板模型分別進行估計。SystemGMM模型由Arellano和Bond(1991)、Arellano和Bover(1995)以及Blundell和Bond(1998)發展起來。而在方差計算上,Windmeijer(2005)指出通過有效的GMM兩步(GMMtwostep)估計法計算出來的標準差,能顯著降低小樣本情況下的估計偏差。據此,本文采用穩健的二步法估計面板模型的標準差。選取這一估計方法主要基于三點理由:一是本文采用年度數據度量環境污染程度,考慮到環境質量在時間上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持續性,會導致解釋變量與隨即擾動項的相關,出現解釋變量的內生問題;二是各省、直轄市本身可能存在不可觀測的固定效應,如果這些不可觀測的固定效應與被解釋變量相關,將會影響估計的一致性;三是本文采用的度量經濟、社會的指標中,存在相互決定的可能(如人口密度和城市化水平,經濟發展水平與工業化比重等)。因此,控制這些解釋變量潛在的聯合內生性十分重要。
二、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模型的實證分析模型(1)結果表明,以各地區財政收入占中央政府財政收入的百分比衡量的財政分權程度與廢水污染、廢氣污染與固體廢棄物污染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即現階段財政分權體制下,我國財政分權體制改革給地方政府帶來了極大的財稅激勵,對地方政府的環境規制行為產生了顯著影響,進而惡化了區域環境質量。以財政分權程度與外商直接投資變量構建的地方政府競爭與環境污染在1%水平上呈現顯著負相關關系,說明了地方競爭程度的上升對環境污染存在顯著的抑制效應。這與以往研究中地方政府競爭會產生“競爭到底”的結果存在一定的差異性(De'murger,2001)。從本文的實際出發,在以收入角度衡量的財政分權體制中,地方政府競爭對區域環境的改善效應表現如下:其一,人均財政收入較高的地區,更有能力加強區域環境治理的投入,進而改善環境質量,獲得層次更高的外資的青睞;其二,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可以帶來資本、技術和先進的管理經驗等,在促進區域增長同時能夠帶來較多的溢出效應,提高了區域環境治理的水平與質量;其三,外商直接投資在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同時,能夠顯著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保障和促進了地方政府對環境、教育等涉及區域居民福利的公共產品的財政投入,從而優化了區域環境財政支出結構。(沈坤榮、耿強,2001;江錦凡,2004)。可見,財政分權中地方政府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競爭是全方位的競爭。外商直接投資不僅能夠提高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而且在改善區域投資環境以及公共產品投資等方面具有積極效果,使得在本文的回歸分析中地方政府競爭與環境污染指標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模型(2)的結果中,首先,就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與環境污染間的關系而言,除廢水污染之外,基本上可以驗證“環境庫茲列茲假說”(EKC)在我國是成立的,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衡量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在1%的顯著水平上為正相關,但是廢水污染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系不穩定,并沒有驗證EKC假說,因此,從廢水污染的指標來看,經濟發展水平與環境污染間是去聯系化的(楊瑞龍等,2007);其次,在外商直接投資與環境污染的回歸分析中,外商直接投資與廢水污染、廢氣污染以及固體廢棄物污染間在1%的水平上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說明財政分權過程中地方政府間的競爭行為帶來了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對區域環境污染的改善起到了積極的正面效應,這也一定程度上證明了外商直接投資的“污染天堂”假說以及發達國家污染產業轉移的假說在此是不成立的(鄧玉萍等,2013)。此外,外商直接投資可能帶來較為先進的綠色環保技術和治理經驗提高了地方政府環境治理的效率,并且帶動了區域產業結構的升級轉型,降低了產業發展中產生的環境污染負面效應,加之外商直接投資產生的區域溢出效應使得環保技術擴散和轉移,促進了外商直接投資環保效應的發揮。再次,就產業結構與環境污染而言,以各省級第二產業的增加值與GDP的比值來衡量的區域產業結構狀況與環境污染間在1%水平上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說明區域工業化比重將加劇環境污染程度。模型(3)的結果表明,財政分權仍與環境污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說明財政分權程度的提升將惡化區域環境質量。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仍然會對區域環境污染產生顯著的抑制作用,“污染天堂”假說在我國并不完全成立。經濟發展水平與環境污染仍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說明財政分權進程中以地區生產總值為主的政績考核標準一定程度上使得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過程中,以犧牲區域環境為代價,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以第二產業增加值衡量的產業結構,仍然與環境污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對于其他變量而言,其一,人口密度與環境污染顯著負相關,說明人口密度的提高將會降低區域環境污染水平,由于本文采用的數據時間段是2003—2010年,因此人口密度對環境質量的改善作用可能與我國實施的新型城鎮化戰略以及產業結構轉型加快有關。其二,城市化水平也基本上與環境污染在1%水平上顯著負相關,這進一步說明了新型城鎮化戰略、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的效果初顯,使得區域環境質量改善。其三,環境信訪與廢水、廢氣和固體廢棄物三類污染間的關系在1%水平上顯著,其中環境信訪與廢水污染為顯著正相關,環境信訪與廢氣和固體廢棄物兩類污染為顯著負相關。這也反映了以環境信訪為途徑的居民環境偏好表達機制,與環境污染間的關系雖然顯著但相關性并不穩定,環境信訪機制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財政分權中激勵扭曲程度,促進地方政府與轄區居民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吻合,從而改善區域環境質量。
(二)地方政府行為模型的實證分析1.地方政府的節能環保支出行為通過模型(4)回歸結果可以看出,首先,廢氣污染的環境治理支出與環境污染在1%水平上顯著,即廢氣污染治理支出對廢氣污染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廢水污染環境治理支出和固體廢棄物污染環境治理支出并未對環境污染呈現顯著的抑制效應,這與模型考慮到環境信訪、城市化水平等諸多控制因素有關。其次,在加入環境治理支出后,財政分權變量與環境污染間仍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且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環境治理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對環境污染存在抑制作用,但并未改變財政分權與環境污染之間的正向關系。據此可以驗證分權過程中地方政府節能環保支出與環境污染之間的內在作用機制,以及地方政府在財政分權中對環境污染的投資狀況與環保治理的偏好程度。其他變量系數的符號與前述模型基本一致。2.財政轉移支付行為通過模型(5)回歸結果可以看出,首先,中央轉移支付變量與環境污染基本上在1%水平上顯著,即中央轉移支付與廢氣污染、廢水污染以及固體廢棄物污染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轉移支付行為未能有效緩解地方政府間財政支出競爭中重基礎建設、輕公共服務的問題,此外受到稅收分成的激勵以及轉移支付機制的限制,地方政府不愿意內化外在的污染成本,環境質量改善不顯著。其次,從支出角度的財政分權(fd4)與中央轉移支付構建的交互項(bailfd4)來看,財政分權中轉移支付與環境污染變量基本在1%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說明在財政分權下對轉移支付的競爭性分配,有效地提高了區域環境治理效果。再次,在考慮到中央轉移支付機制后,支出角度衡量的地方政府競爭與環境污染存在正相關關系,這與轉移支付變量和環境污染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的內涵一致。其他變量系數的符號與前述模型基本一致。通過模型(6)回歸結果可以看出,首先,在收入角度衡量的財政分權下,高污染產業增加值與廢水污染、廢氣污染和固體廢棄物污染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一定程度上證明了在財政分權體制下,受到地方經濟發展排名以及官員晉升激勵的考核影響,高污染產業得到快速發展,從而加劇了區域環境污染程度,說明當前財政分權激勵扭曲下產業結構發展的不合理以及對區域環境產生的負面影響。其中,本模型在控制了產業結構變量后,高污染產業增加值仍與環境污染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驗證了財政分權產生的激勵扭曲效應促進了高污染產業的快速發展。據此可以發現,在區域經濟增長競爭以及區域要素流動競爭的壓力下,地方政府為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往往以放松環境規制、稅收優惠以及土地出讓等途徑給予企業大量的優惠,以長期的環境質量換取短期的產值增長,無疑對區域環境產生了巨大的壓力。其次,財政分權變量仍與環境污染在1%水平上顯著,并且財政分權與環境污染仍然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即隨著財政分權水平的提高,環境污染水平也會隨之上升。其他變量系數的符號與前述模型基本一致。
三、模型的穩健性檢驗
(一)穩健性檢驗:以支出角度測度財政分權程度由于已有研究中針對財政分權變量的指標構建爭議頗多,因此本文構建了指標fd4,即各地區人均財政支出/中央政府人均財政支出的百分比,對上述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同樣基于上述三個模型的設計,本文對fd4指標進行了相應的回歸。從表4檢驗結果可以看出,盡管估計值不同(這是由于采用不同指標引起的),但是系數的符號與前述模型基本一致。財政分權變量fd4與環境污染仍在1%水平上是顯著的。其他解釋變量與控制變量的回歸估計值基本與上述回歸一致。
(二)穩健性檢驗:OLS與靜態面板隨機效應在上述模型的分析中,本文分別使用了OLS以及面板隨機效應估計方法,對模型(3)-(6)的兩種回歸方法的分析中,以收入角度衡量的財政分權程度仍與廢水污染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地方競爭程度也呈現負相關關系,廢水治理支出對污染呈現抑制效應,高污染產業仍加劇了區域環境污染程度。其他控制變量系數的符號與上述模型基本一致,說明了本文構建模型的穩健性所在。五、結論與建議本文通過省級面板數據分析發現,首先,現階段財政分權體制下,不完善的財政激勵使地方政府對環境規制的行為發生扭曲:地方政府在橫向經濟增長競爭、稅收返還與政治晉升等激勵下,通過放松環境規制、貸款擔保等政策措施吸引企業投資生產,影響了區域污染物的排放,使得環境質量呈現惡化趨勢。分權過程中地方政府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競爭過程,增加了公共基礎設施等的投資,產生積極的正外部效應,改善了區域環境質量。其次,地方政府的環境治理支出行為即區域環境公共產品供給,在一定程度上對環境污染存在抑制作用,同時也為中央轉移支付機制中進一步加大環保治理的轉移支付力度提供實證支撐。再次,現階段中央轉移支付行為未能有效緩解地方政府間財政支出競爭中重基礎建設、輕公共服務的問題,此外受到稅收分成的激勵以及轉移支付機制的限制,地方政府不愿意內化外在的污染成本,環境質量改善不顯著。最后,財政分權中高污染產業得到快速發展,加劇了區域環境污染程度,激勵扭曲下產業結構發展的不合理對區域環境產生了直接的負面效應。本文的研究結論對當前分權改革中的環境治理提供了新的視角與實踐路徑,帶來的政策啟示主要有三點:首先,在分權改革中要全面考量地方政府行為的作用及其產生的一系列效應,注重宏觀政策引導與政策失靈的糾正。其次,健全區域間有差異的轉移支付機制,發揮其對區域居民福利改善的積極影響與作用。最后,不應再單純以GDP為唯一指標,應該從多種維度完善政績考核標準,促進地方政府對轄區內環境質量的重視,加大環境治理的投入。
作者:張欣怡 單位:北京語言大學
- 上一篇:環境藝術設計專業3dsmax教學思考范文
- 下一篇: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關系研究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