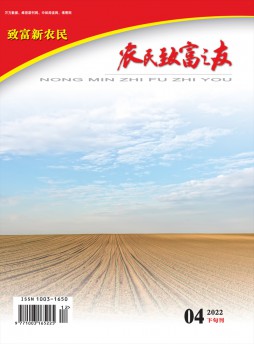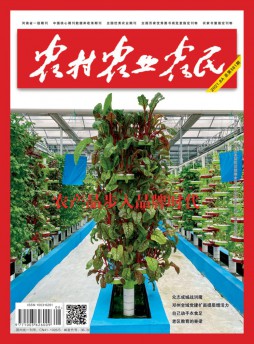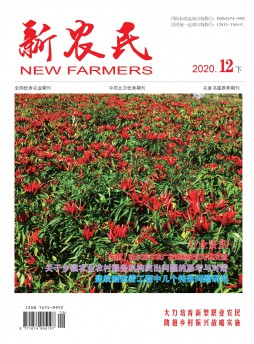農民成員權的集體土地論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農民成員權的集體土地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財產權語義下的成員權
確認農村集體組織成員的成員權,體現出土地對農民的保障功能以及土地與農民之間的歷史聯系。我們應該以集體組織成員的成員權為依托,賦予集體組織成員權更加豐富的財產內容,把成員權打造成一個復合的權利束,“涵蓋了土地承包權、征地補償款分配權、宅基地分配權、股份分紅權、集體福利獲得權等經濟權利以及經濟民主管理權利。”[4]1、承包權。承包權是指集體組織的成員基于成員身份依法承包本集體土地的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簡稱《土地承包法》)第5條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有權依法承包由本集體經濟組織發包的農村土地。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剝奪和非法限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承包土地的權利。”土地承包經營期滿后,承包權又以續展權的形式繼續存。《物權法》第126條規定:“承包期屆滿,由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繼續承包。”續展權不僅強化了成員權的身份性質,也使得土地承包經營權獲得了應有的穩定性。2、優先受讓權。優先受讓權是指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過程中,集體組織的成員基于成員身份享有的在同等條件下優先于非集體成員受讓的權利。優先受讓權是一項法定的權利。侵犯權利人的優先受讓權的轉讓行為,當屬無效。《土地承包法》第33條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時,在同等條件下,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享有優先權。”3、重大事項決定權。重大事項決定權是指集體組織成員對涉及本集體與自身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項依法通過會議的方式集體決定的權利。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以下簡稱《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24條規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項,經村民會議討論決定方可辦理:(一)本村享受誤工補貼的人員及補貼標準;(二)從村集體經濟所得收益的使用;(三)本村公益事業的興辦和籌資籌勞方案及建設承包方案;(四)土地承包經營方案;(五)村集體經濟項目的立項、承包方案;(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七)征地補償費的使用、分配方案;(八)以借貸、租賃或者其他方式處分村集體財產;(九)村民會議認為應當由村民會議討論決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項。”4、撤銷權。撤銷權是指集體組織成員作為村民會議這一農民集體組織最高權力機關的組成成員對村民委員會或村民代表會議的不適當的決定依據程序予以撤銷的權利。《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23條規定:“村民會議審議村民委員會的年度工作報告,評議村民委員會成員的工作;有權撤銷或者變更村民委員會不適當的決定;有權撤銷或者變更村民代表會議不適當的決定。”《物權法》第63條進一步規定:“集體經濟組織、村民委員會或者其負責人作出的決定侵害集體成員合法權益的,受侵害的集體成員可以請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銷。”5、宅基地分配權。宅基地分配權是指集體組織成員依法享有從本集體獲得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屬設施的權利。農村村民一戶擁有一處宅基地。宅基地因自然災害等原因滅失的,宅基地使用權消滅。對失去宅基地的村民,應當重新分配宅基地。宅基地使用權在某種程度上執行生活必需品職能,保障了農民“住有所居”。6、補償權。國家依法征用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作為農民集體成員的農民的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農民有權依法獲得相應的補償。[5]
二、我國集體土地征收進程中農民成員權內容的實質缺失
“隨著近年來全國各地建設規模的極度膨脹,大量耕地被征收,農村集體土地征收糾紛因之愈演愈烈,暴露于其中的法律和制度缺失也愈加引人注目。”[6]在農村集體土地糾紛中,凸顯了農民成員權內容的實質缺失。在征地事項上,主要涉及兩個問題。第一:征收決定是否依照“公共利益”做出?第二:對被征收人的補償問題。關于政府行使征收權的法律規定,主要體現在《物權法》、《土地管理法》等規定中。《物權法》第42條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單位、個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動產。”《土地管理法》第46條規定:“國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準后,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組織實施。”這些規定體現出的征地程序如下圖。隨著土地征收規模的不斷擴大,圍繞著農村集體土地征收而引發的糾紛愈演愈烈。在征收決定如何做出與對相對人如何補償這兩個核心問題上,國家隨后出臺了《征收土地公告辦法》、《國土資源聽證規定》等一系列規定,選擇征地補償這一問題來試圖化解圍繞著農村集體土地征收而引發的糾紛。而對公眾普遍關心的征收決定是否依照“公共利益”做出這一問題,則采取了回避的態度。依照這些規定,有關集體土地的征地程序演變成如下圖。集體土地征收程序的改進,也僅僅局限在“啟動征收程序”與“批準程序”之間增加了一個關于征地補償與安置方案的聽證程序,依然回避了征收決定是否依照“公共利益”做出這一關鍵問題。征收決定過程中集體組織包括其成員意志的缺失,依然使政府處于主導地位。正因為征收程序的不完善,現實中依然無法遏制政府采取“低價征收、高價賣出”的沖動,也導致土地財政成為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久治不愈的頑疾。正因如此,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關于審理涉及農村集體土地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11〕20號,以下簡稱《土地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這一司法文件,試圖為集體土地的征收程序增加一道司法救濟的防線從而對行政征收權加以必要的約束。《土地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一條規定:“農村集體土地的權利人或者利害關系人(以下簡稱土地權利人)認為行政機關作出的涉及農村集體土地的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提起訴訟的,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第四條規定:“土地使用權人或者實際使用人對行政機關作出涉及其使用或實際使用的集體土地的行政行為不服的,可以以自己的名義提起訴訟。”依照這些規定,有關集體土地的征地程序演變成如下。土地征收涉及到某種具體財產屬性的改變。而這種改變,本質上是國家(包括各級政府)與被征收人的具體利益發生了沖突。如果說我國現行土地征收程序中的弊端以行政權被濫用為外在特征的話,那我們就不應把主要原因歸結為“公共利益的模糊性”方面,而應把視角轉向如何約束行政權這種公權力上來。在現代法治社會里,能夠對行政權加以有效約束的,只能依靠司法救濟。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出臺《土地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這一司法解釋給我們最大的啟示,至少給我們指明了改進的方向。
三、創新農村社會管理體制,依法保障成員權的實現
(一)完善農民集體內部治理機制,促使農民集體組織的職能回歸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集體土地由“集體所有、集體經營”的生產模式轉變為“集體所有,家庭經營”的經營模式。作為集體土地的所有者,除了依法對土地的使用、承包事宜進行監督和處理外,受收入來源匱乏與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雙重沖擊,農村集體組織基本喪失了服務農業生產的功能,作為集體土地所有人,無法在農業生產結構調整、農業生產設施的改進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更多地異化成鄉鎮基層政權的派出機構。因此,從社會創新的角度考量,重塑農民集體組織的主體地位,首先要促使農民集體組織的職能回歸,讓其成為一個真正的土地所有人。完善農民集體內部治理結構,是促使農民集體的職能回歸的制度性保障。完善農民集體組織內部治理結構,是實現村民自治的必然要求。“村民自治”的本質是集體重要事務的處理要體現集體成員的意志。但作為一個“人合性”組織,村民的意志最終還是需要外化為集體的意志。因而,村民意志的實現最終依賴于完善的“意思產生、意思實施與監督機制”三位一體的內部治理結構。完善農村集體組織的內部治理機構,需要我們理順“村民會議(最高權力機關即集體意思產生機關)”、“村民委員會(集體意志執行機關)”的關系,把“村民代表會議”打造成農村集體組織內部監督機構而不是特定情況下的權力機構。
(二)完善成員權的司法救濟機制司法救濟制度的欠完善,直接導致在征地程序中農民集體組織成員的意志被公權力所淹沒,有違公平原則。在征地程序中,《征收土地公告辦法》、《國土資源聽證規定》等規定在“啟動征收程序”與“批準程序”之間增加了一個關于征地補償與安置方案的聽證程序,但這一程序依然是行政程序。更為遺憾的是,《土地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條規定:“土地權利人對土地管理部門組織實施過程中確定的土地補償有異議,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應當告知土地權利人先申請行政機關裁決。”而根據《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規定,行政機關的裁決為終局裁決。筆者認為,在司法救濟制度中,把土地征收程序中事關土地權利人切身利益的“征地補償、安置方案和公共利益認定”三個核心問題完全交由法院裁決。并且在提供司法救濟的時間方面,應當盡量前移。只要土地權利人與行政部門在這三個核心問題上存在爭議,就允許土地權利人提起訴訟,交由法院裁決司法救濟制度的欠完善,直接導致集體組織成員與集體組織之間的糾紛不能得到有效化解,不利于成員權的保護。突出表現為法院受理集體組織成員與集體組織之間糾紛的范圍存在不確定性。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23條規定:“村民會議審議村民委員會的年度工作報告,評議村民委員會成員的工作;有權撤銷或者變更村民委員會不適當的決定;有權撤銷或者變更村民代表會議不適當的決定。”但并不明確,當就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決議效力發生爭議以及村委會拒不執行相關撤銷決定時,是否允許集體組織成員向法院提出申請,由法院作出一個撤銷判決。《物權法》第63條賦予受侵害的集體成員可以請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銷集體經濟組織、村民委員會或者其負責人作出侵害集體成員合法權益的決定。但就法律的性質上講,《物權法》是一部關于物權的法律,其規定僅在于發生物權方面的爭議時才得以適用。當出現物權以外的糾紛時,是否允許集體成員向法院起訴,如就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決議效力發生的糾紛、集體成員資格的認定方面的糾紛、本村享受誤工補貼的人員及補貼標準方面的糾紛、村委會成員選舉方面的糾紛等,依然缺乏明確的規定。因此,筆者認為,在司法救濟制度中,應當允許集體組織成員與集體組織之間的一切爭議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以強化對集體成員權的保護。
作者:梁慶賓彭玉旺單位:廊坊師范學院社科部北華航天工業學院
- 上一篇:房屋登記發證的集體土地論文范文
- 下一篇:征收補償標準的集體土地論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