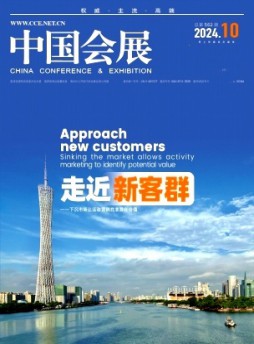中國農業政策改革的影響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中國農業政策改革的影響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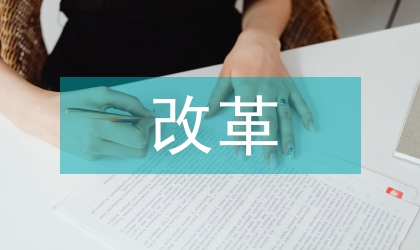
一、分析的框架與方法
(一)分析的范圍
為辨識中國農業政策改革的資源配置影響,本文選擇幾種主要農產品進行實證分析。根據1986—1995年農產品凈進口或凈出口情況,將農產品分為出口傾向農產品(AgriculturalExporbr,包括牛肉、豬肉、大米、玉米和大豆)和進口傾向農產品(AgriculturalImporbr,包括小麥、食糖、棉花和食用植物油)。與此同時,根據資料的可得性,我們選取1986—1995年作為分析的時間區間。
(二)農產品價格變化的觀察與分析
農業政策改革的影響首先表現為農產品相對價格水平或農業貿易條件的變化。因此,觀察和分析農產品價格變化的特征與規律,是辨識20年農業政策改革作用過程的基本方法。影響國內農產品價格變化的因素復雜而繁多,但邊境價格(進出口價格)、匯率以及國內價格干預政策(如農產品定購價格制度等)似乎更為顯著。其中,邊境價格由國際市場決定,具有外生性;國內價格干預政策由政府制定,具有內生性;匯率作為宏觀經濟變量也具有外生性。識別三者對農產品價格變化的影響可判斷農業政策改革的基本走向。根據Quiroz和Valdes(1993)提出的價格決定因素分析框架,假定a農產品在時間t的名義國內價格為NDPat,則有:NDPat=NBPat*NERt*(1+Tat)(1)其中,NDPat表示a農產品在時間t上的名義國內價格;NBPat表示a農產品在時間t上的名義邊境價格;NERt表示時間t的名義匯率;(1+Tat)表示a農產品的“關稅等值”,包含了政府價格干預政策的影響。
對公式(1)稍作變換,農產品實際國內價格(RDPat)可由邊境價格、匯率和價格干預政策來表示,即公式(2):RDPat=NBPatFCPIt*RERt*(1+Tat)(2)其中,RDPat表示a農產品在時間t的實際國內價格,等于名義國內價格扣除消費物價上漲指數,即RDPat=NDPat/CPIt;FCPIt表示國外消費物價指數;RERt(等于NERt*FCPIt/DCPIt)表示時間t的實際匯率,DCPIt表示國內消費物價指數。對公式(2)兩邊取自然對數和一階差分,可產生公式(3):^LnRDPat=^LnRBPat+^LnRERt+^Ln(1+Tat)(3)其中,“^”表示一階差分;RBPat表示a農產品在時間t上的實際邊境價格。公式(3)說明了實際邊境價格、實際匯率和價格干預與國內農產品價格的關系。其含義在于,如實際進口價格的變化率(^LnRBPat)、實際匯率的變化率(^LnRERt)和關稅等值或價格干預的變化率(^Ln(1+Tat))大于零,意味著將引致國內農產品價格上升;小于零表示將引致國內農產品價格下降,零值表示對國內農產品價格變動沒有起作用。在觀察和分析農產品價格變化時,公式(3)中的實際國內價格(RDPat)、實際邊境價格(RBPat,一般用進口價格)和實際匯率(RERt)為已知變量,而(1+Tat)的變化率作為計算殘差求出。在RDPat、RBPat和RERt的變化率較大時,作為殘差值的(1+Tat),不僅反映了價格干預影響,還包含了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但當RDPat、RBPat和RERt的變化率較小時,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影響可以忽略不計。
(三)農業保護影響的分析
判斷農業政策改革對農業部門影響的另一方面,是檢查和評估政府政策調整所引起的農業保護方向與程度或農業資源分配格局的變化。根據研究資料的可得性,本文主要使用三種分析方法,即名義保護率(NRP)、反貿易偏好(ATB)和生產者補貼等值(PSE)。名義保護率(NRP)。NRP(Balassa,1965)指農產品國內價格與國際價格間的差額占國際價格的百分數,即農產品的關稅等值。NRP的計算公式為:NRP=NDP-NBP•NERNBP*NER×100%(4)其中,NDP表示名義國內市場價格;NBP表示名義國際市場價格;NER表示名義匯率。當(1)NRP大于零,表明國內價格高于國際價格,國內政策有利于農業的保護;(2)NRP小于零,表明國內政策不利于農業部門,農產品受到負保護;(3)零值NRP表示國內政策對農業部門既不補貼,也不征稅。反貿易偏好(ATB)。ATB實際上是名義保護率的延伸,其計算公式為:ATB=(1+NRPx)(1+NRPm)-1(5)其中,NRPx表示出口傾向農產品的名義保護率;NRPm表示進口傾向農產品的名義保護率。(1)ATB大于零表示出口傾向農產品的保護水平高于進口傾向農產品,或者說是對出口傾向農產品的征稅水平低于進口傾向農產品;(2)ATB小于零表示對出口傾向農產品的保護水平低于進口傾向農產品,或者說是對出口傾向農產品的征稅水平高于進口傾向農產品;(3)零值表示沒有貿易偏好。生產者補貼等值(PSE)。PSE(Josling,1973)表示取消現有農業支持政策措施后,造成農業生產者收入的減少額與其原來收入額之比的百分數,是測算農業支持政策措施對農業保護程度的綜合指標,包含的政策措施范圍較廣,如價格支持、收入分配、生產要素補貼、政府一般服務以及其他對農業的支持措施。計算公式為:PSE=(GPP-NDP)*Qp+(NDP-NBP*NER)*Q+D-L+BQ*NDP+D-L×100%(6)其中,GPP表示政府收購價格,Qp表示政府收購量,NDP表示名義國內價格,NBP表示名義邊境價格,NER表示名義匯率,Q表示農產品的生產水平或國內供給量,D表示政府對農業的直接補貼,L表示征收的農業稅,B表示對農業的財政支持。(1)PSE大于零表明農業得到保護,正值越大,表示保護程度越高;(2)PSE小于零表明農業處在負保護狀態,農業收入向非農部門轉移,負值越大,表示農業收入轉移的程度越高,對農業的負保護程度越高;(3)零值PSE表示對農業既沒有保護也不征稅。
二、農業政策改革的影響:農產品價格變動的觀察
首先我們利用Quiroz和Valdes(1993)提出的價格決定因素分析框架,解釋國內價格干預政策、匯率和進口價格如何對國內農產品價格產生影響。
(一)農產品實際價格的變動趨勢
1986—1995年中國農產品價格指數資料來源:農業部,《中國農業發展報告’96》;農業部,《中國農村經濟統計資料》;國家統計局,《中國物價年鑒》,歷年各期。如前所述,由于農產品實際價格是名義國內價格扣除物價上漲指數,即RDPat=NDPat/CPIt,因此可得到反映中國農產品實際價格變化趨勢的圖1。圖1顯示了1986—1995年中國進口傾向農產品和出口傾向農產品實際國內價格的變化情況。(1)從總體上看,1986—1995年期間,農產品實際國內價格水平呈上升趨勢,并表現出波動特征。(2)進口傾向農產品的價格漲幅高于出口傾向農產品,高出5•3個百分點。比較而言,1986—1989年進口傾向農產品的上漲幅度低于出口傾向農產品,但1990—1995年進口傾向農產品的上漲幅度高于出口傾向農產品。(3)不同農產品的實際國內價格變化差別較大。如食糖和食用植物油的價格漲幅最高(達47•54%和46•88%),其次是豬肉(42•15%)和棉花(40•25%);大米和牛肉上漲幅度在30%以上;玉米、大豆和小麥價格漲幅分別為25•22%、21•11%和12•12%。(4)實際國內價格變化趨勢顯示,政府農業政策實際上更加傾向于鼓勵和支持進口傾向農產品的生產。
(二)匯率和邊境價格對
農產品國內價格的影響運用公式(3)可計算出表1,即主要農產品實際進口價格、實際匯率和價格干預的變化及其對國內農產品價格變化的影響。1•實際進口價格的影響。(1)對進口傾向農產品而言,1986—1995年其實際進口價格有大幅度上升,上升幅度為21•33%,表明其對國內價格的上漲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2)對出口傾向農產品而言,從總體上看,1986—1995年其實際進口價格下降了22•83%,說明沒有對國內價格的上漲起推動作用。2•匯率變動的影響。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經歷了幾次大的調整,人民幣對美元明顯貶值,1986—1995年實際貶值19•86%,名義貶值141•85%,貶值幅度1986—1990年(38•55%)高于1991—1995年(56•89%)。人民幣貶值一方面推動了國內價格上漲,另一方面放大了邊境價格對國內價格上漲的推動作用。3•農業政策改革的影響。(1)進口傾向農產品的實際國內價格、實際進口價格和價格干預在1986—1995年的變化幅度分別為36•70%、21•33%和-4•50%,其中所選擇農產品(棉花除外)的價格干預均為正值,說明政府所實施的農產品購銷與價格改革等措施對農產品國內價格上漲具有推動作用。(2)相對于進口傾向農產品(價格干預的變化幅度為-4•50%)而言,農業政策改革對出口傾向農產品價格(價格干預的變化幅度為34•37%)的影響更為顯著。(3)棉花的價格干預的變化率為-46•68%,說明政府棉花政策對棉花價格上漲起反方向的作用,這意味著棉花屬于被動提價。雖然棉花國內供給缺口較大,但分析表明,政府棉花購銷及價格政策沒有起到有效支持國內棉花生產發展的作用。
三、農業政策改革與農業保護水平的變動
農產品價格的上升意味著農業政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農業貿易條件。那么,農業政策改革對農業保護的方向與程度或農業資源分配格局究竟有怎樣的影響?利用公式(4)、(5)和(6),我們可對農業政策改革的影響作進一步辨識。
(一)名義保護率(NRP)
由公式(4),可估計中國1986—1995年主要農產品的名義保護率(表2)。(1)農業政策改革使農產品的保護水平有顯著的上升。名義保護率在1986—1995年上升了15•35%,其中1991—1995年間上升了17•01%,明顯高于1986—1990年間的上升幅度(1•31%)。(2)進口傾向農產品的保護水平高于出口傾向農產品。1986—1995年進口傾向農產品名義保護率(NRP)均為較高的正值,而出口傾向農產品NRP為負值,這意味著,過去的農業政策改革具有較強的進口替代戰略導向。(3)畜產品和棉花一直保持較高的負保護水平(如1995年豬肉和棉花的名義保護率分別為-72•63%和-5•28%);糧食類產品的保護水平正在上升;食用植物油和食糖一直處于高保護,尤其是食糖一直維持在相當高的保護水平(1995年的NRP達131•79%)。
(二)反貿易偏好(ATB)
那么,農業政策改革是否具有貿易偏好特征?利用公式(5)可進一步計算出中國1986—1995年反貿易偏好(ATB)的估計值(見圖2)。圖2顯示,中國農產品ATB值均為負值,這意味著1986—1995年中國在農產品貿易方面存在明顯的反出口偏好。因此可以判斷,農業政策改革所產生的政策效應實際上是給予進口傾向農產品的保護高于出口傾向農產品。也就是說,過去的農業政策改革具有鼓勵和支持進口傾向農產品國內生產(進口替代)的偏好。
(三)生產者補貼等值(PSE)
中國1991—1995年出口傾向農產品和進口傾向農產品的PSE如表3所示,1982—1995年中國農業生產者補貼等值。
(1)PSE的估計結果顯示改革以來中國農業保護水平具有波動特征,80年代中期保護水平曾呈下降趨勢,而90年代初則表現為上升趨勢。這與80年代中期所進行的農產品購銷及價格體制改革、90年代初調整農產品價格、設置農產品保護價的實際影響相吻合。由此反映農業政策的調整具有不穩定的特征,因而其對農業部門的影響也呈不穩定趨勢,這與政府政策目標希望實現農業的穩定增長相矛盾。
(2)進口傾向農產品的平均PSE為正值,出口傾向農產品的平均PSE均為負值,進口傾向農產品的保護水平高于出口傾向農產品。但90年代以來,出口傾向農產品保護水平有明顯上升趨勢,而同期進口傾向農產品的保護水平則沒有多大的變化。由此進一步說明80年代期間進口替代戰略在農業政策改革中居主導地位,而進入90年代以來,這種戰略已開始調整。
(3)90年代以來,受國內價格迅速上漲的影響,糧食產品中的大米、玉米和大豆的保護水平上升較快,到1994年和1995年國內主要糧食產品的國內價格已高出進口價格;小麥的保護水平卻有所下降;畜產品始終處于較高的負保護;食糖和食用植物油處于明顯正保護。在所有樣本農產品中,1995年PSE最高的是食糖(57•9%),PSE最低的是牛肉(-98•37%)。這與名義保護率的分析結果相一致,中國農業政策的改革似乎已開始顯現扭曲資源配置的跡象———對比較優勢相對較小的糧食的保護正在迅速上升。
四、農業政策改革與農業收入轉移
農業政策改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農業收入分配和利益格局?不同的農業政策改革措施引起收入轉移的方向與程度不同,如農業正保護措施(如農產品最低保護價、農業投入品補貼、農業科研推廣措施、政府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等)動員非農部門的資源向農業轉移(即收入轉入),相反,農業負保護措施(如現行的糧棉購銷制度等)可能會使農業部門的有限資源向非農部門轉移(即收入轉出)。為評價農業政策改革的這種收入效應,我們對收入在農業和非農業部門之間轉移的方向和強度進行了估計。與估計生產者補貼等值(PSE)相似,把農業收入轉移表示為農業產值的百分數,我們稱之為“轉移強度”。
價格與非價格改革措施均會引起農業收入轉移。本文估計的農業收入轉移主要包括:(1)價格調整所產生的收入轉移,即價格轉移;(2)非價格凈收入轉移(即直接補貼),包括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的生產性支出和用于農產品的價格補貼。由于計算沒有扣除物價上漲因素的影響,因此本文所估計的收入轉移并不是實際收入轉移,而是名義收入轉移。
1•20年的農業政策改革仍沒能抑制農業資源向非農部門的轉移,農業收入繼續向非農業部門轉移,而且隨著改革的深入,近年轉移強度有明顯的降低。如轉移強度最低為1993年的-3•4%,1995年轉移強度為-15•7%,明顯低于1986年的轉移強度(-21•4%)。
2•出口傾向農產品的收入轉出強度較大,1986—1995年年平均為-38•45%,但其轉移強度也呈減弱趨勢。其中,牛肉、豬肉和大米收入轉出強度甚高,年平均轉出強度分別為-28•67%、-25•39%、-77•57%;玉米和大豆的收入轉移的波動較大,收入轉入和轉出的情況均有出現。
3•進口傾向農產品總體上表現為收入轉入,且呈較為穩定的趨勢。但不同農產品的差別較大,如食糖和食用植物油的生產收入轉入;小麥的收入轉入的年份多于轉出的年份;而棉花表現為收入轉出,在1986—1995年中,收入轉入只有1986、1989和1995三年。
五、結果與討論
農業政策改革的影響遠不止本文所論及的范圍。但從本文有限的分析中,我們至少可以發現以下值得深思的問題:
1•農業政策改革對價格反應非常敏感,因此20年的農業政策改革顯示出典型的市場化特征,尤其是農產品購銷與價格體制的變革在促進農業高速增長的同時,也推動著國內農產品價格的顯著上漲,農業貿易條件也因此得到較大的改善。但是,盡管農產品購銷及價格體制的改革以及國內農產品價格的上漲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國農業的保護水平,但農產品價格的持續上升也帶來一些問題,如可能導致非農產品價格的上漲、具有誘發通貨膨脹的潛在因素;推動農產品成本的上升,降低農產品出口競爭的價格優勢等等。顯然,今后農產品價格的改革將成為一個非常敏感的領域。一方面,目前糧棉等主要農產品的購銷及價格體制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而另一方面,簡單的“放開市場”或“提價”改革似乎不是解決問題的理性選擇。
2•無論是對農產品價格變動的分析,還是對農業保護水平的估計,都已顯示出改革以來農業保護水平有明顯的提高,但是,農業政策改革仍然未能使中國農業走出負保護的政策環境,農業收入繼續向非農部門轉移。盡管國家農業投入水平在不斷提高,但仍沒有彌補價格干預所形成的農業收入流出損失。因此可以認為,20年的農業政策改革僅僅是對過去扭曲政策的部分調整。與此同時,宏觀經濟政策(匯率、邊境政策等)也在較大程度上決定著農業資源的配置結構。今后農業政策改革總的目標,應該是擺正農業部門在國民收入再分配格局中的地位,逐步抑制農業收入流出趨勢。
3•中國農業政策改革具有較強的內向性特征,改革始終未能繞開進口替代思想的左右。對進口傾向農產品的保護、而對出口傾向農產品的征稅,以及顯著的反貿易偏好,極有可能持續到今后若干年。今后農業政策改革的走向,應考慮對外開放和貿易自由化的潛在利益與影響,按比較優勢進行結構調整,提高資源配置的總體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