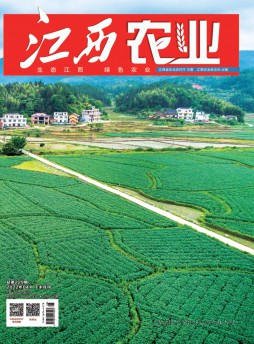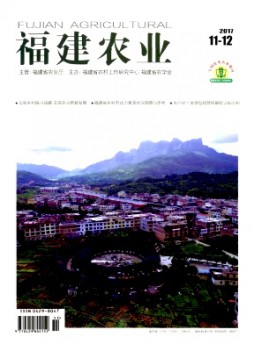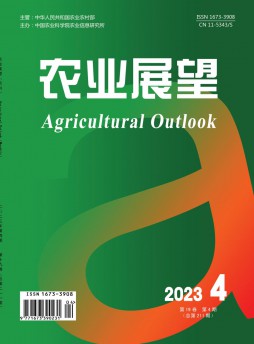農業土地資源集約利用研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農業土地資源集約利用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
我國民族地區已進入了工業化中期階段,新型城鎮化是當前民族地區研究的熱點,農業土地資源集約利用是實現新型城鎮化的物質保證。以我國八個民族地區省份為研究對象,在闡述新型城鎮化與農業土地資源集約利用耦合作用機理的基礎上,構建了基于復合指標的新型城鎮化與農業土地資源集約利用耦合體系,采用實證研究方法對民族地區新型城鎮化與農業土地資源集約利用耦合協調關系進行了定量分析,并根據實證研究結果提出了相應的對策與建議。
關鍵詞:
民族地區;新型城鎮化;農業;土地資源集約利用;耦合
我國地域廣闊,各區域間城鎮化發展水平差異極大,尤其是內陸民族地區,無論是城鎮化質量,還是數量都遠低于東部地區。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民族地區推進城鎮化,要注重民族特色,在土地使用等方面給予差別化支持。研究民族地區城鎮化發展問題,一直是國內學術界關注的焦點。本文研究的民族地區包括內蒙古、新疆、寧夏、西藏、廣西五個民族自治區和青海、云南、貴州三個多民族省份。從“十一五”起,這八個民族省區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城市化率達到35%以上、農業產值降到15%以下,這標志著八個民族省區已逐步過渡到工業化中期階段[1],協調城市與農村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城市反哺農村應成為民族地區未來發展的普通性趨同政策。新型城鎮化是我國城鎮化發展的新階段,新型城鎮化的關鍵在于土地集約利用[2],因此,新型城鎮化應秉承土地的可持續發展理念,本著集約、節約用地原則,走出一條不同于傳統“圈地式”城鎮化的內涵式發展道路。近年來,學術界開始對新型城鎮化與土地集約利用進行了研究,其研究內容更為關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城市或城鎮土地集約利用狀況,對農業土地資源的集約利用研究較少,對于民族地區農業土地資源集約利用的研究則更少,至于民族地區新型城鎮化與農業土地資源集約利用耦合關系研究還未見報道。然而,新型城鎮化與農業土地資源集約利用密切相關,定量揭示二者耦合關系,能更深入和有針對性地提出協調二者發展的對策和建議。
一、新型城鎮化與農業土地資源集約利用耦合機理
耦合源自物理學概念,是指兩個或多個系統由于相互作用而彼此聯系的物理現象,由于自然界物體間普遍具有耦合關聯屬性,對于耦合的研究已滲透到經濟和社會諸多學科中。耦合常用耦合協調度予以表示。本文所指的新型城鎮化與農業土地資源的耦合關系就是要揭示二者內部關聯關系,通過選取合理指標,分析、判斷二者關系是一種正向的推動力還是反向的互斥力。新型城鎮化的核心目標是改“化地”為“化人”,因此,增加城鎮人口,促進人口自愿合理聚集城鎮是建設新型城鎮化基本路徑。為達到“化人”目的,加快農民市民化進程,就需要通過產業調整與升級,推動一大批特色產業和可持續發展的現代服務業向園區和各級中心城鎮聚集。而所謂產業調整與升級,必須通過現代科技來引領,以現代技術為依托,最終完成新型城鎮化經濟的可持續綠色發展。因此,新型城鎮化就是要透過科技引領和經濟發展,實現人口和產業共聚集。單卓然等(2013)在深刻剖析新型城鎮化三大內涵的基礎上,提出集約城鎮化是實現新型城鎮化質量內涵的基礎,其關鍵在于通過集約和高效解決城鄉土地集約使用和城鄉各類設施高效利用的問題[3]。因此,集約化的農業土地資源是新型城鎮化的物質保障和建設依托,只有集約、高效的現代農業才能為新型城鎮化提供充足的高素質勞動力和可供持續開發的土地資源。當前,對于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研究頗多,大致可分為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4]。胡衛星(2014)基于經濟屬性和社會屬性進一步將城市建設用地評價指標分為土地投入與土地產出、土地利用狀況與土地利用結構四類。而當前被多數人普遍接受的農業土地資源集約利用仍然是指通過對土地投入更多的生產資料、勞動和技術,并采取現代農業管理方法,獲取更高收益的行為,即表現為一種投入與產出關系。基于農業土地集約利用的投入與產出關系,并考慮新型城鎮化綠色利用土地和可持續發展要求,本文建立包括土地投入水平、土地產出效益和土地利用程度和土地持續狀況等四大指標的農業土地資源集約利用指標。基于以上分析,建立了新型城鎮化與農業土地資源集約利用耦合機理圖,如圖1所示。
二、指標體系與研究方法
(一)指標體系構建新型城鎮化與農業土地資源集約利用間的相互耦合發展,是一個極為復雜、漸進和長期的過程,此過程中,縱向的時空特征和橫向的差異性相互交織。為定量揭示二者的耦合關系,并進行更好地測度,遵循科學性、整體性、動態性和可量化原則,參考已有研究成果[5],同時為避免單一指標的偏向性,構建了基于復合指標的新型城鎮化與農業土地資源集約利用耦合體系,如表1。由此可見,該耦合體系包括目標層、因素層、指標層三個層次,每個因素層均選取了1個核心指標作為解釋變量,下面將實證研究和觀測新型城鎮化與農業土地資源集約利用的耦合協調度(被解釋變量)。
(二)研究方法鑒于所選指標的正負屬性、量綱不一致以及量級差異,首先采用極差標準法對指標數據進行處理,見式(1)。原始數據的標準化處理后,為獲取新型城鎮化與農業土地資源集約利用的耦合關系,還須對二者綜合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基于以往理論,綜合測度的方法主要有三種,即專家打分法、層次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其中,專家打分法和層次分析法主要借助專家過往經驗對指標權重進行賦值,受人為因素影響較大。而基于多元數據處理的因子分析法,更為客觀,因此,本文選用因子分析法分析新型城鎮化與農業土地資源集約利用的耦合關系,在進行因子分析之前,需要首先進行KMO檢驗和Barlett檢驗。其中:α和β為待定系數,對于民族地區,新型城鎮化與農業土地資源集約利用同等重要,故取值為α=β=0.5,k為調節系數,k=2。然而,耦合度N僅僅描述了兩個系統間聯系的緊密,并無法解釋二者耦合發展的水平,因此,本文進一步引入耦合協調度CP來反映新型城鎮化與農業土地資源集約利用的耦合協調度,見式(4),0≤CP≤1,并且CP越大,表示所研究的兩個系統間耦合發展越佳,反之則越遜,具體的分類見表2所示。
三、實證研究及分析
(一)新型城鎮化與農業土地資源集約利用綜合水平分析基于上述八省、自治區2004年至2013年的統計數據,首先,運用極差標準法式(1)對數據進行處理;然后,對標準化處理后的數據進行KMO檢驗和Barlett檢驗;最后,運用因子分析法得到新型城鎮化與農業土地資源集約利用綜合水平。KMO檢驗和Barlett檢驗結果表明,所有八個省、自治區的KMO檢驗值均大于0.65,Bartlett顯著性水平均為0.000,小于0.05,其中,內蒙古、云南兩個省區的KMO值達到了0.8。這表明本文選取的8個指標適合作因子分析。八個民族省區2004年至2013年新型城鎮化與農業土地資源集約利用綜合水平見表3所示。表3說明,對八個民族省區而言,從2004年至2013年十年間,新型城鎮化與農業土地資源集約利用綜合水平總體均呈現出了不斷增長的態勢,尤其是2010年之后增長最為迅速,這表明最近幾年在國家城鄉統籌和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等戰略支撐下,民族地區城鎮化步伐逐步加快,特別是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了新型城鎮化思路,使得2013年數據比2012年均有大幅度提升。此外,各民族地區新型城鎮化與農業土地集約利用之間未表現出明顯的主導關系,二者綜合發展水平呈現出了交替重合增長的趨勢。
(二)耦合度與耦合協調度基于上面得到的八個民族省區2004年至2013年新型城鎮化與農業土地資源集約利用綜合水平數據,根據公式(2)至(4),計算得到八個民族省區耦合度與耦合協調度如表4所示。表4表明,八個民族省區耦合度呈現出了振蕩變化的趨勢,并且大約在2008年或2009年左右出現耦合度最小值;而它們的耦合協調度大都呈現出了U型變化趨勢,并且U型的低點也大約出現在2008年或2009年左右,之后,各省區大都經歷了瀕臨失調、初級協調,最終達到良好協調、優質協調的發展過程。
四、結論
(1)民族地區兩系統綜合發展水平趨勢總體良好。基于對近十年民族地區新型城鎮化與農業土地資源集約利用綜合發展水平的定量分析,發現民族地區近十年兩系統綜合發展水平態勢良好,數據由負轉正,且后勁較足。(2)民族地區兩系統耦合協調關系日趨強烈。基于近十年民族地區新型城鎮化與農業土地資源集約利用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雖然個別年份兩系統處于中度失調,除此外,大多在初級協調以上,且所有省區最終均發展為了優質協調,說明兩系統間相互作用明顯。但需看到,大多數省區的耦合協調度高于耦合度,說明兩系統耦合狀態還有發展空間。(3)提升管理水平,推動兩系統協調發展。2008年以來,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均獲得了大幅度增長,這與政府注重新型城鎮化建設,又強調提高土地資源集約利用密不可分。西方實踐經驗告訴我們,長期來看,城鎮化與土地集約利用是正相關的,因此,采取長期策略,而不是權宜之計,以制定新型城鎮化發展規劃基礎上的土地綜合利用、集約開發規劃是十分重要旳。
參考文獻:
[1]黃群慧.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階段、特征與前景[J].經濟與管理,2013,(7):5-11.
[2]王春敏.土地集約利用:新型城鎮化的關鍵[J].中國房地產,2013,(3):11.
[3]單卓然,黃亞平.“新型城鎮化”概念內涵、目標內容、規劃策略及認知誤區解析[J].城市規劃學刊,2013,(2):16-22.
[4]王梅,曲福田.昆山開發區企業土地集約利用評價指標構建與運用研究[J].中國土地科學,2004,(6):22-27.
[5]張勇民,梁世夫,郭超然.民族地區農業現代化與新型城鎮化協調發展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2014,(10):87-94.
作者:高新才 張冀民 單位:蘭州大學 經濟學院 蘭州交通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
- 上一篇:土地資源的預測評估范文
- 下一篇:土地資源的合理利用及管理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