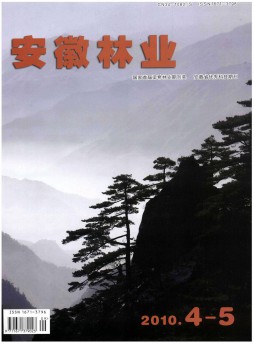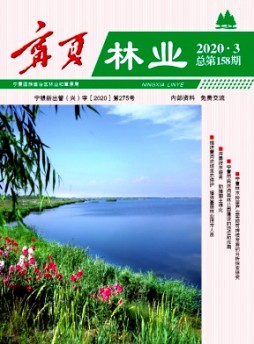林業資源犯罪中的若干問題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林業資源犯罪中的若干問題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并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報告更是提出必須樹立“綠樹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可見生態環境資源保護愈加得到高層的重視。結合我國的森林資源現狀,將保護和打擊林業資源犯罪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特別是針對盜伐、濫伐林木在客觀方面的辨析與濫伐林木在訴訟中如何處理的問題。以正確處理涉案木材問題,才能真正實現保護公民合法財產并打擊生態林業資源犯罪的雙重效果。
關鍵詞:濫伐林木;盜伐林木;客觀方面;違法所得
一、目前我國森林資源現狀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公布的《2015年全球森林資源評估報告》,1990年到2015年全球森林面積減少了19.35億畝,而中國的森林面積增長了11.2億畝。中國目前已經成為世界上森林資源增長最多和林業發展最快的國家。但據2014年我國的第八次全國森林資源清查結果顯示,全國森林面積2.08億公頃,人工林蓄積24.83億立方米,森林蓄積151.37億立方米,森林覆蓋率遠低于全球31%的平均水平,人均森林面積、人均森林蓄積低于世界水平,林業發展仍然面臨巨大的壓力和挑戰。2015年4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全國檢察機關關于開展“破壞環境資源犯罪專項監督活動”和“危害食品藥品安全犯罪專項立案監督活動”的方案》,2016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發起為期一年的第二次“兩個專項”監督活動,2017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發起為期二年的第三期“兩個專項”監督活動,體現了檢察機關積極回應人民群眾日益痛恨的環境犯罪問題,另一方面環境資源犯罪理論調研也在如火如荼的開展。筆者結合司法實踐中針對涉及林業資源犯罪中的幾個問題提出一些粗淺見解,以期拋磚引玉。
二、行為人濫伐的林木在刑事訴訟中應如何處理
對于司法實踐中行為人濫伐自己享有所有權的林木涉嫌犯罪時,其濫伐的林木應如何處理,理論界有不同認識。一種觀點認為應將濫伐的林木認定為犯罪所得予以追繳。理由如下:首先,該觀點得到了司法解釋的支持。根據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濫伐自己所有權的林木其林木應如何處理的問題的批復》,對屬于個人所有的林木,也是國家森林資源的一部分,濫伐屬于自己所有權的林木,構成濫伐林木罪的,其行為已違反國家森林保護法規,破壞了國家的森林資源,所濫伐的林木即不再是個人的合法財產,故對于犯罪嫌疑人實施破壞林業資源的行為取得的林木,屬于違法所得,應當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其次,從堅持體系解釋的觀點出發,根據我國《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條第三款規定的非法收購、運輸盜伐、濫伐的林木罪,與《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規定的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法條競合關系,是特別法與普通法的從屬關系,且屬于從屬關系中的整體競合。探索立法者的立法理念,對于非法收購、運輸濫伐林木的行為也具有社會危險性,故立法者將該行為認定為犯罪予以打擊,應當將濫伐的林木“犯罪所得”處理為宜。如果濫伐林木罪的林木不屬于違法所得,那么就不存在下游的非法收購、運輸濫伐林木罪。筆者認為,根據我國《物權法》、《森林法》的規定,宜將濫伐的林木在刑事訴訟中認定為犯罪嫌疑人所有的合法財產,犯罪嫌疑人的濫伐行為不具有產生違法所得的效果,不因行為人實施對其財物處分行為的違法而改變行為人對其財產所有權的定性,即不再作為違法所得予以追繳。首先,根據我國《森林法》、《森林法實施條例》對林木保護、管理、采伐、法律責任等方面的規定,在違法行為人承擔的行政責任層面肯定了濫伐的木材所有權歸屬違法行為人。《森林法》第三十九條對于盜伐林木的行政責任規定責令補種,沒收盜伐的林木和違法所得并處罰款;對于濫伐林木的行為是責令補種并處罰款。由此可見,《森林法》對盜伐林木和濫伐林木的行政責任作了不同類型的處罰規定。雖然沒收違法所得、罰款等行為都是《行政處罰法》規定的六類行政處罰行為,但是《森林法》作為法律可以對具體行政處罰作出規定,故對于盜伐、濫伐林木的行為只有按照《森林法》的規定處罰類型、幅度執行處罰。《森林法》對濫伐林木的行政責任并未規定“沒收濫伐的林木和違法所得”,至少在違法行為人承擔的行政責任層面肯定了濫伐的木材所有權歸屬違法行為人。其次,結合我國《物權法》第三十九條規定,所有權人對自己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但《物權法》、《森林法》一方面將森林資源作為自然資源規定為國家和集體所有,一方面又將林木規定可以為多種權利主體所有,造成了“一物兩權”的現象。此外,對于林權分包后存在多個林權共有人的情況下,倘若將濫伐的林木認定為犯罪違法所得,那么其中未涉嫌濫伐林木犯罪的行為人的物權也無法保障,林木所有權共有人又不具有被害人身份,不利于保護合法行使物權人的權利,倘若直接認定為犯罪所得予以追繳則有失妥當,不符合客觀林權共同占有的實際現象。
筆者認為,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濫伐自己所有權的林木其林木應如何處理的問題的批復》忽略了保護個人的合法財產所有權,在法律的權益保護規定存在沖突時,制定了損害個人合法財產所有權為代價來保護國家森林資源的制度,但這種因法律規定不健全、不完善造成的惡果,不應該由林木所有權人來承擔。最后,筆者認為,非法收購、運輸濫伐的林木罪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二者在保護內容上有一定的交叉,但二者對所保護的法益存在差異,雖然二罪都妨害司法活動的順利進行,但涉及保護的法益內容上非法收購、運輸濫伐的林木罪更注重對森林資源的維護,側重的是切斷濫伐林木行為的利益輸送鏈條。探討“犯罪所得”就必然要厘清其概念的法理基礎,方能正確把握具體案件中哪些物品屬于違法行為人通過犯罪所獲得的“財物”。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性質,理論上有多種學說,一是追求權說,即犯罪嫌疑人對被害人對自己的財產追求權造成困難的犯罪,其法益體現的是財產保護權;二是收益說,認為本罪的本質在于參與本罪所取得的不法利益;三是違法狀態維持說,認為本質是使由犯罪所形成的財產狀態得以維持、持續。張明楷教授認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以違法狀態為基礎同時考慮追求權說的綜合說。此外結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條認定“犯罪所得”和“犯罪所產生的收益”的理解,必須是通過犯罪直接得到的贓款、贓物和上游犯罪的行為人對犯罪所得進行處理后得到的孳息、租金等。但因為該林木原本屬于行為人所有,行為人對其林木進行經營管理,林木依舊在行為人的管理、控制下,并沒有改變其林木的性質和財產持有人的狀態,故濫伐自己的林木所取得的木材并不屬于犯罪所得。筆者認為,在刑事訴訟階段將濫伐的林木認定為犯罪嫌疑人合法所有的財產較為合理,不能因為犯罪嫌疑人的違法行為而剝奪其對林木享有所有權的權利。鑒于我國《刑法》對濫伐林木罪有可以并處或者單處罰金的刑罰規定,為達到對違法行為人的犯罪預防可以從判處罰金的角度來打擊其再犯罪能力,面對當前林業資源發展的態勢,在既加大對此類違法行為的經濟制裁的同時,又可以避免因為追繳濫伐所得林木所導致的其他矛盾,從法理上來說是合適的。
三、盜伐林木罪與濫伐林木罪的客觀辨析
《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條第一款規定了盜伐林木罪,結合“盜”字來理解本罪的主觀故意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客觀表現為違反《森林法》及相關保護森林和林木的行政法規,擅自砍伐林木的行為,行為違法性主要體現在“擅自”。對于盜伐林木罪中的“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最高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一)》(以下簡稱“《立案追訴標準(一)》”)第七十二條規定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涉嫌擅自砍伐國家、集體、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經營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或者擅自砍伐本單位或者本人承包經營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或在林木采伐許可證規定的地點以外采伐國家、集體、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經營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刑法學對于犯罪構成要求主客觀相一致的觀點,我們可以從本條規定的三類特定行為來推斷或者印證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為目的。對于擅自砍伐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經營管理的林木應屬于盜伐林木的行為這無任何異議,但對于第二種“擅自砍伐本單位或本人承包經營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也屬于盜伐林木的行為,在實踐中,有人認為這項規定并不合理乃至是矛盾的,理由是既然擅自砍伐他人承包經營管理的林木構成盜伐林木罪,那么擅自砍伐本人承包經營管理的森林或其他林木則不涉嫌本罪,因為不可能存在自己盜伐歸自己承包經營管理下的森林或其他林木。而無采伐許可證砍伐自己承包經營管理的林木則有可能構成濫伐林木罪,因為濫伐林木罪在《立案追訴標準(一)》第七十三條將無證采伐本單位所有或者本人所有的林木和超過采伐許可證批準規定的時間、數量、樹種或者方式采伐林木皆認定為濫伐林木罪。筆者不贊同上述觀點,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森林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及《立案追訴標準(一)》對盜伐林木罪、濫伐林木罪的規定是合理的,出現上述錯誤解讀司法解釋的原因在于沒有采用系統解釋的觀點來理解司法解釋的規定。濫伐林木罪是指違反《森林法》的規定,濫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數量較大的行為,行為違法性主要體現為“任意”。濫伐林木的客觀行為可以表述為三種類型:違反林木采伐許可證規定的時間、數量、樹種或者方式,任意采伐自己的林木;未得到許可,任意采伐屬于自己所有的林木;超過林業部門許可采伐的數量,任意采伐他人的林木。筆者認為,對于擅自砍伐本人承包經營管理的森林或其他林木,此處應解決的問題是:行為人擅自采伐本人承包經營管理的林木,此處的林木所有權人是否一定就歸屬于行為人?這里可以結合我國刑法上的“占有輔助人”的觀點。張明楷教授認為,當數人共同管理某種財物,而且存在上下主從關系時,此時刑法上的占有通常屬于上位者,而不屬于下位者。即使下位者事實上握有或者事實上支配財物,也只是單純的監視者或者占有輔助者。因此,區分濫伐林木罪和盜伐林木罪關鍵是區分“任意”和“擅自”,而不是區分是否經過林業部門的批準許可。只要行為人行為對象針對的是自己不享有所有權的林木資源,那么行為則違反盜伐林木的規定,如果行為人行為對象針對的是自己享有所有權的林木資源,那么行為則違反濫伐林木的規定。
[參考文獻]
[1]汶哲,劉勇.法條競合與想象競合簡析———以非法收購、運輸盜伐、濫伐的林木罪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為例.森林公安,2008(4).
[2]阮均.淺談物權制度對林業管理的影響.浙江林業,2008(3)
作者:樊興慧 單位:寶興縣人民檢察院
- 上一篇:對林業養護長效管理機制的建議范文
- 下一篇:林業傳統知識在生態文明建設的作用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