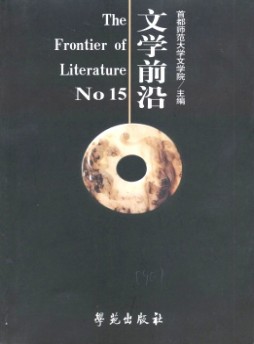文學(xué)地理批評思想初探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文學(xué)地理批評思想初探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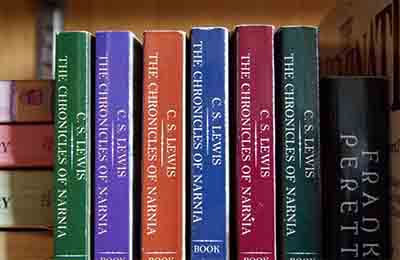
摘要:中國古代的文學(xué)地理批評,發(fā)端于先秦時期,成長豐富于漢魏六朝及其后,是中國文學(xué)批評的一大傳統(tǒng)。迄今學(xué)界尚無研究《文心雕龍》文學(xué)地理批評思想的專門論文,本文乃是首發(fā)。筆者關(guān)于《文心雕龍》文學(xué)地理批評思想研究包括上下兩篇,上篇主要論述了《文心雕龍》文學(xué)地理批評問題提出的依據(jù)、研究方法和基本內(nèi)容之要點,分析《文心雕龍》有關(guān)文學(xué)與地理的一般關(guān)系論的主要理論內(nèi)涵與思想基礎(chǔ)問題;下篇是對上篇提出的《文心雕龍》文學(xué)地理批評論題進行深入考論,將具體研究《文心雕龍》有關(guān)作家、作品及讀者與地理關(guān)系的批評論。本文為上篇,故謂初探。
關(guān)鍵詞:《文心雕龍》;文學(xué)地理;天人合一;“江山之助”
一、引論
一切文學(xué)的研究,文學(xué)的理論與批評,都是文學(xué)的詮釋。文學(xué)地理學(xué),其主要研究有三大理論向度①:第一,文學(xué)與地理的一般關(guān)系;第二,文學(xué)與文學(xué)的地域(區(qū)域地理)之關(guān)系;第三,文學(xué)與地域的文化之關(guān)系。人地觀不僅是人文地理學(xué)研究的核心內(nèi)容與科學(xué)理論基礎(chǔ)②,也是討論中國古代文學(xué)地理問題的理論依據(jù)。換句話說,文學(xué)地理學(xué)是一門跨學(xué)科研究,主要從文學(xué)與地理的關(guān)系出發(fā),以文學(xué)地理為其研究對象,不僅要研究地理及空間與作家及其創(chuàng)作過程、作品、讀者的關(guān)系,還要研究文學(xué)的“詩性地理”(文學(xué)想象、審美感知的地理)、文學(xué)的空間詮釋等問題。中國古代的文學(xué)地理批評思想,發(fā)端于先秦時期,是中國文學(xué)批評的一大傳統(tǒng),《文心雕龍》中的文學(xué)地理批評思想,正是這一批評傳統(tǒng)的繼承、豐富與發(fā)展,對此不容漠視。《文心雕龍》研究成果已經(jīng)較為繁富,例如,研究其《物色》篇“江山之助”論的論文,就有近二十篇之多等,并且涉及文學(xué)地理批評問題。③,盡管如此,但迄今尚無專門而較為全面地去研討其文學(xué)地理批評思想之論著。本文擬從《文心雕龍》全書出發(fā),從其理論與批評體系的整體性出發(fā),同時也從我們力圖構(gòu)建和理解的文學(xué)地理學(xué)的理論批評出發(fā),將二者具體聯(lián)系起來,討論《文心雕龍》有關(guān)文學(xué)與地理的一般的普遍關(guān)系的認(rèn)識問題。
二、《文心雕龍》文學(xué)地理批評問題的提出與研究方法
既然本文是第一次明確提出《文心雕龍》包含有文學(xué)地理批評思想,并予以探討,這就首先需要簡要論析如下兩個問題:第一,從文學(xué)地理學(xué)看問題,先秦至六朝時期文學(xué)地理批評發(fā)生發(fā)展情況如何?第二,依照上述對文學(xué)地理學(xué)簡要說明,《文心雕龍》的文學(xué)地理批評思想包括哪些內(nèi)容,是否符合其實際?文學(xué)地理批評思想,發(fā)端并奠基于先秦時期,而成長并豐富于兩漢魏晉南北朝及其后。作為我國北方文學(xué)和南方文學(xué)的代表性源頭的《詩經(jīng)》和楚辭的研究,其最早的經(jīng)典著作,就是漢代的鄭玄《詩譜》和王逸《楚辭章句》,都包含著豐富的文學(xué)地理批評內(nèi)容。班固《漢書·地理志》,繼承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有關(guān)文化地域的觀念,明確把人之性情、風(fēng)俗與“水土之風(fēng)氣”聯(lián)系起來,所謂“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cè)峋徏保袈暡煌邓林L(fēng)氣,故謂之風(fēng);好惡取舍,動靜亡(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④。這也集中體現(xiàn)在其關(guān)于《國風(fēng)》的分析之中,直接影響鄭玄《詩譜》以史地證詩的批評與詮釋方法。班固等“系水土之風(fēng)氣”說,直接可以追溯至先秦時期《管子·水地》篇等“人地關(guān)系”論的思想,由此還可以追溯至三代“易”學(xué)思想的發(fā)端⑤。人地關(guān)系的觀念,當(dāng)是先民從原始社會逐步發(fā)展到農(nóng)業(yè)文明社會的過程中產(chǎn)生的。《周易》坤卦《彖》辭有“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之論⑥,其實這也就含納了乾卦《彖》辭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tǒng)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的意義①,人文地理學(xué)與文學(xué)地理學(xué)所說的“人地關(guān)系”論中的“地”,包括古人所說的“天”“地”之大自然、人化的自然的內(nèi)容。繼先秦兩漢之后的六朝時期,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鐘嶸《詩品》以及顏之推《顏氏家訓(xùn)》等,都包含文學(xué)地理的批評思想,其中《文心雕龍》作為這一時期最杰出的文論著作,具有較為豐富的文學(xué)地理思想與批評內(nèi)容。《文心雕龍》前五篇所謂“文之樞紐”論,乃全書論文之綱領(lǐng),《原道》篇論析天地之文與人文之文,都是“道之文也”②,其對“自然(自然而然)之道”的論述,如下一轉(zhuǎn)語,我們認(rèn)為其中就蘊涵了文學(xué)與地理(自然)一般的普遍關(guān)系的思想內(nèi)涵;其《宗經(jīng)》與《辨騷》篇,論文之源與文之變,結(jié)合全書看,實際也受到前人有關(guān)《詩經(jīng)》與楚辭的文學(xué)地理批評思想與方法的深刻影響,并能加以整合創(chuàng)新,運用于文學(xué)批評實踐;《樂府》篇明確界定樂府為“土風(fēng)”,論述“趙代之音”“齊楚之氣”③,也可謂是最早的一篇有關(guān)樂府文學(xué)地理批評的專論;《聲律》篇說:“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④這也就涉及到文學(xué)地域性問題。《物色》篇首次鑄就的評論屈原所提出的“江山之助”論⑤,持久而深刻地影響了其后的文藝?yán)碚撆u,例如晚唐司空圖《與王駕評詩書》提出所謂“河汾蟠郁之氣”論等,就是繼承了這種批評思想。⑥學(xué)界迄今之所以忽略《文心雕龍》較為豐富而深刻的文學(xué)地理批評思想,主要是因為研究者尚缺乏文學(xué)地理學(xué)研究的知識與視野。美國學(xué)者艾布拉姆斯(M.H.Abrams)在其名著《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tǒng)》一書中,提出文學(xué)批評的四大要素論:即作品(work)、世界(或譯為宇宙,universe)、作家(artist)與讀者(audience)。⑦文學(xué)地理批評是構(gòu)成《文心雕龍》的一種自覺的批評方式,與其經(jīng)典批評、才性批評、文體批評及知音批評等共同構(gòu)成其文學(xué)批評的范式。⑧從文學(xué)與地理的關(guān)系出發(fā),文學(xué)地理學(xué)之所謂“文學(xué)地理”,無疑是屬于艾布拉姆斯所說的“世界”(宇宙)這一文學(xué)批評要素之中的內(nèi)容。
由此,《文心雕龍》文學(xué)地理批評思想可以分為如下四大方面的內(nèi)容:文學(xué)與地理的一般的普遍的關(guān)系論、作家與地理關(guān)系論、作品與地理關(guān)系論以及讀者與地理關(guān)系論。在此也先將《文心雕龍》文學(xué)地理批評這四大方面內(nèi)容的具體論題與論述,特別以案例的方式列舉出來,以說明《文心雕龍》具有較為豐富的而且是較為系統(tǒng)的文學(xué)地理批評思想。第一,《文心雕龍》關(guān)于文學(xué)與地理的一般的普遍的關(guān)系論。其關(guān)于這個問題的論述,是全書有關(guān)文學(xué)地理批評的理論基礎(chǔ),在其首篇所謂“文之樞紐”論的《原道》篇,就蘊涵其在天人合一的思想文化視野下,論述天地人“三才”的關(guān)系,所謂“原道”,其本義包含這樣的內(nèi)涵:人之文(儒家經(jīng)典與其后的所有作品)乃圣人之心(作家之文心)參贊天地之文(美)而制作出來,這就論述了文學(xué)與地理的普遍聯(lián)系性和論理上的邏輯相關(guān)性。第二,作家與地理的關(guān)系問題,主要體現(xiàn)為《文心雕龍》有關(guān)作家創(chuàng)作個性(才性)及風(fēng)格與文學(xué)地域等方面的論述。《物色》篇論屈原時,提出“江山之助”論,這實際在理論批評的邏輯上包含兩大方面基本內(nèi)涵,即作家的創(chuàng)作個性與風(fēng)格受到“江山之助”的作用,作品的創(chuàng)作與表現(xiàn)內(nèi)容之特點也受到“江山之助”的影響。通觀《文心雕龍》全書,在其文學(xué)史論的歷史鋪敘和論述中,在其有關(guān)作家才性與風(fēng)格的論析中,都具有作家與地理關(guān)系論的批評體現(xiàn)和分析視角。第三,作品與地理的關(guān)系問題,主要體現(xiàn)為《文心雕龍》有關(guān)風(fēng)景論、樂府論、語言聲韻論、文學(xué)傳統(tǒng)與文學(xué)史通變論中的文學(xué)地理批評內(nèi)容。如《辨騷》篇說: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郁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jié)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fēng)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①地域文學(xué)的鮮明的地域個性,是與其文學(xué)創(chuàng)作“以景抒情”分不開的,乃至是與其描寫地域的風(fēng)土人情分不開的,風(fēng)景描寫實際是文學(xué)地理學(xué)研究的中心課題之一。《樂府》篇說:至于涂山歌于候人,始為南音;有娀謠乎飛燕,始為北聲;夏甲嘆于東陽,東音以發(fā);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亦不一概矣。匹夫庶婦,謳吟土風(fēng);詩官采言,樂盲被律,志感絲篁,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覘風(fēng)于盛衰,季札鑒微于興廢,精之至也。②《樂府》中的許多作品也是如《國風(fēng)》一樣,屬于采集的“土風(fēng)”,《樂府》篇的批評,具有突出的文學(xué)地理批評特點,這明顯也是繼承了班固、鄭玄等關(guān)于《詩經(jīng)》的文學(xué)地理批評的傳統(tǒng)。
如上所言,《文心雕龍》的《樂府》篇,可以視為第一篇樂府文學(xué)批評的專論,又因為其中明顯地突出地包含文學(xué)地理批評思想,所以也可以說是第一篇有關(guān)樂府文學(xué)地理批評的專論,注意筆者這里的“有關(guān)”二字的限定意義。《聲律》篇說:夫音律所始,本于人聲者也。聲合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xué)器者也。故言語者,文章關(guān)鍵,神明樞機,吐納律呂,唇吻而已。又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不易,可謂銜靈均之余聲,失黃鐘之正響也。③文學(xué)的地域性差異與方言有關(guān),盡管劉勰《聲律》篇原意不是討論文學(xué)地域性問題,但他對楚辭作品這種“楚語楚音”特點的認(rèn)識是清楚的,對屈原等楚辭作品所描寫的楚地楚物而構(gòu)成鮮明的“驚采絕艷”的藝術(shù)特點和風(fēng)格,也是認(rèn)識明確的。宋人黃伯思《新校〈楚辭〉序》說:“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jì)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④這一關(guān)于“楚辭”的釋義,受到其后直到今天研究者的認(rèn)同。《時序》篇說: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余影,于是乎在。⑤所謂漢賦作品中的“靈均余影”的問題,實際可以視為一個文學(xué)地理批評的重要問題,這就是文學(xué)的地域風(fēng)格與超地域的風(fēng)格問題⑥,同時也是一個文學(xué)傳統(tǒng)的繼承與革新的問題。第四,讀者與地理的關(guān)系問題,《文心雕龍》也有相關(guān)論述,值得深入探討。《知音》篇說:是以將閱文情,先標(biāo)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shù)既形,則優(yōu)劣見矣。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況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昔屈平有言:“文質(zhì)疏內(nèi),眾不知余之異采。(按:見屈原《楚辭·九章·懷沙》)。”見異,唯知音耳。⑦根據(jù)“六觀”方法鑒賞批評作品,最主要是要能夠“見出”作品所體現(xiàn)的獨特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性和獨特的藝術(shù)個性之所在,所謂“見異”;能夠“見異”,才能稱得上是“知音”。那么這種“異”也是與作家作品的文學(xué)地域性有關(guān)的。這就內(nèi)含著這樣的意思:讀者要能深入理解所鑒賞批評的作家作品這種“異”,例如屈原的楚辭作品,就要“知人論世”,其中自然也就包括了解作家生長的地理的、文化的環(huán)境和社會現(xiàn)實處境,了解作家的情志抱負(fù)等。劉勰自己正是從這樣的思考出發(fā),才能夠提出屈原得“江山之助”論這一著名的批評觀點。一切文學(xué)作品創(chuàng)作過程和創(chuàng)作內(nèi)容,可以說都與特定的“時地”有關(guān),但文學(xué)地理學(xué)研究是要從文學(xué)與地理的關(guān)系角度詮釋文學(xué)。因此研究《文心雕龍》文學(xué)地理批評思想,雖然如上所說,可以以世界(宇宙)、作品、作家與讀者這四要素的關(guān)系論,作為考察與分析問題的理論邏輯和途徑,但絕不是要把《文心雕龍》所有的理論內(nèi)容都視為文學(xué)地理批評(如果這樣理解本文的意圖就明顯是錯誤的也是不符合實際的),而是要研究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明確提出的有關(guān)或至少在理論邏輯上有關(guān)文學(xué)與地理關(guān)系的論述。《文心雕龍》豐富的理論批評內(nèi)容,是否包含文學(xué)地理批評思想,其間之理解與確認(rèn)之依據(jù)在此。
三、《文心雕龍》有關(guān)文學(xué)與地理關(guān)系的普遍原理論
《文心雕龍》所謂“文”,可以視為中國文學(xué)批評傳統(tǒng)的“文學(xué)”,乃兼“筆”而言;與“筆”相對的“文”,謂“有韻”之作,包括詩、賦、樂府等,“筆”謂“無韻”之作。今天我們不必非要以純文學(xué)、雜文學(xué)加以區(qū)別,因為從文化研究的立場看,任何一個文化傳統(tǒng)中所認(rèn)為的“文學(xué)”作品就是所謂“文學(xué)”①,任何文體的作品都可能是“文學(xué)”,也可能不是,這其中也與讀者的主觀立場有關(guān)系。《文心雕龍》在具體的論述中,充分運用了經(jīng)典批評、才性批評、文體批評、知音批評等原則與方法,這其中也包括文學(xué)地理批評的原則與方法。總之,《文心雕龍》中所說的“文”,就是“文學(xué)”,本文提出《文心雕龍》“文學(xué)地理批評思想”之“文學(xué)”的內(nèi)涵,主要在上述理解的意義上說的。《文心雕龍》有關(guān)文學(xué)與地理關(guān)系的批評思想,從《原道》篇所論,即可得其要義:所謂“原道”,其本義就是明確闡明“文”本原于“自然之道”。《原道》篇說: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于林籟結(jié)響,調(diào)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锽: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fā)則文生矣。②上述引文,其要確立的理論邏輯之本義,主要就是認(rèn)為文學(xué)既要“自然”(自然而然之義),又要有“文采”,這也是貫徹全書的思想原則;但我們在此可以下一“轉(zhuǎn)語”———這一轉(zhuǎn)語是其論述中所本有的意義:客觀存在的天地萬物(今天我們說的大自然),即“自然之道”的體現(xiàn),其本質(zhì)具有一種“自然而然”的自在自為性,而不是一種主觀人為的存在。注意:我們在此不是說“自然之道”的“自然”(形容詞,自然而然之義),等同于作為名詞“自然”(大自然)的意思,不可誤詮。其《物色》篇說:“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jiān)風(fēng)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③所謂“江山之助”的“江山”的內(nèi)涵,就是指“山林皋壤”,也就是山水田園的自然,當(dāng)然這種自然基本都是一種人化的自然。具體屈原所受到的“江山之助”,實際就是指楚國的山水皋壤、大自然的風(fēng)景、地理。結(jié)合《原道》篇所論,上引《物色》篇這段話,至少包蘊了如下三層內(nèi)涵,也是三條關(guān)于文學(xué)與地理關(guān)系論的普遍原理:其一,作家之心參贊天地之文(自然之道的文)以養(yǎng)育“文心”,作家所生活的具體的地理自然環(huán)境,也就對作家起到了熏育之功,進而可以說,不同地理環(huán)境對作家的熏育就有所不同。這是從作家出發(fā),這可以說是關(guān)于文學(xué)與地理關(guān)系論的一條普遍原理。《文心雕龍》充分肯定屈原的個性才能,《辨騷》篇開篇就強調(diào)“楚人”多才:自風(fēng)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郁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后,奮飛辭家之前,豈去圣之未遠(yuǎn),而楚人之多才乎?①作為楚人的屈原,之所以多才,其間應(yīng)該包括“江山之助”,至少在劉勰論述的本義上,楚地“山林皋壤”是屈原創(chuàng)作《離騷》等奇文的“文思之奧府”。其二,文心因風(fēng)景(包含在“地理”這一內(nèi)涵之中)而起興,這是從作家創(chuàng)作過程來看問題的,也是有關(guān)文學(xué)與地理關(guān)系論的一條普遍原理。作家之心乃會受到大自然的風(fēng)景和地理環(huán)境的激發(fā),而有“文心”,而有“文情”,從而能“為情而造文”,而不是“為文而造情”(《情采》篇),作家所處的地理環(huán)境中,不同季節(jié)的風(fēng)景乃至其間的社會現(xiàn)實境況(物)刺激作家的“文心”,“心”與“物”相交融而產(chǎn)出作品。這就是說,從文學(xué)與地理的關(guān)系看,“山林皋壤”既是感動作家“文心”的原由,也是作家書寫到作品中的內(nèi)容。《文心雕龍》的文學(xué)觀乃是直接繼承先秦兩漢的言志寫心之觀念。這種言志寫心論,在《毛詩序》《禮記·樂記》等《文心雕龍》之前的文論、樂論中都有詳細(xì)論述。
《樂記》說:“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②《物色》所謂“物色相召,人誰獲安?”即是此意。《明詩》篇說: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圣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xùn),有符焉爾。③又說:“人稟七情,應(yīng)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上引《原道》篇繼承《易傳》天地人“三才”說的思想,也是說明這個意思:“……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這實際上也是從作家創(chuàng)作心理過程所謂“感物”的邏輯層面,論析了文學(xué)產(chǎn)生的本源和本質(zhì),是站在作家主體的立場看問題的。其三,“文學(xué)地理”都是經(jīng)過心靈化的體驗與創(chuàng)造,是作家創(chuàng)作出來的“擬容取心”的結(jié)果,這是從作品文本分析出發(fā)看問題的,也是文學(xué)與地理關(guān)系論的一條普遍原理。《文心雕龍》之《原道》篇所謂“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惟人參之……心生而言立”云云,《物色》篇所謂“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云云,“自然”(地理),作為作家審美的對象,作為書寫到作品中的內(nèi)容,即使以表現(xiàn)自然為主的純粹的山水自然文學(xué),都是經(jīng)過“心靈化”了④,自然的風(fēng)景、映入作家心靈的地理環(huán)境的一切景觀乃至社會現(xiàn)實境況,無論是理想(浪漫)的、寫實(現(xiàn)實)的、超現(xiàn)實的書寫,都是為了表現(xiàn)作家的心靈情感和思想的,而且是經(jīng)過作家運用不同創(chuàng)作原則與方法進行過“改寫”,乃至直接是作家想象創(chuàng)造出來的,而不是“自然”與“社會”的“復(fù)寫”。《神思》篇所謂“夫神思方運,萬涂競萌,規(guī)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fēng)云而并驅(qū)矣”⑤。受到“江山之助”的作家,具有各自的才性與才能,因此他們的作品中所表現(xiàn)的“景物”是不同的,并且以表現(xiàn)其不同的心靈情感和思想為目的,所以說,其寫景就是寫情,一切景語皆情語,王國維所謂“昔人論詩詞,有景語、情語之別。不知一切景語,皆情語也”⑥。是故,其創(chuàng)作出來的文學(xué)作品中的“文學(xué)地理”就是個性化的。這不是什么復(fù)雜的理論問題,劉勰《文心雕龍》對此認(rèn)識得非常清楚。其《詮賦》篇說:原夫登高之旨,蓋睹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zhì),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①又其“贊曰”:“賦自詩出,分歧異派。寫物圖貌,蔚似雕畫。抑滯必?fù)P,言曠無隘。風(fēng)歸麗則,辭翦荑稗。”登高所望之“物”(其中包括地理的自然風(fēng)景),通過心靈化而表現(xiàn)在作品之中時,賦與詩歌、樂府等不同,賦更多的是運用“賦”(鋪敘)而少用“比興”(比喻、象征等)的手法,所以是“寫物圖貌,蔚似雕畫”,故《物色》篇說:“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辨騷》篇:贊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fēng)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艷溢錙毫。②屈原具有“驚才風(fēng)逸”的才能與“壯志煙高”的志向,同時得到楚山楚水的“江山之助”,方能寓其“情理”于“山川無極”的書寫之中,作《離騷》等“奇文”,“驚采絕艷”,成為“文變”之典范。對于圣人而言,其參贊天地而著述的“六經(jīng)”,能夠“光采玄圣,炳耀仁孝”,“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原道》)。這就體現(xiàn)了《文心雕龍》的思想原則和批評立場。
四、結(jié)語
從先秦開始,中國古人非常重視天人關(guān)系,至春秋戰(zhàn)國時代,既出現(xiàn)天人相合的思想,也產(chǎn)生天人相分的觀念,道家的天人關(guān)系論更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關(guān)系,而儒家的天人關(guān)系論更強調(diào)人與社會現(xiàn)實的關(guān)系,這在各自的“道”論中體現(xiàn)得最為清楚。而至《易傳》的產(chǎn)生,儒道乃至陰陽家等思想就交融匯通在一起,戰(zhàn)國時期的《管子》一書也有這種傾向,其以論“人地關(guān)系”為中心主旨的《水地》篇,就具有明顯的陰陽與五行思想,《管子·五行》篇說“人與天調(diào),然后天地之美生”③,這就是主張一種天地人三者和諧共生的關(guān)系,是一種天人合一的思想,《管子》“人與天調(diào)”的思想實際是儒、道、法、陰陽諸家有關(guān)思想的統(tǒng)一。魏晉時期,玄學(xué)思潮興起后,《老子》《莊子》和《周易》被視為“三玄”,王弼、何晏等人通過注釋“三玄”,進一步發(fā)展了老子等提出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劉勰《論說》篇贊“平叔之二論”,據(jù)范文瀾《文心雕龍注》,指何晏關(guān)于《老子》解釋的《無為論》和《無名論》,后者尚保留殘文在《列子·仲尼篇》注文中。《無名論》其中說: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自天地以來,皆有所有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無名,故老氏曰,強為之名……”夫惟無名,故可得遍以天下之名名之。④所謂“天地以自然運,圣人以自然用”,明顯有調(diào)和儒道的傾向,就是將老莊之自然之道用來解釋儒家之道,以道解儒。《文心雕龍》也主張“道”是天地自然萬物存在的本身的狀態(tài)與方式,是自然而然的,是自在自為的,“文”是現(xiàn)象,所謂“本乎道”(《序志》),而“道”是本體,有天地萬物,就有“天文”“地文”,所以說“文”與“天地并生”。對《文心雕龍》文學(xué)地理批評思想進行全面探討,還需要對劉勰《文心雕龍》所評論的作家作品進行深入研究。《文心雕龍》關(guān)于文學(xué)與地理(自然)一般的普遍的關(guān)系之論述,都是基于《原道》篇的“道、圣、經(jīng)”三位一體的理論綱領(lǐng)而立論,其中可以看到其思想文化的根柢,實際上具有先秦以來儒道諸家都有所倡發(fā)的天人合一的精神與文化視野。總之,據(jù)上述所論,可以說明,《文心雕龍》中包含的文學(xué)地理批評思想,是豐富而深刻的,不是限于一兩個相關(guān)的命題或偶爾涉及文學(xué)地理批評的論述,而是構(gòu)成全書完整的理論批評體系中的有機組成內(nèi)容;當(dāng)然,我們這里并不是說,《文心雕龍》文學(xué)批評只有或者說都屬于文學(xué)地理批評,絕不可以作出這種誤詮。文中不足之處和不切之論,或有存在,敬請學(xué)界專家與讀者批評指正。
作者:陶禮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