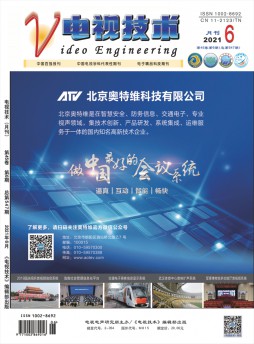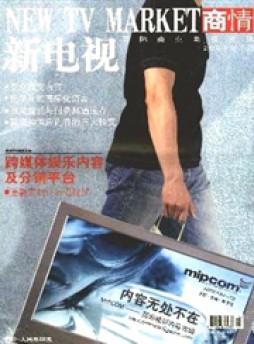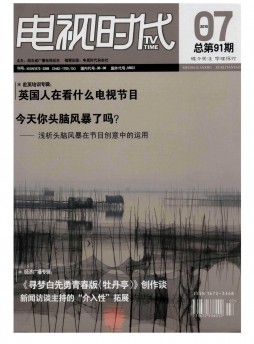電視法治節目中案件報道的實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電視法治節目中案件報道的實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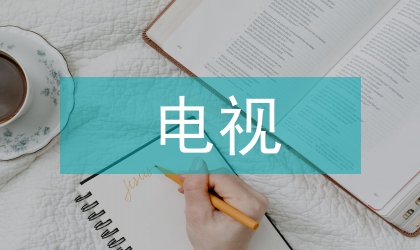
《東南傳播雜志》2014年第九期
一、適度展現刑偵細節
電視法治節目的案件報道通常具有新聞報道的性質。陳力丹先生這樣描述新聞的價值:“或者滿足我的興趣需要、認同感的需要,或者幫助自己對利益相關的問題做出決策。對新聞接受者來說,這樣的新聞是具有新聞價值的”[2]這恰恰說明新聞價值與受眾的娛樂與決策的兩種信息需求相關。刑偵細節對于受眾而言具有新奇的信息價值,其展現首先從這個角度具有傳播價值。一方面案件報道增強了法治節目的趣味性,從電視傳播的角度符合了大部分受眾娛樂的需求;另一方面,案件報道展現公安及司法機關的權威性,對潛在犯罪起到震懾作用,這是決策性信息需求。但是這兩個方面功能的實現與報道內容與方式的選擇是不可分的。有些案件報道著重展現刑偵過程的細節,甚至強調偵破過程的偶然因素,從戲劇審美的角度的確增強了故事的吸引力。同時偵破過程的詳細展現也給潛在的犯罪提供了作案行動指導,這樣的結果相信與法治宣傳的初衷是南轅北轍的。2014年1月14日杭州電視臺《警界41》欄目以《老婦家中遇害謎案》為題報道了一起很簡單的入室行竊導致人命的案件。報道的開頭就用“一聲尖叫,天黑時分,老婦家中離奇遇害”這樣帶有強烈戲劇懸疑色彩的解說詞介紹案件,并以夸張的語氣引起觀眾的興趣。整期節目圍繞案件偵破的詳細過程進行,并且延續強化戲劇沖突的風格。報道中展現了公安機關的案件推理、通過攝像頭的技術偵查,還強調了關鍵線索獲得的偶然性。對刑警的訪談中有這樣一段話:“但是湊得巧也是,木材加工廠的這批木材有一個地方有個洞,他正好從這個縫隙里走過去(被攝像頭拍到了)。”這些報道傳達出兩個信息:破案具有偶然性,攝像頭是破案的必要條件。這些信息與法治宣傳的目的是無關的,同時又對潛在犯罪起到了行動指導的作用。案件細節的展現強化了公安及司法機關的威信為內在目標,案件中的偶然戲劇性因素恰恰會弱化這個傳播目的。結束語中,主持人說道:“陳某(犯罪嫌疑人)的聲音漸漸哽咽了起來,他原本擁有一段佳偶良緣,如今卻只剩下了無盡的悔恨。而今年的春節本應該是合家團聚的時刻,如今留給兩個家庭的也只有深深的沉痛。目前陳某因涉嫌搶劫罪被余杭區人民法院依批準逮捕。”節目最后也只是渲染了一下情緒,提醒受眾要珍惜家庭。
通過上述案例可以看到,刑偵細節具有“設置懸念”與“烘托情感”兩個方面的作用,而其“適度展現”的度,也恰恰需要從這兩個方面進行規范。懸念設置是提升節目可看性所必要的,但是對公安機關的常用偵破方法與手段則需要概述。偵破過程是對犯罪過程的還原,于是一個懸念點就具有犯罪過程與偵破過程的兩面性。例如罪犯留下了關鍵線索,同時公安機關通過刑偵技術掌握了線索,那么在報道過程中,前者是可以詳細接受的,而后者應該是簡略說明的。情感烘托的適度關鍵在于情感的性質,那些與案件具有直接聯系的情緒,如上述案例中結語所述,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就值得烘托;而那些與案件沒有直接聯系的,案件故事中的瑣碎情感就需要摒棄。情感烘托贏堅持服務法治宣傳的原則。當然,僅僅具有情感是不夠的。這顯然與法治宣傳的目標是不一致的。對于上述案例而言,檢察院為什么以“搶劫罪”起訴,陳某殺人行兇是否屬于“故意殺人”,可能會如何量刑以及為什么這樣?這些受眾所不熟悉的法治問題在節目中卻絲毫沒有得到體現。盡管該欄目是以“警界”為素材的,但法治宣傳的深度要求在節目內容得到充分的延伸。這種延伸是對案件故事的超越,是案件細節服務于法治宣傳的體現。
二、議論性結構的應用
電視法治節目中的案件報道,是法治宣傳與新聞事件報道的結合。于是更多的案件報道呈現敘事性的結構,一期法治節目講述一個案件發生的經過以及偵破、訴訟中出現的各種矛盾。這種結構使抽象的法律規范與道德原則遮蔽在曲折的故事之中,各種電視敘事技巧的使用使受眾關注懸疑的案情而忽視其深度信息。當下電視法治節目實踐中,往往是整期節目的案件報道之后,結尾簡短地說幾句“法網恢恢”之類的勸導語匆匆結束。這種敘事結構恰恰是深度缺失的根本性原因之一。康拉德•芬克在《沖擊力:新聞評論寫作教程》中認為,新聞報道中,如果確定基本事實的存在,那么是否具有“激發、解釋和提出倡言”就成為關鍵所在。在激發受眾興趣之后,解釋與提出倡言的組合構成了一種議論性的結構,從而使報道超越了事實層面。議論性結構的使用,法治評論的增添,是當下案件報道所需要的。議論性的結構可以分為兩種,綜合性結構與分析性結構。康德認為:“分析的方法是與綜合的方法相對的,前者從被條件限制者和被奠基者開始直到原理為止,而相反后者從原理到結論或從簡單的到集合的。前者人們也可以稱之為后退的方法,正如人們稱后者為前進的方法一樣。”可以看出綜合與分析的結構從論證的起點開始就具有明顯的區分。
在法治新聞報道中,綜合性的議論結構直接以抽象的法律問題為邏輯起點,在同一個主題之下組織多個類似的案件信息。這樣,節目的時長有效地限制了細節信息的過度展現,同時在多個案例的比較中,一般性的法律問題能通過歸納更直觀的顯現。這種綜合性的議論結構要求豐富的事實素材,同類案件信息的整合是其節目質量的關鍵;同時這種結構也在節目長度上有了更多的要求,十幾分鐘的時間往往難以展開。基于上述限制,綜合性議論結構在當下法治節目實踐中的應用不夠廣泛。《今日說法》欄目做出過類似的嘗試,經常在同一法律問題的統攝下組織多個法律案件,2014年6月11日《高墻外的孩子》通過詳略結合的方式講述了兩個父母服刑的孩子的故事,展現了法律在處理該類型案件中的困境與不足,普遍性得到了展現。在案件報道過程中,節目也注重對此類案件法律程序的解釋。從整個欄目來看,《今日說法》連續三期圍繞“困境兒童”展開,其案件的展現也是由統一的主題統領,這種連續的綜合性的結構方式也強化了案件報道的普法意義。分析性結構以某個典型的案件為報道核心,對案件進行法律、倫理層面的分析。分析性議論結構與敘事結構的區別在于案件信息展現的重點,敘事結構往往強調案件發生的過程、細節,強調外部沖突;而分析性結構更多展現案件的性質、涉案人員的責任、公眾的態度等,強調內部沖突。同時,敘事結構通過敘事強調情感因素,分析結構通過說理強調法治正義。例如,2013年12月7日,《新聞調查———被遺棄的人生》,該期節目報道了南京餓死女童案。21年前這個孩子在出生的時候并不是一個壞人怎么21年就變成了這樣的一個不負責任的人。坦率地講,辯護人很不理解,樂燕怎么會這樣的。本案怎么會這樣的,但是我在知道了她的經歷之后,我變得逐漸可以理解了。它有原因。
上述話語是庭審現場再現中辯護人的辯詞。在電視報道中,通過口語的形式展現,辯護人復雜的情緒在聲音中得到體現。于是,觀眾從新聞事件中感受到的憤怒得到了緩解,轉向對事件整體背景的關注與思考。該報道是體現深度的,是引領受眾從情感層面向思維層面深入的看待案件,這恰恰是案件報道宣傳法治的最終目的。這種深度的實現建立在對案件進行分析的結構之上。盡管《新聞調查》是一檔新聞報道欄目,但是其深度報道的方法是值得法治節目借鑒的。案件報道是法治宣傳與電視媒體結合的必然結果,其直觀性與電視的技術特點可以充分結合,同時經驗事實也能最直接地起到直指人心的作用。但是案件報道需要遵循一定的方法,才能有效地避免法治節目普法功能的喪失。電視法治宣傳深度的實現是一個需要明確普法目標,實踐傳播規律的過程。
作者:齊麟單位:鐵道警察學院
- 上一篇:網絡公益慈善動員模式探究范文
- 下一篇:圖書編輯的必備意識和能力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