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侯孝賢電影的悲劇情懷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淺析侯孝賢電影的悲劇情懷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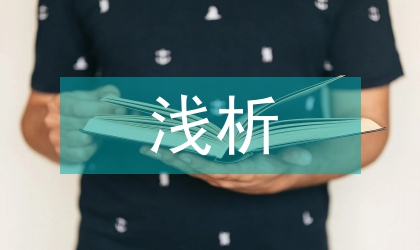
摘要:侯孝賢依據對人生的深刻關懷和認知,結合自身的人生感知和經歷,攝制了多部富有悲劇性色彩的電影,成為臺灣新電影運動的主力,被人們稱為電影悲劇藝術大師。他的電影以悲劇居多,其獨特的悲劇意識和悲劇情懷主要源于他特殊的人生際遇和厚重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侯孝賢主要通過其富有個性的意境營造、場景設計和鏡像語言等表現手法,將生命、親情、鄉情和歷史文化等悲劇主題呈現給世人,同時深刻地折射出侯孝賢電影中社會意識和人文關懷深沉的悲劇情懷。
關鍵詞:悲劇情懷;人文關懷;意境
侯孝賢,臺灣電影導演。1973年踏入電影界,1975年起從事編劇工作,因1980年首次執導第一部電影作品《就是溜溜的她》而成名,引領“臺灣新電影”浪潮,并以“悲情三部曲”確立了臺灣電影泰斗級大師的地位。侯孝賢的每部電影作品都有較高的水準,為臺灣的民眾與歷史記錄下生動的篇章,其中尤以悲劇最為眾人熟知,他電影中慣用的長鏡頭等拍攝方式也成為侯孝賢電影抒發悲劇情懷、關注人生關懷和體驗大眾悲情的特色與標志,獨特的悲劇情懷使得侯孝賢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電影風格。
1.悲劇情懷的形成原因
1.1悲慘人生際遇在侯孝賢導演的電影作品中,絕大多數都是悲劇,悲劇情懷的形成成為其所有作品中的美學意識形態的支撐。侯孝賢的悲劇情懷主要來自與生俱來的悲觀情緒,即侯孝賢本身對人世痛苦的主體性宣泄。他的人生際遇一開始就為他的電影風格奠定了基調,浸滿了他的大部分電影素材,而他的電影主題,也映刻到了他的個人質地里。侯孝賢1947年4月出生于廣東省梅縣,不到一歲時便跟隨父親從大陸遷居臺灣,后由于政治原因無法回歸故鄉,長期定居于臺灣高雄。回想起侯孝賢的童年,更多的是不堪回首的慘痛記憶,他12歲時父親便去世,17歲時母親去世,隨后祖母也相繼過世,親人接二連三的離去使他的童年破碎不堪,他甚至沒有辦法回到自己的家鄉,連維持生計都很艱難,轉眼間變成了一個舉目無親的孤兒。1985年,侯孝賢籌劃拍攝了半自傳體電影《童年往事》,在影片中阿孝這個角色便是侯孝賢本人童年經歷的縮影。正因為這種悲慘的人生經歷,讓侯孝賢在他電影的創作中形成了深刻的悲劇情懷,這種人生的悲涼感在侯氏電影中潛移默化地揭示出來,創造性地闡釋了侯氏電影悲劇藝術觀,讓他能夠冷靜客觀的觀察身邊的人和事,讓他用平靜的眼光去看待真實,探索人生的本質。由此可見,侯孝賢導演的電影,與他本人的成長經歷和生活歷練密切相關,他的“成長四部曲”:《童年往事》、《風柜來的人》、《冬冬的假期》、《戀戀風塵》,可以說是對他青少年成長經歷的完整詮釋。
1.2傳統文化熏陶當代的臺灣電影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在臺灣的新電影運動中尤為突出。作為臺灣“新電影”運動的領軍人物,侯孝賢在20世紀80年代臺灣藝術電影的盛況中是不可忽視的,他創作了許多體現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熱愛與反思的影片,尤其是早期作品,深深地鐫刻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烙印。侯孝賢藝專畢業之后當了編劇,第一個本子就是從元曲改編的。侯孝賢說“我們要把電影拍好不是在于影像處理本身,而是我們對文學、對造型藝術,要有很深的熏陶和熏染。我自己的例子就是從小喜歡看自己喜歡的東西,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1]從小就受傳統文化熏陶的侯孝賢,在他獨特的電影風格中,通過小人物悲慘遭遇的刻畫,來喚起人們的同情,喚醒社會的良知,這是他創作的出發點,同時也符合中國文人悲天憫人的一貫情懷,流露出濃郁的傳統文化傾向。電影《刺客聶隱娘》就是侯孝賢根據唐傳奇故事改編,在這部影片里,他保持了自己長久以來的一貫風格,仍是長鏡頭和固定機位,幾乎沒使用電腦特效,片中演員對白均采用古漢語,正是為了增強歷史感,古文對白成了影片拍攝過程中最大的亮點,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對侯孝賢的影響。出于中國傳統文化對社會和人生的深刻關懷,逐漸形成了侯孝賢式獨特的觀察人生和體會生活的角度和個人見解,在無限時間和空間的流變中,產生了對人生命流動的蒼涼之感,體現電影角色對成長和人生的感慨。也正是侯孝賢悲劇電影中對社會的深刻剖析,顯示了無形的藝術力量。
2.悲劇情懷的題材呈現
2.1彷徨迷失的苦澀青春自1983年開始,侯孝賢攝制了多部關于苦澀青春的電影,除了描寫自己童年悲慘經歷的《童年往事》外,還有講述一群男孩子在高中畢業后的青春成長中遇到的迷茫與困惑的《風柜來的人》,也有林曉陽在經歷青春迷茫后蛻變成熟的《尼羅河女兒》等等。這些影片都以苦澀迷茫的青春為出發點,來烘托整部影片的悲劇氛圍。侯孝賢創作的電影《童年往事》,講述了男孩阿孝在家庭與生活的變化中成長的故事。1946年,阿孝舉家從廣東梅縣遷往臺灣鳳山,在這里,他度過了輕松快樂的的童年。直到久經病痛的父親去世,阿孝的童年生活才落下帷幕。他開始了莽撞、叛逆、躁動不安的青春期,結伙打架、打撞球與老兵起沖突、追求同班的女生等一系列叛逆行為充斥了他的青春,但隨著大姊的出嫁、母親從發現喉癌到痛苦地離世、祖母的過世、高考失利無法讀大學,阿孝經歷了諸多家庭的不幸,以當兵告別了這段苦澀的青春。電影《童年往事》與其說是創作的故事,不如說是侯孝賢對自己童年的追憶在電影中的映射。影片描寫了一個家族的悲歡喜樂,面臨生老病死的態度以及對生命成長的關懷,迷茫和憂傷彌漫在侯孝賢的整個青春時光,也是他的切身感受,電影《童年往事》中關于青春成長的苦澀和蒼涼,為侯孝賢的悲劇情懷奠定了基調。《千禧曼波之薔薇的名字》是2001年由侯孝賢執導的一部有關青春成長的影片。故事講述了一個年輕女孩虛幻顛簸的青春故事,折射出世紀初都市年輕人的青春情感迷失。侯孝賢往往對成長的歲月和青春的逝去流露出淡淡的感慨,青春期的成長總是與痛苦結伴而生的。
2.2哀而不傷的永恒鄉愁作為臺灣新電影運動的先鋒,侯孝賢的許多電影里都少不了關于鄉愁的描繪。他的早期的電影中充滿了悲憫的人文意識,用詩意的鄉土情懷,來抒發他的尋“根”情結。他擅長用意象來烘托思鄉之情,例如火車。在《戀戀風塵》和《南國再見,南國》中的歸途列車,便是侯導對故土的留戀。《南國再見,南國》中的主角們站在火車上,他們不知何去何從,無法回到大陸,更不知道會面臨什么,“南國”就像是舊世界,是故鄉,火車的路徑便象征著對舊世界的背離,也揭示了他們終將離開故土,投入未知時代的洪流中。他們沒有家,沒有親人,更沒有未來,只有背井離鄉的痛苦和抹不掉的淡淡鄉愁,長長的列車連接的不是始發站和終點站,而是連接著新舊兩個世界,也連接著欲望和鄉愁。在《冬冬的假期》中,阿公教冬冬背書,冬冬勉強背出“胡馬依北風,越鳥朝南枝”和“獨在異鄉為異客”,表現了臺灣流離一代對于大陸的眷戀。《童年往事》中的阿婆,傳統保守,有著根深蒂固的鄉愁之情。她始終惦記著大陸,每天鉸紙錢,盼望回大陸后拜祖先。她一次次拖著年邁的身體的試圖能夠走回大陸,卻無奈最終客死他鄉。阿孝的父親聽信老友的勸說,全家遷往臺灣,他以為三五年內可返回大陸,因此甚至不愿意買貴重的家具,在他心里他們只是異鄉人,并不屬于這里。所以無論是侯孝賢本人,還是他電影里的角色,都代表了曾經背井離鄉到臺灣來的那輩人的真實寫照。侯孝賢在這些電影中傾注了自己的悲劇情懷,暗含了“落葉歸根”的強烈信念,使得鄉愁的含義因而變得更加的濃厚。《詩經》云:“哀而不傷”,侯孝賢影片中的永恒鄉愁,無論多么悲哀,最后都不會絕望。對于侯孝賢來說,電影是永遠的鄉愁,是他不斷找尋解讀世界的方式,更是他悲劇電影中必不可少的獨特情懷。
2.3悲天憫人的沉重歷史侯孝賢認為,他拍攝《好男好女》、《戲夢人生》和《悲情城市》的主要原因,正是因為19世紀末至20世紀50年代期間的這段歷史并沒有在臺灣中學的課本里提及,他想要記錄這段時期的歷史,因為它從根本上塑造了人們現在所認識的臺灣,他希望人們可以正確看待和了解它。電影《悲情城市》是關于那個時代臺灣歷史的無奈記憶與臺灣文化身份的最后考證,是侯孝賢導演電影歷程的高峰,也是這一時期的標志性作品。影片以臺灣“二•二八”事件為背景,講述了1945年日本投降到1949年國民黨政府逃往臺灣之前,林氏家族在臺灣殖民化過程中所經歷的世事與滄桑。在這部電影里,侯孝賢將主題、個人命運與時代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從而使個人的經歷與民族的歷史合而為一,以一種更具本人個人特色的敘事方式展示了整個時代。臺灣學者焦雄屏曾經評價《悲情城市》:“通過一個臺灣‘本省人’家庭的毀滅和災變,透過一大片黑暗和光明之間灰色地帶的人世滄桑,直追臺灣40年來政治神話的癥結,家庭變遷實際是民族命運的縮影,是沉重的心靈在歷史陰影中的掙扎。”[2]侯孝賢的多部電影里都蘊含了悲情歷史的主題,正是這種強烈的責任感和悲天憫人的情懷,促使他將目光從小人物轉向臺灣的歷史。這一時期的作品除了《悲情城市》外,還有《戲夢人生》和《好男好女》,合稱“悲情三部曲”,較為真實地記錄了很多人不敢直面或者不了解的悲慘歷史。他始終持以包容的態度和對人文精神的關懷,真誠地關注個體成長和在歷史變遷中的命運,以一個電影人特有的悲天憫人的情懷而不是歷史學家的角度來看待歷史。
3.悲劇情懷的表現手法
3.1悲情意境的營造“意境”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古典美學滋養出來的一個美學范疇。著名美學家宗白華先生指出:“藝術家以心靈映射萬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現的是主觀生命情調與客觀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滲,成就一個鳶飛魚躍,活潑玲瓏,淵然而深的靈境,這靈境就是構成藝術之所以為藝術的意境。”[3]簡而言之,意境就是一種情景交融的詩意空間。侯孝賢悲劇電影意境的營造,在其將電影的詩化過程中得以彰顯。提到侯孝賢的電影詩化,自然會聯想到柳永《蝶戀花》中“佇倚危樓風細細,望極春愁,黯黯生天際。草色煙光殘照里,無言誰會憑闌意。”佳句。他的悲劇電影非常重視影片的詩情和韻味,擅長將不盡的愁思借詩一般的畫面和表現手法寄托于電影中,在侯孝賢看來,悲劇電影的創作手法并不是將故事敘述得多完整,故事情節多么跌宕起伏,而是像這柳永詞一般,在情境中可以領悟到生命的真諦。這種主觀化的美學傾向,使得侯孝賢被人們認為是個抒情詩人,而不是說故事的人。即所謂的“詩性大于故事性”,這和侯孝賢悲劇電影中所散發出的詩性氣質再符合不過。“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在影片《刺客聶隱娘》中,依然可見這種詩化電影的悲劇創作手法,其畫面優美,氣韻悠長,宛如看一幅古典水墨畫,以東方式傳統的含蓄和文言文對白,賦予了侯孝賢電影獨特的意境。影片中無論人物還是時間,既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在侯孝賢看來,這種情感和意境的體現方式契合了沈從文“冷眼看生死”的人生態度,而不管有多少的苦楚與感慨,鏡頭一轉,依舊是滿目的綠水青山。在這樣的詩意敘述下,聶隱娘的孤獨感被放大,影片中每個角色的氣質都沉靜了下來,侯導將中國畫中講究的留白、意境,通過鏡頭語言承載著無數小人物角色的悲涼與凄苦,賦予了影片質樸的詩意氣息,這種悲劇手法使他的悲劇電影暗含著清晰的人文意識。“心無詩意,不敢讀侯孝賢”,侯孝賢的悲劇電影創作藝術是一種靜水流深中透視著絲絲濃情的中國古典美學形態,他期望在入世的現實生活中遁世,儒學的生活態度和道家的思想浸透了侯孝賢電影藝術的視聽表達。
3.2悲情場景的烘托侯孝賢的悲劇情懷還通過場景的烘托來體現電影中的人物關系,從而增加悲劇美的效果。特定的場景產生特定的情感。影片《刺客聶隱娘》中大部分在湖北省內取景,因為利川、隨州、武當山、神農架的景色風光完全符合他對電影場景的想象。影片中聶隱娘在道觀習武的這場戲,便是在武當山拍攝的,南巖立于崖壁之上,泰常觀、飛升崖、雷神洞以及太子洞古樸的場景,與影片的整體的質樸風格非常符合,也意在烘托沉謐悲涼的氣氛。電影《最好的時光》中有三個時代背景,截取了主人公在三個不同時代里截然不同的風情,訴說了一段“三生三世”,情緣未了的愛情。第一段“戀愛夢”和第二段“自由夢”的故事場景,皆是侯孝賢導演本人溜街串巷臨時尋找的場地,而在第三段故事“青春夢”的場景中,主演舒淇迷茫地蹲在屋頂,她背后沒有充滿現代感的寫字樓,也沒有繁華時尚的商場,只有一條真實展現普通人市井生活的臺北街道,這便是對當代臺灣年輕人的真實寫照,以這種自然普通的真實場景來將觀眾帶入影片情境之中,仿佛影片中的悲劇就發生在我們日常的生活中,讓人對逝去時光產生淡淡的傷感。侯孝賢對悲劇場景的設計,呈現給觀眾獨特而強烈的畫面孤獨感,每一處場景的選擇都具有象征意義,不僅可以承載人物之間的悲傷情緒,還可以借此烘托理想與現實之間無情的碰撞,時間與空間二者間冗長的蒼涼感以及人生的混沌與迷惘。
3.3悲情鏡語的運用如果說電影是濃縮版的人生,在兩個小時內講述或短或長的故事,那么大多數電影都是采用快速的表演與拍攝手法,將生活的縮影快節奏地呈現給觀眾。然而,侯孝賢的電影卻是用緩慢悠長的鏡頭,一點一滴真實地再現生活中的時間和節奏,以一種冷靜客觀的目光,注視著電影中的人和事,不緊不慢的娓娓道來,給觀眾帶來前所未有的體驗。長鏡頭是指的是對一個場景、一場戲進行連續地拍攝,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鏡頭段落。[4]對于許多導演來說,長鏡頭也許只是一種普通的鏡頭方式,在特定的情節中才會使用,然而對于侯孝賢來說,長鏡頭卻是最熟悉不過的表達方式,固定長鏡頭、景深長鏡頭、運動長鏡頭,這一切都在他的影片中運用的揮灑自如,已成為他影片最鮮明的印記。在《刺客聶隱娘》中,為了還原中國文化中的儀式感,他用擅長的長鏡頭,描述仆人有條不紊的動作,用幾十秒展現山川湖泊,給悲劇電影本身增添了幾分靜謐感。《童年往事》中父親去世時,阿孝與家人從驚嚇得不知所措,到悲慟再到慢慢接受的過程中,侯孝賢以一種旁觀者態度,采用一系列的長鏡頭,冷靜而深刻,沒有跌宕起伏的劇情、也沒有矯揉造作的鏡頭,給觀眾以慢慢接受和體會的空間,阿孝也在這種生死離別的痛苦中慢慢成長。此時無聲勝有聲,平靜客觀的長鏡頭更加能夠烘托悲劇的氣氛。作為一位擁有冷靜視角和獨特藝術造詣的電影人,侯孝賢通過淡化主觀情緒、空遠悠長的長鏡頭運動方式以及舒緩的配樂,在電影中詩意化的詮釋了故事情境和他所想要表達的悲劇性理念,描寫生命中的吉光片羽,柔情與堅韌并蓄,表現對于人生的終極關懷。
4.結語
侯孝賢是一個擅于用悲劇來抒情的導演,他的電影揭示了當代社會的悲劇形態,他利用獨特的悲劇性理念揭示人們最為孤獨的一面,讓我們去了解現實中人文關懷的真實情感,并窺視了社會底層小人物內心最為沉痛悲傷的一面,但在人生的蒼涼中和心理的悲鳴中,又體現了人們面對苦難的求索和對命運的抗爭。他習慣用這樣的悲劇方式和悲劇情懷來表現出電影中的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溫暖與關懷。他充滿悲劇意蘊的影片,傾訴個體成長與人世滄桑的喟嘆,也是侯孝賢本人對無限時間與空間和生命的感慨。
參考文獻
[1]何玉新.侯孝賢———用膠片與時代作最后的抗爭[J].時代人物.2015(9).
[2]閆彩蝶.剪不斷的鄉愁———試論侯孝賢影片的尋“根”情結[J].福建藝術.2005(11).
[3]宗白華.美學與意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10.
[4]趙天杰.紀錄片拍攝的原則與手法[J].大眾文藝.2018(8).
作者:李奕欣 單位:湖南工業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 上一篇:電影英文字幕翻譯方法分析范文
- 下一篇:文物管理工作現狀及對策研究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