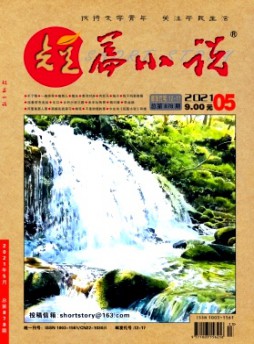小說之敘事藝術共通性探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小說之敘事藝術共通性探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
漢賦與小說不僅在發(fā)生、演變的過程中有著一定的聯系,而且在文體的內在構建上,也有著某些共通性。這種共通性,主要體現在敘事藝術層面上。首先,是敘述事件的憑虛構造;次之乃敘述情節(jié)的怪誕離奇;此外,乃敘述語言的鋪陳夸張。正是文體之間的交融共通,促進了文學的勃興與繁榮。
[關鍵詞]
漢賦與小說;敘事藝術;共通性
袁行霈先生曾云:“一種文體與其他文體相互滲透與交融,吸取其他文體的藝術特點以求得新變,這是中國文學演進的一條重要途徑。”[1]9又說,“小說作為中國古代諸文體中晚出的一類,在其走向獨立的進程中,有意無意地吸收了其他各種‘早出’文體的養(yǎng)分,舉凡詩、詞、歌、賦、曲、文乃至書札、奏疏、判詞、祭文等各種應用文體,均可在小說文本內找到立足之地。”[2]47可見,小說與其他文體的交互影響是存在的。而關于賦與小說在敘事藝術上的研究,學界目前已有不少研究,大多對賦的客主問答敘事體、反復鋪陳的手法、結構方式、諷喻功能、題材等方面進行探討,尤其論述了俗賦中存在的敘事要素與小說的關系。同時認為古代小說中賦體小說的出現,不僅拓展了小說的敘事模式,而且豐富了小說的表現手法。如學者程毅中、白曉帆等對此多有研究。總之在論述賦與小說之關系時,學界大多從文體的發(fā)生、發(fā)展以及文體特征、文體相互影響上去論述,而關于賦與小說的內在敘事藝術的共通性,則只是有所涉及,獨立論文甚少。
一、敘述事件的憑虛構造
漢賦與小說之敘事藝術共通性,首先表現在敘述事件的憑虛構造。“憑虛”一詞實乃漢賦之特質,而小說家言亦多以借鑒。自司馬相如《子虛》賦中假設了“憑虛”公子一角,此后后世多有沿用。“憑虛”暗指故事乃虛構。唐劉知幾《史通•雜說下》云:“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于陽臺。夫言并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敘事,足驗憑虛。”[3]83可見,“憑虛”一詞,實乃虛構假設之意。而漢賦之“憑虛”,誠如易聞曉先生云:“漢賦‘憑虛’反映于體制以及作者的精神氣度諸方面。‘憑虛’乃是漢賦與之俱來的體制特點。”[4]46這里探討的敘述事件的憑虛構造,亦即漢賦體制之特點。而漢賦之“憑虛”,莫如司馬長卿者也。清浦銑《歷代賦話校證》錄《漢書•列傳》語云:“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意。故虛籍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
[5]15可見其言之事乃憑虛構造。除此之外,諸如賈誼之《鵬鳥賦》、楊雄之《逐貧賦》、張衡《髑髏賦》等,也用擬人的手法,憑虛構造故事,或言志或言情。賈誼借與鵬鳥對話,表達自己貶至長沙后低沉的情緒和禍福同門的自我寬慰;揚雄借與貧窮對話,表達了自己守志固窮的決心;張衡化用《莊子》中莊周與髑髏對話的情節(jié),闡發(fā)了大化自然的道家思想等。漢墓發(fā)現之《神烏賦》亦然,但該篇乃純粹故事賦,自始至終是在講述雌雄二烏的遭遇,盡管故事最后有“鳥獸且相憂,何況人乎”的點題之筆,但這是對人生境況的一種反映和感嘆,并不突出表現作者個人的志向、思想等內容。由此可見,漢賦在敘述事件之時,多以憑虛構造之法虛構事件,這與小說敘事之法是共通的。漢時文化中,多言陰陽災異之變,神仙思想與神異方術盛行。神仙方術起源于春秋戰(zhàn)國,《莊子》《山海經》《楚辭》諸書皆有記載,如《楚辭》之《遠游》篇中記錄的“赤松子”“丹丘生”等,都是不死之神,后來在魏晉小說《搜神記》中皆有記載。神仙方術發(fā)展到漢代,空前繁榮。在這些文化因素的影響下,逐漸使得小說得以孕育,而從小說的孕育到最終形成,始終與神仙思想、巫、靈、鬼、方術等文化密不可分,而這些文化思想的共同特質,乃離奇怪誕,憑虛構造,這使得小說在敘事之時,也帶有強烈的憑虛構造色彩。諸如干寶《搜神記•卷一》中,《彭祖》條云:“彭祖者,殷時大夫也。……歷夏而至商末,號七百歲。……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云,禱請風雨,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6]8又有《琴高》條云:“琴高,趙人也,能鼓琴。……果乘赤鯉魚出,來坐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乃復入水去。”[6]9可見,彭祖“號七百歲”,所言非實,大抵形容彭祖之長壽,并非真七百歲也。而“琴高乘赤鯉魚出”,這也非實,如此種種,小說之中比比皆是,不勝枚舉。可見小說故事與漢賦在敘述事件上大多憑虛構造,道聽途說,目的在于引起時人好奇之心,迎合當時社會文化氛圍與政治愛好。
二、敘述情節(jié)的怪誕離奇
敘述情節(jié)的怪誕離奇,也是漢賦與小說的共通性之一。唐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發(fā)言則嗤鄙怪誕,敘事則參差倒錯。”[3]61此乃“怪誕”之語出處。宋李上交《近事會元•卷四》:“又小說云,術士羅公遠導明皇入月宮,聞之尤甚怪誕,不足為證。”[2]45明王瓊《雙溪雜記》:“甚至雜以詼諧之語、怪誕之事者亦有之矣。”[2]46可見,敘事怪誕離奇,乃小說之常性也。漢賦在敘述事件時往往怪誕離奇,這在敘事一類賦中得以很好體現。如1993年2月,連云港市博物館在江蘇東海縣尹灣發(fā)掘了六座漢墓,發(fā)掘簡報刊布于《文物》1996年第8期,撰文介紹了六號墓出土的部分簡牘。其中編號114-133的簡牘,是一篇存664字的《神烏賦》———簡牘“賦”書作“傳”。據同墓所出木牘上面的明確紀年,可知墓主人的下葬時間為漢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從尹灣漢墓中共出土簡牘157件,所載漢字約4萬。《神烏賦》相當于現代的民間故事,屬于俗賦的范圍。它比曹植的《鷂雀賦》、敦煌俗賦《燕子賦》都還要早。《神烏賦》載:今歲不翔(祥),一烏被殃。何命不壽,狗麗(遘罹)(咎)。欲勛(循)南山,畏懼猴猨。去色(危)就安,自詫(詑)府官。高樹綸棍(輪囷),支(枝)格相連。府君之德,洋洫(溢)不測。仁恩孔隆,澤及昆蟲。莫敢摳去,因巢而處。為貍(狌)得,圍樹以棘。道作宮持(塒),雄行求□(材)。雌往索菆,材見盜取。未得遠去,道與相遇。見我不利,忽然如故。雌鳥發(fā)忿,追而呼之:“咄!盜還來!吾自取材,於頗(彼)深萊。止(趾)行(胻)胱臘,毛羽隨(墮)落。子不作身,但行盜人。
可見《神烏賦》為敘事體,大致整齊的四言句式,押了大致整齊的韻,文字淺近,很多奇字怪字,正是堆垛之形容與鋪排,又化經義為文辭,樸素中見儒雅;由哀怨而憤激,溫淳中見風力。雌烏的臨終之言,凄清婉切;雄烏呼號,沉郁悲涼。置于漢賦中,此篇不算長,但敘事又若大賦般,曲折而怪誕。在小說中亦是如此,在《搜神記》中俯拾即是。如《韓憑妻》條載:宋康王舍人韓憑,娶妻何氏,美,康王奪之。憑怨,王囚之,論為城旦。妻密遺憑書,繆其辭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既而,王得其書,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蘇賀對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心有死志也。”俄而憑乃自殺。其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自投臺;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于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賜憑合葬!”王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之間,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相就,根交于下,枝錯于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謂此禽即韓憑夫婦之精魂。今睢陽有韓憑城。其歌謠至今猶存。[6]98-99可見,這出愛情悲劇在敘事時顯得怪誕離奇。宋康王暴虐荒淫,史書多有記載,故事著力對他的暴虐和殘忍作了刻畫。尤其是在韓憑及何氏死后,他還不滿足他們合葬的要求,故意分而埋之,“冢相望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奇跡出現了,就像《梁山伯與祝英臺》中的化蝶和《牛郎織女》中的鵲橋,韓憑夫婦冢間的“大梓木根交于下”與“鴛鴦交頸悲鳴”,這種怪誕離奇的手法運用,使得小說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三、敘述語言的鋪陳夸張
漢賦與小說在敘事藝術上的共通性,不僅表現在敘述事件的虛擬夸張上,還體現在敘述語言的鋪陳夸張上。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中云:“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體物”,指描寫事物與“寫志”,抒發(fā)情志似乎已成為賦體文學研究中千古不刊的論斷。究其文學本源,應與《詩經》之“賦、比、興”密不可分的。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者也。賦之藝術表現,乃鋪成也。從體制特點上看,賦外形似散文,內部又有詩的韻律,是一種介于詩歌和散文之間的文體。加之漢賦繼承了《楚辭》形式上一些特點,講究文采、韻律和節(jié)奏,又吸收了戰(zhàn)國縱橫家鋪張的手法,內容上著力“體物”,也注意到“寫志”,即通過摹寫事物來抒發(fā)情志。總之,賦這一文學體裁,注重鋪成夸張等手法的運用,這在漢大賦里得以很好地體現。司馬長卿《上林賦》云: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浐,出入徑渭;酆鎬潦潏,紆余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tài),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野。汩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陜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澎湃,滭弗宓汩,逼側泌,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溉;穹隆云橈,蜿膠戾,逾波趨浥,蒞蒞下瀨,批巖沖壅,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損墜,湛湛隱隱,砰磅訇磕,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后灝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5]243由此可見漢賦之鋪陳運用之風盛極。此說諸賦家早有論述,毋庸贅言,而小說里也有共同之處。小說往往在其章首處,以鋪陳的語句顯示其風貌。如《搜神記•卷十二》講“五氣變化”時載:“天有五氣,萬物化成。木清則仁,火清則禮,金清則義,水清則智,土清則思:五氣盡純,圣德備也。木濁則弱,火濁則弱,火濁則淫,金濁則暴……”[6]101可見小說亦具有鋪陳性質。其次,小說在多以夸張之語敘述夸張之事,《搜神記》中俯拾即是。總之,漢賦與古小說在敘事藝術手法上有一定的共通性,這主要表現在:敘述事件的憑虛構造與荒誕離奇、敘述語言的鋪陳夸張。正因為文體之間的交融共通,才共同促進了文學的勃興與繁榮。
[參考文獻]
[1]袁行霈.中國文學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王楠.近五年賦體文學與小說關系研究述評[J].河北科技師范學院學報,2013,(4).
[3]劉知己.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易聞曉.漢賦“憑虛”論[J].文藝研究,2012,(12).
[5]浦銑.歷代賦話校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干寶.搜神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作者:安相 單位:貴州師范大學 文學院
- 上一篇:小說《不如歸》在中國的傳播范文
- 下一篇:國際法視野下律師業(yè)自治的現狀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