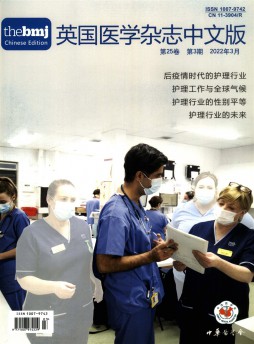評格英國小說家的歷史敘事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評格英國小說家的歷史敘事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國外文學雜志》2015年第三期
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使得大英帝國的殖民體系瓦解,傳統的社會結構、社會秩序、價值觀念土崩瓦解,貧困與縱欲并存,人際關系扭曲,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文化失去規范,人們感到茫然若失。但是,英國并沒有放棄對“大國地位”的追求,尤其是在撒切爾夫人執政期間,政府大肆宣傳“歷史價值觀(以維多利亞時代為標準)”,“在當時,遺產、延續性、懷舊、傳統是十分流行的詞語”。①這種情結在文學上的表現就是20世紀后30年英國小說創作中興起的一股書寫歷史的熱潮。這些作家包括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Swift)、馬丁•艾米斯(MartinAmis)、彼得•艾克羅伊德(PeterAckroyd)、朱利安•巴恩斯(JulianBarnes)、石黑一雄(KazuoIshiguro)、伊恩•麥克尤恩(IanMcEwan)、拜厄特(A.S.Byatt)、薩爾曼•拉什迪(SalmanRushdie)等。他們的歷史小說具有的共同特點是:質疑傳統歷史敘事,解構宏大敘事,建構文本化的歷史。和新歷史主義者一樣,他們認為歷史不過是一種敘事方式而已,人們不可能找到“原生態”的歷史,而只能循著文本蹤跡找到關于歷史的敘事。
與傳統歷史小說作家不同,當代英國歷史小說作家不屑于為帝王將相立傳,他們經常選擇歷史上的文化名人為關注點,例如朱利安•巴恩斯的代表作《福樓拜的鸚鵡》(Flaubert'sParrot,1984)以研究法國小說家福樓拜的生平和著作為線索;彼得•艾克羅伊德栩栩如生地塑造了唯美派作家奧斯卡•王爾德、18世紀建筑家尼柯拉斯•霍克斯摩爾(NicholasHawksmoor)及著名詩人托馬斯•查特頓(ThomasChatterton)的形象。斯威夫特與其他當代歷史小說作家不同,他善于選取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在描寫家庭及家族的隱私、瑣碎事件中凸現社會現實和歷史的變遷。除此之外,斯威夫特還有其獨樹一幟之處:他對歷史敘事與心靈之間關系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討。既然歷史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觀建構性,我們不能知道真正的歷史是什么,為什么還要探尋與思考它呢?它能給當代人什么啟示呢?斯威夫特的歷史小說為這些疑問提供了答案。目前,國內對斯威夫特及其作品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所見只有一部著作,即蘇忱的《再現創傷的歷史:格雷厄姆•斯威夫特小說研究》。為數不多的評論性文章散見于期刊雜志,這些文章多是選取作者某一部小說進行研究,并且大多圍繞其后現作特征展開討論。本文試圖對斯威夫特的歷史敘事進行系統梳理,從“回歸心靈”角度闡釋其歷史敘事的意義。有些歷史學家和哲學家曾經探討過心靈與歷史的關系,德國哲學家狄爾泰說:“歷史學家將自己的心靈注入他所面臨的那些已經消亡的資料中。”②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認為,“歷史是活著的人的自我認識……它只存在于批評和闡釋那些過去文檔的歷史學家的心靈中。”③他說:“我們只能以今天的心靈去思想過去,在這種意義上,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④英國歷史學家柯林武德認為,所有的歷史“只是在歷史學家的心靈中對過去的重演”。
⑤他曾用一個比喻說:“過去的一切都活在史學家的心靈之中,正如牛頓是活在愛因斯坦之中。”⑥當代歷史學家海登•懷特表達了同樣的觀點:“歷史不僅是關于事件,而且關于這些事件之間的關系,這些關系并非事件本身所固有,而是存在于反思它們的歷史學家的心靈之中。”⑦總之,這些哲學家和歷史學家認為關于過去的、原始的、粗糙的資料和文檔并不能自動揭示歷史,其意義是當代歷史學家經過自己的頭腦加工后賦予的。在斯威夫特的九部小說中,《羽毛球》(Shuttlecock,1981)、《水之鄉》(Waterland,1983)及《從此以后》(EverAfter,1992)這三部小說最具有代表性,它們從三個不同方面表明了心靈與歷史敘事之間的關系。小說中的人物都將目光投入到家族及個人歷史中,他們將那些歷史在自己心靈中復活,按照自己的意愿與目的對過去的資料進行取舍編輯,進而重新闡釋和解讀歷史。在此意義上,這些人物所做的工作和歷史學家有一定的相似之處。本文從分析斯威夫特的文本出發,探討他如何拓展了心靈與歷史的關系,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心靈對過去重建”的歷史:歷史不是一個固定的、先驗的、形而上學的存在,它伴隨著我們的敘事和詮釋活動而生成;二、人的心靈在重建歷史的同時也獲得了感悟和凈化。人在心靈深處渴望權力和愛,渴望建立自我認同感,渴望戰勝虛無感,賦予生活以意義。通過歷史敘事和詮釋活動,心靈得到了滿足、慰藉、復蘇和成長。斯威夫特對心靈與歷史敘事之間的關系所作的思考和探索揭示了歷史的本質和意義,他通過小說告訴讀者:回歸心靈是一切敘事的意義所在。
一、《羽毛球》中的歷史詮釋與話語權力
《羽毛球》探討了主人公普蘭提斯如何通過詮釋父親的戰爭回憶錄而獲得權力感,而權力欲望就是人的心靈深處的本能需要。小說的敘事者普蘭提斯在敘事過程中不斷長篇引入他父親的自傳體回憶錄《羽毛球———一個特工的故事》中的內容,二人的話語構成了雙重敘事,對同一段歷史進行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詮釋。父親的回憶錄向讀者展示了一個在二戰期間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舍生取義、膽識過人的光輝英雄形象。普蘭提斯卻認為那本回憶錄是父親美化自己丑行的欺人之作,他父親只不過是“以出賣同志的性命換取自由”⑧的懦夫。事實果真如此么?孰真孰假?普蘭提斯在閱讀父親回憶錄的過程中找出了許多他認為的自相矛盾之處,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父親說自己是馬丁城堡(二戰時期德國蓋世太保設置的監獄)內關押的“唯一一個英國人”(146頁),但是普蘭提斯在另一名相關人員X的檔案中發現他與父親同時被關押在馬丁城堡;(2)父親在敘述中有時稱自己“用心記下了每一個細節”,有時又說“我只記得……有許多我都不記得了。記憶有著自己的審查制度”(147頁);(3)有關父親在監獄中所受的酷刑和侮辱的敘述出現了“縫隙”或“模糊地帶”,關于“審訊室中所發生的一切,父親不是沉默就是有所保留”(105頁),于是普蘭提斯推測那些嚴刑拷打并未發生過,所以父親編不出來那些場景。總之,他認為父親的“聲望只是建立在一個謊言之上”,那本書就是一個“編造出來的歷險故事”(52頁)。他還收集了其他一些模棱兩可的資料來證明父親非但不是英雄,反而是一個“懦夫與叛國者”(183頁)———他屈打成招,出賣了三個英國同胞,然后“在德軍的允許下逃出監獄”(183頁)。
然而細細思忖,讀者會發現普蘭提斯的這些依據都不足以說明問題。以第一個依據為例,X也被關押在同一個監獄,這個材料出現在X的檔案上,可是戰爭期間檔案中的信息經常是漏洞百出,難道X的信息就是準確無誤的么?況且即使X也在這個監獄,他們是各自被羈押,父親也不一定就知道還有一個英國人在那里。我們再來看他的第二個依據,父親有時說他記下了全部,有時又說有些事記不得了,這是正常人的正常反應,人的記憶的確如此,經常是有選擇地記憶,不能據此就認為父親說的是謊言,普蘭提斯是否有些吹毛求疵?再看第三個依據,父親被拷打的經歷太恐怖了,以至于“難以言表”(106頁),因此父親沒有關于那些事件的任何文字,這也在情理之中。普蘭提斯為何認為那些事沒有發生過呢?小說采用“嵌套式結構”雙重敘事者這一手法,突出表現了普蘭提斯敘事的不可靠性。普蘭提斯是主要敘事者,父親是“嵌入式”敘事者,父親的敘事包含在普蘭提斯的敘事中,受控于后者的隨意取舍與裁剪。目前父親患了失語癥,精神崩潰,面無表情,已經住在精神病院兩年之久,因此讀者所獲得的一切信息都來自普蘭提斯。如果將這部小說看作一個舞臺劇,那么在舞臺上盡情表演的是普蘭提斯,他巧舌如簧,隨心所欲,盡情發揮。值得注意的是,他本人就是一個不可靠敘事者(這樣的證據很多,由于篇幅限制不宜細論)。事實極有可能是:父親的的確確是個戰爭英雄。普蘭提斯如此詮釋父親的歷史是受其內心權力欲望所支配,他與周圍的世界不和諧,覺得自己永遠處于“不滿意”(72頁)狀態。他和妻子疏離,“我老婆怕我,她不了解我”(100頁)。他和兩個兒子“沒有任何交流”(211頁),“一點不和諧”(53頁)。他甚至覺得自我異化,“不能隨心所欲”(8頁),每天似乎在“表演”,“角色是別人規定好的”(10頁)。在種種不如意中,父親帶給他的陰影最為濃重,父親的偉大凸顯出他的卑微與無能。
于是,他竭盡所能擺脫父親的影響,向大家證明父親只是一個與他并無區別的普通人而已———一樣的軟弱無能,一樣的自私平庸。如此這般,普蘭提斯獲得了心理上的安慰,找到了自尊感和權力感,就如他自己所說:“緊緊包裹著我的那無形的東西轟然倒塌了,我不由自主地感覺到無比解脫。我終于逃脫出來了。我自由了。”(183頁)他覺得和父親的關系前所未有地“完美平衡”,“我得知了父親的秘密,現在我們之間的關系調整過來,好得不能再好了”(213頁)。在小說結尾處,普蘭提斯的性格有了突飛猛進的改變,變成一個充滿愛心、溫柔體貼的丈夫和父親。有的評論者認為這個變化是他“權力場”轉變的標志,他以前在工作中屈居人下,如今崗位得到了提升,滿足了內心的權利欲望,因此在家就沒有必要再是個暴君了。這樣的解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完全。普蘭提斯的巨大改變可以看作是他自己想象出來的結果。畢竟,我們讀到的只是他自己寫的日記(整部小說是以日記形式呈現的),除了他自己的敘述,我們什么都不知道。評論者卡茲文斯基認為,普蘭提斯學會了如何運用一個更微妙的技巧來獲得權力,而不是通過身體暴力,他“為了擴大和保衛自己的權力,利用文本策略‘創造’或‘發明’了一個自我”。⑨通過書寫“自己”的故事,他建立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個文本的世界,在這里他獲得了妻子、兒子與同事的愛和尊重。在他的想象世界中,他不再需要通過扇耳光讓兒子聽自己的話,他獲得了對妻子和兒子的操控權,而且這種操控是他們樂意接受的。關于普蘭提斯父親的回憶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釋,就像一千個人讀《哈姆雷特》就會有一千種理解一樣。普蘭提斯解讀父親歷史的方式是為他自己的目的服務:尋求權力。他向讀者顯示了他的能力:他可以把英雄變成賣國賊,他也可以取代父親的位置,成為小說《羽毛球》中的“英雄”。通過詮釋父親的回憶錄,普蘭提斯寫成了自己的日記,創造了自己的歷史,獲得了話語權。
二、《從此以后》中的歷史詮釋與自我認同感
《從此以后》中的主人公兼敘事者比爾感到嚴重的歷史斷裂感及自我主體的迷失與異化,于是他將目光轉向了自己維多利亞時代的一位祖先馬修•皮爾斯留下來的一本日記,他開始以自己的方式解讀和闡釋這本日記,并在這過程中體會到前所未有的安慰與自我認同感。“想象”是比爾解讀馬修日記的主要手段。馬修的日記只是一些片段性文字,既不連貫又不完整。也正因如此,比爾才可以有大片的創造空間,才能夠將自己放入歷史和家族中。元小說的敘事手法與大量虛擬語氣的使用時時提醒讀者他所說的只是假想而已,“他(馬修)也許是這么想的……”⑩“他也許是這么個人”(95頁),“他一定是想到了……”(97頁)“我猜想他長得很強壯,看起來有些嚴肅。(對他的長相我沒有任何證據,我一點都不知道他到底長什么樣)”(101頁),這類帶括號的插入語在他的敘述中比比皆是。他也經常毫不忌諱地說:“你不得不想象出那情景……”(101頁)“那是我認為應該發生的,是我希望如此發生的。”(103頁)后來他直截了當地說:“我創造了這所有的一切。”(109頁)“關于馬修,我知道什么呢?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想象出來他的故事、他的心理,我創造了他。我將他從黑暗中拖到光明之處。”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想象”并不是信馬由韁、海闊天空,而是有特別用意的。仔細分析,我們會發現他對馬修日記的詮釋是為自己的心靈服務的,正如他自己所說:“也許我要尋找的不是祖先,而是正相反,我尋找的是我自己,我要知道我是誰。”(249頁)他通過探索與祖先馬修在“精神危機”、“對愛的渴望”這兩方面的共同之處來尋求自我認同感。比爾發現馬修同自已一樣經歷過“精神危機”。馬修的日記記載了從1854到1860這六年時間里的事件,也穿插了對童年、青年和婚后生活的回憶。比爾發現馬修一直在苦苦尋找生活的支柱與力量。年輕的馬修將上帝看作力量源泉、生命意義的賦予者,他認為是上帝給了他不朽的靈魂:“世界表面所有的東西把你帶回核心事實:大自然的杰作;人也一樣,都是上帝存在的跡象。”(103頁)比爾推測在1840年馬修離開牛津大學的時候,他“還沒有放棄對上帝的信仰,仍然相信《圣經》中的每個字都是不變的真理”。(102頁)1854年發生的一件事對馬修影響很大:在萊姆•里吉斯度假時,他偶然之中發現了魚龍化石,他突然感到《創世記》中上帝造人的理論是錯誤的,“我使勁兒盯著這怪物的眼睛”(89頁),“這一刻是我信仰動搖之時,是我的偽信仰開始之時”(101頁)。他意識到人類“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瞬。有沒有人類,世界都是亙古永存的,那么我們為什么還要假設未來給了我們什么許諾,假設我們在創造物中占有一個特別的、永恒的位置呢?”(146頁)1854年他年僅兩歲的兒子菲力克斯夭折了。這一打擊使他的信仰徹底崩潰,1859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的出版更堅定了他的看法,最終他向作牧師的岳父坦白了自己對宗教的懷疑,萬不得已的情況下結束了自己的婚姻。馬修和他的維多利亞時代之所以如此吸引比爾,是因為它們如一面鏡子,反射出比爾自己目前所處的迷茫狀態。馬修的精神危機代表了19世紀后半葉人們的普遍思想,人們開始質疑生命起源與意義、理性與秩序。福爾斯認為:“就如我們現在生活在核威懾時代一樣,維多利亞時代面臨著進化論引起的精神危機。”
斯威夫特在此部小說中暗示了這種類似性,他將比爾媽媽的生日設在日本廣島被原子彈炸毀那一天,象征著“前核武器和后核武器這兩個世界的分水嶺”(244頁)。核武器對比爾的生活軌跡影響深遠,據說他父親的自殺就和廣島事件有關(他因曾秘密參與那個轟炸行動感到愧疚而自殺)。比爾感到20世紀的人們在核時代的憂慮與馬修在“前達爾文”和“后達爾文”分水嶺時期的精神掙扎有暗合之處。馬修日記中提到一個名叫布魯奈爾的工程師,他的工作具有象征意義,它“使陸地與陸地相連,在虛空之間修建一條通道”(151頁)。比爾闡釋馬修日記的意義也在此:在現在與過去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從此以后》與約翰•福爾斯(JohnFowles)的《法國中尉的女人》(TheFrenchLieutenant'sWoman,1969)有很多相似之處:它們都描寫了19世紀中期萊姆•里吉斯的場景,都直接提到了萊爾、達爾文和瑪麗•安妮這些在多塞特鎮的懸崖上發現史前遺骨的人物。《從此以后》與拜厄特的《占有》(Pos-session,1990)在情節方面也很相似,都提到了“對于新出現的維多利亞時期手稿的爭奪、對學術禿鷹的抗爭、對英國金錢政治的諷刺”。瑏瑣但是三位作家的出發點完全不同,福爾斯將現代與19世紀并置,以“元小說”的形式解構傳統小說,以此顯示傳統小說自身的虛構性。拜厄特有意將維多利亞時代詩人的境界和當代人心理狀態進行對照,旨在揭露當代社會物欲橫流、急功近利的現象。而斯威夫特則從心靈慰藉角度來反觀歷史,通過閱讀和編撰馬修的日記,比爾在19世紀人的精神危機與20世紀自己的精神危機之間找到了連續性,找到了心靈的共鳴。似乎先輩馬修穿越百年時空在與他對話,撫慰他那顆辛苦飄零、孤獨無助的心靈。“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他意識到精神迷茫、意義追尋是人類的共相,由此他的自我迷失程度有所減輕,自我認同開始復蘇。除了在馬修身上發現精神危機的共振,比爾也發現馬修與他一樣對“愛”充滿渴望與珍視。露絲是比爾困苦中的希望、悲痛中的安慰。然而命運早早奪去了露絲的生命,比爾的生活希望也隨之消失殆盡,她的死動搖了比爾的自我認知。雖然他保留露絲的照片和她演過的電影,但是他不能將她起死回生,“你們看,什么也做不到。仿真不行,捏造不行,咒語也不行”(270頁)。于是他讓自己成為傳統意義上的上帝式的作者,在自己的想象中、在敘述中把早已作古的馬修復活了,把馬修曾經“對妻子的愛復活了”(100頁)。比爾這樣描述馬修與妻子伊麗莎白第一次見面時的場景:我想象,我創造。我想讓他們曾經幸福地生活過。我怎么知道他們曾經幸福呢?我讓他們第一次見面時候就墜入愛河。那是一個繁花盛開的仲夏日。(226-227頁)雖然馬修最終與妻子離婚,比爾仍固執地認為他們仍然相互愛戀:“他仍然愛她。他寫下了日記:那段脆弱的、羅曼蒂克的感情,一封情書。那么伊麗莎白呢?她保留了那封情書,保留了日記本。她仍然愛他。”
就這樣,比爾給馬修的日記注入了自己的意愿與希望,他希望馬修和伊麗莎白的愛情亙古不變,實際上他是在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他也渴望自己與露絲的愛情永恒不朽,就如馬修的父親作為結婚禮物送給馬修的鐘表上所題的語句:“愛戰勝一切,愛超越一切。愛逾越生死界限。”(111頁)即使比爾不能阻止幸福的滅絕,即使他創造不出“從此以后他們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童話故事,但是他畢竟愉快地嘗試了一把。在想象與重構馬修的浪漫愛情和幸福婚姻的過程中,比爾淡化了內心的痛苦。這部小說的兩個結尾(一個是敘事的結尾,另一個是故事的結尾)都暗示著比爾走出陰影,重建自我。敘事的結尾是在小說最后一頁,比爾追憶了他與露絲在1957年幸福的“第一夜”。比爾所述故事的結尾出現在第八章末尾,比爾將馬修的日記交給了同事的妻子凱瑟琳,瑏瑤希望凱瑟琳與丈夫能“從此以后幸福地生活”(121頁)。這兩個結尾都表明比爾不再感覺孤單、無愛、無用,他保留著與露絲的愛的回憶,他能夠使一對感情疏離的夫妻重歸于好。通過詮釋馬修的日記,重構馬修的歷史,比爾實際上在探索自己的身份,書寫自己的人生,“一半事實,一半假設,就如我重構了馬修•皮爾斯的生活,我重構了我自己的生活”(80頁)。令讀者欣慰的是,他最終的確找到了自我,獲得了自我認同感,重建了真實、穩定、有意義的自我主體。
三、《水之鄉》中的歷史敘事與意義創造
《水之鄉》展現的是一個混沌、“虛無”瑏瑥的世界,在這部小說中斯威夫特暗示人類需要通過歷史敘事來抗拒“虛無”,創造生活及人生的意義。不同于《羽毛球》,在《水之鄉》中作者主要采取的敘事方法不是詮釋已經存在的文本,而是讓人物講故事,使殘酷的現實生活變得可以接受進而生存下去。湯姆的母親海倫忍受著父親與她的亂倫關系,每日過著夢魘般的日子,她就是靠著“講故事”來忍受這樣的生活:那么,海倫•阿特金森是否也同樣相信奇跡?不,但她相信故事。她相信故事就是忍受無法擺脫之事的方式,是解釋人類瘋狂的方式。護士的內心深處潛藏著母性,而在凱瑟琳之家照顧這些神經衰弱病人的三年之中,海倫逐漸把這些可憐而瘋狂的病人當成孩子。就像被嚇壞的孩子一樣,他們最想聽的就是故事。而出于這個發現,她演化出一條格言:不,不要忘卻。不要抹消它。你無法抹消它,而是把它當作一個故事。只是一個故事。是的,一切都是瘋狂的。究竟什么是真實的?一切都是故事。只是故事而已……瑒瑦她講故事不僅僅是為自己而且也幫助她周圍的人和不幸生活作斗爭。她的丈夫亨利•克里克在一戰中變成瘸子并患上失憶癥,海倫經常給他講童話和故事來撫慰他的心靈。已有30多年教齡的湯姆如今面臨著被迫退休的困境,學校給出的表面原因是歷史課被裁減了,而真正的原因是他精神錯亂的妻子瑪麗在超市偷了個嬰兒,這個事件給他帶來了很大的負面社會影響。處于危機中的湯姆開始講故事,他講述了芬斯地區幾百年的歷史,追溯了250年間自己的家族歷史,也回憶了自己和妻子從童年到如今的歷史。我們可以將《水之鄉》整部小說看成一個大故事———湯姆為了厘清事情變得如此糟糕的原因并走出目前困境而講述的故事。這部小說一共52章,其中26章是故事,26章是歷史,可見斯威夫特十分注重故事在人類生活中的意義,他把過去所謂的單數大寫的歷史(History)分解成眾多復數小寫的歷史(histories),把“歷史”(histo-ry)分解成了一個個由敘述人湯姆講述的“故事”(stories)。瑏瑧斯威夫特借湯姆之口給人類下了這樣一個定義,即“是一種講故事的動物”:孩子們,只有動物才完全活在“此時此地”。只有大自然既不知回憶,也不知歷史。但是人類———讓我給你們下個定義———是一種講故事的動物。不管一個人走到哪里,他想留下的絕不是一團混沌,一段空白,而是能撫慰人心的故事的浮標和印痕。他只能繼續不停地講故事,他必須不停地編造故事。只要故事存在,一切就安然。據說,即使是在人生最后時刻,在生命隕落的最后一秒鐘,他會看見自己一生的故事在他眼前飛速閃過。瑏瑨這個定義強調了“講故事”在人類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斯威夫特本人在1992年《星期日泰晤士報》的訪談中表達了同樣的觀點:“我們通過給自己講故事,把自己的生活編成小說生存下去……我們一直在講故事,通過講這種或那種故事來安慰自己也安慰他人,娛樂自己也娛樂他人,充實自己也充實他人。”
在另一次訪談中他再次提到了故事,他認為每個人都在講故事:只是方式有所不同,有些人自覺而為,而有些人不太自覺而已。但我想那是我們身上一種真切的本能……是和神秘、混沌及無序達成妥協的一種本能。它是將個人或歷史經驗處于人的掌控中的一種方式,否則那些經驗就是流動不羈的。斯威夫特借湯姆之口還給人類下了另一個定義,即“人是渴望意義的動物”(140頁)。人類和動物不同,因為人類想理解這個世界,想給自己的生命賦予一定的意義。斯威夫特暗示,雖然“敘說”、“敘事”、“講述”這動作本身不一定有什么作用,但人類需要這個。就如湯姆所說:所有的努力就是為了保持一個欺騙,使事情看起來不是那么無意義。所有的一切就是為了對抗恐懼……你認為我講故事是為了什么?你怎么稱呼它們我都不在乎———解釋、回避事實、編造意義、回避此時此在、教育、歷史、童話故事———它幫助消除恐怖。瑐瑡在這部小說中,人物所尋找的意義并不是歷史或現實的真正意義,而是不同的講述歷史的方式,是人們構建出來的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這在某種程度上和尼采的“適當的虛構”是同一個意思。在《人性的,太人性的》這本書的前言,尼采宣稱“以前從沒有人如此深刻地懷疑過世界的一切”,而現在“上帝死了”,人們開始“在這里或那里尋求庇護———懷著一絲欽佩或敵意,或符合科學的、或有些輕薄的、或有些愚蠢的情緒……在不能夠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東西時,故意地為自己實施、歪曲或發明適當的虛構”。瑐瑣按照尼采所說,人在混沌或空虛的生活中感到恐怖和可悲,于是人必須用自己的想象力和敘事能力進行“適當的虛構”,給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給無序帶來有序和邏輯,給無意義賦予意義:我們應該明白,概念、物種、形式、目的、法則……的建立是一種強制力的結果。好像他們能夠使我們適應這個“真實的世界”;這只是作為一種強制力來為我們自己安排一個世界,使我們的生存成為可能:于是,我們為我們自己建立了一個可以被計算的、被簡化的、被理解的世界。瑐瑤當湯姆談到歷史時說:“歷史本身,宏大敘事,是真空的填充物,對黑暗恐懼的驅除器。”(53頁)他暗示在某種程度上,作為“宏大敘事”的歷史和作為通俗文化的童話、傳說及民間故事一樣,只是人為建構物,只是理解和表征歷史的不同方式而已。它們的目的都是為了給這個“寬闊的、空虛的土地賦予意義”(53頁)。斯威夫特本人曾說過:“在某種意義上,創造故事就是創造意義。創造故事決定了我們理解自己、社會及世界的方式。”瑐瑥在《水之鄉》這部小說中,主人公湯姆以“講故事”的方式將自己家族歷史和個人歷史呈獻給讀者。他認為(其實就是斯威夫特本人認為)所謂的歷史就是由不同敘事產生的人為建構之物,當我們講故事、當我們敘事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抵制“虛無”,就可以給這個混沌的世界賦予秩序和意義。
四、結語
與斯威夫特同時代的歷史小說家,如艾米斯、麥克尤恩、巴恩斯、艾克羅伊德等熱衷于語言形式技巧的實驗,善于用戲仿、拼貼、元小說等后現代表現手法突出傳統歷史小說的虛構性,揭示歷史知識的片面性,并探詢歷史發展的多重可能性。斯威夫特的小說也同樣具備上述特點,但是他更關注當代人內心的渴望和需求。從上述三部小說我們可以看出他對歷史的本質和意義的獨特理解。人類想創造秩序和意義,于是急切地探訪過去從而寫下自己理解的歷史,“我們都按照自己的意圖和興趣,或多或少地發明我們的過去”。敘述和表征過去的方式決定著我們如何看待過去,以及想從過去獲得什么。能否真實再現過去已然不重要,重要的是敘事過程本身所起到的積極的、引導的、“診療般的”作用:“歷史敘事和虛構故事皆受到行為力量的驅使……都是為了使難以承受的現實變得可以承受……使人們能夠安度殘酷的現實。”歷史敘事是保證個人話語被聆聽、個人人格被關注、個體意義得以體現的一種方式,它使我們能夠正視過去,進而更好地面對現在和未來,在這個意義上,“歷史作為所指,沒有被抹殺,而是被吸收和改變,被賦予了不同的生命和意義”。瑐瑨研究歷史最終是為當代人服務,歷史小說的功能尤其如此,這是斯威夫特小說的精髓所在。在現代西方社會,主體破碎,意義缺席,價值虛無,斯威夫特的小說向讀者展示了一個全新的認識歷史敘事的維度,再現了迷惘的當代西方人如何在流動不居的歷史語境中思考現實的困境,苦苦尋覓生活的秩序與意義。作者似乎在告訴人們:歷史敘事能幫助人們回歸心靈家園。
作者:王艷萍 單位:集美大學外國語學院
- 上一篇:《中國佬》中的圖像句子與視覺表征范文
- 下一篇:教育博士培養模式探討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