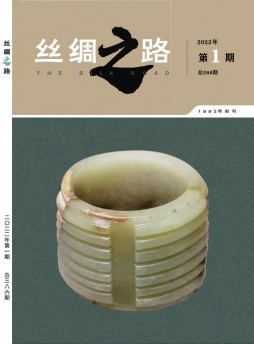絲綢之路音樂研究的現狀分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絲綢之路音樂研究的現狀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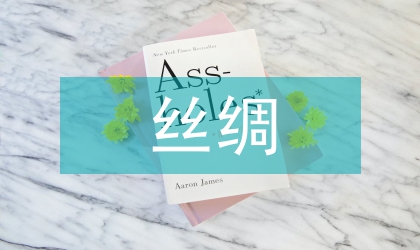
摘要:絲綢之路音樂文化的研究具有獨特的意義,它以音樂為主體,通過樂器、樂人、樂譜、樂律及其它與音樂有關的文化闡述歷史與現今的流變關系,探尋中外音樂交流的歷史軌跡。一直以來,學界在該領域的研究成果豐碩,但是還存在些許不足,寫作此文以期能夠為以后的研究提供宏觀的輪廓性的把握。
關鍵詞:絲綢之路音樂研究研究現狀
絲綢之路,分廣義和狹義兩個層次,廣義的絲綢之路包含北方和南方不同路徑的絲綢之路路線,歷史上曾經有:農業、沙漠、森林、海上等不同的絲綢之路路線。狹義的絲綢之路是指從漢至唐,自長安始,西至河西走廊,經過新疆,橫穿中亞,通過西亞,進入歐洲的經貿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在中國音樂界,狹義絲綢之路音樂的研究較為活躍。國內關于絲綢之路音樂的研究開始于本世紀三十年代,常任俠、陰法魯等對絲綢之路音樂文化的研究開辟了一片新天地。馮文慈、周菁葆、杜亞雄等學者在絲綢之路音樂研究方面的成果頗豐。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研究方法的多元、研究視野的拓寬、研究角度的變化以及新興學科的交叉互融等因素,曾出現過多次研究的高峰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本文是依據2017年以前國內學者正式出版的專著和在期刊中發表的論文,通過量化分析的方法對相關文論進行剖析梳理,以期能對絲綢之路論域的研究輪廓有宏觀的把握。
一、國內研究專著
(一)周菁葆著《絲綢之路的音樂文化》①該書是國內較早研究絲綢之路音樂文化的專著,分為上、下編,上編探索以龜茲樂為代表的古代西域音樂文化發展的歷史,下編主要進行現代絲綢之路音樂文化的研究,重點對伊斯蘭國家和地區的音樂文化進行比較研究。
(二)杜亞雄著《海上絲綢之路的音樂文化》②該書以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音樂文化為研究對象,系統介紹了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及北非各國的音樂文化以及主要的樂種,對了解海上絲綢之路各地域的音樂,考察中外音樂交流史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三)杜亞雄,周吉著《絲綢之路的音樂文化》③該書對我國境內絲綢之路沿線的陜西、甘肅、青海、新疆以及中亞、西亞的音樂文化進行了系統的解讀,在絲綢之路音樂研究以及中外音樂文化交流方面具有重要的價值。
(四)宋博年,李強著《絲綢之路音樂研究》④該書的內容涵蓋了古代埃及、印度、波斯、阿拉伯的音樂文化以及中國先秦以降至明清時期的絲綢之路音樂文化。著作聚焦音樂本體,地域跨度及時間貫穿的張力大,論述音樂文化交流史中相關聯的問題,提出了很多新的思路和新的觀點。
(五)陳凌,陳奕玲著《胡樂新聲:絲綢之路上的音樂——西域文明探秘》⑤介紹了絲綢之路音樂特別是西域音樂文化的發展。(六)金秋著《古絲綢之路樂舞文化交流史》⑥該書是介紹絲綢之路樂舞文化的著作,是一部絲綢之路樂舞文化研究的簡要歷史著作。另外,楊蔭瀏著《中國古代音樂史稿》⑦;吳釗、劉東升著《中國音樂史略》⑧;常任俠著《絲綢之路與西域文化藝術》⑨;林梅村著《西域考古與藝術》⑩;馮文慈著《中外音樂交流》;趙維平著《中國與東亞音樂的歷史研究》;宋博年著《西域音樂史》等著作中都有關于中外音樂文化交流或絲綢之路音樂論域的論說。
二、國內研究論文
筆者通過圖書館、期刊、學術會議論文集、知網等收集到這一論域的論文100余篇,時間跨度為1984年—2017年,研究成果呈上升趨勢,特別是2013年9月出訪中亞地區重要的國家——哈薩克斯坦,提出了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隨后的2014、2015年絲綢之路音樂文化的研究迅速升溫,2016年和2017年達到高峰。(見下圖)絲綢之路音樂研究數據趨勢圖一:研究的視角主要集中在:
(一)絲綢之路音樂文化的交流、傳播與融合研究;
(二)西南絲綢之路音樂研究;
(三)跨文化及南北絲路音樂的比較研究;
(四)絲綢之路與漢唐音樂研究;
(五)絲綢之路與佛教音樂、敦煌古譜研究;
(六)西域音樂的歷史觀照;
(七)絲綢之路音樂本體研究與個案觀察;
(八)十二木卡姆研究;
(九)絲綢之路古樂器研究;
(十)絲綢之路音樂美學研究;
(十一)絲綢之路音樂研究的延伸思考等。絲綢之路音樂研究視角分類圖二:
三、對研究現狀的分析
長久以來,學者們在絲綢之路音樂研究的相關論域中默默耕耘,成果豐碩,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也應該看到,在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還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現在:
(一)古今研究的不平衡性。根據圖二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古代部分,涉及到絲綢之路音樂文化的歷史流變考證,探尋中外音樂文化交流蹤跡等視角。毫無疑問,歷史流變、史料考證是十分重要且非常必要的研究內容,馮文慈、張前、周菁葆、杜亞雄、趙維平等學者在相關論域建樹頗豐。然而,絲綢之路音樂文化又極具現實意義,我們的研究視野應該兼顧古、今二個層面,既要探尋歷史發展的軌跡又要關注當今絲路音樂的發展,然而,就目前的研究現狀而言對現實問題的闡述還不夠充分。
(二)架構絲路音樂文化研究的模式顯得尤為迫切。改革開放至今,特別是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后的2016、2017年間各期刊的發文總量每年達20余篇,研究成果值得肯定,但是,看似成果繁多的絲路音樂研究存在重復性、不平衡性等問題。筆者認為,由于絲綢之路音樂文化的論域較為寬泛,應該盡快架構研究的模式,認真規劃,合理布局,這樣有利于集中研究,便于突破某些熱點、難點問題,同時也可以避免重復研究和“趕時髦”的一哄而上式的研究。
(三)研究方法應該注意的問題。就目前的研究現狀而言,雖然絲路音樂文化多元視閾的闡釋成果頗豐,但是從音樂史學和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的視角闡釋仍然是該論域的主要切入點。其中從音樂史學角度的研究占有更大的比重,以下主要從音樂史學的視角剖析在研究方法的運用上應該注意的問題。音樂史學的研究主要借助音樂考古、音樂圖像、音樂文獻等學科,依托文獻、文物、民間遺存,即“三重證據法”進行研究。
筆者通過分析文獻提出以下需要注意的問題:
1、避免對音樂信息認識的“看圖說話”。絲路音樂文化研究涉及的音樂圖像較多,對于音樂圖像的解讀往往容易出現“看圖說話”,這表現為混淆“形式的傳承”與“實質的傳承”之間的區別,缺少“辯證的”“變化的”“綜合的”思維,看似注重實證,有一說一,但是仔細分析這種“實證”是缺乏綜合考量的。客觀歷史事件發生的背后一定是包含復雜的、動態的因素,有一說一的“實證”并不能最大限度的還原歷史,往往還會出現“僵化的”“片面的”歷史認識,所以我們應該采用辯證、變化、綜合的思維全面思考,采用實證和邏輯分析相結合的方式,厘清“形式的傳承”與“實質的傳承”之間的區別。
2、注重對音樂文獻、文物的“再認識”及“精密解讀”。“文獻法”“文物法”是音樂史學研究的重要方法,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在該論域的研究中往往容易犯“拿來主義”的錯誤,缺少對文獻、文物的“再認識”和“精密解讀”。所謂“再認識”是指對原有史料的重新審視,它是經過若干年學術沉淀后的一種肯定、否定、再肯定的辯證思考;而“精密解讀”是指應該把史料放置于歷史的大背景下綜合考量,仔細求證。就絲路音樂論域而言,更應該注意從中外音樂交流的事件中(戰爭、貿易等等)探尋音樂活動,從而發現一些“新材料”為研究作支撐。
3、研究過程中加強“田野調查”工作。歷史信息不是孤立的、片面的存在,應該是立體、豐滿的,歷史事件的發生需要考慮其文化生態系統,這種文化生態系統包含民風、民俗、地方志等,以往該論域的音樂史學研究不太注意對于民風、民俗、地方志的“田野調查”工作,這樣的結果致使我們不能綜合的、立體的、全面的認識歷史。鑒于上訴,在以后的研究中我們應該注意挖掘文獻的新材料并對已有文獻材料進行再認識及精密的解讀。應該注意“形式的傳承”與“實質的傳承”之間的區別,防止音樂圖像研究的“看圖說話”。還要對已有的考古成果進行再挖掘、再認識,并且隨著音樂文物的不斷發現對音樂歷史進行“證史”“補史”等工作。應該結合“田野調查”,充分利用民風、民俗及地方志的多重考證來闡釋相關問題。最后,在研究方法中還要注意運用對比法、測量法、定量分析等方法為我所用。絲綢之路音樂文化的研究具有獨特的意義,它以音樂為主體,通過樂器、樂人、樂譜、樂律及其它與音樂有關的文化闡述歷史與現今的流變關系,探尋中外音樂交流的歷史軌跡。一直以來,學界在該領域的研究成果豐碩,但是還存在些許不足,寫作此文以期能夠為以后的研究提供宏觀的輪廓性的把握。
作者:李虎 單位:沈陽音樂學院大連分院講師
- 上一篇:藝術專業中國古典舞教學內容方法分析范文
- 下一篇:信息化背景下戲劇檔案管理研究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