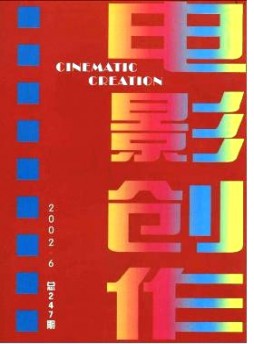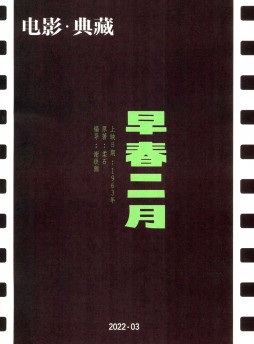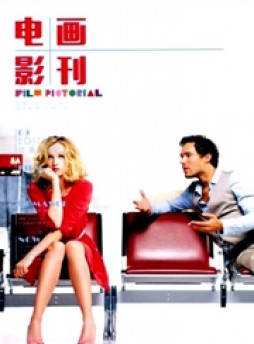電影的草原敘事與空間美學(xué)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電影的草原敘事與空間美學(xué)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馬克思主義美學(xué)研究》2017年第1期
摘要:本文以中國蒙古族電影作品為研究對象,從電影敘事和空間美學(xué)的視角,深入剖析了蒙古族電影物理空間、抽象空間和隱藏空間三位一體的草原敘事理論體系,歸納總結(jié)出蒙古族電影的空間美學(xué)特征,為對電影敘事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關(guān)鍵詞:蒙古族電影;草原敘事;空間美學(xué)
談到電影敘事,大部分人會立刻想到電影時間,從而忽略“電影空間”這個重要的問題。幀是電影的最小單位,每一幀展現(xiàn)著一個畫面,而每一個畫面都是由空間實現(xiàn),再由電影本身的講述和觀眾心理補(bǔ)充,使得空間和空間自然縫合,產(chǎn)生電影時間進(jìn)展的效果,從而完成敘事及表意工作。蒙古族題材電影的時空處理帶有明顯的“行動整一律”特征,即相對固定機(jī)位的單向度拍攝,時間的轉(zhuǎn)換必須兼顧空間的轉(zhuǎn)移,時空之間形成了高度一致性,幾乎看不到好萊塢影片中同一時間內(nèi)不同空間或同一空間內(nèi)不同時間的切換,畫面剪輯依照的邏輯是特定時間中對應(yīng)的空間,或者說是特定空間中的一個時段①。草原是蒙古族電影中重要的空間承載地,是草原文化的內(nèi)部空間展示以及引發(fā)敘事走向的重要原因,草原、馬背和蒙古包形成草原敘事的特殊概念。本文從中國蒙古族電影的草原敘事分析入手,對其敘事方法以及空間美學(xué)進(jìn)行梳理歸納,從草原、馬背和蒙古包三個特定的草原敘事物理空間分析入手,逐漸延拓至電影的抽象化空間和隱藏空間,研究其典型特征和相互關(guān)系,探索其中的草原民族文化和人民精神需求的銀幕書寫方法技巧。
一、永恒的陳述式物理空間
蒙古族是具有古老傳統(tǒng)的游牧民族,經(jīng)過幾千年的錘煉形成了強(qiáng)大且固定的草原文化。草原文化就是世代居住在草原地區(qū)的先民、部落和民族相繼創(chuàng)立的與草原生態(tài)相適應(yīng)的一種文化,也就是草原民族創(chuàng)造的文化②。蒙古族人有著熱情奔放、自由豪邁、積極進(jìn)取、樂觀向上的優(yōu)秀民族精神,視草原為生命和心靈的寄托,以馬為日常交通工具和理想承載,將蒙古包看做是他們的棲息地和家園港灣,所以草原、馬背、蒙古包是蒙古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聯(lián)系物,也是“自我”視角的滿足,是其內(nèi)心不可或缺的精神凈土,同樣也是蒙古族電影里永恒不變的物理空間。在蒙古族電影敘事中常常將本族的風(fēng)俗特色展現(xiàn)在以上三個具體的物理空間里,可以說,草原、馬背和蒙古包承載著蒙古民族獨有的生命體驗和生命意識的審美意象。大多數(shù)的蒙古族電影都是以草原展開敘事(開端),以馬背、蒙古包作為敘事空間縫合(中段),并以草原作為敘事結(jié)束(結(jié)尾),既沒有多線敘事或繁雜人物關(guān)系也少有好萊塢式的蒙太奇交叉剪輯,而常使用經(jīng)典三段式戲劇結(jié)構(gòu)進(jìn)行故事講述,最多給予回憶段落作為空間轉(zhuǎn)換。這種特點符合蒙古族純粹的生活方式和樸素的傳統(tǒng)美德要求,也遵循講述者和被講述者的內(nèi)心訴求。蒙古族電影對草原空間的歌頌和細(xì)膩的情感描寫都充分展現(xiàn)出蒙古族人民對根的本能追求和執(zhí)著眷戀。
一千三百年前南北朝時期的民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fēng)吹草低現(xiàn)牛羊”形象地展現(xiàn)了草原包容舒展的雄壯之美。草原作為家園的能指是生存境地的符號,古老的蒙古族群世代生活于草原,人民的信仰、風(fēng)俗、習(xí)慣甚至價值觀、世界觀都因此被賦予了深厚的草原氣質(zhì)———傳統(tǒng)保守且永恒不變。由文學(xué)作品改編的蒙古族電影《黑駿馬》中草原被大量鏡頭書寫。在主人公白音寶力格幼年時期,草原總是被陽光照耀,鍍上了一層圣潔的金邊,孩子們在草原上嬉笑打鬧地度過無憂的時光;隨著其第一次離開家鄉(xiāng)再回到草原時,物是人非,草原也進(jìn)入寒冷的冬季,生命似主人公的內(nèi)心一般枯竭和潦倒;當(dāng)他經(jīng)過大風(fēng)大浪帶著著名歌手頭銜第三次回家準(zhǔn)備釋然心結(jié)的時候,草原進(jìn)入了夏季,所有的希望都在蠢蠢欲動,一切都是嶄新的開始;漸漸地草原進(jìn)入了金燦燦的秋季,主人公也面臨第三次離開。從富有生命力的綠色夏草場到金黃遍地的秋營盤再到皚皚白雪的冬窩子,從幼年到少年再到青年,從學(xué)前期到上小學(xué)再到外出求學(xué),從三次來到草原到三次離開草原,電影敘事也采用按時間先后順序的陳述方式進(jìn)行,在永恒的草原空間中生命將生生不息,顯示出生活的無常和倫理的規(guī)律,而旁白作為敘事的第四維空間,娓娓道來的聽覺補(bǔ)充不僅擴(kuò)大了空間想象也將故事的脈絡(luò)清晰展現(xiàn)在銀幕上。有異曲同工之妙的蒙古族電影《天上草原》亦如此,該影片不惜用大量的空鏡頭來展現(xiàn)草原的完美,運(yùn)用緩慢的鏡頭節(jié)奏講述了氤氳如烏托邦的家鄉(xiāng)。蒙古族電影中將馬比喻成踏實勤奮的精神象征,馬背更是實現(xiàn)奔騰熱血理想的敘事空間。蒙古民族被稱為是“馬背民族”,他們崇拜蒼天,認(rèn)為馬是天上掉下來的神騭,沒有馬,民族就失去了神明,他們用馬打下家園,贏得戰(zhàn)爭,擁有草原和糧食。
“馬上動作片”,即影片采用豐富的高難度的馬上動作突出蒙古族的性格特點,展現(xiàn)馬背民族的風(fēng)采,具有很強(qiáng)的觀賞性,也是一種民族電影與類型電影的重合體③。電影《悲情布魯克》從25分36秒開始在短短2分44秒里,使用59個鏡頭之多,一反蒙古族電影中善用的舒緩節(jié)奏,用快切蒙太奇方式進(jìn)行剪輯,講述草原英雄們對抗日本人侵襲,保護(hù)馬群不受傷害的敘事段落,每個鏡頭都準(zhǔn)確地描寫了騎士們在馬背上的颯爽英姿和勇敢彪悍的形象,情緒氣氛緊張,讓人大呼過癮,與此同時也不斷地著重強(qiáng)調(diào)蒙古族的特殊的馬背生活和倔強(qiáng)的生命力。《黑駿馬》中白音寶力格意外撿到一匹遺棄黑色小馬駒并將其撫養(yǎng)成黑駿馬鋼嘎哈啦,主人公在馬背上完成了從長大→初戀→訂婚→外出讀書→回家→得知愛人懷上別人的孩子→無法改變→絕望離開的敘事脈絡(luò)。影片上半段隨處可見駿馬和馬群,下半段只有一匹和鋼嘎哈啦很像的黑駿馬,寥寥數(shù)筆,馬背的存在和奶奶給予的安全感一樣,一旦逝去便是敘事中的轉(zhuǎn)折點。蒙古包作為蒙古族人“家”的具象物,是蒙古族人民遮風(fēng)避雨的溫暖空間,也是拉近或疏離人與人之間情感的地方,它永遠(yuǎn)屹立在興興向榮的大草原之上,有著不可替代的審美價值。在蒙古族電影敘事中,對蒙古包空間的應(yīng)用是區(qū)別室外草原空間的典型電影手段。《圖雅的婚事》里,影片開片和結(jié)尾都是在蒙古包里舉行的一場婚禮,形成環(huán)形敘事。面對二婚的丈夫和前夫、兒子和罵了他的小伙伴兩對人大打出手,圖雅傷心地鉆進(jìn)蒙古包哭泣,此時鏡頭給予仰拍角度,使得為了活下去而選擇帶夫再嫁的女性形象變得高大,同時也讓兩個男人、一個女人、兩個孩子的屋檐變得更窄更艱辛。在狹小空間展現(xiàn)人物內(nèi)心是為了讓觀眾看到圖雅對未來隱隱擔(dān)心的一個窗口,人物活動的空間和人物的心理空間形成一組對稱關(guān)系,較好地完成電影敘事。無論歷史車輪如何滾滾向前,草原、馬背、蒙古包三個空間永遠(yuǎn)以參照物的最初樣態(tài)存在著,見證著萬物生靈的成長和自我確認(rèn)的過程。蒙古族電影敘事雖看似采用平鋪直敘的陳述方式,但將時間的無可抗拒和家園的堅強(qiáng)后盾渲染得無比有力。
二、抽象化空間敘事的精神意指
在影片的敘事中,空間其實是種在場,始終被表現(xiàn),結(jié)果是,有關(guān)空間坐標(biāo)的敘事信息被大量地提供出來,無論選擇何種取景方式④。尼克﹒布朗在《電影敘事修辭學(xué)》里強(qiáng)調(diào)電影敘事在乎的是“視點”問題,是“誰看”、“看什么”的問題,這凸顯了觀眾的位置。觀眾在一個讀解/捕捉意義的回溯中組織起影片的所指,在對意義的期待過程中組織起影片的能指,它將我們對影片的觀看功能轉(zhuǎn)化為理解功能,畫面的意義從不直接兌現(xiàn)在一幅畫面之中,而只出現(xiàn)在觀眾的記憶里⑤。電影中的空間展現(xiàn)只是純粹客觀地將故事展現(xiàn),所有的空間都建立在物理空間之上,但表達(dá)的內(nèi)容是通過敘事技巧,給觀眾極大的想象思考空間,觀眾會自行體會,思考或反思,從而可以解讀出更多電影意指,在抽象化的意指空間中凸顯了電影視覺化的詩意美學(xué)表現(xiàn)力。蒙古族電影的典型敘事特點是通過電影與特有民族文化的結(jié)合,實現(xiàn)了草原、馬背和蒙古包等具象的物理敘事空間到精神家園、英雄、愛情、母親等抽象化空間敘事精神意指的映射。草原或蒙古包對于蒙古族人們來說不僅僅是家和故鄉(xiāng)的指代,更多的是精神家園和理想烏托邦。不同于漢族電影,蒙古族電影中表現(xiàn)對家園和故鄉(xiāng)的愛是以“捍衛(wèi)”作為關(guān)鍵詞。成吉思汗的后代繼承著剛烈的血脈,民族英雄帶領(lǐng)著人民不斷地和敵人、環(huán)境苦苦抗?fàn)?只為了保護(hù)天賜與的寶貴凈土,驍勇善戰(zhàn)的英雄們策馬奔騰在夕陽之下,揮舞手中的大刀,熱血揮灑草原,雖難以用個體之軀敵對強(qiáng)大勢力,但視死如歸的豪邁品格激蕩人心。電影《嘎達(dá)梅林》的開篇段落便是一位老人正在忘我拉著馬頭琴,鏡頭拉遠(yuǎn),引入眼簾的是一望無垠的綠色大草原,鏡頭接著徐徐升起,是藍(lán)天白云的典型草原風(fēng)光,伴隨悠揚(yáng)的樂曲,讓人沉浸在自然給予的美好之中,同時對家鄉(xiāng)的熱愛也油然而生。
隨著封建制度的瓦解,加上軍閥對草原的破壞,整個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遭到了嚴(yán)重破壞,嘎達(dá)梅林帶領(lǐng)的百姓們起義,視圖恢復(fù)草原生態(tài)并獲得真正的自由,但最終以失敗告終,草原逐漸沙化。在影片中,嘎達(dá)梅林有一場關(guān)于激發(fā)百姓保衛(wèi)草原的重要宣講,這場戲使用仰拍角度展現(xiàn)嘎達(dá)梅林通過激情昂揚(yáng)的宣講激起了百姓的振奮,贏得了擁護(hù)。本片段以講述者、傾聽者、觀眾的三重空間很好的表現(xiàn)出來,觀眾也同樣被振奮,所有人都在期待這場革命的開幕,這就達(dá)到了電影敘事的雙贏效果。整部影片雖然都建立在物理空間之上,但是每個細(xì)節(jié)都在描述戰(zhàn)爭的意義并非是贏,而是為了保衛(wèi)精神家園,這個空間便是抽象概念空間。馬背雖是前文中闡述的物理空間,但往往展示了更深的意指。馬在蒙古族電影中也有男性的指代,形容男子剛毅果敢、強(qiáng)壯英俊。《黑駿馬》中年幼的白音寶力格抱養(yǎng)到奶奶家,和小索米亞有一段經(jīng)典的男人與馬因果關(guān)系對話,鏡頭以固定機(jī)位的大全景展現(xiàn)了一個對未來無比憧憬的美好空間,省去了不必要的贅述,讓觀眾自我補(bǔ)充了“家里來了一個男人之后的生活”的故事:有了男人就會有馬,生活也就沒那么難了。馬背也是蒙古族電影中展現(xiàn)男女情愛的理想空間,《悲情布魯克》中,男女主人公在馬背上馳騁,在廣闊天地自由享受純真的愛情,夕陽下的剪影讓錚錚誓言更加永恒,電影空間隨著升格鏡頭和優(yōu)美的民族音樂擴(kuò)大,蒙古族青年對于純愛向往的精神世界也添加了柔和的詩意美。蒙古族電影偏愛母親和女性形象,展現(xiàn)母親女性形象的抽象電影空間也一再被強(qiáng)調(diào)。草原除了男子,還有勤勞善良的勞動婦女們,用她們無限的柔情和包容的胸懷哺育著一代代草原子民。蒙古族電影表面上都是英雄們和男人們的成長過程,女性們的精神世界是被動等待的,背負(fù)責(zé)任和義務(wù)去料理家庭瑣事,但是若沒有這些堅強(qiáng)的后盾,哪里會有他人的成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中母親訶額倫對成吉思汗有重大影響,對其每次選擇都會客觀給予建議,這給之后兒子成為民族英雄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額吉》講述了困難時期上海3000名孤兒遷移到草原上被各個家庭領(lǐng)養(yǎng)的故事,片中母親的形象沒有過多的戲劇化描寫,而是用最樸素的敘事手法展現(xiàn)偉大的母愛,母親總說:“有牛糞燒著,蒙古包才不冷;有愛撐著,日子才不苦”;《圖雅的婚事》里圖雅日夜操持生計,女人扛起男人的活兒,認(rèn)為“死不算本事,能活下去才是本事”;《黑駿馬》中奶奶也是典型蒙古族女性形象,在白音寶力格第二次告別家鄉(xiāng)時,畫面的左邊,奶奶灑馬奶為孩子祈福,牽掛和不舍都鐫刻在蒼老的臉頰上,懷著身孕的索米亞入鏡放置在畫面的右側(cè),滿面愁容,兩位同樣牽掛白音寶力格的女性的特寫鏡頭出現(xiàn),她們內(nèi)心的意指毫無保留地放大在銀幕上,沒有哭天搶地,沒有撕心裂肺,這樣隱忍的女性形象讓人更加難忘,所有的離別之苦的內(nèi)容無需多言,聊聊幾個鏡頭點綴中敘事已經(jīng)被推向了高潮。
三、省略缺席的隱藏空間
電影空間往往被看到,但通常也會省略部分空間,這就是缺席空間或隱藏空間,看似節(jié)約成本不多贅述,實則補(bǔ)充了現(xiàn)行敘事中的空缺。缺乏一定的省略空間便會造成表意障礙,讓敘事變得含混不清,把電影的屏幕空間和鏡頭以外的省略空間放大,能夠極大地提升觀眾的參與性和代入感,電影作品的可觀性也越強(qiáng)。在蒙古族電影中,基本不會離開草原去講故事,這是典型忠實于固定空間的敘事方式。但隨著時代的發(fā)展,除了戰(zhàn)爭題材影片,情感為主的蒙古族電影開始逐漸關(guān)注草原外的“遠(yuǎn)方”,這代表著城市、現(xiàn)代化、科技、異族等新鮮元素。一望無垠的草原邊界是否還是草原,那里是哪里?于是產(chǎn)生了“那里”和“哪里”的重疊空間,影片將遠(yuǎn)方設(shè)置成一個隱藏空間,向往但卻模糊,同時也讓蒙古族人自己進(jìn)行反思和凝視:蒙古在哪里?牧民們聽說了外面的世界,開始懷疑傳統(tǒng)的生活,渴望一成不變的生活得到改變,這使電影人物的“成長”變得糾結(jié),帶上了憂傷的電影氣質(zhì)。
此類蒙古族電影的敘事模式和走向有二,其一為異族文化的入侵,讓草原人民知道除了草原和牛羊,還有燈紅酒綠的大千世界,于是想要尋找,接著選擇離開,最終發(fā)現(xiàn)離開家園就像浮萍無根,還是要回到屬于自己的草原;其二為在外面世界受到過傷害的他者突然到來,草原和民族的友好讓他者漸漸找到自我,留下或者離開都已經(jīng)帶有草原的印記,這較好地體現(xiàn)了草原的“融他性”特點。兩種敘事模式,都始終在草原上講故事,把“遠(yuǎn)方”作為省略缺席的空間隱藏起來,做淡化處理,這樣的隱藏空間在蒙古族電影中無疑起到了重要的敘事作用。《綠草地》里7分21秒中近景畢力格去溪邊打水→7分34秒中景發(fā)現(xiàn)乒乓球的神情→7分41秒大全景乒乓球從畫框右入畫→7分50秒全景空鏡頭乒乓球水中漂來從左到右→7分55秒空鏡頭乒乓球全景→8分3秒畢力格決定下水撿球→8分12秒中近景猶豫中,突然發(fā)現(xiàn)的乒乓球成為了外部世界的重要符號。導(dǎo)演不惜電影時間,緩慢地表現(xiàn)孩子發(fā)現(xiàn)→愣住→思考這是什么→-決定去撿→再次猶豫這一系列的人物內(nèi)心思考過程,敘述得極細(xì)膩,一個小小的乒乓球承載了最多的遠(yuǎn)方的信息。接下來在進(jìn)京獻(xiàn)球的路程中,當(dāng)畢力格誤入一所小學(xué),推開一扇門,聽到無數(shù)的乒乓球彈跳起的聲音時,展現(xiàn)在他眼前的不再是那個神一般的小球,而是全部的遠(yuǎn)方。電影省略了他所看到的乒乓球畫面,外部世界依然被隱藏,仍然保存著草原敘事的純粹,但引發(fā)思考的空間更大。《季風(fēng)中的馬》講述了傳統(tǒng)草原人中烏日根受到現(xiàn)代城市的誘惑,最終放生心愛的馬帶著兒子走向城市的故事。
影片中,城市自始至終沒有出現(xiàn),但代表城市的符號隨處可見。影片將城市這個外部空間極盡放大,甚至具有諷刺意味地展現(xiàn)在淳樸善良的牧民面前,隱藏的空間充當(dāng)了最重要的敘事部分。《天上草原》《黑駿馬》《額吉》都有外部世界的他人突然入侵,異族孩子被草原母親抱養(yǎng)的劇情出現(xiàn)。《額吉》中的錫林夫放棄了回鄉(xiāng)機(jī)會,認(rèn)清自己是牧民,選擇終身做草原的兒子,而另外兩部電影中的主人公都是帶著草原印記回到最初的軌跡。這些影片中,在完整的故事鏈里,隱藏異族空間、轉(zhuǎn)場或開放式結(jié)局等方式弱化了外部世界,完成了他者和自我的轉(zhuǎn)換過程。遠(yuǎn)方看似自由,但道路荊棘密布,傳統(tǒng)若被現(xiàn)代替換,后果不堪設(shè)想,這是電影想要留給觀眾的疑問,現(xiàn)代化的空間敘事被隱藏得若隱若現(xiàn),物理空間缺席,用四兩撥千斤的力道,讓誘惑的遠(yuǎn)方變得沉重和難以到達(dá),揭示人還應(yīng)在有根的地方才會腳踏實地生活下去,非家鄉(xiāng)之地都只能是他者般的過客。在電影敘事中,空間是先于時間完成的,想要完成優(yōu)良的電影敘事系統(tǒng),物理、抽象和隱藏空間的構(gòu)建尤為重要。蒙古族電影的敘事和空間緊密相連,從蒙古族電影的代表作品中,可以歸納總結(jié)出蒙古族電影空間使用的三種典型形態(tài)和主要特征,雖不完全,但幾乎囊括絕大多數(shù)電影的敘事技法,這為深入理解蒙古族電影的敘事空間提供了良好的范本。本文拋磚引玉,希望廣大的電影藝術(shù)研究者和創(chuàng)作者能對蒙古族電影空間的構(gòu)建予以更多關(guān)注和更加深入的研究。
作者:劉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