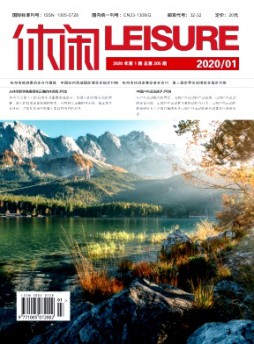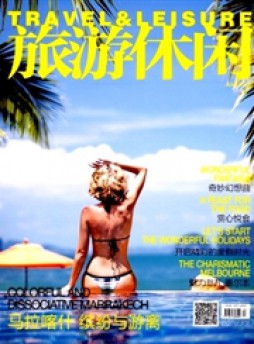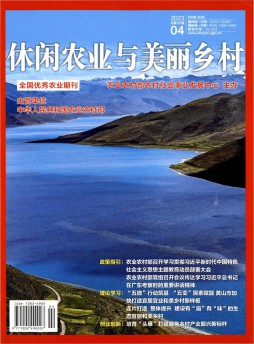休閑文化的人物畫特色探討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休閑文化的人物畫特色探討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文章對四川人物畫題材以及當代四川人物畫休閑文化題材出現(xiàn)的原因進行研究分析,從中折射出四川畫家對當代休閑文化影響下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現(xiàn)狀的關注,透溢出對當下的“景觀”社會的反叛和疏離,以及對現(xiàn)代性追逐的抵觸、對曾經(jīng)流行的崇高美學的反思,表現(xiàn)了大眾消費文化與畫家世俗情結的暗合。
一、四川地域環(huán)境對人物畫的影響
以成都平原為代表的四川“閑”文化的發(fā)展與演變順應著整個中國的文化發(fā)展趨勢,出現(xiàn)了“心閑”向“身閑”的轉(zhuǎn)化軌跡。由于天然的地理位置和氣候,由岷江和沱江水系沖擊而成的肥沃土地使這里的人自古就過上了水旱從人、不知饑饉的日子。西漢時期,成都的織錦業(yè)已十分發(fā)達,從成都出土漢代畫像磚《煮鹽圖》可以窺見當時的煮鹽、繅絲、織綢、冶鐵、兵器、金銀器、漆器等手工業(yè)已很普遍,由此帶來商業(yè)的發(fā)達,成為六大古都之一,這是四川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的第一個高峰。第二個高峰出現(xiàn)在安史之亂后唐玄宗逃往西蜀,大量中原人士追隨而來,很快將成都催生為重要的文化中心,當時名列全國四大名城(長安、揚州、成都、敦煌)第三位,其商貿(mào)經(jīng)濟地位,有“揚一益二”的美名(揚州第一,益州即成都第二)。此后,歷前后蜀四代皇帝,直到北宋初年,成都地區(qū)的經(jīng)濟文化經(jīng)歷了東漢以來最興盛的時代。再至明清,由于政治和文化中心向東北方向和東南方向轉(zhuǎn)移,四川在這一時期的文化、經(jīng)濟和政治也就被邊緣化了。文化與經(jīng)濟之間一直存在相依帶水的關系,東漢時期是第一個高峰期,而唐玄宗入蜀避難也促成了佛教石刻造像和壁畫的發(fā)展鼎盛。第二個高峰時期,五代北宋,出現(xiàn)了黃筌、蘇軾兩位書畫家,影響了此后一千年以來寫實花鳥畫和寫意山水畫的發(fā)展。黃筌和兒子黃居寀最擅花鳥畫,他將唐代剛剛開始的花鳥畫推向一個獨立的繪畫門類,與傳統(tǒng)的人物、山水兩大畫科并立,構成了中國繪畫的三大畫種。在五代十國時期,后蜀主孟昶在成都建了第一個皇家畫院“翰林圖畫院”,任用黃筌掌管翰林圖畫院,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設皇家畫院。北宋太宗的翰林圖畫院,其寫實主義畫風深得北宋太祖、太宗賞識,北宋畫院又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黃氏繪畫藝術的原則與標準作為品評、鑒定宮廷畫師藝術水準的原則與標準。正當宮廷畫家黃筌寫實主義花鳥畫風在北宋大行其道時,文人蘇軾卻在倡導一種與黃筌從理論到技術都完全相反的水墨寫意畫風,他盛贊王維“觀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這種逸筆草草不求形似的態(tài)度促使元代完成了從寫實到寫意的飛躍,繪畫只是移情遣性,抒發(fā)胸臆,追求筆情墨趣,輕形重意,詩書畫印開始融合,相得益彰。文人畫(寫意畫)最早影響主要在山水畫領域,后來揚州畫派和上海畫派將蘇軾的文人畫思想推進到花鳥人物畫領域。黃筌和蘇軾對家鄉(xiāng)四川的文化影響是深遠的,無奈明清以后中國經(jīng)濟文化重心的東移,四川一直沒有再出現(xiàn)過對中國繪畫史有影響的畫家,直到民國時期出現(xiàn)了張大千和蔣兆和的作品,在筆墨技法和人文價值方面對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國畫師發(fā)生了影響。隨著城鎮(zhèn)化的發(fā)展,娛樂與休閑生活方式不斷增加,作為與現(xiàn)實聯(lián)系最緊密的人物畫題材,也緊隨社會的脈絡而跳動。
二、當代四川人物畫題材
傳統(tǒng)市井休閑人物畫題材主要有時令風俗、商販買賣、民間戲藝、盤東行旅、放牧垂釣、耕織捕魚,這些畫大部分描寫平民生活、再現(xiàn)社會風貌,散發(fā)著濃郁的生活氣息。自然淳樸趨于平民化的題材內(nèi)容,自宋代以來成為描繪市民世俗生活的重要素材。2000年成都幾位書畫家與民俗專家精心合作,以《清明上河圖》為圖式,作了一幅長約30米,寬0.3米的《老成都》民俗風情畫長卷,完美真實再現(xiàn)了民國后期(1940年代中期)舊式成都的風貌。這種日常生活的藝術呈現(xiàn)與許多懷舊情調(diào)的文藝作品一樣,皆是對現(xiàn)代性的自覺反思。自在、自由、閑適既是傳統(tǒng)農(nóng)耕文明的一種基本生活方式,也是文人的一種揮之不去的情結,本質(zhì)上也是人的一種永恒的精神向往。在現(xiàn)當代,藝術家敏銳地捕捉到這種世俗生活變遷的當代意義,他們或懷舊或反思或白描地展現(xiàn)了當代人們的休閑生活。題材主要有:游賞娛樂、競技休閑、民族風情、市井圖像等等。
(一)游賞娛樂題材成都除了在元宵節(jié)這些大型的節(jié)日有舞龍表演和觀燈活動外,還有自己的地方特色。早在西蜀年間,成都游賞習俗與文化藝術就結合起來了,到了唐宋,基于商業(yè)的需要,每年各種專業(yè)性市場不斷:一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市、四月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寶市、八月桂市、九月藥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趕集逛街成了市民的休閑活動,隨著出行方便,以前閉塞的小鎮(zhèn)被人所知,其保留住的街道、宅院、堂館、廟觀、牌坊等建筑和木雕、石刻、民俗活動吸引人們蜂擁而至,畫家鄧楓《煙雨柳江》系列表現(xiàn)了市井小民的生活情態(tài)以及喝茶、聊天、釣魚、觀景照相等等日常生活,真實地呈現(xiàn)了市井小民的生活景象,折射出川人的休閑文化如靜淌的河流,從遙遠的地方融入到當代人的生活中。《煙雨柳江》在圖式、語言上放棄主從關系的刻意布陳,回避對人物的極力雕造,是對傳統(tǒng)筆墨程式的有意放棄,從而在藝術風貌與趣味上與所表達的主題及文化意趣達到一種吻合。
(二)民族風情題材四川西部橫斷山脈有一條被稱為藏羌彝走廊的河谷地帶,主要聚居了藏、羌、彝等少數(shù)民族,艱苦的環(huán)境磨練了他們意志,多民族的聚集生活也養(yǎng)成了他們開朗豁達的性情,與漢民族不同的生活習性很容易成為民族風情的寫照。20世紀以來,藝術家們深入民族地區(qū),從少數(shù)民族老百姓身上獲得創(chuàng)作的靈感,擴展了中國人物畫題材。如黃胄的《慶豐收》《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方增先的《母親》《帳篷里的笑聲》,李伯安的《走出巴顏克拉》等等。生活在四川的女性畫家朱理存,她以女性細膩的眼光、母愛的情懷去關注少數(shù)民族婦女。1973年她用水墨寫意與寫實造型相并的手法創(chuàng)作了《叔叔喝水》,藏族小女孩兩手端著兩碗水,笑容燦爛,“叔叔”隱匿于畫面,女孩腳邊的幾頂紅軍帽子傳遞出“叔叔”的信息。作品沒有采用女孩、解放軍歡聚一起的群體大畫面,而是通過個體形象表現(xiàn)群體氣度,這本來是傳統(tǒng)人物畫的表現(xiàn)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傳統(tǒng)人物畫里對個體形象的塑造往往是仕女高士,近現(xiàn)代以來,普通人的形象也可以占滿畫幅,個體形象成為社會集群的命運和生存狀態(tài)的濃縮。
(三)市井圖像題材以都市集鎮(zhèn)社會生活為題材的作品中商販買賣是最為常見的。南宋畫家李篙創(chuàng)作過大量反映市井生活的作品,如《市擔嬰戲圖》《貨郎圖》,富有濃厚的生活氣息。此外還有以城市中最為常見的湯茶小販為題材的,如南宋佚名的《賣漿圖》,劉松年的《茗園賭市圖》。茶館最能反映成都人的休閑狀況。四川畫家曹輝的《太平場茶鋪紀事》就表現(xiàn)了一段成都老茶館歷史,表達了他對都市化進程中殘留的或已消失的平實的鄉(xiāng)土生活的一種深深的眷念與追憶。
三、當代休閑文化題材出現(xiàn)的原因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四川人物畫的題材以表現(xiàn)平凡的、日常生活化的普通人物取代了建國時期的革命領袖和英雄人物,四川畫家對當代休閑文化影響下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現(xiàn)狀的關注,透溢出對當下的“景觀”社會的反叛和疏離,透溢出對現(xiàn)代性追逐的抵觸,透溢出對曾經(jīng)流行的崇高美學的反思,以及大眾消費文化與畫家世俗情結的暗合。
(一)對“景觀”社會的疏遠的意識“景觀”一詞的原意是指觀看、被看,1967年德波的《景觀社會》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異化理論推及到影像傳媒領域,認為這是一個顛倒的世界,我們看到的并不是真實的。正如德波在對基督教的批判中,他說在基督教神學語境中,上帝之城的幻想取代人之真實的感性生活,這是一個“符號勝過實物、副本勝過原本、表象勝過現(xiàn)實、現(xiàn)象勝過本質(zhì)”的顛倒時代,我們今天因為影像的介入,景觀本是表象,但是它取代了本質(zhì)。隨著商業(yè)化的深入,中國社會的景觀化誘騙并奴役著大眾,平庸的娛樂和無聊的消遣,噬咬著人們的心靈。于是人們樂于流于表象而無意探究本質(zhì),樂于看電視選秀節(jié)目或肥皂劇來消磨他們的空閑時間,樂于流連在高度商業(yè)化的休閑生活中。對休閑狀態(tài)下人們?nèi)粘I畹恼宫F(xiàn),是對當下“景觀社會”的疏離,日常生活本身既包含瑣碎與平庸,又包含卓越與神奇。它是我們看到的表象,也是本質(zhì)。曹輝《老茶館•偶爾也有女人來》,其表象是對民國時期川西女性的市井生活的眷念與追憶,兩位女性幾乎占滿了整個畫面,年長的女性手里拿著長長的煙斗,有靠背的竹椅子圍合成一個私密空間,將嘈雜混沌的背景隔離開來,前景清晰的女性頭部和背景頭像構成穩(wěn)定的三角形,厚重而斑駁的渲染使畫面帶有了歷史的滄桑。女人的眼光注視著前方,前方有什么東西吸引她們觀看吸引她們偶爾來坐坐?這就是表象下透漏的本質(zhì)。畫家沒有全景式地展現(xiàn)茶館這一空間,從兩位女性偶爾來茶館坐坐我們可以猜度當時的四川茶館已經(jīng)是評書、戲曲藝人極好的舞臺,茶館中的精彩表演吸引了男男女女顧客,茶館不僅僅是男人閑聊、商販穿梭的空間,它已經(jīng)初步具有了當代公共空間的屬性。
(二)是對現(xiàn)代性追逐的抵觸現(xiàn)代性問題涉及到社會變遷的方方面面。在藝術上,首先,精英藝術逐漸從與社會的對抗中尋找藝術發(fā)展的新方向,這些藝術家既不滿意現(xiàn)存的博物館之類的藝術機制,也不滿大眾文化的商品文化氣息,于是走出博物館,在大自然中去尋找藝術與自然的結合。這些大地藝術對現(xiàn)代主義提出了一個嚴峻的挑戰(zhàn):藝術和真實的邊界在哪里?因為這種邊界在現(xiàn)代主義者那里一直是努力捍衛(wèi)的。其次,打破了藝術內(nèi)部界限。在建筑領域,曾經(jīng)在二戰(zhàn)后風靡戰(zhàn)后國家的國際主義風格,被那些復雜的、個性化的、融合多種傳統(tǒng)要素的風格所取代,建筑不再僅僅是功能性的空間,而具有了更多的文化意義。再次,精英藝術在消費社會里日漸演變?yōu)椤拔幕a(chǎn)業(yè)”,通俗文化不斷地商品化,娛樂媒介的巨大增長,迫使自主的藝術經(jīng)歷一系列激進的自我變化,到后現(xiàn)代時期,自主的藝術轉(zhuǎn)向了商業(yè)性的時尚活動中,雅俗的界限消失了。最后,機械復制時代使藝術品的復制充斥于世界各地,摧毀了真實與想象的邊界,而媒介更是越來越操縱人們對現(xiàn)實的判斷和認知。“的確,在時間的流轉(zhuǎn)中,我們正遭遇現(xiàn)代都市不可抑制的物質(zhì)空間的更新、再造,人們在釋放著對城市革故鼎新的激情,以索取標示其現(xiàn)代性特征身份證的同時,溫情脈脈的市井圖像也變得模糊起來,原汁原味、原情原欲的生活樣態(tài)漸行漸遠,正在消失于我們對對現(xiàn)代性生活方式的狂熱追求而變得淡然的記憶中。”油畫家高小華最近幾年反映市井小民日常生活作品《后街》,不是簡單生活表象的再現(xiàn),而是描摩出在我們追逐現(xiàn)代性的過程中,在城市高樓林立的景觀中,有很多人在現(xiàn)代性和傳統(tǒng)、欲望之間的真實情景。
(三)對曾經(jīng)流行的崇高美學的反思。20世紀50年代崇高與美已經(jīng)擺脫了西方語境中的形式限定,它成為精神力量。在文藝創(chuàng)作中,“革命樂觀主義”“革命英雄形象”“三突出”是崇高美學的具體體現(xiàn),人物畫作品被政治性人物壟斷,人物被分解為“英雄人物、正面人物、中間人物、反面人物”,即使畫面出現(xiàn)一般的民眾形象,也只是政治問題的需要,他們本身也成為政治性的符號。而現(xiàn)今的四川藝術家將視覺轉(zhuǎn)向市井生活,轉(zhuǎn)向休閑狀態(tài)中的市井小民,既是對曾經(jīng)流行的崇高美學的反思,也因其形象的真實、樸實、生動而更真實再現(xiàn)了溫情脈脈的市井文化。
作者:鄧楓
- 上一篇:小學美術課堂滲透德育教育之路范文
- 下一篇:設計的書衣中漢畫圖像運用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