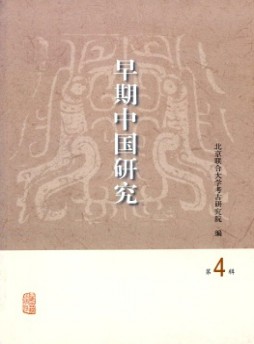早期現代漢語及其特點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早期現代漢語及其特點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現代漢語是發展的,形成了變化明顯的現代漢語史。關于“早期現代漢語”這一概念,學界有不同的理解。刁晏斌從現代漢語史的角度進行了界定,認為當指現代漢語史的第一階段,即“五四”時期至1949年。現代漢語史視角下的“早期現代漢語”是現代漢語形成和發展的重要階段,其語言特點可以概括為五個方面:紛紜復雜、文白夾雜、歐化色彩濃重、方言摻雜其中、有發展變化。
關鍵詞:現代漢語史;早期現代漢語;文言文;舊白話文;新白話文
一、引言
語言是發展演變的。社會語言學認為“語言與社會結構保持著共變的關系”,“當社會生活發生漸變或激變時,語言———作為社會現象,同時作為社會交際工具———毫不含糊地隨著社會生活進展的步伐而發生變化”[1](P3-4)。從“五四”運動以來近一百年的發展歷程中,中國社會經歷了社會制度、經濟體制、思想觀念、文化教育等領域的重大變革,這些變化無疑都會投射在語言的發展變化中。正是在社會和語言共變的大背景下,刁晏斌在1992年首先提出“現代漢語歷史發展研究”這一構想[2],并在此基礎上于2000年正式提出“現代漢語史”這一命題[3],由此開始了現代漢語史的學科建設。現代漢語史的提出和建立,推動了現代漢語共時研究的縱深發展,對整個漢語史是一種不可或缺的補充[4]。正是因為有了現代漢語史理論的指導,人們開始嘗試“共時中的歷時研究”,并把目光放到了早期現代漢語階段。
二、“早期現代漢語”的界定及研究意義
“早期現代漢語”在學界是一個比較含混的概念,人們一般用它來指稱早期階段的現代漢語,但卻沒有特別明確的時間界限。汪維輝(2012)在《研究早期現代漢語和漢語教育史的重要資料———介紹樸在淵、金雅瑛編〈漢語會話書〉》一文中,提到的多種資料是產生于1910—1930年,所指的早期現代漢語大致也就是這一階段。汪維輝(2014)在《〈漢語·華語抄略〉札記》一文中又提到了“早期現代漢語”這一概念,“兩種新發現的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漢語》和《華語抄略》,為我們提供了又一份研究早期現代漢語和東北方言的可貴資料”。近代漢語的下限一般被定為清代前半期[5](P3),或者16世紀末17世紀初的清初(最晚《紅樓夢》形成以前)[6](P216),或者18世紀中期[7](P6),這些觀點歸結起來就是明末清初。通常來說,18世紀中后期至20世紀初被看成是近代漢語到現代漢語的過渡期,因此,汪文所說的前一個“早期現代漢語”大致對應現代漢語的早期階段,后一個當為近代漢語的晚期和近代漢語向現代漢語的過渡期。現代漢語的上限始于“五四”時期,這已經成為學界大多數人的觀點。針對學界極少數不同看法,刁晏斌補充:“現代漢語的形成應以書面語為標準”,現代漢語的劃分“是求異而不是求同”[8](P6,P9),而且“現代漢語的最終確立時間,外來形式是一個重要的標準和指標”[9]。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在這一點上達成共識。何九盈認為“現代書面語的發展過程,在相當程度上是歐化的過程”[10](P44),徐時儀認為“從本質上看,五四時期的白話已是一種新語言系統”,“古代白話和五四時期后的現代白話雖然都是白話,但就思想體系而言,現代漢語和古代漢語是兩套語言系統。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結合現代漢語史的研究,刁晏斌重新定義了“早期現代漢語”。他將現代漢語分成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919年“五四”運動至1949年;第二階段:1949年到1966年“”開始;第三階段:10年“”(1966—1976);第四階段:改革開放至今(1978年至今),并且認為“如果分期不必過于苛細的話,二三兩個階段也可以合而為一,視為同一階段中的兩個部分”,其中第一階段是早/初期現代漢語階段[3]。刁晏斌在討論“港式”中文與“早期現代漢語”的聯系時,進一步明確現代漢語史三個階段的觀點,再次強調“早期現代漢語”是指從“五四”時期到1949年的第一階段,為現代漢語的形成和初步發展時期[11]。基于上述認識,我們認為刁晏斌關于“早期現代漢語”的界定是合適的,所指明確,界限清楚。“早期現代漢語”,不同的領域和學者也會使用“國語”一詞指稱。何九盈說“現代標準漢語,從前叫‘官話’、‘國語’,現在叫普通話”[12](P34),徐時儀認為“五四”時期的“新語言系統,又稱為‘國語’,后又成為現在的現代漢語”[12](P381),《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對“國語”的釋義是“本國人民共同使用的語言。在我國是漢語普通話的舊稱”。
“普通話”正式指稱漢民族共同語是在1955年,這一名稱被法律確定之后,“國語”一詞便被廢止,但在臺灣“國語”的名稱并未改變。著眼于新中國成立以前的語言研究,早期現代漢語與國語在時間上大部分交疊,在表達不嚴密的情況下,二者混用,可以理解,但從現代漢語的發展角度來看,還是使用“早期現代漢語”這一概念為好。早期現代漢語相對于整個現代漢語史來說,體現為現代漢語研究的整體性、系統性和連續性。現代漢語是動態發展的,早期現代漢語階段有不少語法現象不同于現代漢語后面兩個階段。可是,目前的語言研究一般還是把近百年的現代漢語當作一個共時平面,并且把目光主要放在后面兩個階段上,結果一是研究不全面,二是得出的結論缺乏普遍適用性。以介詞“對于”為例。人們一般認為“表示人與人的關系,只能用‘對’”[13](P182),但早期現代漢語中使用“對于”的用例卻很常見,如“這是我對于你們底希望”(許地山《落花生》),“故他家的人對于我特別要好,他的祖母常常拿自產的豆腐干、豆腐衣等來送給我父親下酒”(豐子凱《憶兒時》),“但我對于她還是不大信任,郵票固然可以在門前買,可是待發的信還是不肯直接交給她”(馮至《羅迦諾的鄉村》)等。再如副詞“比較”,一般認為“表示具有一定的程度。不用于否定式”[13](P75),“‘比較’后邊一般不能用否定副詞,如一般不說‘這個電影比較不好’‘今天比較不熱’”[14](P225),但在早期現代漢語中,“比較”修飾否定表達的現象卻很常見,如“有兩個是上海某藝術大學的學生,一個比較不漂亮點的是剛從北平來的學生”(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這樣一來,她可以比較不陌生”(錢鐘書《圍城》)。諸如此類的現象還很多,因此加強早期現代漢語的研究實在必要,而且勢在必行。綜合來看,早期現代漢語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意義和價值。首先,它可以幫助人們相對全面地了解早期現代漢語的面貌,從而建立一個客觀、完整、發展的現代漢語史。其次,它可以促進現代漢語的本體研究。這一階段的研究成果可以為其它階段提供借鑒和參照,并從不同角度修正現代漢語研究的某些結論。再次,它還可以為海峽兩岸的語言對比研究提供有力支持。刁晏斌指出“兩岸語言的共時差異,其實是早期‘國語’分化的結果,是在不同社會環境中歷時發展變化的結果和體現,兩岸民族共同語書面語之間的共時差異,體現為兩岸語言與早期‘國語’之間的距離”[15]。最后,早期現代漢語研究對母語教學、對外漢語教學以及全球華語教學都具有重要價值。
三、早期現代漢語的特點
早期現代漢語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內涵豐富,特點突出。刁晏斌曾對早期現代漢語的語法特點進行總結,認為“至少有以下四個非常明顯的特點:紛紜復雜,同義形式多,‘超常’用例多,有發展變化”。[16](P320-323)綜合考察早期現代漢語的語法現象,同時結合詞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筆者嘗試將早期現代漢語的特點總結為以下五個方面。
(一)紛紜復雜“紛紜復雜”是相對于文言文、舊白話文而言的,也是相對于現代漢語后面兩個階段而言的。先說詞匯方面。詞匯是語言的風向標。這一時期整個社會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新舊思想、文化、理念、生活方式等都存在種種沖突,政治斗爭、革命抗戰是這一時期的重要主題,因此既有表現傳統守舊的慣常詞匯,如“大戶、老爺、姨太太、佃戶、典妻”等;也有表現新式開放的新生詞匯,如“董事、股票、影院、統購、八路軍”等;還有大量的外來詞,來自英語的外來詞有“坦克、摩登、維他命、幽默、沙發”等,來自法語的外來詞有“公社、布爾喬亞、納粹、法西斯”等,來自蘇聯的外來詞有“杜馬、蘇維埃、布爾什維克、盧布”等,來自日語的外來詞有“左翼、特務、情報、干部、重工業”等。可以這樣說,早期現代漢語時期,舊詞仍在,新詞迭出,舊詞裹挾著新詞,常用詞夾雜著外來詞,共同匯入語言的洪流。再看語法方面。以實詞為例。有不少名詞可以用做狀語,如“誠意的/地告訴”“勇氣的/地說”“友誼的/地解釋”等,不少名詞可以受副詞修飾,如“最貴族”“比較劣勢”“很表情”等;動詞的重疊形式在個案上也遠比今天復雜,除了常見的“AA”式、“ABAB”式以外,還有“AB———AB”式,如“打算——打算”,有“AO(賓語)———A”式,如“哄他一哄”,有“A———AB”式,如“探———探險”,還有“A(了)——AO(賓語)”式,如“親(了)———親我的額頭”等,而且還有現代漢語后面兩個階段不大使用的個案重疊形式,如“捧場捧場、鬼混鬼混、借住借住”等;形容詞的重疊形式也更豐富,有“AABB”式的,如“嚴嚴肅肅”“親親切切”“伶伶俐俐”,有“ABB”式的,如“重沉沉”“陰愁愁”“暖旭旭”,有“AA”式的,如“痛痛”“懇懇”“潤潤”,可以重疊使用的形容詞,數量也遠遠超過現代漢語后面兩個階段。句子層面的紛紜復雜更是突出。在句子成分方面,這一時期出現了大量聯合主語、聯合賓語、聯合狀語、聯合定語、聯合述語共帶一個賓語的現象。例如:(1)日間的疲勞,和這晚餐和溫存的老人底態度,對于這吃過人間辛苦的人,有如一杯清醇的醍醐。(李霽野《三幅遺容》)(2)《巨人世家》卷三有贊美肚子的一章,尊為人類的真主宰、各種學問和職業的創始和提倡者。(錢鐘書《吃飯》)(3)她卻靜靜地,靜靜地,若有所感似的,和著沙沙的葉聲,暗暗地流下淚來。(韋素園《春雨》)(4)我們希望那種醉人的、刺人的、提拔人的、撫摸人的作品。(田漢《靈光》)(5)他們一方面翻譯著,談論著,稱頌著雷馬克,別方面寫著戰爭小說,剛剛和雷馬克絕對相反的戰爭小說。(瞿秋白《青年的九月》)以上各句都出現了不同成分的聯合形式,尤其是聯合狀語和聯合定語的運用,相對于文言文和舊白話形式,句子的復雜程度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在這一階段,還有不少按今天的語法規則無法分析的句子。例如:(6)因為從那里面,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辛酸,的掙扎。(魯迅《祝中俄文字之交》)(7)我們發見自身的錯誤而批評之便是一種覺悟的底初步。(《少年中國》May.15,1921,V.2,Num.11《詹姆士底宗教哲學》(方東美))例(6)中“的善良,的辛酸,的掙扎”的并列形式,例(7)中“的底”連用形式,目前已經很難見到。這些“超常”表達,如果按今天的眼光,可能都要歸入病句之列,但尊重語言事實,歷史地看待這些語法現象,是我們應該秉持的正確態度。
(二)文白夾雜早期現代漢語中有不少來自文言文的句法形式。刁晏斌指出這一時期存在不少“古句”和“準古句”,“所謂古句和‘準古句’是指一句話中全部或部分地采用了古白話甚至于文言的句子形式,由此而形成的句子”[16](P209)。例如:(8)此外尚有更重要者,則為道德之講究。(蘇青《論紅顏薄命》)(9)東波云“因病得閑殊不惡”,我亦生平善病者,故知能閑真是大工夫,大學問。(冰心《閑情》)早期現代漢語中,還出現了不少文言句式和白話句式嫁接的句子。例如:(10)凡是丫頭肖虎的,頭發黃的,鼻梁碰傷的,眼睛太小的,牙齒歪斜的,價錢總得殺它一下。(秦牧《私刑·人市·血的賞玩》)(11)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司馬遷的說過……(《為人民服務》)(12)狀元公許仕林也者,何嘗是白蛇與許仙的兒子呢,不過是我們愚民百姓派去的代表而已。(聶甘弩《蛇與塔》)(13)祿也者,拆穿了說就是吃的東西。(夏丏尊《談吃》)例(10)(11)中“丫頭肖虎的”“有個文學家叫司馬遷的”用的是文言句法定語后置形式,與“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各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漢語·律歷志》)、“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論語·子路》)的文言表達一致。例(12)(13)中主語“狀元公許仕林”和“祿”后面都帶上了文言文常用的提頓語氣詞“也者”。對比來看,早期現代漢語中真正意義上的文言句式不是很多,大多是經過梁啟超“新民體”影響后的文言形式,帶有太多的異質成分。陳平原說“晚清的白話文不可能直接轉變為現代的白話文,只有經過梁啟超的‘新文體’把大量文言詞匯、新名詞通俗化,現代白話文才超越了語言自身緩慢的自然進化過程而加速實現。”[17](P1-2)半文半白、文白夾雜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早期現代漢語承襲了舊白話文的大量詞語和句法形式。嚴家炎指出傳統白話小說中經常出現的“便”(相當于“就”)和“道”(相當于“說”),在早期現代漢語中“這類詞出現的頻率是相當高的”,并列舉了魯迅的《孔乙己》,全文只有三千字,“便”字出現了25次,比間或使用的“就”和“就是”要多得多,“道”和“說道”出現了13次,比單純用“說”字也要略多一些[18]。請看:(14)幸而寫得一筆好字,便替人家抄抄書,換一碗飯吃。可惜他又有一樣壞脾氣,便是好喝懶做。坐不到幾天,便連人和書籍紙張筆硯,一齊失蹤。(15)有一回對我說道,“你讀過書么?”……孔乙己等了許久,很懇切的說道,“不能寫罷?”……(我)懶懶的答他道,“誰要你教,不是草頭底下一個來回的回字么?”此外,文白夾雜的形式還體現為舊白話文句法形式的間雜使用。例如:(16)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淡。(朱自清《背影》)(17)無奈貧乏逼我,……,結果我的作品,就一天劣似一天。(冰心《文學家的造就》)例(16)中的程度副詞“很”修飾“是”的組合表達,是舊白話文中的常見形式[19],例(17)中的“一天劣似一天”的遞進差比形式,也是來自舊白話文語法[20]。在早期現代漢語中,我們看到不少文白有效融合、雅俗共賞的美文,如魯迅、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郁達夫、梁實秋等人的優秀作品,但也存在著大量文白融合得不好、文白錯雜、違和感突出的作品。可以這樣說,文言文和舊白話文對早期現代漢語的影響、干擾和滲透比現代漢語其它階段都更為突出、明顯。
(三)歐化色彩濃重吸收外來形式是現代漢語形成和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現象。外來詞大量涌入,激活了漢語中某些舊有詞綴的使用,如“-者”“-家”等,并直接影響了一批新生類詞綴的產生和發展,如“-主義”“-化”“-性”“-式”等。專就語法形式而言,主要體現為借鑒和吸收以英語為代表的印歐語語法,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歐化現象。早期現代漢語的歐化現象非常突出,因此才有學者認為現代漢語是中西文化的“混血兒”,才有了20世紀50年代語言規范化運動影響下的某些去歐化現象[21]。關于早期現代漢語歐化現象的總結,最早見于王力先生的《中國現代語法》,20世紀50年代的著作《五四以來漢語書面語言的變遷和發展》對歐化語法現象也作了大量介紹。謝耀基在前人的基礎上對歐化現象進行了相對全面的總結,既有詞法,也有句法,共涉及二十多個方面[22]。下面依謝耀基所列條目,僅從句法角度作簡單的舉例說明。首先,看詞的組合方面的歐化。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動詞性結構共同支配一個對象,例如:(18)對于知識分子,應該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們。(《論政策》)動詞前連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助動詞,例如:(19)她是來享受,她不能,不肯,也不愿,看別人的苦處。(老舍《駱駝祥子》)人稱代詞、專有名詞前面加上修飾成分,例如:(20)我的孩子們:憧憬于你們的生活的我,癡心要為你們永遠挽留這黃金時代在這冊子里。(豐子愷《給我的孩子們》)其次,看句子方面的歐化。主語往往可省而不省,也就是說主語變得必需。例如:(21)我望著外灘一帶的燈光,我記起我是怎樣地送別了一個我所愛的人,我的心開始痛起來,我的不常哭泣的眼睛里竟然淌下了淚水。(巴金《做大哥的人》)關聯詞語的使用由“隨便”變得“需要”。例如:(22)因此他雖在少年工人的群中,因為年紀知識,得到相當敬禮,然而背后卻也受他們不少的嘲笑。(王統照《刀柄》)最后,看句式運用方面的歐化現象。“被”字句的普通使用,已不限于不愿意或不愉快的事。例如:(23)上得樓來,做了母親的世瑛,乍看見我似乎有點羞怯,但立刻就被喜悅和興奮蓋過了。(冰心《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是”的使用變化如英語“be”般普遍和必需。例如:(24)雨雖暫時不下,地上是稀濕。(俞平伯《重過西園碼頭》)以上列舉的歐化現象都是在英語影響下通過翻譯和模仿而產生的新興語法形式。早期現代漢語時期還存在不少“漢語中罕用的語法形式由于印歐語言影響的推動和刺激作用而得到迅速發展的現象”[23](P1)。以處所補語句為例。張赪認為“元明時期,‘在L’一般不能位于‘V+O’后,只有動詞賓語是帶有數量修飾語的名詞賓語時才有少量的‘V+O+在L’句,‘在L’后置的句子里如果動詞要帶賓語一般是用介詞‘把/將’將賓語提到動詞前,在元明時期的標準語里這一規律非常嚴格’”[24]。在早期現代漢語中,我們看到了很多“V+O+在L”句,其中“O”常常沒有數量修飾語,如“護士放我在他的背上”(冰心《分》),“當下家樹拿了帽子在手上,在樓廊下來往徘徊著”(張恨水《啼笑因緣》),“把眼睛的藍色發揚光大起來,……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滅臀部過度的曲線”(張愛玲《更衣記》)等。這種處所補語句的大量出現與英語處所介詞結構“on/in/at+locale”置于句尾的句子結構的翻譯和模仿有很大關系。總的來說,這一時期出現的大量外來詞和大量歐化語法現象,使早期現代漢語帶上了濃重的歐化色彩,因而“洋味”十足。在現代漢語的發展過程中,有些歐化語法形式已經沉淀為漢語的語法底層,而那些因“硬譯”“生譯”等方式產生的“不中不西”“食洋不化”的歐化現象則隨著語言的發展而銷聲匿跡。
(四)方言摻雜其中張中行說“文言大致是超方言的;白話不然,雖然大多用所謂官話,卻常常不能離開方言”[25](P227)。漢語方言眾多,因此追求“言文一致”必然會打上方言的烙印,方言表達成分摻雜其中實屬難免。需要指出的是,“五四”時期,新白話文創作者們同時有意提倡方言俗語的使用,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中主張的八事之一就是“不避俗字俗語”,并進一步認為“今日作文作詩,宜采用俗語俗字”。早期現代漢語中不少新白話文作品都帶著一定的方言色彩,這主要體現為對方言詞匯的吸收,語法相對來說并不是很多。漢語眾多方言之間的差異主要在于語音和詞匯,語法區別不大,落實在書面上,則主要體現為詞匯,語法總體來說很少。雖然方言語法對書面語影響較少,但有些表達形式的方言性還是非常明顯的。以老舍的作品為例,北京口語中常見的句式隨處可見。例如:(25)他們走得要很穩,脖子上要有很大的力量,才能負重而保險不損壞東西。人們管這一行的人叫作“窩脖兒的”。(《四世同堂》)(26)好人?城全教人家給打下來了,好人又值幾個銅板一個?(《四世同堂》)(27)我沒叫他給我買票呀!我給他錢,他不要!(《二馬》)例(25)中的“管……叫作……”,例(26)中的“教……給……”,例(27)中的“叫……給”都是北京口語中常用的句式。老舍的作品帶有濃濃的京味,既有詞匯的原因,也有語法的原因。再以“動詞+代詞賓語+否定補語”為例。這一語法形式產生于舊白話文,并延續使用到早期現代漢語中,但這一形式在另一方面也體現著某種方言性,吳語、湘語和西南官話中現在還在一定范圍內保留這種用法。也就是說,早期現代漢語中“動詞+代詞賓語+否定補語”的使用,既體現著與舊白話文語法的一脈相承,在某種程度上也體現著方言語法對新白話文的影響和滲透。在這一時期的語料中,我們發現吳語作家作品中出現這一形式的用例相對更多一些。例如:(28)康大叔顯出看他不上的樣子,冷笑著說,“你沒有聽清我的話;看他神氣,是說阿義可憐哩……(魯迅《藥》)(29)偶呀,平仄呀,押韻呀,拘束得非常之嚴,所以便是奉天承運的真龍也掙扎他不過。(周作人《山中雜信》)(30)我再三攔阻她不住,鄭媽自去溪邊洗尿布去了,一會兒便捧上一大碗青菜炒年糕來。(蘇青《揀奶媽》)(31)方家沒有房子,害你們新婚夫婦拆散,他們對你不住,現在算找到兩間房,有什么大不了得!(錢鐘書《圍城》)可以這樣說,方言詞匯和語法的摻雜和吸收,是造成早期現代漢語紛紜復雜的又一個重要因素。
(五)有發展變化刁晏斌在總結早期現代漢語語法的特點時,特意指出“有發展變化”這一點,認為“現代漢語由最初形成到粗具規模、初步穩定,其間必然要經過調整完善,以至于‘吐故納新’,總之,必然要經過一個變革的時期,而這也就是初期現代漢語的發展變化了”①[22](P323-324)。“五四”新文化運動廢除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可是當時的人們對如何進行白話文創作并不清楚,由“無法可依”到“有法可依”,必然會經歷一個明顯的發展變化的過程。筆者在上文提到這一時期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文白夾雜”,這是針對總體情況而言的。具體來講,20年代借鑒文言語法和舊白話文語法的現象普遍,“古句”和“準古句”很多,文白夾雜現象比比皆是,但是隨著新白話文創作的不斷成熟,文言語法成分不斷降低,文白相對更能有效融合。以結構助詞“之”的使用為例,筆者抽查了《全集》第1卷和第4卷的部分作品。
四、結語
早期現代漢語處于漢語新舊轉變的重要時期,以當時的口語為基礎,既有延續下來的文言成分和文言格式,又有宋元明清傳承下來的舊白話詞匯和句法形式,還有大量外來詞和歐化形式,可謂文白交雜,異質相間,古今中外多種語言要素共存于同一平面,因而形成了絕對動態演變、相對靜態聚集,多源而一統的現代漢語。紛紜復雜、文白夾雜、歐化色彩濃重、方言摻雜其中、有發展變化,這五個方面的特點比任何一個時期都更突出、更典型,因此可以看成是早期現代漢語的五個突出特點。早期現代漢語異質龐雜,特點多樣,這也是一般的語法研究者回避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些特點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背后的深層次原因還需進一步梳理和研究。
作者:崔新穎單位:河北經貿大學文化與傳播學院
- 上一篇:高校“現代漢語”課程趣味教學范文
- 下一篇:信息化時代漢語教學人才的培養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