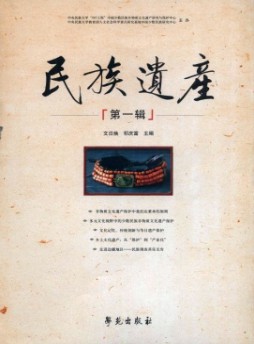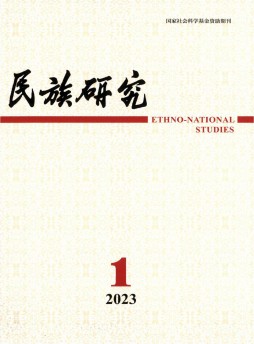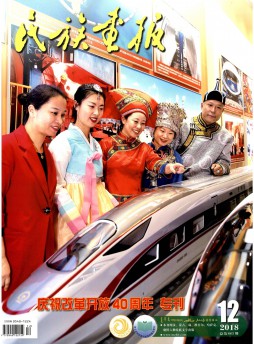辰韓的民族構(gòu)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辰韓的民族構(gòu)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社會科學(xué)戰(zhàn)線雜志》2014年第三期
一、“韓侯之國”的移民
“韓侯之國”僅見載于《詩經(jīng)•大雅•韓奕》,是一首贊美韓侯的史詩,詩的最后一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shí)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shí)墉實(shí)壑,實(shí)畝實(shí)藉。獻(xiàn)其貔皮,赤豹黃羆。綜合全詩,可以得到三方面的信息。一是韓國主曾先后兩次受周的冊封,一次是“先祖受命”,即周初,周王“封建親戚,以蕃屏周”。⑥封武王之子為韓侯,國接蠻服。《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載:“邗、晉、應(yīng)、韓,武之穆也。”杜預(yù)注:“四國皆武王子……韓國在河?xùn)|郡界。”洪亮吉詁:“《郡國志》河?xùn)|郡;河北,有韓亭。”韓侯的主要職責(zé)是鎮(zhèn)撫北方諸民族,初時(shí)功德顯著,但后來國勢漸弱,一度失去了先祖的殊榮;另一次是“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周宣王(前827—前782)召韓侯之后接受天子的冊命,并恢復(fù)其先祖舊職,擔(dān)當(dāng)“侯伯”,管理穢(亦作追)、貊諸族。同時(shí),將穢、貊之地作為屬國加賜給韓侯,其統(tǒng)治區(qū)大體包括了整個(gè)北方,成為北方部諸國之“侯伯”⑦。二是韓侯之國的封邑韓城是在燕國民眾的幫助下修筑起來的。關(guān)于韓之故城的位置,說法不一,主要有今陜西大荔縣東北說⑧和今河北省固安縣境說⑨等不同認(rèn)識。但由“燕師所完”的韓城顯然不會在上述位置,張博泉指出,此韓候城“其地必與燕近,其城當(dāng)在周之北土之內(nèi)”,“韓侯城當(dāng)于燕東與燕近之穢貊地區(qū)求之”。瑏瑠三是韓侯在做侯伯的過程中政績卓著,穢、貊之民誠心奉周,貢納不絕。值得關(guān)注的是,周宣王時(shí)期,周初召公奭所受封的燕國的領(lǐng)域已經(jīng)達(dá)到遼西地區(qū),瑏瑡東北地區(qū)的孤竹、山戎等民族皆服事于燕,而燕國在周代與東亞其他部族的關(guān)系中,亦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然而,隨著北方少數(shù)民族的崛起與不斷釁邊,作為侯國,燕保護(hù)治內(nèi)與周邊蠻夷的能力弱化。宣王之世,為穩(wěn)固“北土”①,任命韓侯為新的侯伯,管理穢貊等北方民族事務(wù)。因而,“燕師所完”的新韓城應(yīng)在靠近穢、貊區(qū)域,大概位于遼西,有學(xué)者推斷大體在醫(yī)巫閭山附近地區(qū),即今遼寧省阜新或北鎮(zhèn)一帶。②《詩經(jīng)》中的韓侯,鄭玄理解的是周武王封于今陜西省韓城的韓侯,并認(rèn)為穢、貊族原來處于今陜西韓城之北,后來為狁所逼,逐漸向東遷徙。這種見解存在頗多問題。據(jù)《逸周書•王會篇》載,在成周之會時(shí),穢、發(fā)(貊)與肅慎、良夷等東北民族同列朝拜周王,所以,穢貊是東北民族無疑。民族學(xué)界公認(rèn),穢、貊的分布區(qū)起自今醫(yī)巫閭山西麓,向東直達(dá)今吉林省中部和遼東地區(qū)。韓侯之國的重建,意味著周人對穢、貊控制力的加強(qiáng),這也因而成為宣王中興的一個(gè)基礎(chǔ)點(diǎn)。韓國學(xué)者尹乃鉉認(rèn)為,《韓奕》“是西周宣王時(shí)稱贊韓侯訪問西周王室所唱的歌”,而韓侯是古朝鮮的統(tǒng)治者,他“訪問了西周王室,以首腦外交廣泛地結(jié)成婚姻關(guān)系”,“韓侯迎娶西周宣王的堂兄弟的女兒姞氏為妻”,在這首詩中,“還有韓侯奉受自先祖?zhèn)兊奶烀拷邮芰宋髦鼙狈剿胁孔逡约鞍放c貊的諸國,成為它們之長的內(nèi)容”,進(jìn)而認(rèn)為“古朝鮮是集合了諸侯國和許多部族而構(gòu)成的一個(gè)國家……不過韓奕篇中,在諸侯國中只談到追和貊,而不見此外的諸侯國的名稱”③。尹乃鉉的說法是不客觀的,按照他的說法,古朝鮮果真是韓侯之國,那么無論古朝鮮如何廣大,朝鮮王即是“韓侯”,因而,確定朝鮮王即是周天子的封侯。當(dāng)然,我們所說的箕子之國、韓侯之國皆為周天子所分封的諸侯國,二者顯然不是同一回事。東漢時(shí)期的王符在《潛夫論》中指出,韓侯之國“其國也近燕”是合乎歷史真實(shí)的,但是,對于他所說的“其后韓西亦姓韓,為魏滿所伐,遷居海中”,④則需要進(jìn)行科學(xué)的辨析。正如羅繼祖先生指出的那樣,“入海之韓與衛(wèi)滿時(shí)代遠(yuǎn)不相及”,衛(wèi)滿所伐“乃是辰國后人箕準(zhǔn),而不可能是入海之韓”⑤,但羅繼祖、劉子敏⑥皆認(rèn)為韓侯之國在西周末或東周初遷居海東,半島之“韓”的得名與韓侯之國東遷有關(guān)。筆者亦贊同此說,但細(xì)節(jié)認(rèn)識有所不同。關(guān)于韓侯之國人遷至朝鮮半島南端的時(shí)間。據(jù)《竹書紀(jì)年》載,周平王十四年(前757),韓侯之國為晉所滅。⑦韓侯后裔之一事晉國為大夫,“得封于韓原”⑧,這一支也即是后來“分晉”的三卿(韓、趙、魏)之一韓。此外,大批韓侯國人遷離故地,其中一支來到朝鮮半島南端。論及其遷居朝鮮半島南端的原因,有必要首先追溯箕子?xùn)|走問題。武王滅商之后,“箕子不忍周之釋”⑨,于武王元年(前1046)浮海瑏瑠而至朝鮮半島南部,并建立辰國。瑏瑡辰國名稱的由來,據(jù)蒙文通先生考證,“宋、魯亦曰商、魯(吳語),商而曰辰,亦猶‘參辰’之即‘參商’乎?宋為微子之國曰辰,則海中古之辰國即箕子之國也”瑏瑢。以“商”與“辰”在意義上的聯(lián)系進(jìn)而提出殷之遺裔箕子所建之國的國號曰“辰”的可能性。羅繼祖進(jìn)而引用《史記•鄭世家》中“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shí)沉,居曠林,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的說法,認(rèn)為“商代祖先瘀伯始封之地,主辰,那么箕子的國號叫辰,應(yīng)該說還是遠(yuǎn)有淵源的”①。箕子們本為殷商遺民,對避居之地以“辰”命名是合乎情理的。春秋初期,韓侯之國亡于晉后,遺人四散而走。其中一支浮海投至箕子之辰。其原因筆者認(rèn)為有二。一是春秋初期,周王朝所確立的各種典章制度開始崩解,宗周勢微,個(gè)別諸侯越來越強(qiáng)大,而韓侯等宗室自保尚且不能,拱衛(wèi)周室更談不到,兼且不愿為晉等諸侯之臣,故而采取回避,遠(yuǎn)遁他鄉(xiāng);二是箕子為殷代三賢之一,頗得周武王器重,克殷之后,武王曾向箕子請教治國之策,《史記•周本紀(jì)》載:“武王已克殷,后二年,問箕子所發(fā)亡,箕子……問以天道。”箕子向武王講述了《洪范》。《尚書大傳》亦載,在箕子“不忍周之釋”而走之朝鮮之后,武王“因以朝鮮封之。”韓侯是武王之后,耳濡目染的箕子記憶,使其投奔箕子居地,率眾來到“古之辰國”。而大約與此同時(shí),箕子后人遷居至大同江流域的良夷居地。②東遷韓人將遷居之地順理成章地命名為“韓”,同時(shí),古“辰”之名依然保留,便成為文獻(xiàn)所載之“辰韓”。
二、移往辰韓的秦人
《后漢書•韓傳》中有一段關(guān)于秦人移往辰韓的記載: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為徒,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為秦韓。《三國志•韓傳》中有類似的記載: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名樂浪人為阿殘;東方人名我為阿,謂樂浪人本其殘余人。今有名之為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國。由上面的記述可以得到兩方面的信息。一是,遷入韓地的秦人皆是避役而來。秦王朝的統(tǒng)一僅持續(xù)了十幾年,便因繁重的兵役、徭役以及賦稅而招致反抗并因而亡國,這些避役而來的秦人逃來的時(shí)間估計(jì)是在公元前210年左右;二是,馬韓“割東界地”給這些秦人,使其保持聚族而居,故而被朝鮮半島土著人融合的情況較弱,基本保持了秦人的語言、習(xí)俗等方面的民族特色。那么,這些秦人,包括此前的箕子及韓侯之國人是通過怎樣的路徑遷徙的呢?我們認(rèn)為,海、陸兩條路線皆存在。首先,從海路而言,中國東部沿海通往朝鮮半島的海上交通遠(yuǎn)在新石器時(shí)代已經(jīng)開辟。當(dāng)時(shí)主要有兩條路線,一是走渤海之路,先到遼東半島,再走黃海,前往朝鮮半島南端;二是由山東半島出發(fā),跨黃海直達(dá)朝鮮半島南部。由今山東半島的龍口市到遼東半島的大連只有127海里。③到了戰(zhàn)國時(shí)期,我國的水上交通工具大為改進(jìn),木板船和帆船得到應(yīng)用,浮海遠(yuǎn)航的現(xiàn)象已經(jīng)普遍出現(xiàn),燕、齊方士出海尋仙已見載于史籍,及秦漢時(shí)期前往日本列島、朝鮮半島的海上道路更是暢通無阻,其中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東渡事件就屬徐福東行。進(jìn)入朝鮮半島南部的秦人系通過陸路輾轉(zhuǎn)而至應(yīng)該是客觀真實(shí)。《史記•匈奴列傳》載:“燕亦筑長城,自造陽(今河北省獨(dú)石口)至襄平(今遼寧省遼陽市)。”秦在原燕長城的基礎(chǔ)上,續(xù)修長城,據(jù)《魏略》載:“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筑長城,到遼東。”經(jīng)考證,“遼東”之長城修筑至今朝鮮清川江南岸安州,即江西郡咸從里一帶的狹長地帶。①又據(jù)《史記》和《漢書》之《朝鮮傳》載,這一朝鮮半島西北隅在漢初已經(jīng)成為“空地”,而“空地”的形成,當(dāng)與移居而來的秦人為逃避繁重的賦役有關(guān)。其逃避的方向是“塞外”,主要是東向避入今平壤地區(qū),即良夷故地,這一地區(qū)后來為箕氏朝鮮建國之地,也是漢武帝所置之樂浪郡地;同時(shí),一部分秦人未在樂浪地區(qū)居留,而是繼續(xù)向南遷徙,有相當(dāng)一部分來到辰韓之地,居于辰韓的秦人認(rèn)為“樂浪人本其殘余人”,而秦人稱“我”為“阿”,故而“名樂浪人為阿殘”,②即說明辰韓的秦人系從秦故空地上下障經(jīng)由樂浪地區(qū)而來。
三、遷往辰韓的古朝鮮人、漢人以及倭人
《三國史記•新羅本紀(jì)》載,“六村”之民為朝鮮遺民,所謂“朝鮮”,包括箕氏朝鮮和衛(wèi)氏朝鮮兩個(gè)政權(quán)。關(guān)于箕氏朝鮮遺民移入辰韓的情況,據(jù)《后漢書•東夷傳•三韓》記載: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為辰王……朝鮮王準(zhǔn)為衛(wèi)滿所破,乃將其余眾數(shù)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為韓王。準(zhǔn)后滅絕,馬韓人復(fù)自立為辰王。可知,箕準(zhǔn)打敗馬韓之后,取代馬韓人成為三韓部落聯(lián)盟的盟主,自稱為“韓王”,而原盟主“辰王”至箕氏滅絕之后才復(fù)用。那么在箕準(zhǔn)為韓王期間,隨其至三韓的箕氏朝鮮的遺民應(yīng)該也有相當(dāng)一部分來到辰韓之地。對于衛(wèi)氏朝鮮人遷居辰韓的情況,據(jù)《魏略》載:“初,右渠未破時(shí),朝鮮相歷溪卿以諫右渠不用,東之辰國,時(shí)民隨出居者二千余戶,亦與朝鮮貢蕃不相往來。”所言“貢蕃”應(yīng)為“真蕃”之誤。從“右渠未破時(shí)”可知,歷溪卿率眾東走事系發(fā)生在漢武帝發(fā)兵攻打衛(wèi)氏朝鮮期間,即元封二年(前109)秋至三年夏。早在衛(wèi)氏朝鮮滅亡前夕就有一部分貴族與百姓因政見不同而出走至辰國,那么,在衛(wèi)氏朝鮮滅亡之后有一部分朝鮮人向東南方向遷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據(jù)《三國史記•新羅本紀(jì)》載,奈勿尼師今二十六年(381),“遣衛(wèi)頭入苻秦,貢方物。苻堅(jiān)問衛(wèi)頭曰:‘卿方海東之事,與古不同何耶?’答曰:‘亦猶中國時(shí)代變革,名號改易,今焉得同?’”從衛(wèi)頭名字特征以及應(yīng)對的文化素養(yǎng)來看,有可能是衛(wèi)氏朝鮮王室的后裔。在衛(wèi)氏朝鮮建立前后,文獻(xiàn)中關(guān)于漢人遷居朝鮮半島記載較多,僅《史記•朝鮮列傳》所涉及的就有三處。一是“(衛(wèi)滿)聚黨千余人,魋結(jié)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過浿水(今清川江),在箕氏朝鮮西鄙之地定居;二是衛(wèi)滿招徠“燕齊亡命者”,勢力漸強(qiáng)之后,東進(jìn),滅亡箕氏朝鮮;三是衛(wèi)氏政權(quán)傳到第二代王右渠時(shí),“所誘漢亡人滋多”。大批漢人的遷入,致使古朝鮮的民族結(jié)構(gòu)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從原來的“朝鮮蠻夷”,到融入較多漢人的新的民族共同體。衛(wèi)氏朝鮮存國80余年,加之當(dāng)國者本身是來自于燕地的漢人,所以衛(wèi)氏朝鮮境內(nèi)漢人的“朝鮮蠻夷化”較輕。及衛(wèi)氏朝鮮滅亡,有一部分原衛(wèi)氏朝鮮的漢族迫于政治形勢而南遷,也是順理成章的。但更重要的是,在漢四郡設(shè)置之后,漢族與朝鮮半島南端的韓族的人員交流就顯得更加頻繁起來。據(jù)《魏略》載:至王莽地皇時(shí),廉斯鑡為辰韓右渠帥,聞樂浪土地美,人民饒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qū)雀男子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名戶來,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材木,為韓所擊得,皆斷發(fā)為奴,積三年矣。”鑡曰:“我當(dāng)降漢樂浪,汝欲去不?”戶來曰:“可。”辰鑡因?qū)魜韥沓鲈労Y縣,縣言郡,郡即以鑡為譯,從芩中乘大船入辰韓,逆取戶來。
降伴輩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鑡時(shí)曉謂辰韓:“汝還五百人。若不者,樂浪當(dāng)遣萬兵乘船來擊汝。”辰韓曰:“五百人已死,我當(dāng)出贖直耳。”乃出辰韓萬五千人,弁韓布萬五千匹,鑡收取直還。《三國志•韓傳》云:桓、靈之末,韓濊強(qiáng)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為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興兵伐韓濊,舊民稍出,是后倭韓遂屬帶方。由上引資料可知,流入辰韓的漢人后來大多又從辰韓流出,但不可能沒有遺留。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到高句麗占領(lǐng)樂浪、帶方二郡之后,二郡的遺民也多流入百濟(jì)、新羅,有一部分由二國轉(zhuǎn)而遷入日本,當(dāng)然也有相當(dāng)一部分留居于故地。倭與辰韓以朝鮮海峽相隔,其間的交通路線在新石器時(shí)代已經(jīng)開辟,兩岸居民往來頻繁。海峽中的對馬島東臨日本海,西瀕黃海,為控扼朝鮮海峽的咽喉之地。從對馬島至韓國的釜山,僅約三十海里,假以簡單的輔助便可以泅渡。史載,“瓠公,本倭人,初以瓠系腰,渡海而來,故稱瓠公”①。瓠公腰系葫蘆泅渡海峽,證明新羅與倭國來往之方便,而像瓠公這樣的倭人居留辰韓之地,應(yīng)該也不在少數(shù)。及新羅立國之后,倭人留新羅的情況正是屢見不鮮。在好太王碑文中也可獲得相關(guān)信息:“王巡下平壤,而新羅遣使白王云:倭人滿其國境,潰破城池,以奴客為民……十年庚子,遣步騎五萬,往救新羅。從男居城至新羅城,倭滿其中。官軍方至,倭賊退。自倭背急追至任那加羅從拔城,城即歸服,安羅人戍兵。拔新羅城、鹽城,倭寇大潰,城內(nèi)十九,盡拒隨倭。”有日本學(xué)者依據(jù)這則記載認(rèn)為,位于朝鮮半島南端洛東江流域伽耶地方的任那,日本人曾在此在設(shè)置有“日本府”②,此說遭到各學(xué)學(xué)者質(zhì)疑,③筆者亦認(rèn)為“日本府”一說子虛烏有,然而在任那地方曾住有相當(dāng)數(shù)量的倭人還是可以肯定的。這些倭人后來有的回國,而有一部分融入新羅之中。應(yīng)該指出的是,在三韓時(shí)代,朝鮮半島土著民族并沒有姓氏,經(jīng)過對外來文化,尤其是漢文化的不斷吸入,到新羅和駕洛國時(shí)代,才在脫胎于韓人社會之后開始使用漢姓。從新羅王族樸、昔、金三姓的產(chǎn)生情況來看,他們都不是辰韓的土著民族,這就給人一種錯(cuò)覺,認(rèn)為這三姓人家皆非辰韓的原住民,加之相關(guān)傳說的神異色彩,因而增加了新羅在“血統(tǒng)”上的復(fù)雜性。但是,筆者認(rèn)為,新羅早期的社會組織“新羅六部”是在原來的“辰韓六部”的基礎(chǔ)上轉(zhuǎn)化而來的,而辰韓的基本人種是土生土長的,盡管存在上述諸多“外來戶”,但并不是辰韓民族的主流。
作者:苗威單位:東北師范大學(xué)歷史文化學(xué)院
- 上一篇:接受美學(xué)的開放性范文
- 下一篇:保教人員健康體檢工作意見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