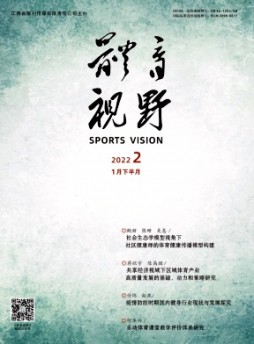體育權力的思考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體育權力的思考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體育文化導刊雜志》2014年第七期
1體育權力概念解讀
那么,何謂體育權力?體育權力即體育組織機構以其掌握的體育資源對其成員或非成員具備的強制性支配能力。在已有的相關文獻中,體育權力一般都是通過引申奧運權力、體育仲裁權力、體育違紀處罰權力等下位權力概念來進行確認。如李宏斌認為,奧運公權力是指在奧林匹克運動的管理過程中,由國際奧委會掌管并行使的,處理奧林匹克運動的公共事務、維護公共秩序、增進公共利益、協調不同集團、組織、個體之間利益的支配力量[6]。朱江華、崔德霞認為,體育行政權力是指國家或地方以及部門的體育組織和管理活動中,各級體育行政部門貫徹國家意志、實現既定管理目標的一種強制性能力[7]。實際上,李宏斌所指的奧運權力屬于社會體育組織權力。類似的權力機構還包括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AS)、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GAISF),譬如國際籃聯、國際田聯、國際足聯等。而朱江華、崔德霞定義的體育行政權力指的則是政府體育組織權力。例如我國的國家體育總局,以及體育總局下屬的各個部門,如田徑運動管理中心、射擊射箭項目管理中心等體育機構擁有的權力。因此,體育權力是一個廣義的權力概念。
2體育權力的來源
關于體育權力的來源,當前流行的觀點主要有以下兩種。第一種觀點認為,體育權力來源于體育組織內部的章程契約。霍布斯、洛克、盧梭等西方學者是社會契約論的主要代表。盧梭認為,在遠古時代,惡劣的自然環境不利于人類的生存;如果不改變原有獨立的生存狀態,人類就有可能滅亡。于是人們聯合在一起簽訂契約,運用共同的力量來保衛每一個人的安全和財富。相應的,每個個體將自己的部分權利轉讓給集體,這就是國家權力的起源。社會契約論者的觀點大致可以概括為一句話,那就是:每個結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權利全部都轉讓給整個集體[8]。國內學者姜明安也認可這一觀點。姜明安認為,社會自治組織(如足協、其他單項體育協會、其他行業協會,如律協、消協等)具備權力的理論依據在于:公民可以通過建立社會自治組織和自愿轉讓部分權利給這些組織(這些組織可能是行業性的,也可能是區域性的,隨著全球化的發展,還可能是國際性的),使之承擔部分社會管理職責,行使部分社會公權力[9]。另外一種觀點則認為,體育機構權力的來源是多元化的。除體育組織的內部章程外,政府授權與法律賦予也是體育權力的重要來源。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第四條規定:“國務院體育行政部門主管全國體育工作。國務院其他有關部門在各自的職權范圍內管理體育工作。”《體育法》第四十八和四十九條又規定:“在競技體育中從事弄虛作假等違反紀律和體育規則的行為,由體育社會團體按照章程規定給予處罰;對國家工作人員中的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在體育運動中使用禁用的藥物和方法的,由體育社會團體按照章程規定給予處罰;對國家工作人員中的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筆者以為,社會體育組織與體育行政機構是兩個聯系緊密卻又有明顯不同的概念。所謂社會體育組織(協會),簡言之,就是由一群熱愛體育且志同道合的人自愿結合而產生的體育組織。縱觀國際體育組織的發展歷程,從17世紀英國皇室、貴族中開始出現高爾夫球俱樂部;到19世紀歐洲各類民間體育協會的興起、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產生;以及綜合目前世界各國社會體育團體的現狀來看:自主參加、志愿結社無疑是體育社會組織產生自治權的主要來源。因此,社會體育組織的權力普遍來源于體育社會團體內部的章程契約這一觀點顯然更符合邏輯推理。事實上,體育法只是對體育社會組織已有的權力進行了認可。
3體育權力的基本特征
作為眾多社會權力中的一種,體育權力與政治、文化、經濟等諸多權力一樣—在本質上具有以下幾點基本屬性。
3.1委托性正如國家權力來源于人民授權,體育權力的委托性指的是體育權力的使用者并非權力的實際擁有者。恰恰相反,而是體育組織成員賦予“掌權者”某些權力,并要求相應體育組織機構或個人承擔某些具體義務。如負責實施《全民健身計劃》、組織并開展競技體育活動、維護和保障運動員的合法權益等。本質上,體育權力是為了有效地發展體育事業而由全體意義上的組織成員或社會公眾的權利讓渡而形成的。
3.2相對性權力絕非單向度的。作為一種支配他人的能力,體育權力存在于權力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體育關系中。正如裁判手中的哨子對于運動員來說,就是一種權力的象征,離開了作為權力對象的運動員,裁判便不構成權力。
3.3工具性體育權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為了促進體育事業發展,實現體育公正、公平的一種強制性保障工具。霍布斯指出,“權力是一個人為取得未來某種具體利益的現有手段[10]”。當體育權力“駕馭”的好的時候,它就是實現社會公眾及運動員體育權益的有效路徑,而當體育權力出現“脫韁”—權力尋租現象的時候,體育權力就會成為一些人牟取私利的工具。
3.4強制性強制性是體育權力最為重要的屬性,也是權力能夠衍生出其他各種屬性的基礎。以裁判權力為例,很明顯,體育賽場上運動員必須服從競賽章程、比賽規則,即使裁判出現誤判,比賽結果也不得更改。
4體育組織機構—體育權力的載體
任何權力都必須在一種有序穩定的社會結構中才能得以運轉,這種有序穩定的結構體系即為組織。龐德認為,法律和國家都不構成權力,它們只是對權力進行系統化的組織和體系化的行使[11]。當組織瓦解,權力便不復存在;譬如國家政權的更迭,隨著新的國家政體產生,原有國家機構的權力便失去效用。羅素也認為,任何組織都涉及權力的某種再分配。這個組織可以是純粹自愿的,例如俱樂部;也可以是生物上的天然團體,譬如家族或氏族;還可以是強制性的,比如國家。不同類型的組織擁有不同的權力,可以想象。假如今天沒有類似國際奧委會、國際足聯、國際田聯這樣的體育機構,不僅體育競賽很難開展,體育權力也將無處容身。因此,體育權力與體育組織密切相關,體育組織機構是體育權力的重要載體。
5體育權力的異化與沖突
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文中指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2]。事實上,權力本身并不存在善惡之分,但孟德斯鳩卻道出了權力根本上存在的一大缺陷:即權力極易被掌權者所濫用。如前所述,體育權力本質上是一種公權力。體育權力的使用者是被授權的相關體育組織、體育機構官員,或者裁判。由于權力行使者和擁有者主體的分離,就為二者的意志與利益相悖留下了空間,為權力的異化提供了機會。
5.1體育權力權利化體育權力的權利化是指體育權力在實行中出現掌權者將體育權力當作個人私權來使用的一種情況。權錢交易和以權謀私是體育權力私化現象中最為常見的兩種類型。中國足球腐敗案中的“假球黑哨”現象就屬于典型的權錢交易。據英國《泰晤士報》報道,國際足聯副主席哈亞圖和委員阿瑙馬在2022年世界杯選舉中以150萬美元的價格將選票出賣給了卡塔爾。國際奧委會前任副主席霍德勒曾公開對記者說:“從1996年到2012年的四屆夏季、冬季奧運會申辦過程中都發生過賄選行為;超過5%的國際奧委會委員出賣過選票。”美國KTVX電視臺曾報道,鹽湖城奧組委在2002年冬奧會申辦過程中為國際奧委會委員的子女提供了近40萬美元的獎學金。此外,為取得2000年奧運會舉辦權,悉尼奧組委曾向非洲的國際奧委會委員行賄。在決定第27屆夏季奧運會舉辦城市的前一天晚上,澳大利亞奧委會官員科茲還宴請了肯尼亞的委員穆克拉(CharlesMukora)和烏干達的恩揚維索(FrancisNyangweso),并且現場贈送兩人7萬美元。結果在第二天的投票中,北京以兩票之差輸給悉尼,與奧運會擦肩而過。體育權力的權利化是對體育權力實質目標和本質用途的一種背離。不僅侵蝕了體育公平、正義的基礎,而且嚴重損害了權力客體的合法利益。
5.2體育權力對體育權利的否定體育權力對體育權利的否定主要體現在體育權力的政治化傾向上。政治權力本身很難直接干涉體育,體育政治化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體育權力機構甘愿充當政治權力的代言人。由于國際體育組織可以通過否決或準許某一國家的參賽資格來施加自身的政治影響力。因此,體育權力機構很容易淪為政治權力的工具。以國際奧委會為例,因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國際奧委會取消了日本和德國參加1948年倫敦奧運會的資格。1964年,印尼因企圖越過國際奧委會建立“新興力量運動會”而被禁止參加東京奧運會。1970年,因在國內采取種族隔離制度,國際足聯和國際奧委會取消了南非運動員的參賽資格。70年代著名的游泳運動員讓提•斯基那(JontySkinner)由于不愿放棄南非國籍而被禁止參加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而另一名南非長跑運動員左拉•巴德(ZolaBudd)卻憑借加入英國國籍獲得了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的參賽資格。同樣,前800米世界紀錄創造者,肯尼亞人威爾森•基普凱特自1990年起就代表丹麥參賽,但國際奧委會卻禁止他代表丹麥或以個人身份參加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而另一方面,原荷蘭速滑運動員巴特•維爾的坎普則通過加入比利時國籍參加了長野冬奧會,并獲得了男子5000米速滑的季軍[13]。顯然,體育權力對體育權利的否定從根本上違背了體育不分國界、平等參預這一基本準則。
6結語
作為公權力,體育權力產生于社會公眾集體權利的讓渡。體育權力的實質目標在于維護體育社會團體的公共利益。因此,體育權力是體育運動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權力又是一把雙刃劍,權力尋租現象一直是體育權力的伴生弊病。中國體育在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由現行體制滋生的權力尋租現象不在少數。為此,我們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但是,如何真正做到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牢籠,實現體育權力回歸服務體育社會大眾的本質,則需要我們對體育權力進行更加深入地剖析與闡釋。
作者:王炫鋒劉桂海單位:華東師范大學體育與健康學院
- 上一篇:草根籃球賽事的發展趨向范文
- 下一篇:搏克運動的文化研究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