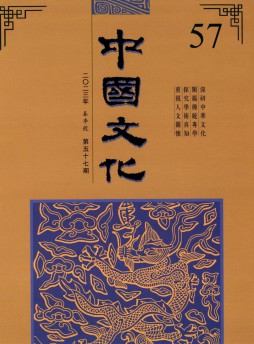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解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解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發展的今天,中國與西方國家在世界觀、價值觀、思維方式、倫理道德以及宗教信仰方面仍然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世界觀是人們對世界總體的看法,包括對自身在世界整體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又稱宇宙觀。中國傳統的世界觀與西方國家的世界觀完全不同。中國人的世界觀是一種“天人和諧”的思想,講究“天人合一”,提倡體驗人與自然界萬物的息息相通、和諧交融。然而,西方國家的世界觀認為“天人對立”,以古希臘為源頭的西方文化認為天地萬物都是獨立存在的個體,人在自然界中是主體,占有主導地位,強調人要對自然界進行認識、征服并加以改造。價值觀是人們對社會存在的反映,處于同一文化的社會成員在不知不覺中習慣并共享同一種價值觀念。從價值取向來說,中國人注重集體主義,忽略個人利益,提倡謙遜,做事情避免張揚。然而,西方人崇尚個人主義,崇尚個人奮斗,認為個人利益至高無上,做事情講究表現自己。受到“天人合一”思想和“集體主義”觀念的影響,中國人注重整體的思維方式,注重感性認識,做事情注重整體性和綜合性,喜歡從整體到局部,由大到小,由遠及近。然而,西方人的思維方式是分析性的,注重理性的分析,做事情注重個體性,由小到大,由近及遠,從局部到整體。此外,中西方在倫理道德觀念方面也存在著很大的不同。中國人注重“仁、義、禮、智、信”,注重自身的內省和提升,與他人交往講求謙遜善良,注重與他人的人際交往。然而,西方人則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講求個人的自由與利益。在宗教信仰方面,中西方同樣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中華民族是個具有多種宗教信仰的民族,大部分中國人信奉的宗教為佛教和道教,佛教和道教主張人們要積德行善、強調因果報應,人們向神和佛祈禱,可以得到幸福與平安。而西方國家的宗教主要是基督教。上帝是世間萬物的創造者,上帝創造了人類,信奉上帝的人才會得到上帝的拯救,人生而有罪,需要用一生去懺悔、贖罪,死后方可進入天堂。西方宗教的原罪說使西方社會非常重視秩序和制度的建立和遵守。可見,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在方方面面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不同國家之間文化產品的翻譯和消費過程屬于一種跨文化交際行為。當跨文化交際者對對象國的世界觀、價值觀、思維方式、倫理道德觀念和宗教信仰都十分了解和接受時,這種跨文化交際行為就會進行的相對順利;相反,當跨文化交際者對對象國的世界觀等都不了解甚至并不接受認同時,這時的跨文化交際過程就很困難并很有可能失敗。對此,一些學者提出了“文化折扣”和“文化接近”的概念,這兩個概念可以很好的解釋中國的文化產品到西方國家時為何頻頻遇到障礙。相對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中國文化產品而言,西方國家的受眾更加傾向于選擇與自己具有相同或相近文化背景的文化產品進行消費。這樣,“文化折扣”小和“文化接近性”大的文化產品更容易在相應的國家之間進行貿易流通。然而,中國同西方國家在文化上差異較大,除了一小部分熱愛中國文化的小眾人群和海外華僑之外,國外的受眾很難對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知識有所了解和掌握,因而也就很難選擇中國的文化產品。
此外,在雙方文化差異較大的情況下,不同的人對同一事物就會有不同的假設,因而對同一文化作品做出不同的解讀。例如,法國劇作家貝克特(Beckett)的名作《等待戈多》有一個英譯本和一個中譯本,英譯本傾向于闡釋它反映了基督教思想,而中譯本則傾向于反映佛教思想。原因在于:英譯本譯者自身深受西方傳統教義———基督教的影響,“上帝”在其心目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于是把劇中描寫的諸如“拯救靈魂的某種力量”、“白胡子牧羊人”、“小牧童”等意象自然而然地與“上帝”及基督教教義聯系起來,將其視為一出宗教劇;而中譯本譯者受中國最廣泛的傳統宗教——佛教的影響,潛意識地把這些意象與“菩提樹”、“佛祖”及佛教教義聯系起來[2]。不同國家的譯者對同一作品的內涵做出不同意義上的解讀,不僅體現了不同文化背景對個人交際行為的深遠影響,同時也說明了譯者充分考慮到了不同國家受眾群體的文化特點進而做出了不同的選擇。文化的巨大差異不僅會影響受眾對文化產品的選擇與購買行為,同時還會使不同的譯者、編者和消費者對同一文化產品產生不同的解讀。可見,文化差異在文化對外傳播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中國文化產品“走出去”面臨的一個客觀的文化原因。
一、語言障礙
目前,中國的文化產品在世界文化產業中影響較小的一個客觀原因就是語言障礙。眾所周知,英語是世界上最為廣泛使用的語言之一。世界上有十多個國家將英語作為母語,七十多個國家給予英語以官方地位,并且中國、德國、日本、俄羅斯等一百多個國家將英語作為第一外語進行教學。國際互聯網大約90%的內容使用的均為英語。普遍的官方地位、學習和使用人口的眾多以及分布的廣泛,已經使英語當之無愧地成為一門全球通用語[3]。因而,英語類的文化產品在世界文化進出口貿易中占有先天的優勢。雖然世界上不同國家學習中文的人數逐年增加,更多的人愿意主動了解中國文化,然而中文在世界上被使用的范圍還并不廣泛,能夠讀懂并精通中文的海外人士少之又少。中國文化產品的海外受眾群還相對較小,海外市場空間非常有限,中國的文化產品還遠遠沒有進入海外主流的文化市場。中國的文化產品在出口他國時本身存在著語言這一客觀的障礙。語言是人類的交際工具,語言也是文化傳播和意識形態傳播的重要載體。中外很多學者都就語言與行為認知,語言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進行過深入地研究與分析。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而不是一種自然現象,語言無法脫離社會而存在,不是一種孤立存在的自在物。具有相同語言的人們更容易進行交流,他們的思維方式以及對同一事物的認知更為一致,對本語言文化產品的理解也較為容易,對同一文化產品的解讀較為一致。相反,不同語言的人們交流更為困難,對他國語言的理解總是停留在某個層面,很難深入地把握文化產品的真正內涵。英語是世界上被廣為使用的語言,因而英語文化產品在世界范圍內受眾較多,能夠看懂和理解英語的受眾群較大,因而美國和英國等英語國家在文化產品出口貿易和對外傳播方面優勢明顯。相反,中國的文化產品由于中文使用范圍的客觀限制,目前在出口市場及對外傳播方面很難與英文產品相抗衡,西方國家的人們更愿意選擇自己讀得懂的語言種類的文化產品。雖然,不同語言的文化產品可以被翻譯成其他語言,但翻譯效果和翻譯成本還是影響了中國的文化產品走向海外。
二、文化輸出與文化安全
如果說中西方在文化差異和語言障礙方面的因素是中國文化產品走向世界所面臨諸問題的客觀文化原因,那么文化輸出與文化安全方面的因素則是中國文化產品走向世界所面臨問題的主觀文化原因。文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在世代繁衍生息的實踐過程中所創造和積淀下來的物質和精神財富,是一個民族、國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和條件。人們總是用本民族的宗教、語言、歷史、習俗來界定自己,文化賦予了每個人確定的特殊的文化身份[4]。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也可理解為“一種借助內聚力來維護本體身份的連續過程”[5]。世界文化應該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征,各種文化的地位應該是平等的,世界文化是世界上各民族多元文化的相互交融,各國都應該對他國文化予以尊重和理解。當今世界,伴隨著國與國之間交往的日益密切,全球化的趨勢勢不可擋。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文化全球化的趨勢也加快了腳步。然而,文化全球化并不是一種超越意識形態的現象,文化全球化中充斥著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彼此之間意識形態的對立和斗爭,充斥著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文化霸權等行為。1990年,美國學者約瑟夫•奈(JosephNye)出版了《美國定能領導世界嗎》(BoundtoLead:TheChangingNatureofAmericanPower)一書。在這本書中,約瑟夫•奈提出了“軟實力”(SoftPower)的觀點。這一概念的提出引起了西方國家的廣泛重視,并引導了西方國家國際戰略的調整。“軟實力”是指文化、生活方式、價值觀和國民凝聚力等。“軟實力”是一個國家的文化與意識形態訴求,它是一種通過吸引力、感召力和同化力而不是強力獲得理想結果的能力[6,7]。大量的事實可以證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憑借自己在經濟、軍事、科技等方面的優勢,利用大眾傳媒的各種工具向發展中國家進行文化輸出。西方國家充分認識到“軟實力”在國家綜合國力中的重要作用,以文化為外部包裝,以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等為核心內容,借助本國強勢文化的力量,充分對其他國家進行文化侵略,以達到本國的政治經濟目的。
同時,出于本國文化安全的考慮,西方國家實施各種相應的顯性或隱性文化管制以限制他國文化產品的進入。國家文化安全問題是一個涉及到國家文化主權、民族凝聚力、社會繁榮穩定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性問題,西方國家對此問題非常重視。法國在國際貿易中著名的“文化例外”原則就是出于國家文化安全問題的考慮。此外,以英國為例,出版社在登記注冊方面表面上享有充分的自由,只需按照要求具有一定的資金,先到政府有關部門登記,然后領取出版社的營業執照就可以。但實質上,英國政府對出版業的法律限制是極為嚴格的。英國直接和間接管理出版的法律除了《大憲章》、《權利請求法案》、《權利法案》等憲章性文件外,還有《版權法》、《淫穢出版物法》、《青少年有害出版物法》、《官方機密法》、《誹謗法》、《消費者保護法》、《圖書貿易法》、《星期日貿易法》、《圖書貿易限制法》等相當完備的法律體系,使出版業的各個環節都置于政府與法律的控制之下[8]。英國對于本國的出版社都會有如此嚴格的法律監管,可以想象,如果一家中國的出版機構想在英國進行出版活動將會面臨多少困難和監管。總之,西方國家在文化輸出和維護本國文化安全方面都處于絕對的優勢地位。這種宏觀的大形勢,也使得中國的文化產品在傳播到一些國家時遇到了很多問題。中國在進行對外文化傳播的過程之中,針對所面臨的問題需要分析受眾國家的政治經濟等具體原因,但同時還需務實地分析文化本身這一要素。中國文化在“走出去”過程中所遇到的諸多具體問題在現象上貌似為政治或經濟原因,但透過現象分析其本質,反而是“文化差異”和“語言障礙”這兩個客觀的文化因素,以及“文化輸出與文化安全”這一主觀的文化因素。因此,中國政府和企業在文化“走出去”過程中,應該認真地從文化視角解讀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深刻研究思考文化本身這一要素,制定一系列有的放矢的措施,從根本上推動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讓中國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作者:王娟單位:中國傳媒大學社會服務與發展辦公室
- 上一篇:兒童哲學及教育啟示范文
- 下一篇:英語教學中國文化教學的重要性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