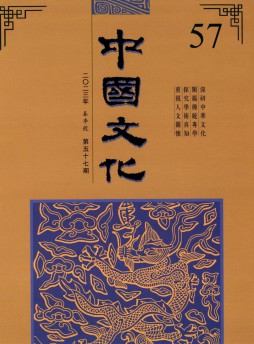中國文化競爭力研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中國文化競爭力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隱喻競爭的文化比較視角
自晚清伊始,中國迫于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而大開國門。西方文明在軍事和經濟侵略的掩護下,對中國文化也形成了強有力的沖擊,甚至導致整個傳統秩序的全面性和整體性崩潰:“晚清以后中國文明突然整體性地瓦解了,不但是政治制度瓦解(表現為清朝統治的合法性危機、帝國式政治控制的松動,以及地方勢力的崛起)、經濟制度瓦解(表現為傳統小農經濟在近代工業經濟面前的日益崩潰),而且連教育和文化體系都全盤瓦解。作為其中的一個標志,科舉制度在1905年的廢除,最終意味著傳統中國的整個政治—文化機制的徹底崩解”[4](P181)。近代中國在軍事、政治、經濟上的實質性失敗,不但引發了無數中國人對由傳統價值和文化所支撐起的文化自我確認的深刻質疑和嚴重不自信,也樹立了一個在西方世界看來最能反襯西方文明而強化西方中心主義的東方文化比較對象。于是,從黑格爾到馬克斯•韋伯,都以一種隱含著西方文化在與中國文化的較量中競爭獲勝的論調,開啟了在以文化比較來隱喻競爭的過程中突顯西方中心主義的理論視角。這樣的視角雖以服從西方話語權為前提,卻能讓我們從中找到解讀中國自身文化特質的有效途徑。黑格爾對中國文化的比較論述,主要見于他的《歷史哲學》和《哲學史講演錄》兩本書中。他之所以要把中國文化納入他的比較范圍,是服務于他對人類歷史所作的哲學研究。因而他對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歷史的解讀完全是以他的哲學理論為出發點的,換言之,即是用冷峻的理性主義和嚴密的思辨哲學這樣一種體現著自我精神中心的方式去呈現中國文化的全部。所以,理解黑格爾的哲學是理解他比較論述中國文化的關鍵。
我們知道,黑格爾哲學的理論核心就是絕對精神構成了一切自然和社會現象的本源和基礎,而構成的原則便是自由———“精神的自由并不僅是一種外于他物的自由,而是一種在他物中爭得的對于他物的不依賴性,———自由之成為現實并非是由于在他物面前逃走,而是由于對他物的征服”[5](P751)。在黑格爾看來,世界歷史就是對世界精神發展的記載,而且以自由為尺度把世界歷史分成了三個階段:屬于低級形態的是東方各國,只知道一個人自由(即君主,所以是專制主義的);屬于中間環節的是希臘和羅馬世界,只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貴族);屬于最高形態的是日耳曼民族,知道一切人絕對是自由的,即知道人類之為人類,應該由精神的自由程度來決定其最特殊的本性。除此之外,黑格爾還通過比較中國的道德、哲學、宗教、科學和社會制度等,在其理論框架內想象性地論證了中國文化中主體性和內在性的缺乏。不可否認,盡管我們看到黑格爾筆下的中國文化,確切地說已然只是他那包羅萬象又嚴密深奧的思想體系的構成部分,但卻因為將龐大的中國文化體系整體地納入了他的理論框架之中,使文化批判(針對中國文化)在達到了精神層面的深度的同時亦被涂抹上了一層令人神往的系統邏輯的理性色彩。因而黑格爾對中國文化的比較論述便可理解為是以西方中心主義的理性勝利來放大了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比對,從而將文化競爭的潛臺詞變為合理的書寫。
如果說黑格爾對文化競爭的隱喻還只是潛藏在精神意識的理性思辨之中,那么馬克斯•韋伯卻是通過用中國為什么沒有發生資本主義的問題作為回答資本主義為什么只是在西方產生的論據之一來完成他那著名的“韋伯命題”,現實地將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的競爭由黑格爾那合理的潛臺詞變成了一種赤裸裸的對峙。而韋伯的結論是:作為一種觀念的文化對社會發展具有起決定作用的力量,于是擁有新教倫理的西方資本主義自然超越了缺乏獨特的宗教倫理的中國,并且這種能夠啟力資本主義的文化觀念的缺乏還加強了家產制國家結構及大家族對資本主義生成發展所造成的障礙。誠然,“韋伯的比較論同時是一種演化論:帝制中國和西方中世紀皆是傳統式的社會,有傳統式的支配(家產制)及其相應的倫理(‘法則倫理’與‘儀式倫理’),從而帝制中國的支配與宗教倫理的秩序之發展階段便被等同成西方現代社會的支配與宗教倫理等秩序之發展階段的前期,形成落后于西方社會發展的想象”[6](P339)。以致對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特質的探究卻在比較的視角里隱喻了中國落后于西方的競爭結果。可是我們不要忽略了,韋伯的論證不僅提供了探索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特質的模式,同時也啟示了解讀中國文化特質的方式。所以,當對中國文化進行以競爭為指向的思考時,選擇像韋伯“在中西之別中把握西方的特殊性才是其重心所寄”那樣,以內化了競爭目的性的比較視角去分析中國文化的特性便毫無疑問地成為了必然。
二、突顯競爭的文化批判視角
對于西方世界的闖入,中國人在經受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切膚之痛之后,雖曾一度以高呼要全盤西化的姿態屈從于西方文化的話語,但是仿效西方議會政體與民主政治而建立的中華民國共和政體,因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等事件的發生所顯現的極度無能,加上西方資本主義文化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所暴露出來的種種丑態,一種彌漫著悲觀與失望的克制冷靜終將中國人拉回到了理性的邊緣———不可盡學西方,亦不能盡廢傳統。當然,也拉開了與西方文化之間的文化戰爭序幕。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清醒之后的中國人終于在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之后,毅然選擇“把目光投向那些其本身就是批判西方社會的西方社會主義理論上,而不是投向那些維護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的西方傳統自由觀念上”[7](P23)。而且,“只有中國共產黨從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把消滅私有制、實現公有制的社會主義作為理想,并通過暴力革命成功地取得政權,建立了一套以黨為核心的政治集權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其間雖有基于文化傳統、社會環境和實際需要而作的種種‘中國化’努力和隨機性調整,但直到21世紀初,這一體制也依然有效地塑造著中國政治文化和社會結構”[6](P244)。因而可以說,中國最終選擇了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為指導,并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這當中所蘊含的歷史深意已然指向了通過解讀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是如何對西方資本主義文化進行內在批判,繼而啟發構建同處于現代化場域中的中國文化競爭力的既定思路———如何從文化批判中尋找到競爭的突破口。馬克思關于文化的論述,主要體現在對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決定的文化受資本滲透控制后對人性的嚴重壓抑的深刻揭露,并以揭示精神文化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歷史起源、發展過程和未來前景來指明對資本主義文化發起抗爭的導向:“人的能力是文化競爭力的本質”、“人的實踐是文化競爭力的基礎”、“人的交往是文化競爭力的直接動力”[8](P31、32)。從馬克思的文化理論原點出發,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批判和葛蘭西的文化霸權分別從意識形態和實踐策略兩個向度對資本主義文化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批判。
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批判以對啟蒙思想和大眾文化的批判最為顯著。首先,對于“啟蒙何以成為批判的對象”,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解釋是:“啟蒙并沒有兌現自己的承諾,恰恰相反由于自身的內在邏輯它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而“這種理性的自反性最為極端的形式無疑就是法西斯主義”[9](P320)。為此,在《啟蒙辯證法》一書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把批判的矛頭通過法西斯極權主義指向了整個歐洲資本主義現代文明的內核,即“作為全部資產階級人本主義理論基石(其實也是整個西方工業文明本質)的啟蒙精神———人類中心主義、工具理性支配論和歷史進步觀”,在他們看來,“文藝復興以來被資產階級自由意識形態捧上了天的啟蒙理性(這也是整個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深層邏輯支撐點),在推進物質生產力極大發展的過程中逐步地顯現出自身具有的兩重性質:即解放與奴役”[9](P322、323)。于是,在進入到文化領域的反思時,阿多諾則直接將啟蒙作為了文化工業之大眾欺騙的特性的注腳———《文化工業:作為大眾欺騙的啟蒙》,這種欺騙的實質被指認為啟蒙自身的悖論———把自然從神話中解放出來,又以理性的名義剝奪掉了人身自然的權利———既構成了大眾文化的內質,又催生了自由解放的幻象,因此大眾文化便成為了一體化與普遍性的意識形態的典型代表。“法蘭克福學派對于大眾文化那種機械單質性、復制性、普遍性、一體化、標準化的批評正是從這里發展出來的”[10](P45)。簡言之,法蘭克福學派以意識形態來架構物質生產和精神文化之間的關聯,從而達到對資本主義文化的批判。如何對其加以創造性轉化以后用來分析與批判中國改革開放以前的思想控制與極權主義意識形態,這是陶東風所認為的法蘭克福學派帶給他的最大啟示。
相較于法蘭克福學派充滿思辨色彩的文化意識形態批判模式,葛蘭西以實踐哲學為理論基礎而建構的霸權理論,則將對資本主義文化的抗爭策略性地引向了爭奪領導權的道路。“對葛蘭西來說,研究實踐哲學是為了在歷史中將之實現出來,以促成無產階級自我意識的提升與自覺”,其理論指向在于“通過歷史與思想史的批判考察,使大家超越常識、超越現有意識形態,在對常識與意識形態的前提性批判中,使自己走向更高的認識生活的形式,獲得思想霸權,實現對社會生活的改革”[11](P112)。而葛蘭西所提及的歷史,主要是意大利文化與政治運動史,特別是對馬基雅維利與克羅齊的批判思考。因此,形成于他的《獄中札記》一書中的霸權概念,是統一在其哲學理念和政治理念之中、并最終以文化霸權的實現為其理論的最高形態,且指明了以哲學上的自覺意識為歸依的文化霸權建構必定以一場改變群眾心態、傳播哲學新事物的文化戰斗來完成,而戰斗的過程便是在政黨的統領下,由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產生出來的組織化的知識分子帶領人民大眾奪取技術和知識的領導權,以達到真正解構技術意識形態的目的,其競爭的意味已不言而喻。由此,“葛蘭西對知識分子與霸權關系的討論,不僅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實現了知識分子政治歷史地位的自覺,而且開啟了當代知識分子討論的先河”[9](P140),這對思考構建中國文化競爭力無疑也是有借鑒意義的。
三、反思競爭的文化他者視角
然而,要達到以中國的文化力構成對話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競爭身份,還需要借鑒同源于第三世界之國際秩序身份的后殖民主義的文化理論經驗。“如果說殖民主義與新殖民主義主要關注的是西方宗主國與殖民地國家或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經濟關系;那么,后殖民主義理論則集中關注第三世界國家與民族與西方殖民主義國家的文化上的關系”[10](P113)。后殖民主義理論曾帶給中國人巨大的思維刺激:“無論是東方主義還是其他的西方后殖民理論,其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吸引力與其說是向他們介紹了一種新的西方文學與文化批判模式,還不如說為他們提供了重新反思中國傳統文化(或東方文化)、中西方文化關系以及五四文化激進主義這些長期困擾中國知識分子的老問題的新視角、新尺度”[10](P202、203)。但是,就對文化競爭的考量而言,若還是僅從西方/東方的二元對立模式出發來消解西方中心主義,那就不免仍是落入了以對立實現抗爭的簡單化套路。應該說,我們今日所要探索的中國文化競爭力,更主要的是要通過強化文化合力、淡化異質對立來獲取自身文化強大的吸引力和說服力,從而重塑中國文化海納百川、和而不同的大國風度。因而,我們選擇以后殖民理論作為反思文化競爭有可能面臨某些理論陷阱的線索,正是站在了文化他者的視角上進行的。對后殖民理論形成的現實背景,亨廷頓提出了他一貫犀利的看法:如同“東亞沒有將其經濟的迅速發展歸因于對西方文化的引進,而是歸因于對自身文化的伸張”那樣,“如果非西方社會感到與西方相比自己相對弱小,他們就援引西方的價值觀,如自決、自由、民主和獨立,來為其反對西方控制辯護。現在他們不再弱小而是日益強大,于是他們便毫不猶豫地攻擊起他們先前曾用來維護自己利益的價值觀”[11](P73),并導致了非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復興。且不論亨廷頓的觀點是否客觀公正,但他的確透露出一種非西方國家正在以不斷表征某種異質于西方社會(即本土化)的民族文化身份來抗爭、甚至否定西方文化的發展趨勢。其實,同樣的境況在中國又何嘗不曾發生過呢?而且國內學術界對象征著中國現代性開端的五四激進主義思想文化運動的反思,借用的恰恰是后殖民理論,繼而開始抵制西方文化的影響、批判西方中心主義、重估“現代性”和以現代性為核心的啟蒙話語,并以新的國學熱、弘揚熱席卷了中國各地各界。可是,這是否就意味著中國文化在空前地突顯了自己之后便因此成為了競爭中的勝利者了呢?事實并不全然,相應地卻應該對是否被帶到了民族狹隘性、乃至民粹極端性的理論陷阱邊緣進行文化主體性建構的反思。恰如賽義德對于“過激的”本土主義的批評那樣:“他認為民族主義(特別是以反殖民方式表現的民族主義)既具有其必然性,又有其局限性。如果民族主義激發殖民斗爭的對抗性能量,并因而具有其進步意義,那么殖民之后的獨立的實現則應當提醒人們警惕民族主義的局限”[10](P151)。
綜上所述,對中國文化競爭力理論研究視角的選擇理應還存在著其他不同的切入點和建構方式。但是,我們要始終堅持的則是有效地結合中國文化發展實際的理論分析原則,這樣才能為更深刻而全面地解讀中國文化競爭力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作者:楊荔斌單位: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在讀博士研究生
- 上一篇:跨文化視野下的中國文化滲透范文
- 下一篇:留學生中國文化教育分析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