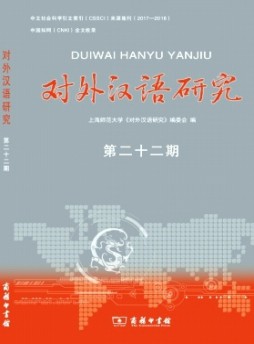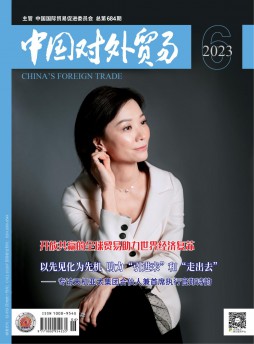對外傳播學的發展綜述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對外傳播學的發展綜述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發展的歷史機遇
隨著中國社會的日益開放,中國民眾對于參與公共事務的意愿也空前高漲。2009年底,外交部設立了“公共外交辦公室”,標志著公共外交成為中國對外傳播的一種嶄新形式。誠如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原會長陳昊蘇所言:國家領導人、各級官員,以及大型活動組織者、工作人員、志愿者,乃至數以千萬計的普通民眾,都是活躍在這個舞臺上的公共外交積極參與者。20多年來,歷史賦予中國“對外傳播”以特殊的使命,也同樣為中國“對外傳播學”的發展提供了契機,吸引了更多的學術人才共同為中國對外傳播學的發展群策群力。
二、20年歷史軌跡
近20多年,是中國對外傳播學從起步到發展的奠基階段;然而,若回溯其緣起,中國的對外傳播學又豈止20多年。中國的對外傳播學直接孕育于中國的對外傳播事業,也就無可避免地在時間上滯后于中國的對外傳播事業。上世紀90年代前后,一批以“對外傳播”和“對外宣傳”為主題的理論著作紛紛問世,其作者則大多是具有幾十年實踐經驗的對外宣傳工作者。1988年,歷史即將邁入90年代,中國第一部對外傳播學著作《對外傳播學初探》問世,其作者正是新中國對外宣傳的優秀實踐者、中國外文局原局長段連城。1999年,歷史即將告別90年代,與前著遙相呼應,段連城的老同事與老鄰居、我國對外宣傳事業的另一位老前輩——沈蘇儒,出版了另一部奠基之作《對外傳播學概要》。兩位大家的學術結晶,滋養于他們幾十年所經歷的時事變遷和人生歷練。盡管遲至90年代前后才誕生,但是追根溯源,兩本著作的源頭卻遠在半個世紀之前。彼時,中國尚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苦撐待變,與此同時,在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過程中,也開始逐步走向世界。1945年7月,年僅19歲的段連城負笈美國,在久負盛名的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攻讀學位。幾乎與此同時,剛剛大學畢業的沈蘇儒也躊躇滿志,在堂兄沈鈞儒的介紹下,開始在重慶的美國大使館新聞處工作,并因此結識了一位對他影響深遠的中國籍同事——劉尊棋。抗戰時期的美國新聞處,是美國在中國進行對外宣傳的專門機構,其負責人是一位來自哈佛大學的年輕教授——后來聞名世界的美國漢學翹楚——費正清。為了能夠發出地道的中文稿件,費正清物色了一批中國籍記者,其中即包括了主持中文部工作的劉尊棋。直到1949年10月1日,劉尊棋被任命為新中國國際新聞局的常務副局長,已回到哈佛教書的費正清才恍然大悟——原來,劉尊棋是當年潛伏在美國新聞處的中共地下黨員,利用美國的財力物力,他在國統區的報紙上刊發了許多有利于抗日動員和民主運動的進步稿件。
借鑒當年在美國新聞處的工作經驗,劉尊棋將國際新聞局打造為一個對外傳播新中國的專業機構;與此同時,年富力強又精通外語的段連城和沈蘇儒也深受其鼓舞,分別成為《人民中國》和《今日中國》兩本對外刊物的骨干力量。歷史是一條源遠流長、永不停歇的大河。從1949年開始,段連城和沈蘇儒親歷了新中國建設與發展的崢嶸歲月,段連城更曾奔赴朝鮮,親身參與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報道與談判工作。上世紀90年代前后,當兩位老人的對外傳播學著作問世之時,讀者在紙面上看到的是他們洋洋灑灑的學術總結與理論歸納,在紙面上看不到的卻是他們半個多世紀以來既勤習西學又扎根中國的生活經驗與生命體悟。段連城與沈蘇儒的學術著作和理論框架,為中國對外傳播學的開宗立派樹立了以實踐為導向的重要標桿。同一時期,一批類似的具有實踐色彩的對外傳播學著作還有不少。①1994年,由國務院新聞辦指導、中國外文局主辦,以探討外宣理論和促進外宣業務為宗旨的專業期刊《對外大傳播》(后更名為《對外傳播》)問世,其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鮮明特征,與中國對外傳播學的源起一脈相承。與此同時,中國外文局、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中國新聞社、文化部對外文化聯絡局等一些對外宣傳的主管單位也編輯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史料檔案。更為珍貴的是,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的三任主任——朱穆之、曾建徽、趙啟正,也分別出版了《風云激蕩七十年》、《融冰•架橋•突圍》和《向世界說明中國》,成為中國對外傳播學的必讀書目。另一方面,隨著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日益緊密,中國對外傳播學的“學院派”隊伍也在日益壯大。事實上,高等院校與科研單位本來就是中國對外傳播學的衍生基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外文局文化學院、新華社新聞學院、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等相繼舉辦了一系列的外宣干部培訓班。正是在三尺講臺上,段連城與沈蘇儒一面悉心講授“對外傳播學”課程,一面追蹤國內外學術界的最新成果,將實踐升華為理論,最終在講課提綱的基礎上整理匯編成了兩部中國對外傳播學的經典著作。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日益頻繁地被國際媒體關注和報道,一些高校學者也開始從學術角度研究并闡釋中國的對外傳播:從傳播學視角借鑒西方的國際傳播理論②;從外交學視角引介西方的公共外交理論③;從文本分析的視角論述對外傳播與國家形象的關系④;從歷史分析的視角梳理中國對外傳播實踐的演變過程⑤。
與此同時,各類專業期刊上發表的有關對外傳播學的論文更是多達上千篇,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對外傳播學研究的欣欣向榮;然而,若要實現對外傳播學的真正繁榮,還有賴于各項研究的深化、細化與中國化。沈蘇儒先生晚年即曾念茲在茲地指出:我們對外傳播工作者已形成為一支人數眾多、人才濟濟的隊伍。過去互不通氣,不能形成合力。現在應該組織起來,建立研究團體,開展各種科研活動,并使科研成果應用到實踐中去。近年來,一批以對外傳播、國際傳播、公共外交為宗旨的研究機構紛紛建立,如:中國外文局對外傳播研究中心、中國傳媒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北京外國語大學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等。2008年10月,清華大學成立了“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對外傳播研究中心”,致力于對外傳播理論的本土化研究。2012年12月,根據十八大報告中“扎實推進公共外交”的中央要求,中國公共外交協會在北京成立,外交部原部長李肇星當選為首任會長。目前,與公共外交和對外傳播相關的職能機構分散于不同的外事和新聞單位,有鑒于此,中國公共外交協會已計劃開展一系列有政策導向性的研究課題,致力于整合各方力量以共同促進中國與世界的相互認知。
三、20年歷史經驗
20多年的風雨兼程,為中國對外傳播學的發展留下了寶貴的經驗,也為后來者的繼續深耕提供了豐富的資料與線索。
第一,在“術”的層面,要繼續借鑒“西方經驗”。近代以來,西方先進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水平促使中國人反思和向往,與西方工商業文明“求同”也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目標之一。毋庸諱言,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處于工業文明的制高點時,其他國家為了發展經濟便不得不與之交流并向其學習。于是,借助經濟優勢,美國在國際輿論界也獲得了“高人一等”的話語權,誠如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公共關系顧問邁克•麥德沃所言:在全球爭取民心向背的角逐中,美國曾經占了上風,因為它支配著形象、偶像和信息的流動,更別提由于美國以及此前大英帝國的霸權,英語成為世界通用的語言。于是,在一場西方業已掌握了“標準制定權”的形象競賽中,在一個輿論傳播的速度和廣度都空前提高的新媒體時代,為了與國際社會有效溝通,中國在對外傳播時便不得不使用“世界通用的語言”,不得不學會更具說服力的表達技巧與傳播創意。近代以來,中國的現代化肇始于向西方學習新技術以發展工業;今天,中國人還必須學習新媒體以講好“中國故事”。這無疑也為中國對外傳播學的發展方向設定了命題主旨。近年來,中國學界對于西方“國際傳播”和“公共外交”理論的學習與借鑒,已經蔚然成風。
第二,在“道”的層面,要努力實現“本土化”。20多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在與“世界的話語”求同之時,對外傳播學若想在中國扎根發展,還必須探索和總結“中國的話語”。不能用“中國的話語”解釋中國問題,這才是中國對外傳播學的根本困境。哈佛大學漢學翹楚費正清曾說:中國是不能僅僅用西方術語的轉移來理解的,它是一種與眾不同的生靈。它的政治必須從它內部的發生和發展去理解。對于中國而言,對外傳播的本質使命即是向國際社會解釋“我是誰”;然而,倘若連自己都對“我是誰”不甚了了,那么不論傳播技巧何等高明與先進,對外傳播也注定是要失敗的——這也是對外傳播學者在從事學術研究時所必須重視的核心問題。遺憾的是,某種程度上,比之“世界的話語”,中國學界現在對于“中國的話語”甚至更加陌生。如果永遠停留在對西方理論的借鑒與引介階段,如果不能以中國的視角去建構屬于中國自己的文化自覺和道路自信,我們這一代學人將注定無法在對外傳播學的傳承和發展中取得新的突破。正如云杉在《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中所言:吸收外來文化,貴在以我為主、為我所用,重在實現中國化、本土化。……只有通過轉化再造,形成中國氣派、中國風格,才能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第三,在“戰略”的層面,要強化“國際視野”。過去20多年,中國的對外傳播學多以西方傳播學為其研究框架;然而,展望未來,作為一門典型的交叉學科,中國的對外傳播學必須重視對外關系與國際問題的戰略研究。對外傳播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其工作者必須兼具外事與新聞的長才;與此相應,對外傳播學也絕非一門簡單的學科,更非套用西方傳播學的某某理論就能夠有所突破。據上世紀50年代任職新華社社長的吳冷西回憶,曾多次批評參與對外宣傳的新聞人們“不懂外交”:對我說,你們辦報的要經常研究國際問題,多同一些有見解的人交換看法,慢慢形成比較符合實際的觀點,遇到國際上突發事件,就不致惶惶無主或臨時抱佛腳。國際的經驗也是如此。1953年,美國新聞署建立,其工作任務是實施一系列借助大眾傳媒的國際交流項目,這些項目被冠以一個全新的名稱——公共外交。曾在美國新聞署工作30多年的公共外交官阿蘭•漢森,在其專著《電腦時代的公共外交》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像我們這些資深的公共外交官心知肚明,縱觀美國新聞署的發展歷程,美國公共外交的根本使命,除了促進美國外交政策的傳播與落實以外,別無其他。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原主任曾建徽同志在回顧自己六十多年的工作經歷時,也曾就中國對外宣傳工作的本質做了如下總結:外宣就是整體外交的一部分。外宣有種獨特作用,就是輿論先導的作用。今天,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國際機遇,我們要抓住歷史的契機,將對外傳播學與中國整體的國家戰略緊密相連,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道路自信為“中國夢”的早日實現貢獻心力!(本文作者:姚遙單位:外交學院國家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
- 上一篇:漁業科技入戶工作意見范文
- 下一篇:醫學通訊系統相關問題探討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