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小說傳播學(xué)論文探討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古典小說傳播學(xué)論文探討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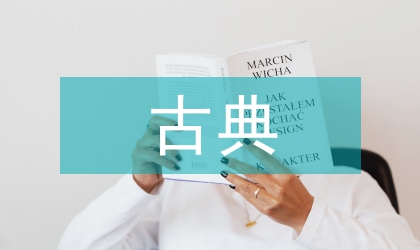
[摘要]基于文獻傳播學(xué)的古代小說研究,可從文獻及其載體的文本信息源、寫作者、文獻傳遞者、傳播渠道、傳播手段及傳播環(huán)境等加以展開。不僅要重視古代小說文獻本身的存在狀態(tài)與動態(tài)變化,也要注意古代小說的文獻載體形式及不同載體間的文本異同。同時,亦應(yīng)探討文獻載體的傳播途徑與內(nèi)容闡述對古代小說流布的影響,關(guān)注歷代制度政令、社會輿論、風(fēng)俗習(xí)慣的變化對古代小說文獻及其載體傳播生態(tài)的影響。當(dāng)文獻的載體形式及其動態(tài)變化、記錄的版本與記錄內(nèi)容的真?zhèn)巍⑽墨I記載所提到的人事及其與時代的關(guān)聯(lián)性等信息,可被確定或大致確定時,即可據(jù)以探討古代小說尤其是通俗章回小說的成書時間、作者問題、版刻系統(tǒng)、傳播歷程等內(nèi)容。
[關(guān)鍵詞]文獻傳播學(xué);古代小說;《水滸傳》;《隨園詩話》
自20世紀(jì)初建立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現(xiàn)代”范式以來,百余年來學(xué)界有關(guān)古代小說的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解決了諸多難題,然仍有諸多未定之論。尤其是對明清時期“世代累積型”通俗章回小說的成書過程、成書時間與作者問題的探討,研究者往往各執(zhí)己見,莫衷一是。因而,轉(zhuǎn)換研究思路,調(diào)整研究方法,或許是推動相關(guān)研究持續(xù)深入的有效對策。從文獻傳播學(xué)視閾研究古代小說即是此中的一種有益嘗試。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學(xué)界雖然對文獻傳播學(xué)理論進行了諸多探討,卻較少進行實踐操作,更別說以之為古代小說研究的指導(dǎo)。文獻傳播學(xué)的研究范圍是在充分把握文獻、傳播的內(nèi)涵與外延的基礎(chǔ)上,探究文獻與傳播二者之間的關(guān)系。文獻傳播學(xué)研究者一般認為文獻是以文字、圖像、符號、聲頻、視頻等為主要記錄手段的一切知識的載體。它亦是人類進行傳播活動的客體。文獻在傳播過程中,易受到傳播時所固有的社會結(jié)構(gòu)(如知識結(jié)構(gòu)、受眾人群、階級身份等)、政治環(huán)境(如制度、政策、政令等)、經(jīng)濟環(huán)境(如商業(yè)環(huán)境、消費水平等)、文化教育(如道德、輿論、風(fēng)俗習(xí)慣、教育水平等)、技術(shù)手段(如印刷技術(shù)、信息傳播的渠道與途徑等)諸多方面的影響,往往具有符號性、動態(tài)性、結(jié)構(gòu)性、普遍性等屬性,呈現(xiàn)出社會化、人文化的特征。①故而,考察文獻傳播學(xué)現(xiàn)象不僅要考察文獻傳播的起源、過程及環(huán)境變化,而且應(yīng)注意文獻傳播過程中的社會基礎(chǔ)及傳播渠道,從而實現(xiàn)文獻的文本傳播與受眾對文獻的闡述二者相統(tǒng)一。同時,我們也要注意文獻本身的存在狀態(tài)及其不同時期、不同載體中的變化動態(tài);甚至,因歷代文治環(huán)境、傳播渠道的不同,對文獻的傳播往往會帶來諸如文獻內(nèi)容可靠與否、文獻載體是否可信、文獻是否具備足以征引的證據(jù)價值等方面的難題。不過,文獻傳播的本質(zhì)意義不僅體現(xiàn)在文獻于受眾闡述的活動中,同時還體現(xiàn)在作者與讀者的持續(xù)的相互作用。姚斯曾在《文學(xué)史作為文學(xué)理論的挑戰(zhàn)》中說:“文學(xué)作品并非是一個對每個時代的每個觀察者都以同一面貌出現(xiàn)的自足的客體,它也不是形而上學(xué)地展示其超時代本質(zhì)的紀(jì)念碑。文學(xué)作品像一部樂譜,要求演奏者將其變成流動的音樂。只有閱讀,才能使文本從死的語言物質(zhì)材料中掙脫出來,而擁有現(xiàn)實的生命。”①可見,從“接受美學(xué)”的理論看,文獻傳播學(xué)的探討還應(yīng)注意文獻受眾人群對文獻傳播意義的揭示與深化,對文獻進行文本闡述維度的影響。據(jù)此,從文獻傳播學(xué)視閾進行古代小說研究時,結(jié)合古代小說所特有的文獻特征及傳播特點、規(guī)律,可從以下幾方面加以展開。
一、重視古代小說文獻本身的存在狀態(tài)及其動態(tài)變化
自《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將“小說家”歸結(jié)為“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②始,不論是見于歷代史志與公私書目中的“小說(家)類”作品(俗稱子部文言小說),抑或是流傳并盛行于彼時社會中下層的通俗章回小說,均為歷代士大夫文人所不屑,甚或不為當(dāng)時的主流文化所認可及接受。在這種情況下,文人創(chuàng)作小說作品時,所言往往只能在裨益圣教、文治及于社會風(fēng)尚有益的情況下,而后才能強調(diào)所寫奇物異事、談資笑噱、軼事趣聞等其他內(nèi)容。這就使得歷代小說的創(chuàng)作,往往呈現(xiàn)出一種相較于經(jīng)史之作而言更加隱晦、隨意的特征,從而導(dǎo)致古代小說作品多呈現(xiàn)出自娛、自寓的創(chuàng)作傾向,且流傳的范圍亦有所局限。甚至,歷代士大夫文人進行寫作時,往往要擔(dān)當(dāng)一定的“風(fēng)險”。這種“風(fēng)險”一方面來源于彼時官府對小說作品的查禁(說詳下),另一方面源于社會輿論的鄙薄。比如,明人瞿佑(1341~1427)寫作《剪燈新話》時,就已坦誠所言“涉于語怪,近于誨淫,藏之書笥,不欲傳出”③。此書涉及明季社會的情欲描寫者頗多,后遭受朝臣以“邪說異端”④為由上褶要求查禁。又如,仿《剪燈新話》而作《剪燈余話》的李昌祺(1376~1452),“其歿也,議祭于灶,鄉(xiāng)人以此短之,乃罷”⑤。皆是個中典型。據(jù)此看來,古代小說的文獻存在狀態(tài)往往會呈現(xiàn)出隱晦、閉塞的特征。這種特征對于據(jù)此探討寫作者的編纂旨趣、文獻流通過程中的版本異樣之處,將有非常明顯的影響,從而增加了許多不確定因素。尤其是,通俗章回小說的文獻存在狀態(tài),更是呈隨意與復(fù)雜特性。在通俗章回小說刻本流傳初期的明代中葉,其間的文獻載體多為刻本形式,且多與當(dāng)時的朝廷機構(gòu)有關(guān)。如明代“都察院”刊刻有《忠義水滸傳》,“司禮監(jiān)”“內(nèi)府”等機構(gòu)刊有《三國志通俗演義》,山東“登州府”“魯府”刊刻《西游記》等。而后,坊間書賈在這些官刻本的基礎(chǔ)上(如《西游記》現(xiàn)存的最早刊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記》就打出“官板”旗號),進行刪改,并大量刊刻。可以說,通俗章回小說的盛行離不開書賈的刊刻、創(chuàng)作并流布。然而,書賈或文人的諸多刪改,致使通俗章回小說出現(xiàn)了篇幅不一、版本各異、內(nèi)容有別的諸多版本。比如,《水滸傳》在流傳過程中就出現(xiàn)過百回本、百十五回本、百廿回本、七十一回本等多種,各本的主要差異雖集中于平遼、征方臘等重要事件的描寫之中,但于其他方面的細節(jié)描寫及其間的旨趣,亦多有差異。又如,在《西游記》的版刻系統(tǒng)中,“世德堂”本、李卓吾評本、楊閩齋刊本、“四游記”楊志和本及清代“證道書”系統(tǒng),各本的差異亦十分突出。這就導(dǎo)致通俗章回小說的文獻形態(tài)頗為復(fù)雜,文獻載體形式異常多樣。時至今日,我們已很難理順某一(類)小說的版刻系統(tǒng)及其動態(tài)演變歷程,更別說細致分析此類小說的編修緣起及其意義。造成此類復(fù)雜現(xiàn)象的緣由在于,歷代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往往會對小說文本隨意進行改動、增刪、補削。此類改動不僅體現(xiàn)在諸如將《水滸傳》“旱地忽律”錯改為“旱地蔥律”“旱地蔥佳”等細微之處,亦體現(xiàn)在對作品情節(jié)的肆意改動之中,甚或改變小說作品的人物形象及蘊意。如楊氏清白堂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所刊八卷八十回本《岳武穆精忠傳》與崇禎間所刊六卷六十八回本《岳武穆盡忠報國傳》中的岳飛形象,就發(fā)生了極大變化,后者著力于刻畫岳飛“精忠”與“愛國”的形象。①等等。因而,通過文獻傳播學(xué)的方式,理順此等小說的文獻狀態(tài),是進行后續(xù)有關(guān)研究的基礎(chǔ)。若是我們對古代小說文獻本身的存在狀態(tài)估計不足,勢必?zé)o法據(jù)此研判此類小說的成書過程、作者問題等。典型之例,則如學(xué)界試圖通過小說文本的“內(nèi)證法”去探討《水滸傳》等“世代累積型”通俗章回小說的成書時間。其間的證據(jù)使用、論證方法及研究結(jié)論往往存在不少問題。比如,學(xué)界熱衷從樸刀桿棒、子母炮、土兵、白銀使用、地理職官制度等“內(nèi)證”去討論《水滸傳》的成書時間,但此類證據(jù)的使用,往往未充分考慮證據(jù)的來源情況。也就是說,此類證據(jù)有相當(dāng)一部分已存在于章回小說《水滸傳》成書之前據(jù)而抄綴的“小本水滸故事”或“水滸戲”中,亦有相當(dāng)部分的證據(jù)原屬于《水滸傳》中后期的刊本所獨有的。此類證據(jù)往往具有不典型、有歧義及可逆的特征,而非含有鮮明的時間坐標(biāo)信息,或獨一無二的特征(且只能出現(xiàn)于某一特定的歷史年代)。②這種研究方式,往往未能充分注意不同的文獻載體對小說文本所做的諸多變動,從而導(dǎo)致討論者所使用的證據(jù),往往是帶有不確定性且非典型的文獻載體。其間而作的研判,引發(fā)爭議也就在所難免。當(dāng)然,我們還應(yīng)充分注意古代小說文獻及其載體,在流傳過程中的社會性、文化性,③甚至文獻的擁有者及傳播者對文獻所進行的人為變動及引發(fā)的爭議。換句話講,由于古代小說尤其是通俗章回小說往往被時人認為屬于“道聽途說”、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致使小說作品的寫作者或佚名或托名而難以確考,小說作品尤其是通俗章回小說作品在流傳過程中,往往易遭整理者、刊刻者隨意改動文本,甚至粗制濫造。如出版者多以營利為目的,偽托古本,制造噱頭,粗制濫造;普通讀者也可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理解對其進行再加工,隨意增刪。尤其是,《三國志通俗演義》《水滸傳》等“世代累積型”的通俗章回小說,在漫長的積累過程中,經(jīng)歷了許多不知名的作者參與創(chuàng)作和修改的過程;即使是此類作品成書以后,由于既不受正統(tǒng)文人重視,也不受正統(tǒng)文化保護,只受市場規(guī)律支配,④導(dǎo)致此類小說作品的文本極為復(fù)雜、內(nèi)涵往往多樣、主題多重而具有廣泛的社會性特征。彼時官府、社會上層文人、普通讀者等不同社會階層、甚至是群體間的傳播行為,對此類小說作品的傳播范圍,有著深遠影響。此類小說作品傳播過程中的官方意識,與民間視角對小說作品價值的解讀重點,亦有別。⑤換句話講,代表不同文化階層的受眾群體,對古代小說作品的解讀有受其本階層影響而形成的特定的主體意識,對古代小說作品傳播的社會環(huán)境的把握難免各執(zhí)己見。諸如此類,對古代小說的文獻狀態(tài)將帶來相當(dāng)大的影響。這也是學(xué)者據(jù)此展開相關(guān)研究前應(yīng)該充分注意的。
二、充分注意古代小說的文獻載體形式及不同載體間的異同
大略而言,古代小說的文獻載體形式主要有小說版本(包括抄本、刻本等),彼時或后世的目錄學(xué)著述(如史志目錄、官藏書目、私家書目等),相關(guān)的族譜與家譜(含墓志銘、廟碑文),時人的札記及筆記記載等多種形式。在使用不同類別的文獻載體之前,我們應(yīng)充分注意所使用文獻載體進行記錄時的時間、地點、方式(如抄、刻、過錄),及相關(guān)信息與討論對象之間的關(guān)系(是直接相關(guān)還是間接涉及,抑或是旁證、反證)。同時,應(yīng)注意此類載體記錄時的消息來源,如文獻載體的記錄者與討論對象是否是直接掛鉤,記錄者是否是“道聽途說”或通過“第三方”文獻獲知而轉(zhuǎn)錄的,是否是綜合多種信息考訂推測的,抑或是主觀臆測的。意即充分考量相關(guān)文獻所承載的知識(信息)是否可靠。也就是說,古代小說的不同文獻載體,對小說作者、文本內(nèi)容及其他關(guān)聯(lián)信息的記錄,可能存在差異。對不同載體的差異之處進行比勘或核實,將是以此為基礎(chǔ)展開相關(guān)研究的另一前提。不過,因不同的文獻載體在傳播過程中可能受到諸多主客觀條件的限制,甚至出現(xiàn)后人有意改動或作偽的情況,使得這些文獻載體的證據(jù)價值大小不一。即便是同一文獻載體,在不同的衍變過程中(即充分注意此類文獻載體的動態(tài)變化),亦可能出現(xiàn)差異之處。這就會在主觀上導(dǎo)致此類文獻載體及其證據(jù)意義在傳播過程中所形成的傳播效果,與文獻接受者所進行的文本闡述活動,二者出現(xiàn)分歧。從而導(dǎo)致學(xué)者對不同文獻載體中的同一文獻內(nèi)容,進行多樣乃至相矛盾的解讀意見。這種現(xiàn)象,同樣普遍存在于通俗章回小說之中。典型例如袁枚(1716~1797?)《隨園詩話》不同版本對《紅樓夢》的差異記錄及其引發(fā)的爭議。據(jù)研究,早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八月前即已開雕,①有效糾正了此前學(xué)界普遍認為的此書最早版刻是乾隆壬子(1792)的認識。之后,乾隆五十七年(1792)又仿乾隆五十四年(1789)小倉山房刻巾箱本,開雕了(約于嘉慶二年以后完成)《隨園詩話》16卷《補遺》10卷。②道光四年(1824),又對乾隆壬子刻本進行篡改,重新刊刻。因而,見于文獻記錄及今存的《隨園詩話》版本十分豐富,達六十余種③,也相對復(fù)雜。計有《隨園詩話》16卷《補遺》10卷(如泰州古籍書店藏稿本2卷、乾隆五十七年小倉山房刊本、道光四年刊本、道光七年小酉山房刊本、道光十三年刊本、同治五年三讓睦記刊本等),《隨園詩話》16卷《補遺》4卷(如小倉山房刊本、貫經(jīng)樓藏板本、學(xué)余堂藏板本、同治三年九經(jīng)堂刊本、同治十年重刊本等),《隨園詩話》16卷《補遺》8卷(如小倉山房刊本、嘉慶元年刊本等),《隨園詩話》16卷《補遺》1卷(如民國二年上海中華圖書館排印本等),《隨園詩話》16卷《補遺》6卷(如民國三年上海章福記石印本等),《隨園詩話》15卷《補遺》4卷(如日本內(nèi)閣文庫藏山淵堂刊本林述齋手校本等),《隨園詩話》10卷《補遺》2卷(如日本文化元年大阪河內(nèi)屋太助刊本等),《隨園詩話》5卷(如民國三年上海鴻寶齋石印本)等多種版刻系統(tǒng)。在眾多版本中,既有家刻本又有坊刻本,諸本的文獻價值不一。其中,那段為學(xué)界熟悉且多用來證明曹雪芹為江寧織造曹寅子輩之依據(jù)的文字,即道光四年己酉本《隨園詩話》所言:“康熙間,曹練(楝)亭為江寧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fēng)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當(dāng)時紅樓中有女校書某尤艷。雪芹贈云:‘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汙潮回?zé)徂D(zhuǎn)加。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差些。’‘威儀棣棣若出河,應(yīng)把風(fēng)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束態(tài),笑時偏少默時多。’”其間的諸多文字并不見載于乾隆壬子(1792)刻本。有學(xué)者曾對《隨園詩話》的早期家刻本進行了細致比較,發(fā)現(xiàn)乾隆壬子(1792)之后的刻本(包括家刻本與坊刻本),將乾隆壬子本“中有所謂”等字樣,通過剜改書版等方式徑直改為“明我齋讀”,甚至“以抽換整葉書版的方式來達到文本改動的目的。”④相比此書的早期家刻本而言,坊刻本更是無“明我齋讀而羨之”等字樣。在這種認識下,有學(xué)者比對袁枚之孫“倉山舊主”袁祖志(1827~1898)親自校印的《隨園三十六種》(光緒十九年),發(fā)現(xiàn)《隨園詩話》所言曹寅之子曹雪芹撰《紅樓夢》、雪芹贈詩妓女等內(nèi)容,系袁祖志(家刻本的主要刊刻者)篡改且偽造的。⑤20世紀(jì)初期,由于對《隨園詩話》版本的不熟悉、甚至未曾清理過《隨緣詩話》版本刊刻變化的胡適、俞平伯等“新紅學(xué)家”,據(jù)此而作的《紅樓夢》與江寧織造曹寅有關(guān)的判斷。⑥現(xiàn)在看來,恐怕問題不少。可見,通過深挖不同的文獻載體與同一文獻載體的動態(tài)變化對解讀古代小說的影響,是可以有效糾正學(xué)界的某些研究思路與研究結(jié)論的。
三、文獻載體的傳播途徑及內(nèi)容闡述與古代小說的流布
那么,古代小說的文獻載體如何進行傳播呢?換句話講,如何把握文獻及其載體的符號性、動態(tài)性、結(jié)構(gòu)性、普遍性等屬性?大致而言,古代小說流布過程中的傳播途徑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讀者通過對文獻及相關(guān)載體的閱讀學(xué)習(xí),直接接觸傳播對象,從而獲得相應(yīng)的感性認識或理性認知。在此基礎(chǔ)上,展開對古代小說的品評。當(dāng)古代小說的版刻系統(tǒng)混亂、甚或版本已佚而無法據(jù)以做進一步研判時,讀者直接閱讀或評論的意見,將是對相關(guān)小說作品進行諸如作者問題、成書時間、版本衍變等方面研究的重要文獻依據(jù)。二是,文獻載體的所有者或記錄者,通過與他人的交流進行傳播。如文人雅集、商業(yè)活動、當(dāng)面告知、書信往來等方式。這種傳播方式往往帶有特定的時空坐標(biāo),可以從參與談?wù)摰膶ο蟾髯缘奈募⒀哉撝校瑢ふ叶嘀刈C據(jù)。因而,此類傳播方式對于探討古代小說的流布情形亦頗有益處。三是,通過文獻的版本載體之刊刻而流傳。如紙質(zhì)文獻的刊刻與過錄,“叢書”“類書”的收集與整理等。這種傳播方式因保留了古代小說流布過程中的不同文獻載體,故而,有助于比勘同一小說作品在不同文獻載體中的差異變化(如單行本與“叢書”“類書”之間)。四是,文獻接受者的二次或多次轉(zhuǎn)引,聽聞于第三者等間接學(xué)習(xí)方式而獲得。古代小說在流傳過程中,因第一手文獻湮沒無聞時,可以借助文獻接受者的二次或多次轉(zhuǎn)引及談?wù)摚プ糇C該小說的成書、傳播等的存留。不過,由彼時社會知識階層向民間傳播與由民間傳播推及上層知識群體,兩種傳播路徑對古代小說的傳播效果、傳播范圍、傳播意義往往有不同的影響。尤其是,間接獲知的方式,往往會影響文獻傳播的準(zhǔn)確性及進行文獻文本闡述的客觀性。這就需要具體情形具體分析。在充分注意小說作品文獻載體的證據(jù)價值及傳播途徑有別的基礎(chǔ)上,我們還應(yīng)考慮如何對形式及價值有別的諸多文獻載體進行文本闡述。眾所周知,文本是文獻傳遞的內(nèi)容與受眾闡釋的對象,文獻的內(nèi)涵與意義往往需要通過受眾對文本的閱讀并闡釋而進行的。作為文獻傳播的重要監(jiān)督形式,受眾者的文獻評論行為對傳播的文本,從形式到內(nèi)容的描述及闡釋、對文獻傳播效果與意義的分析及評價,往往會影響相關(guān)文獻受利用的情形。據(jù)此而言,基于文獻傳播學(xué)視閾下的古代小說研究,應(yīng)充分注意彼時或后世的目錄著述、時人的札記及筆記記載等載體形式對文獻傳播的重要性。此類文獻對補充相關(guān)小說作品文本闡述的缺失作用不容小覷。當(dāng)對古代小說文本的分析存在不確定性、可逆性、非典型性時,由于今人距探究對象的時間間隔過于久遠,難免影響到文本闡述的客觀性與科學(xué)性。而通過彼時或后世的目錄著述、時人的札記及筆記等的文獻評論行為,將有助于今人進行文本的客觀闡述,挖掘討論文獻的意義。當(dāng)然,解讀歷代讀者的詮釋行為時,應(yīng)注意過度詮釋對被詮釋文獻之文本解讀的不良影響。比如,學(xué)界探討《三國志通俗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等作品的早期傳播時,通過比對不同版本挖掘其間差異的研究方法,無法有效解決此等小說的成書時間與早期傳播情況,甚至無法對此類小說作品的現(xiàn)存版刻進行體系歸納與系統(tǒng)分類。那么,透過此類小說產(chǎn)生及流傳之初的評論者所產(chǎn)生的評論意見,充分考慮此類小說不同版本的衍變及其差異,將“內(nèi)證”與“外證”相結(jié)合,實行“理證”與“事證”并重的研究策略,或許能夠有效推進相關(guān)問題的探討。在這方面的研究實踐中,效果較為理想的則屬對《水滸傳》成書時間的討論。當(dāng)從《水滸傳》文本中尋求“內(nèi)證”的方法,引發(fā)廣泛爭議而無法有效解決此書的成書時間時,如在“內(nèi)證”法用力甚深的學(xué)者,亦逐漸注意從同時期的諸多文獻載體中尋求“外證”依據(jù)。而此中充分注意“外證”且兼顧“理證”“事證”并用力甚深者,當(dāng)屬李偉實、王齊洲、王麗娟等人。他們一方面抓住“崔后渠、熊南沙、唐荊川、王遵巖、陳后岡謂:《水滸傳》委曲詳盡,血脈貫通,《史記》而下,便是此書。且古來更無有一事而二十冊者”等時人談?wù)摯藭木蹠ㄊ录ㄟ^挖掘李開先、陳束、王慎中、唐順之、熊過等在一起討論《水滸傳》的時間界限,①從而展開討論。另一方面,透過明代的“水滸戲”“水滸葉子”(如杜堇《水滸人物全圖》)①及錢希言《戲瑕》②、熊過《故相國石齋楊公墓表》③、陸容《菽園雜記》④、張丑著錄文征明小楷古本《水滸傳》⑤、朱有燉“偷兒傳奇”二種⑥等同時期的其他“外證”,充分注意不同文獻載體的有關(guān)記載,論證過程兼顧“理證”與“事證”,以判斷此類“外證”的存在時間、傳播情形及與《水滸傳》的關(guān)聯(lián)程度,從而組成系列的證據(jù)鏈以判斷《水滸傳》的成書時間。又如學(xué)界論爭不休的《水滸傳》作者問題。這個問題自《水滸傳》流傳之初始,就已相當(dāng)紊亂。在《水滸傳》明代刊本的題署、明季目錄學(xué)著述、相關(guān)族譜與家譜、明人札記等《水滸傳》流傳早期的多種文獻載體中,或作施耐庵,或作羅貫中,或署施、羅二氏,眾說紛紜。在這些文獻載體中,大部分或作施耐庵一人(或作羅貫中一人)的文獻載體的記錄者,與《水滸傳》之間并非直接相關(guān),所言的信息來源多系“聽”“聞”或閱讀“故老傳聞”(如所謂“天都外臣”序本《水滸傳序》曾言“故老傳聞:洪武初,越人羅氏,詼詭多智,為此書共一百回”),研判結(jié)論難免多屬感性認識,甚至存在互抄與隨意發(fā)揮等現(xiàn)象。而現(xiàn)存《水滸傳》早期刊本的題署與明代目錄學(xué)著述,多作“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如鄭振鐸原藏的嘉靖殘本《忠義水滸傳》、楊定見本《忠義水滸傳》等),“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如《百川書志》卷六“史部•野史”)。同時,郎瑛《七修類稿》等時人札記、李贄《忠義水滸傳序》等早期評論者,這兩類文獻載體亦將施耐庵、羅貫中二人并舉。通過這些多重證據(jù)可知,施耐庵與羅貫中對《水滸傳》最終定型的作用甚大,兩人皆是作品的重要編纂者,不可隨意抹殺其中任何一人。⑦可見,若是我們能夠充分注意不同文獻載體的信息來源、與評論對象的關(guān)系及其記載內(nèi)容的異同;那么,據(jù)以多種文獻載體所共有的信息內(nèi)容而組成的證據(jù)鏈,將有注意于進一步辨明討論的難點,從而規(guī)避某些不必要的非學(xué)術(shù)性爭論。雖說此類研究的結(jié)論不一定完全正確,但論者畢竟為相關(guān)研究建立了一個既可以對研究方法及過程進行檢查、又能對文獻載體本身及文獻內(nèi)容解讀進行多方驗證的討論平臺。伊•拉卡托斯《科學(xué)研究綱領(lǐng)方法論》曾指出:科學(xué)研究的價值在于所提出的某些理論或假說得到了事實的客觀支持或反對;科學(xué)研究的方法則是通過提供能夠有效證明某種理論或假說的事實或文獻的正面啟發(fā)法,以建立保護其說的“硬核”證據(jù)鏈;或者通過提出某種具有反面意義的“輔助假說”以建立使其“硬核”得到有效鞏固的“保護帶”證據(jù)。當(dāng)某種“輔助假說”,經(jīng)過文獻記載或經(jīng)驗式的事理推導(dǎo)的證明或證偽的嚴(yán)密論證后,其將從“輔助假說”上升為一種具有“硬核”證據(jù)的、業(yè)已證明的科學(xué)結(jié)論;即使這些“輔助假說”最終被證明不可信,它們也是有價值的———排除了“輔助假說”的多種可能性,使得研究在事實的客觀支持或反對中,進一步靠向真理之一面。科學(xué)研究必須建立在一個可供討論的、具有科學(xué)合理特性的研究平臺內(nèi),否則科學(xué)研究的證明或證偽,將任由研究者的主觀闡釋隨意夸大。⑧伊•拉卡托斯的觀點,將有助于啟示我們從文獻傳播學(xué)的角度,建立一個古代小說研究的科學(xué)且客觀的討論平臺。———充分考慮不同文獻載體的傳播途徑及效果,在確定或基本確定此類文獻載體的時空坐標(biāo)及與研究對象的關(guān)系之后,就可以據(jù)此對研究對象做進一步的研討,進而論證具有“硬核”證據(jù)且已經(jīng)證明的“輔助假說”,能否上升為各方都認可的“定論”!
四、歷代文治環(huán)境對文獻載體傳播及文獻內(nèi)容解讀的影響
由于明清時期的小說作品,往往“假托怪異之事,飾以無根之言”,而致“市井輕浮之徒,爭相誦習(xí)”,彼時統(tǒng)治者往往擔(dān)憂此類“邪說異端,日新月盛,惑亂人心”。①故而,明清時期頒布了大量禁毀小說作品的政令,令都察院、司禮監(jiān)等中央機關(guān)并地方政府嚴(yán)厲焚毀。尤其是,清代康、乾時期,多次頒布詔令嚴(yán)禁書賈刊印、書肆販賣與租賃被查禁的“淫詞小說”;針對私撰者、刊印者、買賣者乃至監(jiān)管不力的官員,提出過諸多懲罰措施。從刊刻、租賃、售賣、閱讀等諸多環(huán)節(jié),嚴(yán)格管控古代小說的流布。可以說,明清時期的官府針對古代小說作品長時間、高頻率、多層次的諸多禁令,對與小說有關(guān)的文獻及其載體形式的傳播生態(tài)有著深遠影響。這種文獻傳播的政治控制行為,一方面挫傷了文獻傳播者與受眾的積極性,甚至致使受眾群體形成對文獻及其載體的偏見與排斥;另一方面,導(dǎo)致了與小說相關(guān)的文獻及其載體的傳播范圍與意義大打折扣,以致壓縮了文獻傳播的渠道與路徑。這是學(xué)者探討“世代累積型”通俗小說成書時間與作者問題時,囿于文獻缺失而各執(zhí)己見的根本原因。比如,《四庫全書總目》之《季漢五志》提要批判《三國志通俗演義》“乃坊肆不經(jīng)之書,何煩置辨”②,以致《三國志通俗演義》《水滸傳》等通俗章回小說并不為以政教秩序、人倫道德為編纂思想與價值歸宿的《四庫全書總目》所認可,③從而不為清代統(tǒng)治階級所認可,致使此類小說作品在清代往往被當(dāng)作“誨盜”作品的典型而遭到多次查禁。可以說,貫穿有清一代的小說查禁行為,使得涉及明末清初時政問題的時事小說及歷史演義小說、與彼時文治背景不合的艷情小說等“淫詞小說”,往往遭到諸多查禁。乾隆時期,通過編纂《四庫全書》的行為以嚴(yán)控文網(wǎng),就全毀、抽毀、刪改過數(shù)量眾多的小說作品,使得被影響的小說作品在“四庫全書叢書本”的文獻載體之中,往往與其他版刻系統(tǒng)存在相當(dāng)大的差異。同時,不同時期的社會道德、輿論乃至風(fēng)俗習(xí)慣等,對該時期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文獻閱讀者的閱讀傾向及旨趣,亦會帶來效果不一的影響。古代小說的文獻及其載體傳播,亦只能在符合特定時期特有的道德要求、文化秩序及規(guī)范的基礎(chǔ)上,才能進行正常有效的授受活動。比如,經(jīng)歷了乾隆時期所謂“若將淫書一概什襲,流傳后代,能保子孫不過目乎?少年心志易惑,是為祖為父者,教之為不肖為禽獸”④等社會輿論的抨擊,彼時的諸多藏書家都將“各種淫詞艷曲及諸凡小說之類”(夏敬秀《正家本論》卷下“閑書勿藏”)⑤,歸為不可收藏之列;甚至,周亮工《書影》、阮葵生《茶余客話》、查嗣瑮《查浦輯聞》、孫詒讓《溫州經(jīng)籍志》、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等清季學(xué)人就曾對此前的藏書目著錄通俗章回小說提出過諸多嚴(yán)厲批評。⑥也就是說,彼時藏書家、士人階層的批判言論,形成了彼時社會輿論及道德要求對小說作品的認知意見。這就一方面限定了小說作品的流傳及閱讀范圍,另一方面對彼時小說作品的內(nèi)容選擇亦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那些“玷品性”“敗閨門”“害子弟”“多惡疾”的小說作品⑦,顯然都在社會輿論的高壓抨擊之列。此類文治環(huán)境已經(jīng)深深影響古代小說的流傳范圍與定位品評,必然進一步限制相關(guān)作品的文獻載體形式與載體原本內(nèi)容的存留,⑧甚至影響相關(guān)作品的傳播范圍與意義展現(xiàn)。晚清時期對《水滸傳》的“誨盜”與《紅樓夢》的“誨淫”官方定位與社會輿論,就使得此類作品只能當(dāng)時文教及輿論的嚴(yán)控下,進行隱形式的傳播。由此而言,學(xué)者應(yīng)充分注意歷代文治環(huán)境對古代小說文獻載體及其流布、文獻內(nèi)容的解讀所產(chǎn)生的影響。這是據(jù)此展開相關(guān)研究前所應(yīng)注意的又一前提。概言之,從文獻傳播學(xué)視閾探討古代小說研究,應(yīng)充分注意文獻及其載體的文本信息源、寫作者、文獻傳遞者(包括知識傳播者、消費者、利用者等)、傳播渠道、傳播手段及傳播環(huán)境等方面,暨文獻、受眾、傳播活動、傳播技術(shù)及傳播環(huán)境等五要素對古代小說傳播的影響。從傳播學(xué)及接受美學(xué)的角度講,一部作品問世之后緊接著就是流傳過程,是作品的傳播和接受使其價值及意義得以體現(xiàn)。探討作品的意義只有在其成書并流布以及在流傳過程中的影響范圍內(nèi)進行;即使某作品已成書卻未流傳開來(注意:這是一個假說,并非“事實”證據(jù)),從中蠡測該作品的成書過程與作者生平,所有討論都將屬于推論而無法被證實或證偽,抑或是缺乏能自圓其說的“硬核”證據(jù)或輔助性的“保護帶”。此類研究在伊•拉卡托斯看來是“不科學(xué)”的。新作品成書或流傳(借閱、傳抄、刻印等)后,就有了信息傳播或相關(guān)記錄,存在被談?wù)摶虮灰玫惹闆r,這是作品被承認存在的前提,也是探討該作品寫作者生平的重要文獻依據(jù)。因而,以相關(guān)文獻記載為基點,借用傳播學(xué)的方法討論古代小說的相關(guān)問題,是符合邏輯及學(xué)理規(guī)范的。當(dāng)這些文獻記載的相關(guān)信息———諸如記載這類文獻的作品及其作者、記錄的版本及記錄內(nèi)容的真?zhèn)巍⑽墨I信息點的可靠度、文獻記載所提到的人或事及與時代背景的關(guān)聯(lián)性等方面———可被確定或大致確定時,就可據(jù)為參照物以討論古代小說的有關(guān)問題。
作者:溫慶新 單位:揚州大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