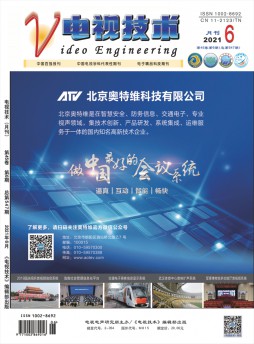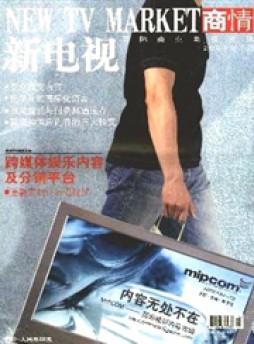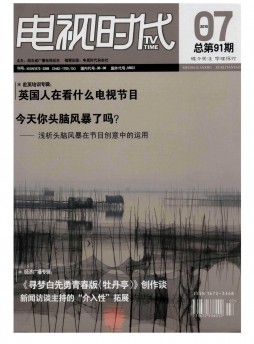電視電影類型敘事體系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電視電影類型敘事體系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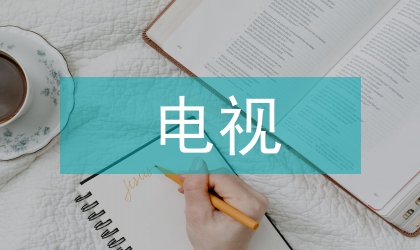
電視電影作為重要的大眾文化產品,應該明確其目標觀眾,根據觀眾的興趣和需求來定位其創作方向。在《當代電影》舉辦的幾次重要的電視電影學術研討會上,專家們都提出了電視電影類型化的創作策略,這顯然是從廣大觀眾的心理需求出發所做的考量。從類型化敘事的層面來看,可以說邱懷陽編劇的作品形成了一種成功的商業片模式。他熟練的以類型敘事模式講述一個個高度戲劇性的精彩故事,同時在類型的敘事外殼中納入對現實的敏感關注與呈現。在其精準的類型化敘事結構中,現實問題被轉化為類型中的沖突,以某種嫻熟而準確的敘事策略層層深入,并獲得觀眾所期待的理想解決。但是,邱懷陽同時也是一個成熟的作者,有其一貫的風格和美學自覺性。他在創作中將類型技法和個人風格融合到每一部作品的敘事中,使其作品得以在大眾文化生產的脈絡中保留了作者的某種鮮明個性。
一、社會現實生活的基底
邱懷陽的作品無論故事多么高度戲劇性,總是有一個社會現實生活的基底,在精心設計的故事結構中,以細節的塑造來保留現實生活的質感。這種與現實生活的親近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現實題材,二是情節的現實質感。一方面,從題材的角度看,邱懷陽對社會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問題保持了高度的敏感性與關注,這使他有可能將現實生活的種種矛盾與問題納入他的作品。而對現實生活的關注,來自邱懷陽對人性的體察與把握。在這一點上,《合同父子》中父母與兒女的關系,《從心相戀》中新婚男女的關系,在當下的中國都市生活中都具有很典型的現實意義。《從心相戀》中邱懷陽以一個喜劇性的故事來表現新婚青年男女之間的微妙關系。邱懷陽超越了一個簡單的歡喜冤家的類型故事,從更為寬廣和復雜的層面上呈現出了男女關系。故事的戲劇沖突建構包括了兩種人際關系——愛情關系與婚姻關系。戲劇沖突的引發是由于兩種關系都出現了裂隙。愛情關系往往只涉及兩個人,因此相對單純,但是其中又包含了一個更為基本的人類關系,即人與人的溝通和理解。比如,丹丹和曉濤第一次大的爭執是由兩人在買房這件事上的分歧導致的,這來自溝通的錯位。婚姻關系則更為復雜,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認為,婚姻現在不是私事,從來就不是私事,也不可能是私事。婚姻關系包括子女與父母、與配偶的父母的多重關系,這種復雜性勢必會帶來多樣化的矛盾沖突,這也是影視劇常常以婚姻為表現對象的原因。在丹丹與曉濤關系的變化中,他們與長輩的關系作為復雜的變量,改變和塑造著兩個人的關系。邱懷陽將現實生活中的這種復雜人際關系結構成為一種真實且飽滿的故事織體。
《合同父子》的父子矛盾更為單純,但也更為尖銳。在當代社會生活中,家庭的父子矛盾可以說是比較普遍的問題,這種矛盾的原因卻一點也不單純,兩輩人觀念的差異、情感交流的缺失,都有可能導致父母與子女的無法溝通。在人類的關系網絡中,親緣關系是最基本也是最為獨特的,列維•斯特勞斯的親屬單位三原子——血緣、繼嗣、姻親,衍變為一個復雜的關系網絡,使人類區別于自然。此網絡成為可與自然匹敵的獨立體,與自然既對立又統一。小海與父親看似尖銳不可調和的矛盾,其實只是來自相互的不理解,而這種父子間的較勁最后又變成兩個男人間的沖突。這種家庭內部的情感矛盾,在邱懷陽的書寫中,成為一個高度具象、劍拔弩張的矛盾關系,這使在現實生活中本應顯得平淡的親情矛盾戲劇化了。另一方面,邱懷陽也創作了大量具有高度戲劇性的娛樂電影,比如涉案片和愛情喜劇。在這類作品中,創作者保留了對現實生活細節的把握,形成了戲劇化故事帶有質感的現實基底,使得這類作品也帶有一種現實主義的外觀。這種現實基底是一個類型作者的難能可貴之處,使這類戲劇故事避免流于淺薄化的虛假和造作。嚴格來說,一個優秀的類型敘事作品必然有其現實面向,而不是脫離現實的胡編亂造。
二、文本的類型敘事策略
邱懷陽的作品總是以一個類型敘事的模式建構的,正因如此,他對現實的思考與呈現才能以一個跌宕起伏的戲劇性故事帶來高度的觀賞性與娛樂性。類型敘事是大眾文化生產中最具有生產性和最豐富的資源。認為電影應該以嚴格的現實主義方式反映社會生活的觀點,早就被證明了與電影的社會屬性和工業屬性相悖。電影介入社會現實的深度不能作為評判電影的唯一標準,因為電影的娛樂屬性從來都是不可缺少的面向。在這個意義上,類型這個概念絕不是一個負面的評價。更何況,在類型敘事中,文化與社會問題同樣是可以被納入和呈現的面向。類型本身是一個復雜的文化場域,類型的傳統作為固有的規則框架,并非是完全消極的,而是可以作為一個意義衍生的新場域。類型電影在當下中國的電影創作中還未建立起一套完整成熟的模式,因此說邱懷陽的作品是類型電影,顯然是不充分的。但是,他的敘事手法與劇本結構方式,有著明顯的類型敘事的痕跡。下面筆者將從幾個方面來分析這種類型敘事策略是如何體現在邱懷陽的作品中的。我們不妨先來考察典型類型電影的特征,進而能夠對邱懷陽的作品有一個準確的判斷。
1.類型的娛樂雙重性——快感原則和道德建構作用
類型電影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娛樂形式,是娛樂活動的一種載體。娛樂活動代表著一種“非生產性的、反文化的活動,表現被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壓抑著的基本價值和需要”。“娛樂活動對于社會的作用一樣,也是一條逃避現實原則的手段,是快感原則自由自在地發揮作用的地方。”(1)邱懷陽的幾部作品都表現出某種一致性,即有意識地追求一種觀賞性,無論是充滿戲劇性的娛樂作品,如《危險少女》、《終極游戲》、《我心中的朱麗葉》、《北京童話》等,抑或是高度貼近與關注現實的作品,如《合同父子》和《從心相戀》,邱懷陽都精心設計情節的起承轉合,制造引人入勝的戲劇性沖突,從而達成了某種觀看的愉悅效果。娛樂活動具有某種雙重性特質。雖然很多種娛樂是和社會行為準則背道而馳的,但還有一些娛樂恰恰是在“努力建立這種道德準則的理想典范”。類型電影就是這樣一種娛樂活動,既是主流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又是與之分離的。“它與這種意識形態抗爭,卻又能反映行為準則和它的道德結構。”(2)
這種雙重性在某種程度上存在于所有形式的娛樂之中。這種娛樂的雙重性在邱懷陽的作品中體現得尤為突出。《危險少女》是一部混合了黑幫元素、警匪元素與愛情元素的商業電影,每一種類型敘事資源在本片都被充分調動,以便最大限度地提供觀賞快感。小關與14歲的菁菁類似愛情的微妙關系,緊密交織著交易與小關的臥底身份這兩條線索,形成人物關系的巨大張力,敘事節奏的緊張感也在故事推進中被推至最緊繃的狀態。這里所構造的情感關系,混雜了懵懂愛情的甜蜜感,人性在墮落邊緣的緊張感,它們成為快感原則的構成元素,這種超越平淡生活的刺激故事,滿足了觀眾的觀賞心理。但是,這種快感的建構方式又絕不違背主流意識形態和社會道德準則,這恰恰表現了娛樂的另一重特質。正如菁菁所言,她不確定這是不是愛情,但毫無疑問,這的的確確是一種愛。一種更為抽象和崇高的“愛”將影片的情感關系升華為符合社會行為準則的理想關系。同時,菁菁喜歡的小關是黑社會小混混,也是一種帶有道德模糊性的感情,但是小關的警察臥底身份,又使菁菁的這種戀慕轉變為合乎道德準則的行為。這里就體現了娛樂的一個準則,即把“社會禁止的體驗和被允許的體驗結合起來,其結合方式竟能使前者顯得合理而后者得到豐富”。(3)
如果說,菁菁對小關的戀慕多少帶有某種叛逆性與不倫性,那么小關的態度和行為就將這種越過了道德邊界的情感變成了一種神圣的、可以被接受甚至令人感動的高尚情感。小關在這種關系中,從始至終都像大哥哥一樣,關心菁菁的成長,挽救她于墮落邊緣,幾乎可以被看做是理想的化身。小關的善良與勇敢代表了一種正面的價值觀,與菁菁任性肆意的放縱行為形成一組二元對立的沖突關系。
2.類型的敘事慣例任何觀眾對類型的熟悉都是一種經驗積累的結果。類型具有特殊的邏輯和敘事形式,觀眾經過重復地觀看同一類型的影片之后,“類型的敘事模式開始變得清楚,而觀眾的期待也開始成型”。(4)
類型的模式不只與敘事的元素有關,還與主題有關。由于觀眾有某種固定的期待,影片最終的結局就幾乎是在預料之中的,但也因為結局的可預料性,在結局到來之前的情節發展就格外重要,這種發展是否合情合理、跌宕起伏,直接影響了觀眾對預期結局的心理感受。無疑,邱懷陽對類型電影的敘事慣例有著深刻的了解,使他跌宕起伏的戲劇性作品往往不會走向意料之外,而始終是在情理之中給出結局,不會對觀眾產生隔膜感。如果你認為意料之中的作品是類型僵化老套的表現,就大錯特錯了。觀眾對類型故事的期待與喜愛正是來源于這種熟悉感和可以預料的結局,如果作者非要制造一個深刻的悲劇性結局或完全出人意料的結尾,就會產生令人不快的陌生感與疏離效果,這顯然是違背觀眾期待的。比如《終極游戲》的故事設置就是在一個懸疑片的框架中,將黑色電影的元素與愛情元素納入其中。懸疑線索的發展伴隨著愛情的一步步萌生,在秘密揭開的情節點上,愛情關系的情感力量也達到高潮。作者以懸疑與愛情來制造觀賞快感,并以男主角的高尚道德來化解影片中的超越秩序的行為。本片采用了典型的懸疑片外殼,一個無辜的人被卷入一場精心策劃的陰謀中。女主角是一個神經質的神秘女子,她的闖入將男主角喬梁帶入一個危險的境地。在這部作品中,作者對類型敘事慣例有一個全方位的熟練運用。男女主角的第一次相遇幾乎與阿爾德里奇的《死吻》如出一轍。喬梁在不明就里的情況下決定協助這個叫劉欣的女子,策劃了一次假的綁架,這種人物關系存在于許多黑色電影中,比如《馬耳他之鷹》。而結尾處劉欣真實的身份被揭示,原來她不是劉欣而是劉欣之妹劉明明,她冒名頂替的目的是使喬梁成為劉欣之死的替罪羊。這種移花接木的情節設置幾乎直接對應了希區柯克的《眩暈》。筆者此處的類比并不是為了指出作者對經典作品進行了模仿,因為類型本身就是一個經驗累積的文本場域,觀眾之所以喜歡觀看類型電影,就是因為這些反復出現的敘事元素,能夠有效地對觀眾心理發生作用。對于類型電影的作品序列而言,重復與累積正是不可或缺的,是類型之所以形成的必要條件。而判斷一部類型作品的優劣,敘事元素的使用能否有效率地制造預期效果就成為重要標準。電影類型本質上是一個“敘事系統,因此可以從其基本的組合元素來檢視它:情節、角色、場景、主題、風格等”。托馬斯•沙茲認為,“當類型變成電影工作者和觀眾之間一種心照不宣的合約時,類型電影就變成是履行這個合約的實際事件”。(5)
在邱懷陽的作品中,他能夠輕松地將具有現實關注的作品,按照類型電影的敘事模式來構造,這是由于他能夠在類型的慣例中構造敘事的基本元素,使現實主題通過類型的敘事元素來呈現。比如《從心相戀》是在一個典型的歡喜冤家式的浪漫喜劇故事的外殼下探討現實問題,其敘事模式與人物關系的建構完全是好萊塢瘋癲喜劇的方式。唯一不同的是,丹丹和曉濤這對青梅竹馬的戀人在影片開始不久就結婚了,但這不是一個傳統瘋癲喜劇結尾的大團圓結局,反而是一切矛盾沖突的起點。而在影片結尾,經過一系列因緣際會,兩人才終于等到了期待中的完美結局。在情節發展過程中,兩人因相愛與不理解而發生的唇槍舌劍形成喜劇效果,卻最終逐漸轉化為心靈的貼近。本片如傳統的瘋癲喜劇一樣,注重語言的諷刺效果與視覺的喜劇效果,劇情節奏十分緊湊。次要人物被表現為一些有著怪癖的扁平人物,用以制造喜劇效果,比如曉濤愛說教的父親和丹丹愛給別人做雞蛋羹的姥姥。《合同父子》就其故事沖突的屬性而言,并不是被構造出來的戲劇性事件,而是最具有社會現實感的真切問題。然而作者還是采用了典型的類型敘事手法,圍繞著“合同”這一情節動機來發展人物關系和結構故事。父子間矛盾沖突的引發,最終以“合同”這一具象之物作為其承載物,將抽象的情感矛盾轉化為具象的沖突對立,并圍繞著這個一紙合同為出發點,強化矛盾的不可調和性,并最終在戲劇性的轉折中解決矛盾。在類型的敘事慣例中,沖突得到清晰的解決是影片必然的結尾,于是,“合同”作為具體的激勵事件,把人物沖突的復雜性簡化了,使其有可能得到一個圓滿的解決。
3.類型作為解決問題的策略
類型具有一個重要的功能:解決問題。我們甚至可以“將電影類型定義為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6)如沙茲所說,“所有電影類型都處理一些威脅社會秩序的形式——暴力或人類的心理問題”。(7)
在電影類型發展的初期,類型一再遭遇特定文化中的意識形態沖突,并由主要角色的行為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法。類型電影這個解決問題的功能,即主要角色和他們采取的解決方法,影響了類型不同的形式,并以此區分出許多不同的類型。這一點再明顯不過,比如愛情瘋癲喜劇、家庭情節劇以及黑幫片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都形態各異。《合同父子》中親情的沖突,《從心相戀》中戀人的矛盾,《危險少女》中法制道德與不法分子的對立,呈現了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問題。但無論解決方式的差異有多大,類型作為一種主流文化產品,保有某種共同的價值觀,“在引發和解決文化沖突的過程中,類型電影頌揚我們集體的情感,為社會沖突的解決提供意識形態的策略”。這一點與藝術電影完全不同,藝術電影在深入探索人類的種種問題時,盡管也存在意識形態的差異,卻完全不打算彌合這種差異,而是將差異與現實問題放大。藝術電影絕不提供一個假想性的解決。而在類型電影中,往往會有一些社會沖突——個人/社區、文明/荒蠻、秩序/混亂——破壞社會的穩定狀況,但是電影結束時,這些“其實永遠存在著的文化對立問題都會被一一解決”。(8)
類型隱含的價值觀和理念系統,即意識形態和世界觀,決定了類型的戲劇沖突和問題解決的方式。邱懷陽的作品中,總能以一個戲劇性的理想解決方式維持社會的穩定結構和價值理念,這正是類型敘事的核心所在。通常,“每個類型都有一個不變的核心——展現它主題的對立和不斷發生的文化沖突。”如果認為類型是一個問題解決的策略,那么這個“不變的核心就是現實問題,而各種解決方法就是它可變的表面結構”。(9)歸根到底,這也多少能夠解釋何以邱懷陽的作品常常具有一個現實生活的基底。如果說,《合同父子》和《從心相戀》關注了現實生活中切實存在的問題與矛盾,那么,諸如《終極游戲》和《危險少女》這類高度虛構的作品則在類型敘事的模式下,隱含了人類社會更抽象的矛盾沖突,比如《危險少女》中的善與惡或《終極游戲》中強勢資本與渺小個人的沖突。但是,無論是具體抑或是抽象的現實問題都能在類型敘事中獲得解決。類型電影的劇情,“不是由單一主角不斷變化發展的觀點組織而成的一連串事件,而是隨著文化沖突對立的強化而發展,這種對立的沖突最后以我們所預料的解決方式解決的過程”。(10)
由于類型電影中沖突和沖突最終被解決都是可預期的,而非一個能否解決的懸置答案。于是,我們的關注點自然從直線的、因果關系的劇情,轉移到沖突本身以及解決的過程。這正如觀眾在邱懷陽作品的開端,即便能夠預料到沖突會被解決,但是這種沖突依然吸引觀眾的注意力,引導觀眾跟隨劇情的發展。這個解決過程在《從心相戀》中被設置得最為典型。人物間沖突的根源是情感溝通中的錯位,但是這種抽象沖突以某種物質現實的問題表現出來。丹丹想買房過二人的幸福生活,這種美好的理想在曉濤看來是不切實際的。曉濤父母指責兩人不負責任的打胎決定,卻被丹丹誤解為他們不想要孩子。這些交流的誤會漸漸累積為不可調和的沖突矛盾,導致了兩個人的分手。于是,類型所具有的解決問題的功能開始發揮作用。分手了的男女主角雖然在情感上依然相愛,但在客觀現實中兩人本來應該成為陌路人。于是,作者巧妙地使用了一些外來的力量介入兩人若有若無的關系。曉濤被朋友拉去電視征婚,正好被丹丹看見,同時丹丹的生活中也有一個追求者。這兩種外來的力量看起來是在把兩個人拉向相反的方向,實際效果卻恰恰相反。兩人因為各自的追求者,而意識到其實他們愛的還是原來的那個人,于是在誤解被消除后,兩人重新走到了一起。這是典型的瘋癲喜劇中常用的類型寫作手法。男女主角的矛盾沖突,實際上是將他們拉在一起的一種作用力。比如霍華德•霍克斯在《星期五女郎》里,或者是卡普拉在《一夜風流》里,都在男女主角沖突的關系上加諸反向的作用力,使其在一次次爭吵中,越來越貼近對方。類型的基本文化對立或內含的戲劇沖突,表現出它最基本、最重要的特色。在類型敘事中,沖突的解決與一個戲劇性的結局有關,在這樣的結局中,“妥協或是暫時解決沖突的方法,都被投射到一種文化和歷史的永恒之中,造成這些沖突被徹底解決的假象”。(11)
如果沖突是外在的威脅,則在結尾處被毀滅和消除,如《危險少女》中被繩之以法的黑幫老大,或者是《終極游戲》中觸犯法律的毒販和綁架者。如果沖突是由個人情感內部引發的,則以融合的方式解決,比如《合同父子》中父子間的冷漠疏離,或是《從心相戀》中青年男女的矛盾誤會。現實中的文化及意識形態的沖突在類型電影中都被轉化為情緒性的表現,并因此獲得解決。
4.對現實問題一個假想的情緒性解決筆者認為,邱懷陽敘事的內在邏輯也是類型化的,這不僅包括他設置沖突和組織情節的方式,也包括他對故事主題所隱含的文化沖突的處理方式。典型的類型敘事以一個戲劇性的結局解決了它所隱含的現實的文化和意識形態沖突,但這種解決仍然“不具有解決現實基本文化沖突的功能。而類型敘事持續受歡迎的原因正是在于指出了那些對立在現實中無法解決和妥協的本質”,比如《合同父子》中父子間的沖突在當下的社會是多么典型與普遍,但又難以調和。類型敘事中,“沖突本身只是被放在一個情緒的文本中,并在其中獲得迅速的(即使是不完全合理的)解決。類型的解決是一個縮減的過程:極端的對立情形不是透過其中一端力量的消除而消減,就是透過兩種力量的融合而變成一個單位”。每一個類型電影的標準結局都含蓄地接受了對立的價值。一些在現實中無法(或很難)解決的沖突,在類型中被戲劇性結局輕易地化解了。從某種程度上講,這是類型中的某種斷裂,是反敘事的邏輯,但是這種邏輯正是“好萊塢故事公式的基礎,因為一個好萊塢式的快樂結局的要求排拒了沖突的復雜性和深層特質”。(12)
所以,嚴格來講,類型電影具有提出問題的能力,卻無力回答。這樣的說法也許有些消極。但是,從根本上來看,藝術作品無法也不應該承擔解決現實問題的功能,尤其是作為娛樂形式的類型電影更是如此,能夠將某一類現實納入影片已經足夠了,并且,為其提供一個情緒性的解決才能滿足觀眾的觀賞需求。其實,類型能夠存在和發展,也正是因為它不斷通過敘事文本詳細描述,并且檢驗現實社會的基本文化沖突。這恰恰是類型積極的方面。類型的意義不僅僅是強化價值觀,同樣也具有挑戰和批評的可能性,可以說類型“發展存在的基本動力就是不斷和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進行溝通”。(13)
邱懷陽顯然對類型敘事的這一特征有著清晰的自覺性,以至于他的作品中,無論矛盾多么尖銳,總能巧妙獲得一個理想的解決方式。《合同父子》中的矛盾沖突來自父子間情感交流的缺失,導致了無法溝通和相互誤解。結尾處,父子和解在最終的時刻到來。這是典型的通過一個戲劇性的轉折獲得的想象性解決:兒子從公司經理處得知,自己的工作是在父親的暗中幫助下得到的,他才明白父親一直暗暗關心著他。這種巧妙的情緒上的和解多少帶有一些心理撫慰作用。沖突的解決方式,不是將父親與兒子的兩種價值觀融合使其共存,而是通過忽略一種價值觀,最終認同另一種更符合社會準則的價值觀形成的解決,即兒子走上了父親希望他走的路。說它是一種想象性的解決,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兩代人的價值觀沖突依然存在,而這種沖突幾乎無法通過一個戲劇性事件獲得解決。然而,在類型敘事中,這種解決是一種必然的操作方式,唯此才能達到類型的文化功能。《從心相戀》的結局同樣也是一個類型的想象性解決。丹丹與曉濤最終再次走到了一起,情感上的溝通帶來了和解。但是,在故事開端引發他們矛盾的種種現實問題,其實無一得到有效的解決,比如在誰家跟誰的父母住、買房子、要小孩等等。這些問題依然尖銳地存在于現實生活中,包括他們價值觀的沖突。但是,類型慣例給了影片一個情緒性的解決方式,即偉大的愛情戰勝了日常生活的種種瑣碎之事,于是,男女主角就“永遠永遠地在一起了”(片中曉濤的一句臺詞)。這當然是敘事邏輯帶給我們的解決方式,在類型慣例中,作者和觀眾以一種默契達成了交流與共識,認同了這種想象性結尾。但這個“愛情最大”的敘事邏輯,在影片開始兩人產生矛盾時為什么不發生作用呢?這當然就是類型敘事之外的問題了。類型敘事中,作者絕不會給我們一個“萬靈丹”式的解決方式,因為觀眾也根本不期待一個這樣的解決,而更愿意看到一個圓滿的結局。
5.類型敘事的文化儀式功能——建構與加強社會主流價值類型作為一種大眾文化娛樂形式,是由制片廠、創作者及大眾共同書寫出來的,旨在塑造和加強集體的價值和理念,因此必然是一種文化儀式。這種文化儀式的根本作用是融合多種多樣的價值觀與矛盾沖突。雖然從根本上來說,藝術作品無法也不可能承擔解決現實問題的功能,藝術作品只能盡可能忠實地反映現實的狀況。但是,做一種文化儀式的類型電影,就承擔了解決社會問題的文化功能,雖然這種解決注定只能是想象性的解決。邱懷陽的作品,當然也不是單純具有娛樂作用的商業電影,而是承載了這種文化功能的作品。不同類型的儀式功能不盡相同,大體上可以分兩類,一類是頌揚社會融合的價值,另一類是支持社會秩序的價值。前者傾向把態度不穩定的情侶或家庭成員看成社會的小縮影,他們情緒上的和解,代表了他們與穩定環境的融合。比如《合同父子》和《從心相戀》中,其結局給出的解決方式就是某種融合,通過融合或消除其一來化解兩種相異價值觀的沖突。后者以一方(常常是男性)的行為來解決對立的沖突,由他來穩固和加強社會秩序,比如在《危險少女》和《終極游戲》中就采用了第二類的解決方式。《危險少女》中,小關這個人物形象被賦予了多重的價值,勇敢、正直、無私,他是完美人性的理想化身,代表了正義的一方。龍海成則作為他的對立面成為惡的象征,而在這個二元對立的價值之間,危險少女菁菁幾乎是在善與惡的邊緣迷惘地掙扎。如果說菁菁是一個善惡分明的人物,明確傾向善或惡的一面,故事就單一乏味得多。但是,恰恰是這個在道德上處于中間地帶的人物使這一組二元對立具有了更大的張力與緊張感。善與惡的對立不再是界限分明的,而是被一個不分善惡的少女所模糊的,兩邊的力量都把少女往各自的方向拉,于是,戲劇沖突就更加復雜了,并由此形成了幾組人物關系。在影片結尾,小關被殺,原本脆弱的菁菁卻近乎英勇無畏地協助警察逮捕了犯人,并且多年后,這個曾經善惡不分的女孩成了嫉惡如仇的人民警察。于是,小關所負載的精神力量被轉移到了幾乎在墮落邊緣的菁菁身上,可以說,他的犧牲拯救了這個危險少女的心靈。在這個典型的臥底故事中,正義一方的勝利鞏固了社會秩序,達成了類型的文化功能。《終極游戲》中,喬梁這個人物形象也承擔了道德拯救者的角色。這個人物的設計最能體現出編劇邱懷陽對傳統類型電影敘事模式的成功改造,使其在主流意識形態中被接受和認可。開始,作為大資本的受害者和走投無路者,喬梁完全有理由成為綁架的合謀者并與策劃綁架的劉欣平分贓款,而編劇也讓我們在故事的推進中誤以為喬梁真的這么做了,他甚至冷酷地拒絕了劉欣的愛,這樣的情節就很接近好萊塢黑色電影的模式。然而,當情節進一步推進,喬梁參與綁架的動機是多么無私和高尚,他只是為了幫助劉欣在謊言中編造出來的那個有病的母親,而自己一分錢也不要。于是,黑色電影中軟弱墮落的男性角色,被改寫成了理想道德觀的化身,這就成為了一個套用黑色電影模式,但實際上更接近英雄書寫的故事。如果非要給這部電影挑毛病,筆者認為,這個人物到這里已經近乎完美了,而編劇似乎還嫌他不夠完美,于是,讓他做了一件更高尚的事,讓他設計把害死“真劉欣”的毒販子送到警方手里。在他崇高道德的感知下,“假劉欣”(劉欣之妹劉明明)也去公安局自首了。這樣,這個人物是更完美了,可完美得有點像一個假人。但是,類型敘事中的典型英雄角色通常就是一個道德高尚的完美形象,這樣的角色對于加強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是不可或缺的。于是,《終極游戲》的這個完美男主角,也必然是在類型的敘事邏輯之內而顯得合情合理了。
結語
類型化敘事是電視電影創作的一條最為有效的路徑,從閱聽大眾來看,對于故事的需求,以及對于觀看愉悅感的渴望,在類型電影中能夠獲得最大化的滿足。“類型”對于大眾文化產品的生產而言,無疑是一種最具生產性和豐富性的敘事資源,類型作為一種敘事慣例,并不會帶來創作的僵化,對此巴贊曾經高度評價類型的特質,認為類型的傳統就是創意自由的基礎。當然,只有一個好的創作者才能賦予類型敘事更豐富的意義,而不是把類型帶入成規與框架中。在當下中國電視電影創作的多樣化嘗試中,一些優秀的作者讓我們看到了類型發展的新景象,邱懷陽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作為一個創作者,他有講一個好故事的愿望,也有對人性的深切關懷與對社會現實的關注,而且在這兩者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希望這樣的創作者,能夠繼續豐富大眾文化產品的創作,帶給我們更多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