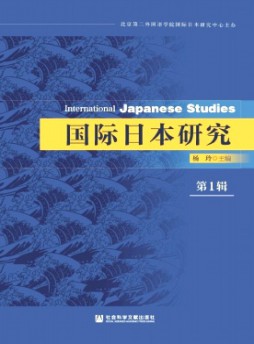日本無聲電影研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日本無聲電影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伊藤大輔導演的《俠盜治郎吉》(1931)。池田富保導演的《彌次喜多善光寺詣》(1921)、《尊王攘夷》(1927)、《彌次喜多尊王篇》(1927)、《彌次喜多鳥羽伏見篇》(1928)。筑山光吉導演的《涉川伴五郎-霧島山蜘蛛退治的場》(1922年)。伊丹萬作導演的《國士無雙》(1932)。衣笠貞之助導演的《瘋狂的一頁》(1926)、《十字路》(1928)。村田實導演的《路上的靈魂》(1921),五所平之助導演的《伊豆的舞女》(1933)。成瀨巳喜男導演的《小人物加油吧》(1931)、《非血緣關系》(1932)、《與君別》(1933)、《夜夜入夢》(1933)、《無止境的街》(1934)以及小津安二郎導演的10余部無聲片①。從這些陳舊發(fā)黃的影像中我們可依稀管窺日本無聲電影之一斑。
叛逆的武士
在這些影片中,武士片占去了絕大部分。被稱為“日本電影之父”的牧野省三(1878—1929)在他五十歲大壽那年(1928年)執(zhí)導了日本電影史上的里程碑作品《忠臣藏實錄》。影片取材于真實的歷史事件,描寫受辱的淺野藩藩主因行刺禮賓大臣吉良而被處死。以大石內(nèi)藏助為首的淺野家臣韜光養(yǎng)晦為舊主復仇,最后在主公墳前切腹以酬主恩。日本電影史上,《忠臣藏》題材電影總共拍了幾十個版本,每次翻拍都灌注進了時代精神和導演的個體精神投射。牧野省三的《忠臣藏實錄》可以說是對武士道精神最正統(tǒng)的影像闡釋,因為武士道的核心就是“忠與義”。四十七武士明知前面是死亡,卻義無反顧,慷慨赴死,忠肝義膽,直沖霄漢。正義與邪惡、忠與奸涇渭分明。但稍往里窺伺,在其下面仍然隱藏著一條反抗叛逆的暗線:四十七武士都是失去了主公、被拋離出體制之外的浪人,他們看似為主公復仇,實則是向體制挑戰(zhàn)。1920年代中后期,一種具有無產(chǎn)階級思想的“傾向電影”開始在日本流行,編導們站在底層和弱者立場描寫社會黑暗,反映底層民眾生活的悲慘,蘊藏著對現(xiàn)存政治體制的反抗與顛覆。這種思潮也影響到武士片,使得武士片往往將“社會批判毫不費力地隱藏于武士的盔甲下”①。牧野省三的《忠臣藏實錄》自覺不自覺地帶上這種“犯上作亂”的時代精神的影子。
而下面幾部作品則走得更遠,主人公大都是被主公放逐、含垢忍辱、放浪形骸的浪人。他們的主公不是對下屬愛護有加,而是趨炎附勢,心胸褊狹,甚至荒淫殘暴。由壽壽喜多呂九平編劇、二川文太郎導演的《雄呂血》被佐藤忠男譽為“日本電影青春期的作品”,描述年輕氣盛的武士久利富平三郎在一次老師的酒宴上被富家子挑釁而被迫出手。勢利的老師偏袒富家子,讓平三郎受罰。事后,平三郎又被誣陷對老師的女兒存有邪念被逐出師門,背井離鄉(xiāng),屈從命運,隨波逐流。善良被誤解為軟弱,忍讓被誤解為可欺,虎落平川,人見人欺,聲名狼藉。即便如此,命運仍不放過他,直將他逼到死角。《鯉名銀平雪候鳥》中的主人公銀平暗戀著茶館老板的獨生女阿市,但阿市卻偏偏與他的盟弟卯之吉兩情相悅,私訂終身。懷著深深的絕望,銀平遠走異鄉(xiāng),四處流浪。多年之后,回到故鄉(xiāng)的銀平得知卯之吉與阿市被地痞流氓勒索,為了那不曾泯滅的愛情和生來打抱不平的性格,銀平出手相救,最后深陷囹圄。影片寫出了為了心愛的人的幸福,不惜放棄一切的悲劇英雄的痛苦與悲哀。同類影片還有《逆流》。從上可看出,這些主人公原本善良正直,心地單純,卻不為世俗所容,被迫向惡濁的社會發(fā)出挑戰(zhàn),最后一個個被社會所吞噬。在這些影片中,女人是一個重要的能指符號,主人公懷著純潔的愛情,但所愛的女子大都心已另屬,他們只有浪跡天涯。在藝術中,女性從來都是社會的投影,女性的拒絕與倒向象征著社會對他們的舍棄與放逐。相比來說,伊藤大輔導演的《俠盜治郎吉》中的治郎吉則是一個敢于亮出自己身分,鋤強扶弱,劫富濟貧,單槍匹馬向現(xiàn)存體制挑戰(zhàn)的俠盜,也只有他是勝利者。與上面影片不同的是,正是女人的愛情在危難中拯救了他。《怒呂苦》以幕府末期基督徒武士與幕府軍之間展開的一場生死之戰(zhàn)為背景,描寫武士靈之介在戰(zhàn)場失利,戀人被殺,身患重病,身陷重圍,以寡敵眾,終于身陷囹圄,家破人亡。演員市川右太衛(wèi)門以驚人的感染力演活了這個身敗名裂的孤獨武士的絕望與悲壯。至于《鞍馬天狗前后篇》和《鞍馬天狗恐怖時代》是描寫幕府時代的尊王攘藩的故事,反映了廣闊的社會和歷史畫面。總之,反抗、復仇是這些影片的關鍵詞,它們所塑造的一大批為社會體制所不容的浪人組成的悲劇英雄系列,強烈的反抗叛逆精神和社會批判指向是1920年代中后期日本社會深刻的內(nèi)在危機和郁積在人們心中的反抗破壞欲望在電影里的投射,也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日本電影觀眾審美趣味的自然轉換。當然,這些也與當時傳入日本的美國西部片的影響有關,從這些主人公身上我們不難看出西部片中那一個個孤膽英雄的身影。
武士片似乎與生俱來就偏于悲情色彩和正劇風格,但下面的影片則皆以喜劇出之。牧野省三的兒子牧野正博(1908—1993)在他20歲那年導演了著名的《浪人街》第一回、第二回。兩部影片片名相同,但故事情節(jié)各自獨立。現(xiàn)在能看到的《浪人街》第一回只保留了片尾的高潮打斗部分。《浪人街》第二回仍以既好事又游手好閑的浪人為表現(xiàn)對象,用喜劇手法表現(xiàn)幕府末期沉淪底層的浪人們的日常生活,市井氣息撲面而來,草根階層生活躍然紙上,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帶有很強的市民電影風味。與父親《忠臣藏實錄》采用當時最強大的明星陣容不同,《浪人街》第二回全部聘請當時年輕的無名演員擔綱表演。以《浪人街》第二回為代表,池田富保導演的《彌次喜多尊王篇》、《彌次喜多鳥羽伏見篇》,伊丹萬作導演的《國士無雙》,再加上牧野省三導演的《雷電》,或表現(xiàn)武士的狂妄自大,色厲內(nèi)荏,或表現(xiàn)浪人的人性弱點,或表現(xiàn)相撲士在人情天倫與職業(yè)操守之間的尷尬,風格滑稽詼諧,解構了武士片的悲情色調,開創(chuàng)了一種全新的喜劇武士片。
日本電影“是從復制歌舞伎舞臺劇開始的”①,早期的武士片表現(xiàn)的都是英雄豪杰,在表演上沿襲了歌舞伎的傳統(tǒng),舞臺痕跡明顯,程式化色彩濃厚,扮演武士的演員往往只是從容不迫地揮刀舞劍,擺出武打招式即可,“與其說是戰(zhàn)斗倒不如說是舞蹈的劍術”②。即便到1920年代初,歌舞伎痕跡依然明顯。如1921年由牧野省三導演的《豪杰兒雷也》中打斗場面就帶有濃厚的歌舞伎色彩,武打招式完全是事先設計好、事先演練過的,與中國京劇的武打招式非常相似。該片是日本電影史上的第一部特攝片,運用了停機重拍技術,將劇中人與蛤蟆、蛇和蚯蚓等進行剪輯。然而,觀眾越來越不滿足于這種花拳繡腿的歌舞伎模式,到1920年代中后期,武士片的寫實主義被廣泛采用,場面富于動作性,武打動作充滿著一種動的力感,刀劍鏗鏘,血肉橫飛。以《浪人街》第一回為例,演員們奔來跑去揮劍砍殺的場面配以三味線伴奏,加上辯士繪聲繪色的現(xiàn)場解說,使打斗顯得異常熱鬧有趣,而演員敬業(yè)的出色表演使得打斗場面非常逼真,讓人如臨其境。尤其是采用蒙太奇手法攝進旁觀者的表情,使打斗場面具有很強的立體感。《忠臣藏實錄》片尾那場雪夜廝殺更讓人驚心動魄,熱血沸騰。此外,與日本劍術一劍致命飄然而去不同的是,這些武士片中的武打大都是漫長的大殺陣,主人公身陷敵陣,以寡敵眾,敵我雙方如蟻群聚散,如蛟龍進退,場面宏大,波翻浪卷。短促的鏡頭轉換,敏捷的蒙太奇手法,令人目眩的速度感和動作感,使得這個時期的武士片鏡頭流暢而富于生氣,動感十足,與此前的歌舞伎武士片不可同日而語。日本無聲電影時代的武士片培養(yǎng)出了一大批超級電影明星,如尾上松之助、市川右太衛(wèi)門、嵐寬壽郎、片岡千惠藏、和阪東妻三郎等。
愛情與倫理
無聲片的第二大系列是愛情片與倫理片。20世紀30年代初中期,溝口健二導演了數(shù)部表現(xiàn)女性命運的無聲片———《折紙鶴的阿千》、《唐人阿吉》、《瀧之白絲》、《東京進行曲》和《黎明之初》,尤其是《折紙鶴的阿千》和《瀧之白絲》,幾乎奠定了溝口電影的基本范式:“女人為男人的成功而辛勞,男人雖然會如愿以償,但女人卻不因此而得到報償。”③《折紙鶴的阿千》中的農(nóng)村青年宗吉只身一人來到東京,在偌大的人海里,舉目無親,夢想破滅,自尋絕路時幸被阿千所救。兩人脫離黑幫后,同住一個屋簷下,情同姐弟。為了宗吉能夠完成學業(yè),阿千不惜賣身,然而這一切宗吉全蒙在鼓里。多年后,宗吉如愿以償當上了醫(yī)生,而阿千卻沉淪社會底層,病入膏肓,命若天壤。《瀧之白絲》中美麗而好勝的水藝師白絲為了愛情,供心上人村越欣彌去東京帝國大學攻讀法律,為了湊錢給欣彌,她不得不以身體為代價去借高利貸,但比生命還重要的錢半途卻遭搶劫,她刺死了陷害她的高利貸主,身陷囹圄。而審判她的法官恰恰是她朝思暮想的愛人欣彌,白絲被處死刑,欣彌也受著良心的自責自殺身亡。不論是阿千還是白絲都是出污泥而不染,為了所愛的男子嘔心瀝血,甘愿犧牲一切的底層女性,在她們身上,姐姐、母親、戀人三種身分或隱或顯地融為一體。影片竭力描寫她們的美德與悲哀,將對她們的贊美與懺悔之情交融在一起。
仔細考察,這些影片有三類人組成:女主人公;“壞男人”———他們是陷害女主人公的黑幫頭目、高利貸者等,代表著社會的強權和惡勢力;男主人公,他們是社會的弱者,來自底層,在女主人公的資助與愛情的護航下,他們得以進入社會的上層。應該說,這些作品打上了導演很重的生活經(jīng)歷和情感的投影,因為溝口的姐姐就是這樣一個為了全家去作藝妓,還要接濟照顧他這個“終日無所事事、被鄰居看做阿飛之流的”弟弟④。溝口的母親很早就去世,對于溝口來說,家姐既是姐姐又是母親。從這些影片中的男主人公身上我們分明看到了溝口自己的身影,不過,吊兒郎當、“被鄰居看作阿飛之流”的“我”變成了從逆境中奮發(fā)向上終于成功的有為青年,這可以看作是溝口在白日夢中對自己的期許和拔高。一句話,溝口無聲電影中自傳性的“我”在里面起了很大作用,幾乎是三足鼎立中的重要支柱。然而,溝口后來的作品只剩下受難的女主人公和壞男人,而“我”的身影逐漸退隱。無獨有偶,小津安二郎的《東京之女》(1933)也是描寫姐姐為供養(yǎng)弟弟讀書,白天工作晚上做暗娼,弟弟知道后沒法面對親愛的姐姐竟會從事這么“低賤”的職業(yè),終于自殺。佐藤忠男曾說這類題材電影的誕生有其社會原因,在明治維新后的日本社會,“貧窮子弟立下出息發(fā)跡心愿,其無理的努力就得加諸于家里的女人身上。為了使弟弟上大學,姐姐就去賣身”①。只是溝口健二在生活經(jīng)歷和情感傾向的基礎上將這點“擴大深化”罷了。愛情片的另一名作是1933年五所平之助導演、田中絹代主演的《伊豆的舞女》,描寫一段風雨路上的感傷邂逅,青春期一段朦朧而美好的初戀。但影片插入了過多的社會元素,投下了較濃的人性陰影,擠壓和稀釋了愛情的純度。而且將“我”最后選擇離開歸因于不想耽誤熏子的幸福(溫泉旅館老板決定將熏子娶為兒媳)也與原著不符。在演員方面,男主角過于高大強壯(下巴還有一道疤痕),少了原著中主人公那份憂郁、青澀、純正的學生味。《伊豆的舞女》共有六個版本②,相比來說1974年的西河克己版更貼近川端康成小說的風格。
在倫理片方面,1921年村田實導演了被譽為“日本電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路上的靈魂》。然而,與其說是日本電影,不如說是高爾基的小說《在底層》的電影版以及西方基督教教義的視頻演繹,從衣著、化妝到字幕、主題都與日本電影相去甚遠。影片有兩條線索,一條是與老父爭吵憤而離家的游子杉野浩三郎一身落魄帶著妻女回到故鄉(xiāng),在大風雪之夜又被老父趕出家門,凍死在雪野中。一條是兩個刑滿釋放、饑腸轆轆的流浪漢鶴吉和龜三因為偷竊反受到主人家的小姐邀請參加圣誕晚會,酒足飯飽后重踏新的人生路。《路上的靈魂》題材本來應生發(fā)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傾向”主題,但影片偏離階級斗爭和社會控訴主線,著重表現(xiàn)基督教的博愛、寬容和救贖。在藝術上,最大的特點是平行蒙太奇的運用,兩條線索并行發(fā)展并最終交匯在一起。又通過對比蒙太奇將兩類不同處境的人的悲歡哀樂進行反襯,一方是圣誕節(jié)別墅里的狂歡,一方是冰冷谷倉中的垂死掙扎。一方是美味佳釀,一方是饑腸轆轆。一方是對素昧平生的流浪者的收容,一方是老父對親生兒子的拒絕。一方是兩個流浪漢酒足飯飽后開始新的人生,一方是不被老父原諒的兒子凍死雪野。一方是遠方游子對家的渴望,對父親的幻想,一方是冷酷父親對兒子的放逐。其次是攝影手法上的大膽革新,幻想、回憶、聯(lián)想鏡頭被廣泛而嫻熟地運用,它們介紹背景,交代人物關系,極大地增加了影片的含量,使得影片緊湊而精致。在布景上,導演將外景地設置于寒冷的北國風光,巍巍群山,無邊雪野,呼嘯的寒風,漫天的暴風雪,設置出一個冷酷而蕭條的世界。而與其對應的內(nèi)景則是溫暖的房間,熊熊的爐火,熱乎乎的飯菜。在這兩種布景上擱置不同人的命運,巧妙而有力地凸顯出影片的主題。而成瀨巳喜男1930年代執(zhí)導的《與君別》、《夜夜入夢》、《無止境的街》、《非血緣關系》和《小人物加油吧》等影片則主要采用平實的寫實主義手法來表現(xiàn)家庭倫理沖突。除了《小人物加油吧》以喜劇手法表現(xiàn)底層人民生存的艱難,帶有“傾向電影”的“傾向”外,其它四部電影幾乎清一色地描寫女性的生活和情感世界,這些女性雖然地位卑微,生活艱難,但心地善良,心靈潔白,堅韌執(zhí)倔,外柔內(nèi)剛。如果說溝口作品中的女性最后破罐子破摔,自甘沉淪,成瀨作品中的女性卻挑釁性地不向命運屈服,帶著不用別人來憐憫的決絕態(tài)度,努力從逆境中抬起頭來,勇敢地面對生活,卻竭力保持住作為女性尊嚴的最后底線。實際上成瀨巳喜男后來尤其是戰(zhàn)后的電影一直沿襲著這種題材、人物塑造的套路和美學風格,變化不大。然而,成瀨巳喜男主張“電影是生活,不是戲劇”,因此他的電影往往像日歷一樣記載著蕓蕓眾生的生活,缺乏加工提煉,缺乏高潮,從而造成了成瀨電影的平鋪直敘。小津安二郎的《我們要愛母親》的主題就像這具有訓誡味的片名一樣,描寫一個母親與前妻兒子之間的感情,道德說教意味較濃,概念化痕跡明顯。
從藝術性上講,這部影片明顯弱于此期小津的其它影片。除此之外,齋藤寅次郎導演的《黎明之初》講的也是一個悲歡離合的故事,丈夫早夭,年輕的母親不得不忍心拋下愛女,多年之后,母女重逢,百感交集。《小雀嶺》描寫一個賣糖果的少年德太郎,一邊唱著死去的母親教他的賣糖歌,一邊尋找失散父親的故事,是一部充滿了父子親情與人情味的感人之作。這些作品中只有《東京進行曲》中的道代小姐最后找到了一個好的歸宿,其它的都以悲劇結束。《唐人阿吉》是日本電影史上非常知名的電影之一,內(nèi)容描述了江戶時代末期美國駐日本的首任領事———TownsendHarris之妾阿吉的生平。我們所能看到的這部作品是1930年拍攝的《唐人阿吉》的宣傳影片。最后我們要說的是衣笠貞之助導演的兩部前衛(wèi)影片———《瘋狂的一頁》(1926)和《十字路》(1928)。《瘋狂的一頁》是衣笠之助與日本新感覺派作家川端康成和橫光利一合作的影片,以瘋人院為背景,描寫一位父親為了女兒的幸福,企圖將患精神病的妻子帶出瘋人院的故事。但這部實驗性極強的影片留給觀眾印象最深的與其說是故事,不如說是片中那些明暗光線的跳躍,往外翻騰的幻覺,幻想鏡頭的廣泛運用,動態(tài)倒敘和快節(jié)奏剪輯,開創(chuàng)了日本電影史上表現(xiàn)變態(tài)心理電影之先河,在1970年代寺山修司一系列的實驗短片、《死在田園》和鈴木清順的“大正三部曲”(《浪浪者之歌》、《陽炎座》和《夢二》)中似乎可以窺探它的余脈。《十字路》以表現(xiàn)主義的手法表現(xiàn)一對姐弟的悲慘命運,弟弟為了風塵女爭風吃醋,姐姐為了保護弟弟,最后釀成悲劇,主題卻是對社會的揭露與控訴。到處是陷阱,一張張猙獰的面孔,一群群醉生夢死之徒,濃重的黑暗,一對風雨中的“小燕子”走投無路,終于被社會所吞噬。影片表現(xiàn)手法大膽前衛(wèi),如表現(xiàn)神經(jīng)錯亂的幻覺,風格化的布景,攝影上的疊印幻化技法,而側光和特寫的運用恰到好處地凸現(xiàn)了那個黑暗罪惡、扭曲畸形的世界。但過于先鋒前衛(wèi)的試驗也使得影片曲高和寡。
草根、童年與青春
表現(xiàn)草根階層的悲歡哀樂和孩子們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是1930年代小津安二郎電影的主要內(nèi)容。前者的代表是“喜八三部曲”———《心血來潮》(1933)、《浮草物語》(1934)和《東京之宿》(1935),它們以寫實主義的鏡語、善意的調侃和深切的同情描寫喜八這位樂觀沖動、心地善良的小人物在找工作,對待愛情,處理家庭問題時的遭遇,將日本社會的人情世態(tài),庶民階層的喜怒哀樂盡現(xiàn)于銀幕上,與山田洋次的《寅次郎的故事》系列異曲同工。相比小津的后期作品,社會的扇面打開得較為開闊。尤其是《浮草物語》更包含了后來小津家庭倫常劇的基本元素和情感取向,它幾乎是整個小津電影的微縮版,1959年更被重拍成彩色片《浮草》。另外,我們也注意到“喜八三部曲”明顯受到當時“傾向電影”思潮的影響,通過展示底層人民生活的艱辛和苦難來達到對社會的控訴。然而在描寫中由于側重于底層人之間相濡以沫的感情以及愛情的佐料和孩子們的童趣,沖淡了本來應具有的悲劇氛圍和批判的火力,風格溫和諧趣。
而以詼諧幽默的語調,以一雙慈顏藹藹的目光和會心的寬厚笑顏講述孩子們的趣事,是小津早期電影樂此不疲的主題,其實從某種角度看,“喜八三部曲”也可看作是兒童電影。小津一生表現(xiàn)兒童生活的影片有三部:《我出生了,但……》(1932年)、《長屋紳士錄》(1947)和《早安》(1959年),但無聲電影只有《我出生了,但……》。影片講的是一對哥倆在同學太郎家中看電影,平時他們眼中那么偉大威嚴的父親在電影里卻在上司和同事面前故作滑稽之相以討好取寵,并當著孩子的面卑躬屈膝地給同學太郎的父親遞煙送火獻殷勤。像山一樣高大的父親的形象在孩子們的心中轟然倒塌,“偉大的爸爸”成了一個破滅的謊言。他們再也坐不住了,沒等電影放完就跑回了家。“爸爸總教我們作偉人,而爸爸自己卻不怎么偉大”。只是因為太郎的爸爸是公司的董事長,是發(fā)薪水的,爸爸就這樣低三下四。但是在學校,太郎是他們的手下,聽憑他們指揮。在孩子們心中,第一次感到孩子世界與成人世界、家中的父親和在公司上司面前的父親竟會出現(xiàn)這么大的反差。爸爸向他們解釋“其實我也不想討董事長的歡心,但也因此使生活舒適了許多”。媽媽說“若爸爸沒有薪水,你們便不能上學,沒有飯吃了”。小哥倆聽不進這些,開始絕食。按照他們的邏輯,太郎的爸爸偉大是因為富有,那么富有就偉大嗎?他們一口認定,爸爸不是偉人,爸爸是個膽小鬼!他們再也瞧不起父親,他們以有這樣沒有骨氣的父親而感到羞愧。夜里孩子們流著眼淚睡著了,但這個心結并未解開,它們會纏繞孩子們一生。“不知道他們以后是否也要如此忍氣吞聲地活下去?”望著孩子們睡熟的稚氣的臉,爸爸嘆息著說。影片生動地再現(xiàn)了兒童世界,在童年純潔的湖心里倒映出了一個陌生、變形的成人世界,表達了成人世界的等級觀念對兒童心靈的戕賊和傷害。“孩子的身影是小津電影中一道獨特的風景,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孩子們稚嫩的歌聲喚起了觀眾心靈久違的感動和對逝去歲月的無限緬懷。”①小津影片中的孩子大都淘氣而倔強,天性未泯,性格各異。只要寫到孩子總會讓影片的氣氛輕松愉悅。《東京之宿》表面上是寫底層社會生活的艱難,但小哥倆天真的童趣將生活中的艱難和沉重沖淡。哥哥將父親交給的包袱甩給弟弟背,弟弟肚餓不背。哥倆賭氣丟下包袱。可等他們后悔回頭,包袱已被人撿去。爸爸找工作四處碰壁,一家人饑腸轆轆,為了安慰父親的頹喪,大兒子給父親“敬酒”,給弟弟“盛飯”,苦中作樂,畫餅充饑,在白日夢中酒足飯飽,讓人笑中帶淚。而《心血來潮》中的“小大人”富夫的性格也塑造得栩栩如生,為了父親叔叔能上班掙錢,早晨用木棒敲他們的大腿催他們起床更讓人捧腹。
除了孩子外,青年題材也是小津前期電影的一個重要內(nèi)容。《年輕的日子》(1929)講述兩位無憂無慮的學生哥愛上了同一個女孩,由同學一變而為情敵,為了親近自己的心上人,兩人爭風吃醋,挖空心思。不料女孩的芳心另有所屬,兩人美夢成空,面對挫敗,黯然神傷。這是一部輕松諧謔的青春喜劇,充滿著導演對青春時代的懷念。倘說《年輕的日子》表現(xiàn)的是“愛情幻滅”的話,《我畢業(yè)了,但……》(1929,描寫大學生畢業(yè)后找不到工作)、《青春之夢今何在》(1932,學生時代的好友工作后身分轉變?yōu)樯舷录墸爸髌陀袆e”)等片表現(xiàn)的是青年人步入社會后理想與現(xiàn)實的巨大落差,盡管有幻滅和挫敗,但青春氣息濃郁,凄涼中有溫馨,人生凋殘的遠影遠未到來。《非常線之女》是小津少見的黑幫題材電影,不管是在小津電影還是同時代的電影中,都是一個異例。但影片摒棄了黑幫電影慣常的火拼打斗場面,而是努力發(fā)掘黑社會人物身上向善向上的沖動及在善惡的十字路口上苦苦掙扎的心路歷程,最后終于迷途知返,走向新生。
不了解日本的無聲片,就不能了解后來的日本電影,理不清日本電影的淵源繼承關系(因為日本導演一直有翻拍舊作的傳統(tǒng))和導演風格之演變,更不能了解日本的民族性、文化傳統(tǒng)和時代精神對日本電影的影響。上述有限而殘缺的無聲片為我們了解日本早期電影打開了一個小小的窗口,同時也為國內(nèi)日本電影的研究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影像資料。(本文作者:黃獻文單位:武漢大學藝術學系)
- 上一篇:小議廣播的輿論監(jiān)督作用范文
- 下一篇:村委財務一月一公開工作意見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