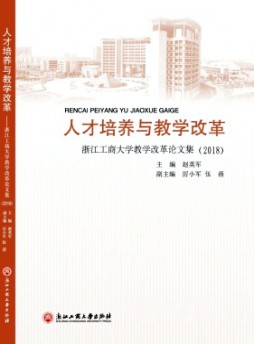人才培養論文:創作型電影人才的培養綜述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人才培養論文:創作型電影人才的培養綜述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作者:倪震單位:北京電影學院
從綜合性大學的文科院系中,培養理論研究型電影人才的成果非常顯著。二十年來,成批的電影史論碩士和博士加入到研究隊伍中來,形成了人才濟濟、理論面貌不斷更新、方法論和研究領域不斷拓展的新局面。突破與創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研究和重寫中國電影史方面,顯示出青年理論工作者的高度熱情和求索精神。在史料挖掘和微觀研究領域不斷取得有益的成果;第二,在中國電影產業研究領域,配合當下電影發展、體制轉型、市場化建設的進程,追蹤現實演變,以產業實踐理論促進電影生產和電影經濟發展;第三,在中國主旋律電影主流大片的創作特別是類型電影的現實發展中,進行跟蹤研究,以理論化的視角,對上述課題進行深入的、聯系實踐的檢察和探討,對創作界產生近距離的反饋和有力的影響;第四,促進兩岸三地的電影史論交流,開展國際化的電影理論往來和學術互動,在電影理論學術研究方面,迅速地實現了與國際接軌,在短短20年的時間中,實現了電影理論人才的有效接續、代際更新和多類型史論人才的配套,實現國外現代電影理論的介紹引進以及本土化的轉型,實現了中國特色電影理論的初步體系化、多元化,這不能不說是文科綜合性大學研究型電影理論人才培養的結果,這是一項成效明顯的電影理論教育的歷史性成就。
相比之下,創作型電影人才的培養,也同樣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收獲。從中國電影年產量逐年增長,到2012年為止,年產電影達到700部(包括電視電影)左右的數字來看,表明創作型電影人才如雨后春筍,不斷涌現,這是十分喜人的現象。但是,從數量眾多的國產片中,有多少部能進入院線放映,即使進入了院線,從上座率和票房數字來看,獲得的反饋卻是并不令人樂觀的。隨著中國電影市場不斷開放,在外國影片在中國市場上所占比率不斷上升的現實面前,國產電影的質量問題明顯突現,國產電影的競爭力和適應新挑戰的前瞻性尖銳地擺在我們面前,一個突出的戰略性任務不容回避。創作型電影人才的培養迫在眉睫。
探索創作型電影人才培養的中國模式
正如綜合大學在理論研究型電影人才培養方面獲得了顯著成績一樣,在創作型人才培養方面,各院校在近二十年間亦都取得了不同的成就與經驗,輸送了青年電影創作人才。如中央戲劇學院、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影視與傳媒學院、上海戲劇學院、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等院校,都獲得了碩果累累的教學成績。在探索創作型電影人才培養模式方面做出了不同的貢獻。
筆者多年來求學及服務于北京電影學院。因此,就自己的切身體會,想通過回顧與梳理北京電影學院的教學建設與體制改革,從個案分析來研討創作型人才培養的實際情況。北京電影學院創建于1956年,是一個單科型電影院校。在20世紀50—60年代,是中國唯一的一所培養電影專門人才的高等學校。在50年代建國初期的歷史環境和國際關系格局下,中國和蘇聯關系良好,經濟建設和文化教育事業處于全面學習蘇聯的歷史化階段之中。北京電影學院建校之前,曾經對莫斯科電影大學做了詳細考察,因此,在建校體制方面,是參考單科型電影學院的專業設置結構,分導演、表演、攝影、美術、錄音各系。后來又增設電影文學系和電影工程系。這樣的建制一直延續到1966年“”發生。新時期開始以來,與全國改革開放形勢同步,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北京電影學院先后派出多批人員,從校領導、系主任及各系科骨干教師,遍訪歐美、日、韓各國的電影院校進行考察、交流,有的教學人員以訪問學者的身份較長時間在國外電影院校考察和了解他們的教學狀況和建設特點,系統地了解不同院校的教學體制及教學方法,從而促進了北京電影學院的教學改革和體系重構,實現了吸收眾家之長的新型單科型電影學院建制。
作為單科型電影院校,北京電影學院以培養創作型電影人才為明確方向,從20世紀50年代建校以來,在近六十年來的教學實踐中,培養了不同代際的創作型電影人才,向中國電影工業體系輸送了不同類型的電影創作人員:
第四代電影導演:吳貽弓、丁蔭楠、胡柄榴、謝飛、張暖忻、黃蜀芹、李前寬、肖桂云、韋廉、滕文驥等。
第五代電影導演: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吳子牛、胡玫、李少紅、尹力、馮小寧、顧長衛、侯詠、霍建起、黃建新、張黎等。
“第六代”電影導演:賈樟柯、王小帥、婁燁、路學長、管虎、張元、寧瀛、章明、張楊等。
在以上各階段出現的不同代際中國導演,都生逢其時地對他們所處的歷史時期,對中國電影做出了不同的貢獻,奉獻了優秀的電影作品,展示了他們各自堅持的美學追求。最有現實意義的是,面對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當下,面對市場挑戰的嚴峻形勢,北京電影學院培養的最新一代電影導演,又投身到新形勢的洶涌波濤中,展現了不畏競爭,與時俱進的姿態:寧浩:《瘋狂的石頭》、《黃金大劫案》滕華濤:《失戀33天》、電視劇《蝸居》、《浮沉》烏爾善:《刀見笑》、《畫皮2》王競:《我是植物人》、《萬箭穿心》林黎勝:《消失的村莊》、《百萬巨鱷》莊宇新;《愛情的牙齒》、《隋朝來客》劉杰:《馬背上的法庭》、《碧羅雪山》薛曉璐:《海洋天堂》程耳:《第三個人》、《邊境風云》徐靜蕾:《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杜拉拉升職記》曹保平:《李米的猜想》、《光榮的憤怒》姜偉:電視劇《潛伏》、《借槍》以上這批導演的名字,或許沒有第五代導演那么響亮,沒有“第六代”導演堅持個人化、作者性的立場那么鮮明頑強,但他們面對電影市場的嚴峻殘酷,面對低成本投資的條件苛刻,挺身而出,智慧出眾,明確地承擔起勇斗市場環境又堅持藝術品質的創作路線,正開創出中國青春氣息濃厚的一片新氣象。這個名單并不完整,也沒有寫全導演群體代表性人物,僅僅展示一所電影院校,在不同時代向電影工業系統輸送的專業人才。對于單科專業型院校而言,考察其教學體制和教學方法成敗之最好標準,便是它能否向本專業輸送頂尖型人才集群,而且這種培養和造就的成果是可持續發展并與時俱進的。
北京電影學院培養創作型電影人才,有以下幾個方面,形成其辦學特色:
第一,明確定位自己是單科或創作型電影人才培養基地,以專門化、小規模、尖端性人才培養為辦學方向。專門化的特點,就是以導、表、攝、錄、美、編劇、電影管理人才為專業建構,以創作實踐型人才為明確的目標,扎扎實實地培養各專業理論聯系實踐的學生。大量實踐,鍛煉動手、操作能力,了解和勝任本專業最新技術動態,適應和完成現代電影生產任務。小規模的含義是不盲目擴大為綜合性、配套齊、大而全的景觀式大學,而是在時代演變過程中根據自身特點合理發展,從求精求新的意義上,不斷提高和創新單科式創作型人才培養的質量和水平。尖端化是從20世紀50年代建校到新世紀的當下,學院內始終彌漫著、延續著一種電影神圣的空氣、學生們高度熱愛電影、終生獻身電影的虔誠精神和藝術崇敬成為一種傳統。學習電影和從事電影工作不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信仰。尖端人才的養成不僅僅是知識豐富、基礎扎實,首先必須是對電影藝術的神圣信仰和終生奉獻的忠誠。
第二,有一支獻身電影教學事業、精通本專業電影業務,自身創作實踐過硬的教師隊伍。北京電影學院從20世紀50年代建校起,第一代學院領導章泯、鐘敬之和吳印咸本身就是學術權威和杰出專家。20世紀80年代以后,留校任教的謝飛、鄭洞天、張暖忻教授等不但是優秀的教師,而且是承上啟下的第四代導演中的代表人物,先后執導了《湘女蕭蕭》、《黑駿馬》、《鄰居》、《臺灣往事》、《沙鷗》、《青春祭》等標志性作品;其后,張會軍、謝曉晶、穆德遠、黃英俠、孫立軍教授成為又一代身兼學院領導又承擔教學和電影創作任務的教授群體,將電影學院的體系建設和教學創新帶進了新世紀十年快速發展的軌道。更新一代的青年教師隊伍,繼承并發展了忠誠教學工作,又創作影視精品的傳統,取得了新世紀影視觀念突破性的藝術成果。例如:姜偉導演的電視劇《潛伏》、《借槍》,在諜戰題材電視劇創作上取得了人所公認的創新性成果。莊宇新導演的《愛情的牙齒》、王競導演的《我是植物人》和《萬箭穿心》、薛曉路導演的《海洋天堂》、林黎勝導演的《百萬巨鱷》、梅峯編劇的《春風沉醉的晚上》,等等,都具有明顯創新價值。幾乎每一部作品都引發了業界同仁的關注和論評,體現了學者編導的創作特色和探索性品質。因而引起了在校學生的研究熱情和加深親師感情。以創作型電影人才為培養目標的院校中的教師,如果自己不在創新實踐上以身作則,創作領先、觀念領先、拿出過硬的作品展示自身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拿什么說服學生,用什么新鮮經驗跟學生交流呢。這跟理論研究型電影院校的教師著作等身,理論創建人所共識的道理是一樣的。照本宣科,一本講義用十年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北京電影學院在教師隊伍建設上,代代相傳的實踐為重,身體力行、勇于創新、影視作品領風氣先,成為一個充滿責任感的教學/創作傳統,這是建設一所有生命力、可持續性的創作型電影藝術院校的根本立足點,學校建設的生命線在于教師隊伍的建設。
第三,在完善的電影史論和創作理論教育下的大量動手實踐。“既然是培養創作型電影人才,那就多多地讓他們實踐為主,多拍多動手練習就行了。”這樣的主張和實際訓練,可以造就出在片場熟練操作的人員,但很難培養出深諳電影歷史,明確創作規律和自我歷史定位的創作型電影專業人才,事實上在培養目標上就已發生了分野。電影史論教學、創作理論教學和各專業(導、表、攝、錄)應用理論教學是相互關聯、分層次結構又各具專門特色的教學系統。之所以能形成“宗教般”的電影信仰、癡迷程度的電影忠誠,就在于不可缺少的電影文化和電影歷史的教學。它永遠引領著一代又一代學生樹立自己的電影理想,熱愛電影熱愛到癡迷程度,推動著學生廢寢忘食地要用電影手段來表達自己對人生的看法、對世界的感受、與世界電影大師的創作對話、對當下電影現狀青春沖動地尋求突破的渴望。只有在這種精神狀態下的“多動手、多實踐”,才是充滿活力的動手實踐,才是靈感閃躍的短片拍攝和片場實習投入。而不是為動手而動手、為實踐而實踐的苦力勞動、變相打工。電影史論教學、創作理論教學和大師研究,不僅是知識傳授和基礎課程,而且是電影理想教育和電影人生建設。電影學院能夠一代又一代地輸送出與時俱進的導演及各門類主創人才,在強調實踐性、動手能力強的訓練前提之下,較為扎實的電影文化和創作理論教學,是一個始終十分受到重視的環節。不但教材要隨著社會現實和時代演變而更新,教師隊伍和教師本身也必須隨著社會觀念、社會狀況的演進而更新。
第四,專業設置和教材更新的與時俱進。20世紀90年代以來直至2012年的當下,隨著世界電影工業的發展,數字化技術迅速普及和不斷革新、類型電影創新趨勢日益明顯,促進和推動著電影教育領域的改革和創新。首先,體現為專業設置的拓展和更新。例如,2011年1月,美國柯達公司宣布破產。這在整個世界電影工業史上,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它標志著用膠片生產電影的歷史的終結,也意味著建立在膠片技術基礎上的種種生產程序和藝術處理特點的改觀。因此,以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為例,傳統的課程設置,就相應地進行了調整和改變。電影膠片課及其相聯系的曝光技術課,歷來是電影攝影入門的基礎課程,立刻讓位于數字化技術為主的感光元器件課。核心技術基礎課的改變,同時也導致任課教師的替換和課程、器材使用的改變。多年來的膠片曝光及照明技術課都產生了新的內容更替,視聽數字影像技術的教授和實踐,成為了新的攝錄方法的學習,并且導致了專業設計和技術、藝術內容訓練的改觀。除此而外,新媒體技術的運用,特效設計與特效制作的課程的建立,也深刻地影響到電影美術系課程和專業方向的拓展和新建。這都說明,傳統電影技術傳統的改觀和各門類新技術拓展的現實,深刻地促動和重構著電影教學的內容與形式的重構,意味著電影新生產力的革命性變化,與創作型電影人才的培養,是相輔相成互為依存的。
第五,加強交流、積極互動,共同探索創作型電影人才培養的中國經驗。我國高等電影院校中,無論單科型電影學院,還是綜合性大學中的電影院系,都在積極地進行著創作型電影人才的培養,優秀的青年創作者不斷地從南北各地院校中涌現,有的青年影視才俊經過短期培訓,或者自學成才,在電影、電視劇組里摸爬滾打,從實際的創作鍛煉中脫穎而出,成為獨特的影視創作者,奉獻了出人意料、生氣勃勃的電影作品。這說明,影像時代的成才道路是多種多樣的,來自生活的創造性發現,始終是一切藝術也包括影視藝術真正生命力之所在。在中國電影年產量如此快速增長的當下,人才的涌現、人才的不同成長道路是一個特別令人振奮的現實。
但是,培養創作型人才的高等專業學校,畢竟是造就各專業電影人才的主要基地和系統化教育的機構。在我國存在這么多的專業化電影院校、系科的現狀下,就創作型人才的培養方式和教學特點上展開積極的學術交流和經驗介紹,互相學習、借鑒和觀摩,顯然是有益的舉措。更進一步,還可以在全國互動的情況下,漸漸形成各有重點、突出強項、各校既配套齊全,又形成本學院在全國范圍內比較突出的重點科系,在某一專業的教學建設、教學方法上形成獨特的優勢;在全國布局上,呈現各有秋千、各有強項的學術藍圖,對節約教育資源,造成合理競爭,形成有序中的多元化電影教育系統,是有積極的促進作用的。
創作型電影人才和電影新生產力的建構
電影藝術是一門工業化的藝術。電影工業的不斷革新和發展,與電影生產力的更新,形成密切相關、血肉交融的關系。電影生產力的更新,由外部條件的變化和內部因素的變化兩個方面來決定。外部條件指的是社會制度、社會政治、經濟環境和意識形態的變革;內部因素指的是電影技術、電影工業體制發生革命性變化,也會促使電影生產力更新。而世界電影史和中國電影史的演進,生動地證明了電影新生產力的發生、成長和發展,與上述的外部和內部條件演變的密切關系。以中國電影史為例來說明電影新生產力的發生與成長,是很鮮明有力的。1949年新中國建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文化事業各領域發生了重大變化。解放前,上海作為中國電影主要基地,形成了雄厚的電影工業基礎和編導、演員及各專業部門的完整系統,是20世紀30—40年代中國電影生產力最集中、最強大的所在。然而新政權的成立,要求更新和重構符合新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新的電影生產力。
“長影”、“北影”、“八一”迅速崛起,構成了在布局上、性質上、藝術特點上面貌一新的電影生產力。上海電影制片廠也在經受了《武訓傳》、《關連長》、《我們夫婦之間》的烈火錘煉之后,產生了《南征北戰》、《渡江偵察記》這樣的標志著工農兵美學,展現革命烽火,樹立革命英雄的社會主義電影新生產力。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拉開序幕,廣大觀眾呼喚電影新生產力的誕生和電影新作品的展現。當時,一批反映“”悲劇和撫慰創傷心靈的傷痕電影,曾經產生過巨大的影響,老一輩的電影工作者,渴望一切回到20世紀50—60年代的現實主義話語,覺得這就是電影工業上撥亂反正的最理想狀態。然而,第五代電影破門而出。繼而,娛樂片的初潮悄然而來,無論從歷史觀點、電影形式、消費心理上,都呈現出與50—60年代傳統現實主義另辟蹊徑,重敘新篇的動力。從一個方面說明,社會改革、社會跨進的形勢,呼喚電影新生產力的萌發、成長和形成,已是不容回避也無法阻擋的現實。
當下,中國電影進入了21世紀第二個十年。《失戀33天》和《畫皮2》傳遞給我們一個清晰的信息:中國電影新生產力的萌芽已經破土,觀眾呼喚電影新生產力的成長和壯大。面對90后已經成為電影消費的主要人群,即將迎來新世紀以來出生的更新一代的青、少年觀眾,他們作為在電視機和電腦和游戲機面前長大的一代,作為在網上二次消費、微博互動的一代,對于電影觀賞的要求、接受心理的變化,必然成為呼喚電影新生產力成長的社會呼聲和有力推動。
第一,社會呼喚新的電影關注現實、觸及現實、人性關懷,反映人的生存狀態、生命價值、自由發展和人格尊嚴。《失戀33天》、《海洋天堂》、《萬箭穿心》、《邊境風云》、《二次曝光》、《云上的太陽》等等新作品,都從不同角度展示了上述的人性主題和人文精神。生命關懷和個人情感在這些電影中得到了細致的撫慰式敘述和個人化的表達,電影開始走上對人生狀態和個人命運極富關懷、極其尊重的階段。隨著十八大春風吹拂中國大地,關懷人民生活的改善,深入到每個平凡心靈,微觀化、個性化的藝術表現主題和電影形式必將繼續延伸,銀幕上下成為對于人的精神世界和內心體驗越來越豐富多樣的表現。電影新生產力的表現,首先就會在這個社會性命題上得到明確的、充分的展示。
第二,類型電影的拓展和藝術水平的提升,是電影新生產力的表現。電影市場的不斷成熟、電影消費的多元化需求和外國電影占領中國市場份額的不斷擴大,都催促著中國電影產品必須不斷提高優質化水平和增強市場競爭力。而類型電影種類的拓展、類型電影特點和規律的掌握,成為新生產力主要突破和提高的關鍵任務。不錯,近年來中國內地在這一方面有長足的進步,寧浩、張一白、徐靜蕾、烏爾善各位導演在不同類型上都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然而,與美國類型片,特別是科幻片和香港類型片的暢行無阻相比,我國內地在類型短缺、敘事創新、明星效應等方面,顯然有待大踏步拓展和多元化創新的努力。電影新生產力的建構離不開這方面的重點加強。
第三,數字化和電影新技術的建設和創新,是一個重要加強的領域。《畫皮2》的突破性效應,不但是票房紀錄的一次成功標志,更重要的是數字化技術與魔幻題材在工業運作、拍攝實施、團隊建設和創意實現這一生產運作體系上的一次成功實踐,在現代電影工業化操作上,如何以點帶面,不斷擴大此種生產經驗,不斷拓展不同題材和不同的電影創作團隊的建設,顯然是事關新生產力構置和不斷培養、不斷輸送各專業相關人才的重要課題。
第四,隨著中國電影面對世界市場,拓展軟實力影響,傳送中國和平崛起。國際主張的形勢需要,中國電影關注世界形勢,構思和創作有關的國際題材,表現人類主題,促進國際和諧關系的電影作品,必將受到充分重視和付諸實施。在中國經濟已經名列全球第二,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介入世界政治事務和成為促進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的當下,中國電影在關注和生產表現人類主題、反映國際關系方面的電影作品是遠遠不夠的。不論從投送中國影響力或是從世界電影市場上收取經濟利益方面來看,這都是不容回避的創作任務。中國電影新生產力的建構,離不開新型的創作型電影人才群體的培養,這個迫切的電影文化建設的任務,明確地擺在我們面前。我們需要不斷探索、交流互動、更新觀念,為了更好地實現這一任務而踏實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