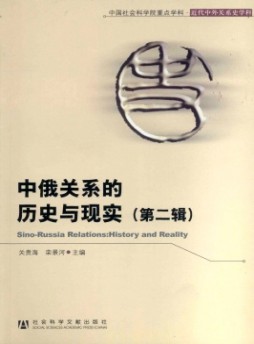現實題材論文:論青年導演現實題材革新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現實題材論文:論青年導演現實題材革新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作者:任小鵬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一與第六代導演的現實題材作品相比,當下青年導演們的現實題材影片沒有第六代早期作品中的青春叛逆與先鋒氣質,沒有他們對現實“原生態”式客觀記錄的美學追求,也沒有他們轉入“地上”之后所延續的客觀、冷峻風格。當下青年導演的現實題材影片,一開始便將鏡頭對準當下社會的普通人,以或荒誕、或戲劇化、或超現實的情節敘述,展現他們的生存困境與精神困境,講述他們的青春夢想與現實際遇。雖然,同樣關注的是當下現實社會底層的人,但與第六代導演作品客觀記錄社會“邊緣”人物相比,青年導演現實題材影片的情節所體現出的后現代式的獨特氛圍,能夠獲得更多觀眾的認可,特別是《鋼的琴》、《Hello!樹先生》等影片,能夠贏得更多80后、90后觀眾的共鳴。沒有經歷第五代少年時期插隊的人生磨難,沒有遭遇第六代改革開放初期內心的躁動不安,成長在新時期較為優越物質條件下的青年導演,他們少年時期的成長經歷培養出了他們不同于前輩的玩世不恭的“痞氣”與天真浪漫的“傻氣”。這種“痞氣”與“傻氣”在他們的作品中,體現為一種當夢想遭遇現實時而“不擇手段的”一種荒誕性。這種荒誕因源于對夢想的執著而令人折服,因忠實于對現實的復原而讓人感到沉重,從而產生了“笑中含淚”的喜劇效果,這是這些影片贏得當下年輕觀眾喜歡的主要原因,如標志著張猛個人風格形成的影片《鋼的琴》。
影片《鋼的琴》講述了一個為了生計而四處奔波的父親,為了爭得對女兒的撫養權,在買鋼琴無望、偷鋼琴無果的無奈之下,選擇發動親戚朋友造鋼琴的故事。影片以大段的灰暗色彩與老膠片式的泛黃色彩,整體營造出了現實的黯淡氛圍,卻又在時而憂傷,時而懷舊,時而歡快的音樂中調侃著這種黯淡。對于生活在當下的像陳桂林和他的朋友這樣的一群人,時代已經將他們拋向了社會的邊緣,他們就像影片中貫穿始終出現的那兩根煙囪,屬于已經逝去的那個年代。就如同賈樟柯電影《二十四城記》中所講述的那樣,對于420廠的員工而言,昔日的青春年華,昔日的成就與榮耀,早已被裹挾在社會變遷的滾滾潮流中,一去不復返。然而,該片與《二十四城記》的不同之處,也是該片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影片并未像《二十四城記》那樣,僅僅停留在對現實的復原上,而是以積極的態度,用具有荒誕氣息的故事情節調侃著這種現實。影片中像陳桂林這樣的一群掙扎在社會底層的人,面對殘酷的現狀,并沒有因為自身的社會身份的邊緣化而悲觀絕望、隨波逐流,而是選擇了積極樂觀地與生活、與命運抗爭。如片中“汪工”在職工的動員會上所說的,煙囪對于他們而言,“就像是一個被我遺忘了許久的老朋友,當有一天聽說他要走的時候,我才意識到,原來他一直就在我的身邊。……,時光荏苒,社會變革,如今為了時展的進程要求他離開,我們總要試著做點什么。”因而,片中出現了在缺工少料的情況下,陳桂林依舊發動親戚朋友造一架鋼琴這樣富有荒誕意味與戲劇性的情節。盡管影片的結尾父親陳桂林克服了種種困難,最終造出了一架鋼的琴,卻還是以失去女兒的撫養權而告終,就像眾人的聯名請愿也未能阻止煙囪被爆破拆除一樣。影片結尾處這種讓理想最終回歸現實,讓夢想破碎在現實面前的處理手法,意味深長。可以看出,青年導演們的現實題材電影中所追求的現實,已不再是完全客觀再現的現實,而是揭開現實外表之后的更深層面的真實。側重于展現當下社會底層人生活的艱辛與無奈的《鋼的琴》如此,探尋當下社會底層人精神困境的《Hel-lo!樹先生》同樣如此。
影片《Hello!樹先生》中的“樹”是東北小縣城里的一個汽車修理工,因為一次工作意外燒傷了眼睛而被辭退,從此,無所適從的“樹”走上了非正常人的生活軌道。失業后的“樹”開始在村里晃蕩,他時而上了村里的面包車,時而上了朋友的摩托車,時而上了同學的小車,企圖尋找點事做來打發無聊的時間。這種看似無所事事、游手好閑的生活,折射出的是在現實壓抑下的“樹”難以走出的精神困境。影片中的“樹”多次出現幻覺,看到夜幕中父親圍著火堆徘徊,看到父親失手殺死哥哥,看到哥哥帶著女友回來參加自己的婚禮,種種幻覺的出現正是“樹”精神孤獨的一種心理呈現。他在不斷地從朋友那里尋找工作的機會,從女朋友那里尋求一種情感的寄托,希望通過生活的忙碌來擺脫精神的壓抑與孤獨。片中的“樹”精神世界的壓抑,一部分源自于現實生活的困境,另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則源自于生存壓迫所形成的無形壓力。片中的“二豬”通過自己與姐夫村長的關系開礦辦廠,通過侵吞公有礦產資源而中飽私囊。盛氣凌人的他橫行霸道,甚至在不告知對方的情況下,以掠奪的方式占有了“樹”家里的田地。在母親的責難下,弱小的“樹”在朋友的婚禮上,企圖借酒后來表達自己對此事的不滿,卻不料惹來更多的欺辱,以至于跪倒在“二豬”面前,尊嚴盡失。對于“樹”而言,潛意識當中這種因生存壓迫而產生的無形的精神壓力,對其構成了不小的打擊。現實生活的壓抑與黯淡,使得他倍感孤獨與絕望,就如同他無意中所說出的那樣:“活著沒意思”。
承受著精神孤獨與壓抑的“樹”,在自認為比自己略低一頭的兄弟“三兒”面前因婚車的事發泄不滿,卻遭到“三兒”更為猛烈的反抗,在這樣的身心雙重打擊下,“樹”變成了半瘋癲的狀態。影片以此為界點,由前半段現實與幻想的呈現,轉向了后半段現實與超現實的交叉敘述。影片《Hello!樹先生》是近年來國產電影中,少有的探尋當下人真實精神狀態的影片,正如德國電影人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曾指出的那樣:“與其說電影反映顯見的信條,不如說它反映的是心理習性(psychologicaldispositions)———那些多少會向意識維度延伸的處于集體心理深層次的東西。”[1]從該片中的“樹”先生的身上,我們看到了我們自己的影子。影片中的“樹”是時代的縮影,是當下中國社會底層人的縮影。在當下社會日益走向權貴資本主義的現實面前,掙扎在社會底層的人,又何嘗沒有面對像“樹”一樣的精神困境呢?盡管該片存在著敘事層面的一些問題,特別是影片后半段超現實敘事的部分,讓很多人開始感到迷惑,不清楚作者想要表達什么,但這無礙于它在探尋當下人們真實精神狀態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積極意義。
二在當下青年導演的現實題材影片中,對于作品表現形式的革新,是這些影片贏得市場的重要原因。這些作品大都舍棄了現實題材影片所慣用的以客觀視點客觀記錄現實的手法,也舍棄了用固定長鏡頭與景深鏡頭來營造真實感的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主、客觀視點的自由切換,以及大量的運動鏡頭與歌舞片段所形成的愉悅視聽感受。伴隨著中國社會的迅猛變遷,處于當下消費型社會語境中的電影觀眾,在進口大片與國產大片的視聽刺激中,早已習慣了視聽奇觀與視聽快感所帶來的觀影體驗,形成了既定的一種審美期待。正如美國學者尼爾•波茲曼所說的,“這是一個娛樂之城,在這里,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2]。因此,堅守長鏡頭理論來創作現實題材作品的方法,對于當下票房占據著主導地位的中國電影市場而言是不明智的,盡管它是最能體現著電影本性的方式。2006年贏得“金熊獎”的《三峽好人》,在票房上卻輸給《滿城盡帶黃金甲》便是最好的例證。青年導演們顯然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于是一開始他們便將自己的現實題材作品呈現在一種輕松、愉悅的視聽氛圍中,用簡潔的電影語言來講述略顯沉重的主題,并將大段的歌舞穿插其中,如影片《鋼的琴》。
影片《鋼的琴》的成功,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應當歸屬于其形式上的成功。影片在鏡頭語言上與聲音語言上的大膽革新,使得這一現實題材影片形成了幽默而不失深刻、輕松而不失莊重的風格特點。具體而言,首先,影片在鏡頭語言上將大量運動長鏡頭穿插在固定鏡頭之間,從而有效地形成了視覺上的流暢與動感,避免了固定長鏡頭可能造成的視覺疲勞。其次,在聲音語言上,影片將富有動感的搖滾音樂,具有憂傷、懷舊氣息的前蘇聯歌曲,上世紀80~90年代紅極一時的通俗歌曲,以及經典游戲音樂等等貫穿在影片的敘事過程中。并且將這些音樂各自不同的情緒特點與片中不同情節片段里人物不同的情緒特點,或結合、或對立起來,從而形成了影片時而懷舊、憂傷,時而幽默、搞笑的特點。這是影片《鋼的琴》作為一部現實題材影片,能夠贏得眾多市場觀眾認可與好評的重要原因。
此外,肖央導演的短片《老男孩》也具有相似的特點。該片流暢的鏡頭語言與大段的背景音樂、歌舞場面的呈現,也很好地克服了現實題材影片本身在形式上缺乏吸引力的不足。作為一部只有43分鐘的短片,《老男孩》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爆紅網絡,確實不容忽視。反觀影片內容,其實,講述的是一個略顯平淡的青春故事。但是,影片之所以能夠贏得網友如潮的好評,除了片中著重渲染的、能引起青年觀眾共鳴的“80’后記憶”,與感情充沛、傾述性強的主題歌曲之外,影片靈活多變的鏡頭語言與多次出現的歌舞場面,也是影片感染力、吸引力的重要來源。對于身處于當下狂歡時代的電影觀眾而言,電視、網絡等多種媒體對人們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的長期浸染,養成了人們碎片化的思維習慣,微電影、微博等“微”現象的盛行就是最好的例證,而這也是人們浮躁心態的根源所在。因此,人們不再愿意花錢去影院觀看一部形式上呆板、凝滯,情節上枯燥、乏味的影片,而《老男孩》中簡潔的鏡頭、靈活的拍攝角度與近乎惡搞式的歌舞場面,就很好地解決了現實題材作品所經常遇到的這一問題。雖然,片中通過出租車內的廣播來標志時代特征、渲染時代環境,通過現實與回憶的不斷穿插來敘述不同時空故事的方法,還略顯生硬與稚嫩,但作為時下頗受好評的青年導演,其不斷走向成熟的個人風格也是讓人充滿期待。
當下青年導演以符合觀眾審美趣味的表現手法,來創作現實題材作品,無疑是對該題材作品創作領域的一種大膽開拓。這種開拓對于處于產業化語境下的中國電影而言,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就像當年寧浩導演的《瘋狂的石頭》激起的熱潮一樣,形式上的革新所帶來的是一種類型的革命。電影只有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中,不斷地更新自己以保持與時代的同步,才能不被時代的潮流所掩埋。
誠然,當下青年導演步入影壇時間不久,處于早期摸索階段,這就決定了其電影創作無可避免地面臨著諸多問題。因此,過早地總結其創作特點將面臨著較大的風險,畢竟他們作品風格的成熟還需要經歷時間與市場的檢驗。但是,就目前他們作品中所體現出來的這種內容與形式上的革新精神,對于產業化語境下中國現實題材電影的發展而言,無疑具有積極的啟示意義。因而,我們有理由堅信,只要這些青年導演能夠在當下風云激蕩的中國影壇不迷失方向,只要我們的觀眾能夠對他們有持之以恒的關注與包容,他們的騰飛將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