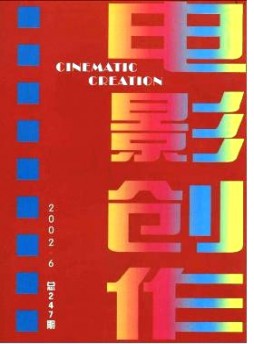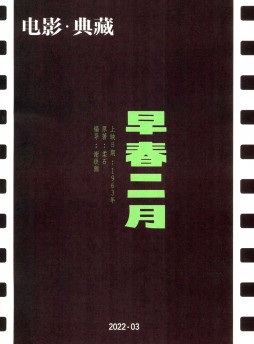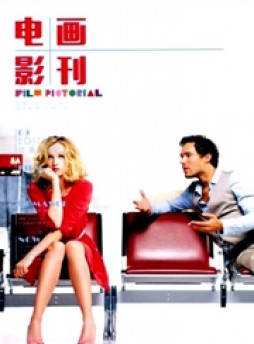電影攝像技師勞動者性質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電影攝像技師勞動者性質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內容提要:本文通過對日本電影攝像技師事件的介紹分析,對承包合同與勞動合同進行了甄別和判斷,對電影攝像技師的勞動者性質和法律地位進行了探討,提出了隨著文學、藝術、影視等特殊領域就業形態的多樣化,及時準確地界定和判斷其勞動者的性質,提供相應的勞動保護的法律課題。
一審:東京地方裁判所2001年1月25日判決,載《勞動判例》第802號第12頁(2001年6月15日)
二審:東京高等裁判所2002年7月11日判決,載《勞動判例》第832號第13頁(2002年11月1日)
一、本案精粹:
簽訂承包合同的承包者,在承包期間因病死亡,能否以勞動者的身份適用于勞動法規,從而獲得勞動者災害補償?本案告訴我們,無論當事人之間簽訂的合同形式如何,都要依據事實上是否存在使用從屬關系等要素來綜合判斷勞動者的性質。
一般來說,電影的拍攝制作是在導演的指揮監督下進行的,攝像師有服從導演指示的義務,雖然該工作的特殊性決定了攝像師要有相當的專業技術和對藝術的理解、表現方式,但不能以這種“自由”的藝術發揮來否定指揮監督關系的存在。本案也是一樣,本案攝像師雖然與電影公司簽訂的是承包合同,但是攝像師的報酬以勞務提供的期限為基準計算支付,每項工作的諾否的自由受到制限,勞務提供的代替性不予存在、攝像器材基本上由電影公司提供,電影公司將攝像師的報酬作為計算勞動災害保險費的基數,等等。從這些因素加以綜合判斷,攝像師是在與電影公司的使用從屬關系下提供勞務的,因此屬于勞動者概念的范疇,受勞動者災害保險法的保護。論文百事通本案歷經16年,終以勞動者側勝訴結案。
隨著文學、藝術、影視等特殊領域就業形態的多樣化,如何及時準確地界定和判斷勞動者的身份成為十分復雜的課題,因此本案判決對今后實務的影響值得關注。
二、案件回放:
本案電影攝像師(1926年8月出生,當時59歲),是日本著名的獨立職業者,曾拍攝過多部電影電視片并多次獲獎,[1]1985年出任日本電影技術獎審查委員,1986年出任日本電視技術協會紀錄片部門審查委員。
本案電影公司欲拍攝一部反映日本東北部文化的影片,導演(兼編劇)與攝像師是故友,對其攝像技術極為賞識,且該攝像師也是出生于日本東北部,有那里的生活經歷和文化熏陶,便極力向社長推薦由其出任該片攝像師,社長表示同意。社長在與該攝像師商談時說,作為本公司的攝像師每天的報酬是2.3萬日元,本片預計拍攝50天計115萬日元,考慮到拍攝前后要來公司處理一些事情,故加算5萬日元,合計120萬日元。另外該電影公司員工每月25日支付工資,本案攝像師提出希望月末支付或者外景拍攝完畢后支付,社長表示同意。由于拍攝實際期間一般要比預定時間長,提前結束的情況幾乎沒有,雙方遂商定即使拍攝時間有所變化,報酬也不改變。就此雙方簽訂了從1985年10月至1986年5月間,該攝像師隨劇組在日本東北部地區拍攝,預定分三個階段共進行50天,電影公司在月末或外景拍攝后向該攝像師支付120萬日元報酬的承包攝像合同。
該攝像師在拍攝期間,曾在日本東北部嚴寒的寺院里連續9天長時間拍攝,有時徹夜拍攝,有時在雪中拍攝,工作環境十分艱苦。1986年2月19日早晨該攝像師在下榻的旅館跌倒,被送往醫院,23日因腦血栓病亡。
由于攝像工作已經完成了三分之二,所以電影公司在已經向該攝像師支付了50萬日元的基礎上,在其死后的1986年3月25日向其遺屬支付了34萬日元,總計支付報酬84萬日元。
本案中,該攝像師還推薦了兩名攝像助手和一名與攝像工作密切相關的照明技師。該攝像師在電影的整個拍攝過程中,只從事攝像工作。根據拍攝的日程安排,沒有拍攝任務時,可以任意從事其它工作,而不必征得電影公司同意。但實際上,該攝像師并沒有充裕的時間同時從事其它電影的拍攝等工作。后來其妻子說,有可能利用2、3天時間為老朋友?缺愫釉?宏的花展攝影。
該電影公司勞動人事管理制度完備,但工作時間、休息時間、休息日、工作守則、勞動紀律等等對本案攝像師都不適用,沒有約束力。
本案攝像師于過去的20年間,在該電影公司工作過5、6次,其報酬一直是按“經營所得稅”來申報,電影公司雖然以文娛人的報酬名義進行所得稅的事先預扣,[2]但在1985年4月至1986年3月期間電影公司在向所轄勞動基準監督局支付該公司的勞動災害保險費時,已經將該攝像師的報酬包含在內作為計算的基數。另外該攝像師加入了東京文化人國民健康保險。
該攝像師死后兩年,其子于1988年2月17日以其父的病故是由該攝像工作直接引起為由,向管轄區的勞動基準監督署長提出依據《勞動者災害保險法》支付經濟補償的請求。1989年8月28日該基準監督署長作出了該攝像師不是《勞動基準法》第九條規定的勞動者,故不予支付經濟補償的決定。
其子于1989年10月請求管轄區勞動者災害補償保險審查官審查,1994年11月24日請求被駁回。
其子又于1995年1月20日向勞動保險審查會提出再審查的請求,1998年6月17日又被駁回。
其子遂向東京地方裁判所提起訴訟。2001年1月25日東京地方裁判所一審判決,其子敗訴。其子不服一審判決結果,上訴東京高等裁判所,2004年7月11日二審判決推翻原判,其子勝訴。當事人均未提出三審上訴,本案歷經16年艱辛曲折終以勞動者側勝訴結案。
三、判決要旨:
本案一審和二審均從以下9個相同的方面(順次不同)對該攝像師是否為勞動者進行了綜合分析判斷。為便于比較,筆者在每個相同判斷基準中將
一、二審的判決意見同時列出。
1、工作上的指揮監督關系
一審判決認為,雖然導演有最終的決定權,但導演與攝像師的職能是業務分工的問題,而不是指揮命令關系。具體來說:
①導演對該攝像師的工作只是給予原則上的把握,而不是事無巨細。
②從追求藝術性的角度來看,導演和該攝像師所處的地位是同等的。
③導演對該攝像師提出的建議予以采納。
二審判決認為,作為電影拍攝來說,攝像師在拍攝過程中,理解和把握導演意圖,基于自己的技術和藝術感悟將攝像具體化,但導演對電影的拍制負有最終的責任。本案也是一樣,關于攝制方法等方面的問題都是在導演的指示下進行,對該攝像師拍攝膠片中的鏡頭的選取和編輯也都由導演最終確定。無論該攝像師技術有多高,工作的獨立性有多強,都不能脫離導演的指導監督而無限制的自由發揮,該攝像師基于導演的意圖進行拍攝,發揮藝術才能,雖然不是顯在的具體的直接的指揮命令,但不能以此否定指揮命令的性質。本案電影拍攝的最終決定權由導演掌握,與該攝像師之間存在指揮監督關系。
2、報酬的性質和數量
一審認為,本件報酬是完成該部電影的攝像任務支付120萬日元,攝像日數有所變化報酬也不變,可見該報酬不是與勞務提供的一定的時間相等價,而是與作品的完成相等價的,因此是承包性質的報酬。
二審認為,雖然是完成該部電影的攝像支付120萬元,但這是以預定拍攝日數等為基準算定的數額,與其攝像助手等的報酬形式沒有本質差異。另外該攝像師合計工作了33天,電影公司雖然以完成了一部的三分之二為理由支付了84萬日元,但33天也恰好相當于當初預定拍攝日期50天的三分之二。所以也是考慮到了與勞動時間等價的因素的。因此與承包性質報酬相比,更具有工資的性質。
3、對委托的工作的諾否的自由
一審承認,合同簽訂后,該攝像師按拍攝日程表工作,而且要理解把握導演的意圖將影像具體化,因此對每項具體工作加以拒絕的自由是受到制限的。但同時又強調指出這種制限是由電影制作的特殊性決定的,而不能認為是由使用者的指揮命令所造成的。比如按照日程安排去拍攝寺院的廟會,地點和時間事實上都是確定好了的,沒有選擇和拒絕的自由。而且在這種情況下攝像、錄音、演出等獨立部門必須合作進行,該攝像師作為工作人員之一也必須按預定日程表統一行動,以提高外景拍攝的效率。此外,把握導演意圖將影像具體化是攝像師本來的職責和應該發揮的作用。所以該攝像師所受到的限制與指揮命令沒有直接關系。
二審認為,一旦簽訂了合同,該攝像師就必須在電影公司指示下按照日程表工作。作為攝像師必須依導演的意圖將攝像具體化,所以該攝像師對每項具體的工作的諾否的自由受到制限。至于一審提到的“電影制作的特殊性質”,應該認為使用者的指揮命令更多的是通過工作內容來實現的,該工作內容已經包含了工作的“一般性質”和“特殊性質”。而且一般來說,使用方對委托的個別工作的諾否自由加以制限是共通現象,并不是電影制作行業所特有的。
4、時間的、場所的制限性
一審承認本案攝像師的工作是按照預定的日程表進行的團體活動。工作場所(包括外景拍攝地)都是被指定的,所以存在很強的制限性。但是一審仍然堅持認為這種制限性發生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還是由于“電影攝制的特殊性質”導致的必要的指揮命令所造成的,因而很難說是直接造成的制限。
二審同意一審關于“有很強的制限性”的認識。但否認一審強調的“電影拍制的特殊性質”是造成制限原因的結論。認為時間、場所的制限對電影拍制的使用者來說必不可少。
5、勞務提供的代替性的有無
一審認為,本案攝像師向電影公司推薦了兩名攝像助手和一名照明師,鑒于該攝像師的聲譽,電影公司尊重了他的推薦意見(以前拒絕其他人的推薦的情況是存在的)。助手們在該攝像師指導下一同工作,但在業務上不能代替該攝像師。
二審認為,導演因為賞識該攝像師的技術才向電影公司推薦,促成了該攝像師與電影公司簽約。其后該攝像師又推薦了攝像助手,所以他的工作有不可代替性,但這正是肯定指揮監督關系存在的一個要素。
6、機械、器具的負擔關系
一審認為,該攝像師使用的器材,除了一次在寺院里使用的是自己的攝像機以外,其它全部由電影公司提供,由此可見該攝像師符合作為“勞動者”的這一要素。
二審同意一審對此問題的事實認證和結論。
7、專屬性的程度
一審認為,在這20年之間,該攝像師在該電影公司只從事了5、6次攝像工作,在本案的電影攝像中,有同時從事其它工作的自由,雖然這在事實上存在困難,但該攝像師仍打算利用2、3天時間為老友?缺愫釉?宏拍攝花展。另外從該攝像師的工作經歷來看,為?缺愫釉?宏拍攝的工作很多,最多的一年從中獲得了600萬日元的收入,所以該攝像師在經濟上不必依靠本案電影公司,其專屬性的程度很低。
二審認為,該攝像師在經濟上不必依靠本案電影公司,這被一審認為是“專屬性的程度很低”,但是,如果對照被承認的指揮監督關系,雖然專屬程度低,但對判斷該攝像師是否是“勞動者”并沒有直接的過多的影響。
8、勞動管理規則的適用
一審認為,本案攝像師與電影公司員工的工作時間、休息時間、報酬形式和報酬支付時間等不同,因此不適用于本案電影公司的勞動管理規則。
二審認為,雖然不適用于勞動管理規則,但由于本案事實上存在指揮監督關系,所以不適用于管理規則這一要素對是否是“勞動者”的判斷沒有大的影響。是電影公司的員工也好,不是電影公司的員工也好,在電影拍攝期間,劇組有關工作人員不適用于管理規則幾成慣例。對于本案攝像師來說,不能把他不適用于該電影公司的管理規則一定看成是否定他為“勞動者”的要素。
9、稅金的負擔關系
一審認為,本案攝像師的報酬被作為文娛者報酬進行預先扣稅,所得稅按經營所得進行申報,雖然僅以報酬的所得稅申報形式來否定使用從屬關系的存在是不恰當的,但是上述稅金的負擔關系的確與該攝像師的報酬形態相吻合。另外雖然該電影公司從1985年4月至1986年3月將該攝像師的收入包含在勞動者災害保險費的計算基數內,這是對該攝影師是“勞動者”的肯定要素。但是這只不過是該電影公司的判斷,不能將其作為該攝像師是否為勞動者的判斷依據,因此不能以此直接判斷該攝像師為“勞動者”。
二審認為,本案攝像師的報酬被作為文娛者報酬進行預先扣稅,所得稅按經營所得進行申報,但僅以報酬的所得稅形式來否定使用從屬關系的存在是不恰當的,而且作為經營所得進行申報與其他被承認為“勞動者”的攝影助手基本上是一樣的,所以不能以所得稅的申告形式來否定該攝像師為“勞動者”。
另外,該電影公司的勞動者災害保險費的計算基數包含了該攝像師的收入,這正如一審判決所說的那樣,是對該攝像師為“勞動者”的肯定要素,至于一審判決認為這不能作為判斷該攝像師“勞動者”的依據,但事實上不能否定它已經成為判斷該攝像師之所以為“勞動者”的要素之一。
從以上9個方面綜合分析和判斷,一審、二審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
一審判決認為,本案攝像師的業務,存在對每項工作的諾否的自由的制限,也存在工作時間、工作場所的很強的制限,但這只是反映了使用從屬關系的表象,電影的拍攝制作,其報酬可以看成是承包工作的報酬,所得稅申報也是按經營所得稅的名目申報,電影公司也以文娛人的報酬為名事先扣除所得稅款,另外本案攝像師對電影公司來說專屬程度很低,也不適用于電影公司的勞動管理制度。
從以上要素綜合分析的結果,該攝像師從事的電影攝像工作是在考慮到工作的風險性并自己計劃承擔其風險的以勞動成果為目的的承包勞動,而不是在使用從屬關系下向使用者提供的勞動,所以不是《勞動基準法》第九條規定的“勞動者”,[3]因此也就不能成為《勞動者災害保險法》上的“勞動者”。
二審判決則認為,本案攝像師與本案電影公司的專屬性低,不適用于電影公司的勞動管理規則,報酬的所得按照經營所得申報,電影公司以文娛人的名目預先扣除稅款等等,這些影響使用從屬關系存在的因素是不可否認的。但另一方面,電影拍制是在導演的指揮監督下進行,攝像師有服從導演指揮的義務。本案也是一樣,被譽為具有高度技術和藝術表現力的本案攝像師也不例外。此外,報酬是按提供勞動的期間算定,對每個具體工作的諾否的自由存在制限,勞動時間、場所的約束性強,勞務提供的代替性不予存在,攝像器材基本上由電影公司提供,電影公司將該攝像師的報酬作為勞動者災害保險費的計算基數,等等。對這些因素綜合分析,該攝像師是在與使用者存在從屬關系的條件下提供的勞務,相當于《勞動基準法》第九條規定的“勞動者”,也相當于《勞動者災害保險法》上的“勞動者”。
四、思考與課題:
1、本案意義
如今的日本電影產業被稱為“夕陽產業”,各種娛樂形式的豐富和手段的更新,以及外國優秀影片的沖擊,給日本電影界帶來了極大的生存危機。為了降低成本,各電影公司盡可能地采用承包等靈活的方式雇傭員工。這也符合電影拍制的特殊性質。因為一部電影從策劃立項到播出放映,要經過較長的周期,而拍制的不同階段又只需要不同性質和類型的勞動者。拿拍攝階段來說,導演、攝像、美術、照明、演員等缺一不可,需要共同合作完成。而到了后期制作階段,則又換了另一批人馬,拍攝階段的許多人可能等待很長的周期才有機會拍攝下一部電影,這樣就造成了人員的閑置,一個方面使他們的專業能力難以保持和提高,甚至出現下降,另一方面增加了電影公司的費用支出。正因為如此,特別是對專業技術較強的崗位,電影公司越來越希望使用承包等靈活的用工形式,既可以保證電影拍制工作的高效率、高質量的完成,又實現了降低成本、節約費用支出的目的。
另一方面,電影拍制工作又是十分艱苦和存在一定危險性的工作。特別是當勞務提供者發生安全事故時,其是否享受勞動法保護的問題便提上日程。
本案歷經16載,其審理過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伴隨非典型雇傭的迅速發展,理論認識的不斷深入和對非典型勞動者保護意識的不斷增強,相信本案判決對影視行業的相關實務會帶來一定影響。
2、對使用從屬關系的再認識
對本案的二審判決,筆者認為還是有值得商榷之處的。
勞務提供者是否是“勞動者”,其中最重要的判斷要素就是與使用者是否存在指揮監督命令的從屬關系。本案導演之所以推薦本案攝像師,是因為賞識該攝像師的才能,是期待該攝像師發揮自己的藝術創造力而不是為了服從自己的指揮命令而去機械地拍攝。這種強烈的藝術要素的確有別于其它行業的勞動。這種創造性的藝術勞動,不是對導演意圖的機械表現和還原,而是基于這種意圖的再創造和藝術升華。有人認為這是“先行的抽象判斷”[4],其實最先行的是導演的“意圖”,“意圖”本身就是抽象的,攝像師就是通過膠片把這種抽象藝術地記錄為現實,而這一過程也同時是啟迪、豐富、修正導演“意圖”的過程。新晨
導演當然有最終決定權,但該權利的行使不僅僅是對某一個具體環節,而且是對該部影片的整體性進行的,比如為形成一個統一的風格,適當的節奏,基調的旋律,等等。從這樣的角度來認識,對攝像師每個具體問題的指揮監督的使用從屬性就變得相對薄弱了。
另外時間上、場所上的制限也是由該工作的特殊性質決定的,不存在選擇上的余地。就好像一名自由職業的歌手,與使用方即使再沒有使用從屬關系,也必須根據合同約定按規定的時間、地點、曲目和演出順序進行演出,這是基于工作內容和工作性質決定的,而不應該認為一定是由指揮監督關系決定的。
本案
一、二審判決完全是按照1985年12月勞動基準法研究會提出的對“勞動者”判斷的基準[5]進行逐條對照分析的,多少有一些機械的、演繹的推導出結論的感覺。在多樣化、復雜化的雇傭形態下,比機械演繹更重要的是要對照和遵循法的宗旨來對具體問題進行綜合的判斷和對應。
注釋:
[1]其中1962年的《陷井》一片(導演:?缺愫釉?宏)以其大膽新穎的藝術創造給日本電影界帶來很大沖擊。1964年拍攝的《沙女》(導演:?缺愫釉?宏)獲法國夏納國際電影節金獎。
[2]根據日本稅收制度,根據不同職業者的預期收入先行將所得稅扣除。年終時根據一年收入所得和家庭成員、經濟狀況等計算出應納稅總額,對預先扣除的稅款實行多退少補。
[3]《勞動基準法》第九條規定的勞動者是“不同職業的種類,在企業或事務所被使用并且被支付報酬者”。
[4]末倉勉:《職業電影攝像師的過勞死事件—東京高裁認定勞動者性的逆轉判決》,載《青年法學家》NO.379.2002年9月25日。
[5]勞動省勞動基準局編:《勞動基準法的問題點和對策的方向》,1986年日本勞動協會出版發行。
擴展閱讀
- 1電影文化
- 2電影傳播
- 3電影現狀
- 4電影發展戰略電視電影
- 5深究傳統電影以及數碼電影結合
- 6電影海報設計
- 7電影類型思索
- 8電影文化闡釋
- 9英語電影欣賞設計
- 10電影中服裝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