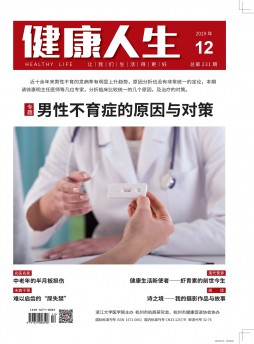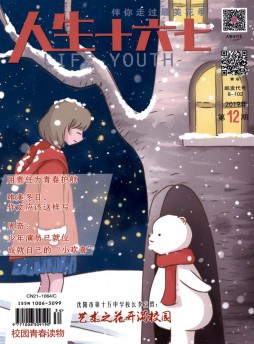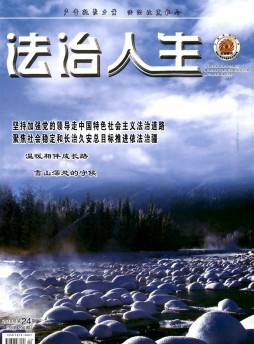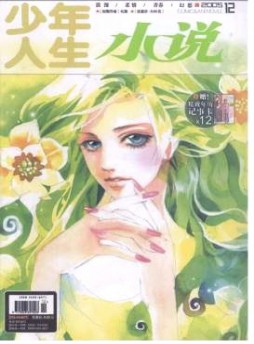茶與皎然的人生情懷分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茶與皎然的人生情懷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引言
(一)人生情懷
每個活著的人都會有他的思想情感、人生追求、審美情趣等,這正是人不同于一般動物的特征所在,也正是人類文明不斷走向發(fā)展的動因所在。人生情懷,就是人的一種心理趨向,包括對人生目標、審美情趣、處世方式、生活方式、生活態(tài)度、人生態(tài)度等的一種混合趨向。人在不同的階段、不同的社會背景下會有不同的人生情懷。人生情懷又反過來影響一個人的生活態(tài)度、生存方式和人生追求等。不同的學(xué)養(yǎng)、不同的人生經(jīng)歷、不同的經(jīng)濟狀況和政治地位等,都會影響人的人生情懷。
(二)禪
禪是佛教中國化的結(jié)果,是佛教的老莊化,也可以說是老莊思想的佛教化。關(guān)于憚,已有很多的研究和很多深入的認識。(1)眾所共識的是:禪本為瑜伽修習(xí)的高級階段,后為佛教吸收,成為佛教禪宗的一種修持方法。禪宗是大乘佛教在中國衍生出的一個宗派,以靜慮和高度冥想作為超度救世的法門。禪是一種生命體驗。“由‘禪’這種生命體驗所達到的禪境,則是一種心靈境界、生命境界與審美境界。禪宗美學(xué)是生命美學(xué),它始終關(guān)注活生生的人的生命活動,探索活生生的人的生命存在方式及其價值。它認為審美體驗活動乃是一種任運自適、去妄存真、圓悟圓覺、圓滿具足的生命活動,一種活生生的人的最高生存方式。”(2)禪宗的特點是:①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見性成佛。②禪宗肯定現(xiàn)實生活的合理性,認為人們的日常活動是人的自然本性的表露,洋溢著禪意,人們要在平平常常的感性生活中去發(fā)現(xiàn)清凈本性,體驗禪境,實現(xiàn)精神超越。③禪宗是繼承道家,又超越道家。(3)禪宗的出現(xiàn),“使中國佛教擺脫了印度佛教的束縛,建立起符合中國文化的特色,吸引并接納中國文人、勞動大眾參與的新型佛教思想體系,使之成為具有中國人文情懷的新興宗教。禪宗的出現(xiàn)與理論上的突破,標志著中國佛教終于完成了由出世到入世、由宗教到現(xiàn)實、由佛國到人間的重大改革,徹底改變了佛教的禪學(xué)觀念和理論導(dǎo)向,……對于推進我國佛教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以適應(yīng)現(xiàn)代社會的科學(xué)發(fā)展,現(xiàn)代人的生活實際和心理狀態(tài),有著積極的意義。”(4)
(三)皎然其人皎然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詩僧,他的著名并不是因為他留下了什么高深的佛學(xué)理論、佛學(xué)著作,而是因為他的佛學(xué)修為、他的詩、他的詩歌理論、他與“茶圣”陸羽的友誼等。關(guān)于皎然的記載,所留下的資料不多,除了他自述生平性質(zhì)的詩《妙喜寺達公禪齋寄李司直公孫房都曹德裕裴從事方舟顏武康士騁四十二韻》之外,還有北宋歐陽修的《新唐書•藝文志》、宋晁公武撰《郡齋讀書志》等的簡單記載:一是他的姓氏、家世:皎然,字清晝,姓謝,湖州人,謝靈運的十世孫,居杼山;二是他與顏真卿的友誼:顏真卿在蘇州為刺史時,曾招集一些文士編撰《韻海境源》,皎然參與其中;三是唐貞元年間集賢院收藏他的文集,曾為湖州刺史的于纃為其文集作序。四是其著作有《詩集》十卷。宋釋贊寧《宋高僧傳•唐湖州杼山皎然傳》對皎然(特別是其入佛門后)有較多一些的事跡記載。元代辛元房的《唐才子傳》、明代董斯張《吳興備志》等對皎然的記載也都不多。所能了解的是:他在年青時曾致力于科舉功名,但科舉落弟,云游四方,博訪名山,曾入道家,中年(35歲左右)時在杭州靈隱寺出家,安史之亂后正式剃度出家,與當(dāng)時湖州、蘇州一帶的名僧齊己、靈澈來往較多,并與當(dāng)時蘇州、湖州等地的官員和文人如顏真卿、袁高、韋應(yīng)物、李冶、陸羽等有很好的交往。從宋代至今,學(xué)者們給予了皎然在詩歌創(chuàng)作、詩歌理論方面較高的評價。當(dāng)代的學(xué)者們對于皎然在中國茶文化方面的貢獻也給予了很高評價,對于皎然最早提出“茶道”一詞,對于皎然對陸羽在茶學(xué)方面貢獻的扶持,都有很高評價。(5)重復(fù)已有的研究沒有多少意義。本文旨在解讀茶在作為詩人與僧人的皎然心中,是怎樣的一種情懷。
二.在茶中求禪、悟禪、享受禪
(一)禪的情懷
天資聰穎、秉性與氣質(zhì)自幼就與眾有所不同的皎然,自幼就有“道”的秉賦,宋代僧人贊寧在《宋高憎傳》中所說:“幼負異才,性與道合,初脫羈絆,漸加削染。”(6)即皎然自幼就有著避離現(xiàn)實世界的情懷。但作為一個受過中國傳統(tǒng)教育塑造的讀書人,并且有著較深厚傳統(tǒng)家學(xué)傳承的讀書人,總是脫離不了追求科舉功名的情懷,“所謂長裾曳地干王侯”,他到京師以詩歌交接公卿大夫們,他的文才得到公卿大夫們的稱贊,《宋高憎傳》中說:“其兼攻并進子史經(jīng)書,各臻其所極,凡所游歷京師則公相敦重。”雖文才超群,但還是科舉落第,他秉性中的“道”性便成了他主要的情懷,他浪跡江湖,求仙問道,戰(zhàn)爭的狼煙使他感悟到佛的世界里將會是一個更好的寄托,于是“安史之亂”后他在杭州靈隱寺正式剃度出家了,從此,他在禪的世界里了度過了他的一生。皎然出家后“禪”的情懷,反映在他所留下的詩與詩歌理論中。從皎然的詩中,我們可以看到:幽壑中孤寂的禪意,山野中極簡單的“野飯”勝過人世間美味的“膏梁”:“卻尋幽壑趣,始與纓級別;野飯敵膏梁,山楹代藻棁。”(7)用禪的情懷去感受的現(xiàn)實世界與凡人感受的現(xiàn)實世界是多么不同!湖州的苕溪草堂所處的環(huán)境,在常人的眼中無非是山青水秀,但在皎然的眼中卻是處處充滿禪意,無論是潔凈的天空,還是平野中的花,還是天空中的白云、山中的石頭、野外的竹子、幽幽月光映照下的石壁、乃至東風(fēng)吹拂下的梧桐與杉樹等:“境凈萬象真,寄目皆有益。原上無情花,山中聽徑石。竹生自蕭散,云性常潔白。……外事非吾道,忘緣倦所歷。中宵費耳目,形靜神不役。色天夜清迥,花漏時滴瀝。東風(fēng)吹杉梧,幽月到石壁。此中一悟心,可與千載敵。”(8)不是心中有禪就不可能有筆下的禪境!即使在回答朋友們的書信中,皎然所展示、所告知的還是那禪境的美妙。在他那著名的《答俞校書冬夜》中他以禪境引相約:“月彩散瑤池,示君禪中境。真思在杳冥,浮念寄形影。遙得四明心,何須蹈岑嶺。詩情聊作用,空性惟寂靜。若許林下期,看君辭簿領(lǐng)。”在《答鄭方回》詩中,同樣告知朋友的是那空明、閑淡的禪境是多么美妙:“是時寒光澈,萬境澄以凈。高秋日月清,中氣天地正。”至于在寺院環(huán)境內(nèi),那更是洋溢著禪的情懷。在《宿法華寺》中寫道:“心與空林共杳冥,孤燈寒竹自熒熒。不知何處小乘禪,一夜風(fēng)來聞?wù)b經(jīng)。”空寂、悠遠、孤寒的禪境中誦經(jīng)的聲音隨夜風(fēng)飄來!皎然享受著這種禪境!在《送清涼上人》中寫道:“何意欲歸山,道高由境勝。花空覺性了,月盡知心證。永夜出禪吟,清猿自相應(yīng)。”花空了、月也盡了、杳渺的夜里,清猿的啼叫伴隨禪吟,對于常人而言那將難于久耐,對于皎然卻是享受!這便是心中有禪,心與境共合于禪!在《陪廬中丞閑游山寺》中同樣描寫了這樣一種孤寂、清幽、遠離現(xiàn)實世界的禪境:“野寺出人境,舍舟登遠峰。林間明見月,萬壑靜聞鐘,擁燭明山翠,交麾云水容。如何股肱守,塵外得相逢。”沒有禪的情懷哪來這充滿禪意的詩句!皎然的詩充滿禪意,表現(xiàn)在他的大多數(shù)詩中,即使是與友人的酬唱之作,也仍然如此。他的詩之所以總是表達禪的意境,正因為他心中有著禪的情懷,他總是在現(xiàn)實世界中去體悟出禪、享受禪!這正是一個禪學(xué)修為高深的的僧人與常人的不同!不僅如此,他還在他的詩歌理論中貫注了禪的情懷。皎然曾著有《詩式》五卷、《詩評》三卷、《詩議》一卷,是中國詩歌理論史上的重要著作,他首次提出了“詩境說”,實際上就是主張詩中要有禪境、要表達與營造禪的意境:秋天里、遠離人跡的竹寺中,“夜靜賞蓮宮,古磬清霜下,寒山曉月中”,從而“詩情緣境發(fā)”,即詩情的產(chǎn)生正是這種禪境!皎然描述了詩境應(yīng)有的狀態(tài):“靜,非如松風(fēng)不動,林纅未鳴,乃謂意中靜。遠,非謂淼淼望水,杳杳看山,乃謂意中之遠。”即要使詩中之境能使人的心達到寧靜、渺遠,這就是詩境!皎然的詩歌理論是以仍然禪的情懷為立論!
(二)茶禪一味
皎然留下了470多首詩,其中有近25首與茶有關(guān),是唐代詩人中寫有較多茶詩的詩人。皎然的茶詩充溢著他禪的情懷,“茶禪一味”反映在他的茶詩中。①茶詩中體悟禪、享受禪。《九日與陸處士羽飲茶》是皎然著名的茶詩,表現(xiàn)了皎然與常人不同的情懷和獨特的審美情趣:常人愛喝酒,不知茶是那么香!實際上,皎然遠不止是表達一種對茶香的享受,而是感受到這種遠離世俗的環(huán)境中品茶的禪意,才覺得茶特別香,他要贊美的不僅是茶香,而是這種環(huán)境中禪的韻味,讓他感到無比的放松與舒坦:“九日山僧院,東籬菊也黃;俗人多泛酒,誰解助茶香?”沒有禪的情懷,哪有這樣充滿禪意的茶詩?《飲茶歌送鄭容》一詩,學(xué)者們都認為反映了皎然深受道家思想影響,詩中所說的“丹丘羽人”、“名藏仙府”、“骨化云宮”、“云山童子”、“金鐺”“香爐”都是道家術(shù)語,不可否認,道家思想對皎然的深刻影響,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禪的情懷深藏于皎然心中,在這樣一首表達道家生活情懷的茶詩中,仍然深藏著禪的情懷:“霜天半月芳草折,爛漫緗花啜又生。”禪的韻味交織在道家境界的追求中!《對陸迅飲天目山茶因寄元居士晟》一詩,皎然直白地談到飲天目山與享受禪有異曲同工之妙:“喜見幽人會,初開野客茶。日成東井葉,露采北山芽。文火香偏勝,寒泉味轉(zhuǎn)嘉。投鐺涌作沫,著碗聚生花。稍與禪經(jīng)近,聊將睡網(wǎng)賒。”煮茶、飲茶便想到了采茶的那種清新之境。《白云上人精舍尋杼山禪師示崔子尚何山道人》一詩,本來是寫聽泉、品茗,但通篇描述的卻是禪境:“望遠涉寒水,懷人在幽境。為高皎皎姿,及愛蒼蒼嶺。果見棲禪子,潺潺灌真頂。積疑一念破,澄息萬緣靜。世事花上塵,慧心空中影。清閑誘我性,遂使煩慮屏。許共林客游,欲從山主請。木棲無名樹,水汲忘機井。持此一日高,未肯謝箕潁。夕霽山態(tài)好,空月生俄頃。識妙聆細泉,悟深滌清茗。此心誰復(fù)得,笑向西林永。”遠離了現(xiàn)實世俗世界,禪的境界、禪的享受是多么雋永!《往丹陽尋陸處士不遇》并不是一首談品茶感受的詩,卻是反映兩茶人間真誠友誼的詩,往往學(xué)者們也歸之為茶詩。這首詩表達的是皎然尋訪好友陸羽未遇的惆悵,但皎然卻是用禪的情懷在描述周圍的環(huán)境,以至于通篇充滿蕭瑟而悠遠的禪意:“叩關(guān)一日不見人,繞屋寒花笑相向。寒花寂寂偏荒阡,柳色蕭蕭愁暮蟬。行人無數(shù)不相識,獨立云陽古驛邊。風(fēng)翅山中思本寺,魚竿村口望歸船。歸船不見見寒煙,離心遠水共悠然。”盡管有著濃濃的惆悵,但意境多么深遠、明凈!沒有禪的情懷,那來這種禪境的描述!茶禪一味在皎然茶詩中。②“茶道”一詞的意蘊。中國的“茶道”一詞,最先由皎然在《飲茶歌誚崔石使君》一詩中提出,這是學(xué)術(shù)界的共識。“茶道”一詞的意蘊倒底為何?皎然沒有闡述,本來皎然也寫有一本詩著作,但已失傳。我們只能從皎然現(xiàn)存的詩文中去領(lǐng)悟。在《飲茶歌誚崔石使君》詩中,皎然描述飲茶所得到的既是道的境界也是禪的境界:“一飲滌昏寐,情思朗爽滿天地。再飲清我神,忽如飛雨灑輕塵。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通過飲茶,他進入到了很愉悅的禪的境界。因而,皎然所說“茶道”便是體悟禪、享受禪之道。這和皎然在他的其他大多數(shù)詩文中所表達的禪的情懷是一致的。茶禪一味,表現(xiàn)在皎然對“茶道”一詞的提出。
三.人間友情純粹如茶
皎然中年出家,成了一名僧人,作為出家之人本該游離于現(xiàn)實俗世之外,但他卻是一個愛交游、酬唱之人,在他的《杼山集》十卷中,皎然所提到的人物大約有300多人,有官員、僧人、處士、道士、文人等,似乎各色人頗多。但其中一大特點是這些人都是有學(xué)養(yǎng)的文化人,所以唐代福琳和尚在《唐湖州杼山皎然傳》中說:“晝生常與韋應(yīng)物、盧幼平、吳季德、李萼、皇甫曾、梁肅、崔子向、薛逢、呂渭、楊逵,或簪組,或布衣,與之交結(jié)必高吟樂道,道其同者則然,始定交哉!”
皎然雖然是佛門中人,但他接受的是禪、是禪宗,禪宗與禪都不否認現(xiàn)實世界,而是肯定現(xiàn)實世界,只是尋求精神上超脫現(xiàn)實世界,所以有些學(xué)者認為禪宗是老莊佛教化或佛教老莊化。皎然正是一個禪學(xué)修為很高的僧人,他始終以禪的情懷、禪的心態(tài)與現(xiàn)實中人交游、酬唱、文會等,盡管與現(xiàn)實中人有很多交往,但始終保持精神上的超脫,這就形成了他與現(xiàn)實世界友人間純粹如茶的友情。許多實例可說明這一點。
顏真卿是唐代名臣、一代大儒、著名書法家,他在湖州任上5年(大歷八年至十二年即773年至777年),他在湖州舉行了一些重要的文化活動,如集合湖州的文士們編訂了《韻海境源》,召集文士們宴集游賞等。皎然與顏真卿有著很密切的交往,留下來的酬唱之詩達22多首之多,這20多首詩反映了他們之間純粹如茶的友情。如《五言奉酬顏使君真卿王員外圓宿寺兼送員外使回》中所寫無非是早晨行走在干凈的石路上,夜晚聽細細泉聲,禪境般無世俗干擾的環(huán)境里,遙望長路,悵望空林。詩中的意境無世俗氣習(xí),顯現(xiàn)了他們干凈、純粹如茶般的友誼,以及高雅的情趣趨向與超脫的生活情懷。《五言春日陪顏使君真卿皇甫曾西亭重會韻海諸生》中所寫還是禪意的境界:風(fēng)吹著樹木,潔凈的天空沒有云片,青翠的山峰下溪水潺潺流淌。皎然根本沒有描述他們是如何相會,只是宣染一種禪境,沒有任何的世俗氣,從中可知,他們的情懷與友誼是多么純粹!
韋應(yīng)物是中國唐代著名山水田園派詩人,他生命的最后幾年(唐德宗貞元四年即788年七月受命至唐德宗貞元六年即788年底)是在蘇州刺史任上度過,最后卒于蘇州。韋應(yīng)物在蘇州期間,皎然與之有過很好的交往,宋代朱長文撰《吳郡圖經(jīng)續(xù)記》卷上的《牧守》記載:“若韋應(yīng)物、白居易、劉禹錫亦可謂循吏,而世獨知其能詩耳。韋公以清為唐人所重,天下號曰‘韋蘇州’。當(dāng)貞元時為郡于此,人賴以安,又能賓儒士,招隱獨,顧況、劉長卿、丘丹、秦系、皎然之儔類見旌引,與之酬唱。”另據(jù)宋范成大撰《吳郡志》卷四十二《浮屠》記載韋應(yīng)物與皎然交往的故事:“僧晝,字皎然,吳僧也。工律詩嘗謁韋蘇州,恐文體不合,乃苦思作古體十篇為贄,韋殊不稱賞,晝失望明日寫其舊制以獻,韋吟諷嘆味不釋手,因語晝云:‘師幾失聲名,不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晝大服其精鑒。”韋應(yīng)物撰《韋蘇州集》十卷中有一首評皎然的詩即《寄皎然上人》:“吳興老釋子,野雪蓋精廬;詩名徒自振,道心長晏如。”皎然也曾寫《答蘇州韋應(yīng)物郎中》評價韋應(yīng)物。他們之間的故事表明他們之間的友誼是很純粹的,他們以共同對詩歌的愛好,以互相對個人品格的仰慕而結(jié)下友誼,如茶水般高雅、純潔,超脫了世俗習(xí)氣。
再看皎然與一個志趣高但身份普通的人交往,如皎然在詩中常提及的山人秦系(皎然有8首詩與秦系有關(guān)),他不過是一個普通的隱士而已,但他志趣高、品味高,皎然與之志趣相投,結(jié)下了很深的友誼。從皎然的詩中可以看到他們之間的志趣。在《五言酬秦山人系題贈》中,皎然描述的是一幅禪境,即他題贈秦系的是禪的境界:走出齋舍,步入杉樹影子中,打開禪院門,看到滿地開著花,云氣飄浮,山石清新潔凈。在《五言酬秦山人贈別二首》中,禪是主題,“相伴住禪臺”,“臥病不妨禪”,“來觀新月依,清室欲漱香”。《七言酬秦系山人題贈》一詩中仍然描述的是空靈的禪境:“云林出空鳥未歸,松吹時飄雨浴衣;石語花愁徒自苦,吾心見境盡為非。”他們之間就是以禪境為共同的興趣、共同的精神寄托,形成了純粹如茶的友誼。
皎然與陸羽的友誼,是中國歷史上的佳話,那可更是純粹如茶,他們以茶禪為共同愛好,陸羽在皎然的支持幫助下才成為一代茶圣,皎然對陸羽尋訪、想念宛如在尋訪禪,如皎然在《尋陸鴻漸不遇》寫道:“移家雖帶郭,野徑入桑麻;近種籬邊菊,秋來未著花;扣門無犬吠,欲去問西家;報道山中來,歸來每日斜”。詩中充滿禪意。禪的人生情懷造就了皎然,在唐代,還不僅僅皎然,還有許多文人,如王維等,從而造就了唐詩,禪的境界成為唐詩的一大特色,許多了唐詩中都有禪境,但都沒有皎然深入與廣泛,皎然大多酬唱詩都在敘述他禪的情懷。
當(dāng)代社會使許多的人都感到壓力大、浮躁,茶與禪對人們都有著重要的價值,可以使緊張生活的人們放松心情,我們也不妨在茶中體禪、悟禪和享受禪,當(dāng)代社會肯定會更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