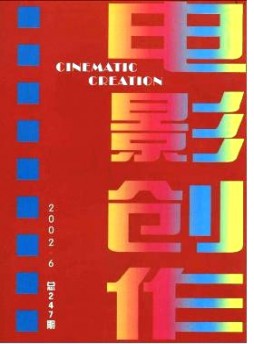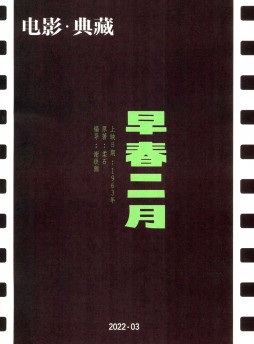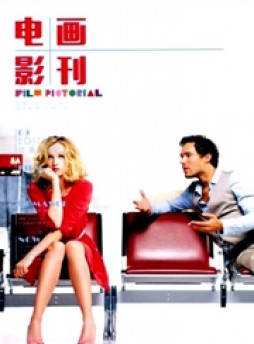電影藝術與娛樂關系研討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電影藝術與娛樂關系研討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作者:鄭惠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雖不愿承認,但這的確有其悖論性存在,歷史浪潮、發展趨勢的確是難以逆轉的。改革開放,中國電影逐漸從政府投資轉向民間投資,走上商業化的道路,市場的激烈競爭和經濟收益成為電影業關注的重心。加之好萊塢浪潮席卷而來,電影人在重重的壓力和金錢的“動力”下,為了迎合這個娛樂化的時代和市場經濟環境下觀眾的口味,扭曲了其藝術觀,帶著觀眾一同沉浸在了沒有精神的影像世界中。除此之外,在以經濟利益為中心的社會環境下,大多數人為生計而奔波,又有多少人有時間和興趣去反思人性的魅力和時代的變遷。連一直堅持自己人文追求的賈樟柯談到這個問題時都說:“一個人坐在車上,從三環、二環走的時候,你看到那些往來的人,大家那么忙,每個人臉上都有心事,匆匆忙忙在城市里奔波的時候,我覺得他們不應該去花錢看那個電影,太累了,其實自己是很灰心,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情況里面,這樣一個生活節奏里面,其實你要求那么多觀眾去看電影,特別是那么貴的票價,我覺得是有它的困難在里面。”觀眾希望在休閑時間里花時間和金錢去買個樂子而不想去買一個反思的心理包袱,市場需求就產生了,所謂大片就被制造來滿足這種觀影需求,如此和諧的娛樂交易過程,藝術根本無法插足。
是觀眾引導電影產業還是電影產業引導觀眾?
電影不論作為一種藝術也好,作為一種產業也罷,都應該有效發揮其對受眾的引導作用。目前看來,這種引導與被引導關系似乎被本末倒置,我并非在否認對觀眾需求的重視,而是認為在提高中國觀眾審美情趣方面,更多應由電影產業來主導,而不是單純的投其所好。電影藝術本性的回歸,并不能指望觀眾有朝一日對其產生了實質需求,暫且不說會不會有這么一天,單是誰該走在前頭從本質上就是錯誤的。在這方面,中國電影業或許應該向時尚業取取經。每年每季的時尚潮流都是由精英階層主導,層層向下發散和推廣,最終在社會上造成觀念的變化和時尚領域的實質性改變。雖然兩個領域存在巨大的差異,但這種傳播模式我認為是相通的,是值得借鑒的。
因此,我認為,電影產業應該對觀眾的觀影習慣和審美情趣進行引導,并且建立良好的溝通機制,讓大眾能夠接受超前或深層的思想,最終形成良好的互動,而不僅局限于由誰滿足誰的狀態。四、我們能不能期待中國電影藝術性的回歸?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明白目前電影藝術的兩大困境:
(一)“叫好不叫座”的電影窘境
賈樟柯可以說是中國電影“叫好不叫座”的典范,他的片子在國際電影節屢獲大獎,但在國內卻面臨著“零票房”的境遇,幾年前的一個專訪中他提到:“來威尼斯,就像回家。”中國電影獲得的藝術肯定需要別的國家來給予,真可謂是一種諷刺。當然這種情況并不僅局限于中國影片,去年奧斯卡最佳影片《國王的演講》在國內院線上映,同樣遭到了票房的“冷遇”;今年奧斯卡最佳影片《大藝術家》在北京國際電影節上追捧者眾多,但要引進到大銀幕上同樣不被國內片商看好。獲獎影片沒人緣,爆米花電影卻受到追捧,名利雙收,這樣的現狀給擁有藝術追求的電影人的打擊可想而知。
五月的國內電影院線,相同的情況依舊在上演。《飛越老人院》、《我11》、《賽德克•巴萊》幾部一致獲得影評人高度評價和業內人士追捧的影片卻在影院排片上遭遇了滑鐵盧,導致這些電影收回投資都成了困難。影院以這些電影拍得不商業為由,不給這些電影檔期,或者安排在最早和最晚的場次,加上今年對境外電影的開放程度增大,面對進口片的強勢和本土情況的制約,留給這些堅持不走商業路線的文藝片導演的只剩“一聲嘆息”了。
(二)電影批評機制的不健全
中國的電影產業鏈有十分薄弱的一環——影評。目前在中國,影評人主要有幾種:一種是學院從事電影批評的專業人員,他們的交流范圍比較有限,基本限于學術領域內,而并不能得到廣泛傳播,由于其專業性過強也不適于大眾傳播;一種是大眾媒體開辟的影評類欄目,但其受市場操控的特征明顯,很難做到公正客觀,除此之外,大眾媒體的影評對影片的藝術價值關注極少,更多的是花邊新聞和炒作噱頭;還有一種就是網絡上的草根“影評人”,但這些人往往僅憑興趣給予一些電影自己的看法,主觀性較強,而專業性不足,使得這個群體的影評只能用“業余”二字形容。重重困難的堆積,似乎在眼前形成了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峰。
這個時候我卻想對這個問題給出我的答案——可以,我們可以期待中國電影藝術性的回歸。今年的第31屆香港金像獎,《桃姐》獨得五項大獎成為最大贏家,它的成功當然也不能代表整個香港電影的復興,只能說是許鞍華對人文主義的堅持最終得到了電影界的肯定。但這部沒有噱頭、沒有過分包裝、沒有華麗效果,在影院看甚至有些沉悶的電影,能夠打敗那些制作精良、票房大賣的電影,獲得大眾和專業人士的認可。從這點,我看到了希望。電影藝術性的廣泛回歸不是什么指日可待的事情,這其中牽涉到除電影產業自身之外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面因素,可能是需要全民素質的提高以及幾代電影人的不懈努力才能達成。
目前,指望藝術電影能與商業大片勢均力敵,實現復興是不現實的,但這并不妨礙我們看到這種實現的可能性。電影的娛樂功能被無上限的利用,觀眾總有一天會對這種娛樂方式感到厭倦,一味的接受這種沒有精神的電影終會讓人感到浪費時間和金錢,我們要相信電影市場和觀眾口味的多元化發展,有內涵的電影終究更經得起比較和時間的考驗。其實可以這么說,我們并不缺少具有藝術性的電影,而是缺少能夠出現在大眾眼前的具有藝術性的電影。這主要源于藝術性電影的導演往往具有先鋒的思想,但這種思想卻是大眾的世俗情感不易接受的,能夠欣賞這種意識的觀眾可以說少之又少。沒有渠道分享這種創作的喜悅,電影導演的創作熱情自然會隨之退卻。
加強溝通或許是緩解這種矛盾的一個方法,關注特定群體的問題(如《桃姐》的留守老人),尋找大眾的普遍共鳴點(如《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的初戀),藝術性電影不能期望為各行各業的受眾所喜愛,找準受眾群體,選擇合適的發行和營銷手段,實現溝通渠道的準確和暢通,導演的精英意識和大眾的世俗趣味之間的矛盾也并非絕對的不可調和。就眼前來說,五月的國產文藝片之所以沒有取得預想的效應,與其宣傳發行和營銷策略的不足息息相關。多數文藝片不敢再黃金檔上和商業片競爭,但可以瞄準新開發的小檔期,如情人節、三八檔等,文藝片可以借助這些小檔期登上大銀幕,取代商業片獨霸銀幕的格局,《觀音山》《桃姐》《晚秋》都可謂是依靠宣傳和營銷成功的例子,這也說明了文藝片在現今的電影市場上并非無路可走。
結語:
雖然遭到種種冷遇,但是藝術電影不會銷聲匿跡。近些年,這類電影在國內沒有市場,走不到大眾眼前,于是開始開拓海外市場,通過進行海外發行來取得經濟收益和下一部的投資,賈樟柯和王小帥就是其中的代表。王小帥說:“我上電影學院的時間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當時并不重視票房,特別講究學術。我直到現在還是非常感謝學校的教育,讓我能夠純凈地面對內心、面對電影。”電影藝術的生命力是不容置疑的,我們應該相信這種生命力,也相信不斷追求這種藝術追求的電影人的信念。在這個“娛樂至死”的時代,內容的重要性會逐漸顯現,電影藝術總有一天會在社會環境、電影產業和觀眾都準備好的時候回歸到我們的視野。
擴展閱讀
- 1電影文化
- 2電影傳播
- 3電影現狀
- 4電影發展戰略電視電影
- 5深究傳統電影以及數碼電影結合
- 6電影海報設計
- 7電影類型思索
- 8電影文化闡釋
- 9英語電影欣賞設計
- 10電影中服裝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