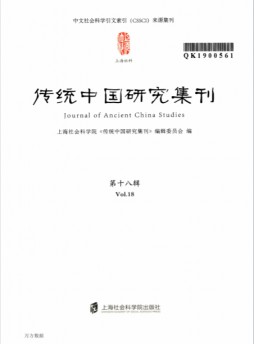傳統(tǒng)法律文化中的公正觀念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傳統(tǒng)法律文化中的公正觀念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政策的公正優(yōu)先于法律的公正
如果能知道社會失序的根本是執(zhí)政者丟棄大道,那么重返大道,執(zhí)行符合大道規(guī)律的政策就標本兼治了。道家學派的莊子則從法律本身的正當性角度對法律的虛偽性提出了嚴厲的批判。“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他認為滿口把道德和法律掛在嘴邊的政治人物,看上去是宣揚倫理綱常,但其實他們和盜竊沒有根本的區(qū)別,只不過盜竊小物件會被他們的法律懲罰,而那些掌握國家話語權的人卻是盜竊了國家的法律和道德,他們利用自己的權力對正義作出有利于自己的界定,從而使得他們對百姓的盤剝變得成為名義上的合法行為,他們不但沒有受到處罰反而還還被授以諸侯公爵的職位。他因此也對孔子宣揚道德仁義的行為進行了嚴厲的批判,“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nèi)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nèi)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nèi)之刑者,唯真人能之。”他他認為孔子等鴻儒是做了不忍一世之害,卻貽害萬世的事情。而如果要摒棄這種痛苦,只有能效仿天地大道、執(zhí)行無私大道的政治家才能做到。在道家看來,法律是被看作為一種細枝末節(jié)的事物,而治理國家的根本在于人,尤其是在于君主能否采取恰當?shù)恼摺!痘茨献印酚羞@樣的比喻記載:“夫臨不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shù),猶不能與網(wǎng)署爭得也。”意即在說,“在江邊釣魚,一整天也不能釣滿一籮,雖然有彎曲的釣鉤,上面有鋒利的倒鉤,纖細的釣繩,芳香的魚餌,再加上有詹何、娟嬛的高超技術,但是所釣之魚也還是不能與大網(wǎng)撲撈相比。”法律僅是一根釣竿,治理國家最重要的是要反思為什么犯罪而不是如何鎮(zhèn)壓犯罪,頻繁動用刑罰不是長治久安的良策。“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yè)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離朱之明,察箴末于百步之外,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diào),而不能聽十里之外。”可見治理社會不能依靠個人的心術,而是要采取順應自然符合大道的根本政策。第二種答案以法家學說為代表,認為治理國家要嚴刑峻罰、平等執(zhí)法。這種觀點突出了法律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性。其一,法家主張法律可以起到定紛止爭的作用,“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其二,嚴刑峻罰可以消除人們逃避制裁的僥幸心理。其三,只有平等適用法律、賞罰分明才能真正獲得權威。“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一民之軌,莫如法。”
不過在法家的學說里,法律和其他手段一樣都是治理國家的策略或者“術”而已。刑罰的最終目的是要實現(xiàn)無人犯法、無刑可用。法家的嚴刑峻罰是建立在對人性趨利避害的心理機制基礎上的。但法家也在思考著如何使國家長治久安的問題,反思犯罪的社會原因。他們認為社會貧富分化是造成犯罪的重要社會原因,“倉廩實則知禮節(jié),衣食足則知榮辱”“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說得就是這個意思。像《管子》、《韓非子》這些法家學說代表作都在開篇闡釋了君主執(zhí)行天道無私政策的先決性,在這點上,法家的思想和道家是一致的,他們都推崇君主替天行道的思想,并且把君主執(zhí)行天道作為政權“合法性”的前提。學界向來把法家學說理解為一種維護君主專制的思想看待,這是有失偏頗的。法家學說始終圍繞著自己的“九惠之教”政治理想展開的。他們對君主都提出了和道家相類似的無為而治要求。“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jié)。”“合格的君主不住美麗的宮室、不聽華麗的音樂,不是因為厭惡這些,而是因為這對于農(nóng)業(yè)和教化有傷害,就好比在冬天不吃冰,不是因為厭惡冰而是因為這有害于身體。”在這點上,法家也主張君主德行的至關重要性,只有效仿天地日月,無私無貪,才能營造官廉民安的社會正氣。而法律都是在“道”的支配下,作為一種服務“道”的手段而存在的,法律還要隨著犯罪形勢的變化而及時變化。
第三種答案以儒家學說為代表,認為國家治理中“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強調(diào)“禮法結合”和“德主刑輔”。儒家認為,德教的效果往往是刑罰無所能及的。《淮南子》記載,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絻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暗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于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誡于此者刑于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其意即說,孔子的弟子巫馬期穿著粗布麻衣改容換貌去觀察季子治理單父的效果,巫馬期看見有人捕魚后又放回水中,就問原因,漁夫答:“季子不希望人們捕魚,我剛才捕到的都是小魚,因此放回水中。”巫馬期說:“季子的德教好到這種程度,能使人按暗中做事都像有刑法在身邊一樣。道德馴服人心的功能是法律所不能及的。統(tǒng)治者的政策具有移風易俗的作用,如果其能施行仁政那么刑罰的適用就會減少,這也是儒家提倡德主刑輔的目標。和其他流派一樣,儒家也對犯罪的深層原因做過探討,《論語•子路》載:子適衛(wèi),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貧困是庶民犯罪的溫床,而要減少庶民犯罪,首先還要增加他們的財富,這就體現(xiàn)了儒家也把社會政策的公正擺在了治國的首要位置,這也是“仁政”的首要意思。假如能使社會財富大體均衡,人人小康,社會政策良好,犯罪和民事糾紛就會減少,對法律的依賴程度也就會減退。
總的看來,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化中,法律并沒有被作為一種至高無上權威得以對待,相反,法律被認為是失道以后的產(chǎn)物或者作為一種實現(xiàn)特殊政治理想的手段。這種思想也深刻地影響到了人們對司法公正的理解。一方面,司法活動要盡量少地動用刑罰手段,如果能通過調(diào)解或教育解決糾紛,反而是更受歡迎的結果;另一方面,司法活動也深受各類天道無私觀念的影響,司法不僅要處理已經(jīng)受理的個案,而且還要充分在個案中表達國家對各階層的普遍關懷的父愛主義思想。此外,司法活動不再是單純的被動行為,司法官員和行政官員沒有嚴格的區(qū)別,司法的職責和行政職責界限模糊,司法官吏要在個案中挖掘出那些隱藏在法律要件以外的糾紛起因并且把它們視為影響定性量刑或者裁判民事糾紛的重要因素,例如甲與乙土地糾紛的起因是什么,張三為什么會行盜,如果處罰李四對其家庭有什么影響,等等。可以說,司法必須承擔其檢討政府政策正當性、有效性的任務,并爭取在“終裁”性的司法環(huán)節(jié)對失效的政策給予最大限度的糾正。
二、崇尚“天道無私”的實體公正
《道德經(jīng)》中講,“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余。”老子認為天道的最高要義就是平衡,按照各種物體和生命的自然需求分配資源,但現(xiàn)實生活中人為制定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卻與此相反,都是為了強勢者的利益而制定。老子以水為比喻,認為真正的大道應當是像水那樣,總是處在最低的位置,滿足所有需要滋潤的萬物,但卻不爭強好勝。“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因此,老子認為真正的公正者應當能效仿天道行無私之惠。儒家的最高理想是“大同”社會,“天下為公”是這社會的總原則,人們各盡其力為社會勞動,生產(chǎn)成果和社會財富均歸社會成員共享,毫無私有觀念,博愛精神支配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實行社會民主“選賢與能”,而被選出來的“賢”者、“能”者則是為社會全體成員服務的公仆。實際上,儒家也十分注重人與人之間在財富和享受社會成果方面的平等問題,正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正如前文所述,法家思想與道家的思想是極為相似的,法家也提出了自己的具體政治理想,即“九惠之教”,老老、慈幼、恤孤、養(yǎng)疾、合獨、問病、通窮、振困和接絕。春秋戰(zhàn)國的三大主流思潮對公正的解讀,都是從實體公正角度延伸出來的,從這里可以發(fā)現(xiàn)中國古代政治哲學不像西方社會那樣把重心放在程序公正方面。實際上,中國古代主流政治哲學是把在與“私”相對應的角度來理解“公”正的,也就是說公者無私。《道德經(jīng)》中講,“圣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為而不爭。”意思是說,執(zhí)政者沒有自己的私人積蓄,他是否富裕取決于他能否像天道那樣公平地給其他人財富,能給天下人越多則他越富有,這就是圣明執(zhí)政者的治國之道,他按照規(guī)律行事,但卻不與天下人爭奪。為什么呢?因為只要天下人人大體平等,那么爭斗就不起,賊盜就會銷匿,國泰民安,社會和諧,這不是執(zhí)政者最大的財富嗎?中國近代無政府主義者還引用《禮記•紀法篇》“黃帝明民共財”的說法以為社會主義學說提供傳統(tǒng)思想淵源,認為“共財”二字“足證太古以前確為共財之制”,并主張“財產(chǎn)廢而為公共,無食人與食于人之分”,如此才能實現(xiàn)“同樂同作,同息同游”的“大同”即社會主義理想。這種把“公”放在與“私”相對應立場上的理解對包括司法在內(nèi)的中國社會各種制度都產(chǎn)生了影響,一是把“公”作為國家的政治理想,也把它作為執(zhí)政者的倫理約束;二是中國古代總體上而言,對私有財產(chǎn)的保護是相對次要的,在必要時為了實現(xiàn)政治理想需要犧牲個體的私有財產(chǎn);三是執(zhí)政者要調(diào)動各種手段包括司法手段以實現(xiàn)天道無私的實體公正,賦予司法工作人員較大的裁量權最大程度地實現(xiàn)個案中的實體公正;四是由于對“私”的潛在抑制,因此司法活動主要是代表國家的司法官吏占據(jù)絕對主導地位,司法官吏和行政官吏一樣都是“父母官”,都要扮演主動且平等保護民眾的角色。如在皮影藝術里,《張飛審瓜》就是一個典型案例。筆者以為,這其中隱含著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化中對判官把握實體公正能力的要求,至于其是否具備豐富的法律知識和程序規(guī)則恐怕不是最核心的。如果判官能“主持公道”,即便其在程序上有輕微的瑕疵也未必失去“公正”的形象,而即便其能精密遵循的程序規(guī)則,如果在實體上失去平衡,也難青史留名。這是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化的特殊之處,其既具有某種當代意義,當然也有需要糾正的地方。
三、以“情理入法”確保公正效果
作為農(nóng)業(yè)文明高度發(fā)達的社會,中國古代對上古社會人們集體耕作中產(chǎn)生的某些倫理規(guī)則給予了最大程度的保留,并且通過文化的形式對這些規(guī)則進行修飾、論證和宣揚。某種意義上說,作為中國最高行政首腦的“宰相”一職,它就保留了十分形象的倫理意義,“‘宰’,就是在酬祭社神的慶典中支持分配‘酢肉’的人,‘相’就是贊禮司儀、陪伺招待。”國家只是放大了的家庭,行政官員和司法官員是百姓的“父母”官,既然是“父母”則處理子女之糾紛定然以倫理要求為最高原則。深受倫理主義影響,人們在處理利與義之間的關系就有傾向性,當利與義發(fā)生沖突而難以調(diào)和時,那么義的價值要高于利。人與人之間不單純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換關系,還有更為重要的感情維系關系。清代著名刑名師爺汪輝祖曾明確地提出,“司治刑名的根本規(guī)范不是法律而是情理”。他說:“幕之為學,讀律尚己,其運用之妙,尤在善體人情。蓋各處風俗往往不同,必須虛心體問,就其俗尚所宜,隨時調(diào)劑,然后傅以律令,則上下相協(xié),官者得著,幕望自隆。若一味我行我法,或怨集謗生矣。”這點不僅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古代的司法活動,也使中國古代的政治活動具有深刻的倫理烙印。由于世間萬象,人情百態(tài),法律不可能對每一個案件都做出適合的規(guī)定。由于事物總是在不停地發(fā)展變化,穩(wěn)定的法律永遠滯后于事物的發(fā)展;由于情與法本身就有相通之處,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情的體現(xiàn),就使得情法允協(xié)成為必要。情法結合之中,既有“法中之情”的理論,更有“法外之情”的實踐。對于“法中之情”,明代人敖英指出:“或問我朝定律,于情法何如?予乃作而嘆曰:至矣哉我朝之律,可謂情與法并行而不悖者也。如十惡不原,法也;八議末減,情也。干名犯義者,法也;得相容隱者,情也。自首免罪者,情也;猶追正贓者,法也。罪有加者,法也;有減者,情也。有從重者,法也;有免科者,情也。凡法之所在而不姑息之者,義之盡也。凡情之所在而必體悉之者,仁之至也。”
事實上,這也是唐律以來所有律要求的“法中之情”的原則。《元史》載,周自強為婺州路義烏縣尹,周知民情,而性篤寬厚,不為深刻。民有爭論于庭者,一見即能知其曲直,然未遂加以刑責,必取經(jīng)典中語,反覆開譬之,令其詠誦講解。若能悔悟首實,則原其罪;若迷謬怙惡不梭,然后繩之以法不少貸。關于“法外之情”,明代記錄了這樣一個故事:“刑部主事王某,在山東做縣令時,有民婦回娘家探親,路遠,婦乘月色獨行。適一樵夫尾隨其后,至野外,握斧大呼,婦驚仆倒地,遂強奸之,盡擄首飾而去。婦號泣奔還,偶遇令出,攀輿哀訴。令曰:‘吾當令人往捕,汝第言失去首飾已耳,毋露奸情也。’遂用巧計捕得樵夫,擁至縣庭,召婦審視,首飾一無所失。因痛杖之百,收監(jiān)時氣絕。召夫責曰:‘爾婦將母,何不伴送?幸盜止利其首飾耳,倘至傷命奈何?’亦笞之十,令攜婦歸家。蓋縣令不令其言奸者,緣律條坐斬,問擬頗重,且恐夫知必棄其婦,故曲為保全耳。”此縣令在審判這一案件時,為了保全婦人的名譽,叮囑當事人把案中強奸一節(jié)滿下,可謂世事洞明,人情諳練,從而既懲辦了罪犯,又避免了一場悲劇的發(fā)生,雖法外用情,但乃“情法兩全”。
以“情理入法確保公正的效果”還有一個意思就是要注重案件的判決能否真正化解糾紛,實現(xiàn)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在中國清代康熙年間,有名為陸隴其的判官。據(jù)野史記載,陸隴其每次審判盜竊犯時都會問其為什么要犯罪。犯罪人都以貧窮難以度日為由狡辯。但陸隆其并不因此勃然大怒。接著就會讓犯罪人學習紡紗,并且告之要學會了才能釋放,若不然則罪加幾等。犯罪人為了能早日出獄都會用心學習。但在釋放之日,陸隴其都會叮囑犯罪人:“這紡紗線不過一百多錢,現(xiàn)在幾天內(nèi)除去你們吃飯之費用,起碼有幾百錢的收入,如果你日后再犯盜竊之罪,你我都無話可說了。”大多數(shù)犯罪人出獄后都會改過自新,只有那些三次以上仍不思悔改者,陸隴其才會采取狠招,即令差役將犯罪人急驅上千步,然后灌下熱醋,使其終身咳嗽,不能為盜。陸隴深刻地認識到,眾生平等,萬物有情,單純對犯罪人判決刑罰并不能根治盜竊,只有解決犯罪人的社會生存問題才能真正實現(xiàn)法律的目的,也就是說司法活動不單純是機械適用法律的活動,還是創(chuàng)造社會政策的過程,只有那種實現(xiàn)法律預期目的的司法裁判才算是效果良好的司法活動。
四、司法官是實現(xiàn)公正的關鍵因素
由于“情理入法”是中國古代司法活動的重要特點,因此,適用法律的關鍵就不在于法律本身的規(guī)定,因為“法律不外乎人情”,倘若司法官員能敏銳地捕捉到人情常識,即便其在法律知識上略有欠缺,也能通過對倫理規(guī)范的詳熟而打通與法律的溝壑。對人情常識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教育和經(jīng)驗。正是因為如此,中國古代是十分重視禮治教育的。盡管司法官員要接受法律類別的考試或者訓練,但通觀古代教育,儒學的倫理教育是全部教育的基礎課程和核心課程。實際上法律作為治國的輔助手段,主要是用以闡釋倫理秩序合理性的。除了教育,經(jīng)驗的積累同樣重要,在面對法律空白或者相互矛盾時,如何填補法律的空白或者取舍法律的適用是難以完全依靠教育的,取決于具體個案中相互沖突價值的排序,它需要個體在實踐中去感悟。司法官員要能根據(jù)“五聽”這種技巧像“獨角獸”那樣能辨別出犯罪嫌疑人或者訴訟雙方供述的真?zhèn)魏托睦頎顟B(tài),要依據(jù)破案的經(jīng)驗和智慧從各種復雜的犯罪現(xiàn)場找出蛛絲馬跡還原事實的客觀過程,發(fā)現(xiàn)事實的真相,從而實現(xiàn)懲惡揚善的實體公正。可以說,中國古代的司法重心不在于研究法條之間的關系,也不在于被動地聽取訴訟雙方的辯論,而是要最大限度地發(fā)現(xiàn)案件客觀真實,通過對法律的靈活運用維護天倫人情的正當秩序,法條只是司法官員審判時的參考或者是其所要考慮的部分因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古代的審判也是一門特殊的藝術。因此,中國古代司法公正的實現(xiàn)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司法官員自身的道德修養(yǎng)、審判智慧甚至個性天賦。《仁宗實錄•包拯附傳》記載:“拯嘗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又有告殺牛者,拯曰:‘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服。”《孝肅包公傳》記載:“久之,知揚州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曰:‘第殺而鬻之。’俄有告私屠牛者,拯曰:‘已割其舌矣,非私殺也’。盜色變,遂引伏。”
有平民向包拯報案,說是自己家牛的舌頭被盜割了,但沒有其他任何證據(jù),要是嚴格按照法律的話,包拯也是可以不受理的。但包拯沒有如此“守法”,而是采取引蛇出洞的方式對案件進行長線審查。同時他允許牛的主人宰牛以便挽回損失,而根據(jù)宋代的法律,私自宰牛是不被法律允許的,包拯也沒有拘泥于法律,而是本著“為民”的心態(tài)允許被害人宰殺。另外,包拯破獲此案關鍵在于他的經(jīng)驗和智慧,即通過對犯罪嫌疑人言辭行為與心理狀態(tài)關系的準確把握。中國古代出現(xiàn)了許多富有豐富審判經(jīng)驗和智慧并且名垂千古的司法官員,例如唐代著名法官徐有功,長期擔任專職審案官,因敢于嚴格執(zhí)法,犯顏直諫,平反了成百上千的冤案,救活人命無數(shù)而名留青史。有些司法官員還將這些經(jīng)驗加以總結,例如宋代法官宋慈專門寫了《洗冤錄》一書,充分展現(xiàn)了中國古代司法官員的智慧。可以說,中國古代司法體制的核心不是規(guī)則化的程序,而是權力架構下具有充分能動性的司法官吏。
五、以程序和外部監(jiān)督防范“不公”
中國古代具有濃厚“人治”色彩的司法運作機制也伴隨著司法擅權的普遍發(fā)生,為此中國古代也注重對司法權的制約和監(jiān)督。其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司法審判中司法官員必須遵行的部分剛性程序;二是司法裁判必須接受上級司法機關或合議機構、監(jiān)察機構、甚至是君主的復核,如果司法官員在這兩個方面不能合格過關,則將承擔極為苛刻的法律責任。可以說,中國式的司法確實不是獨立意義上的司法,它的做出的“公正”裁判也并非完全意義上的“終裁性”決定。在某種程度上而言,與同時期的其他國家訴訟法律制度相比,中國古代的訴訟法律制度并不顯得落后。只不過,西方國家同時期的訴訟法律制度主要是通過賦予當事人訴訟權利而日漸完善,而中國古代的訴訟法律制度則是通過限制司法官員的審判手段而漸趨縝密的。
中國古代主要通過以下幾個重要的程序性規(guī)定防范司法官員濫權或枉法裁判的:一是,設立較為明晰的級別管轄和地域管轄制度。以唐代為例,唐代有縣司、州府、尚書省、大理寺、中書門下五級,其中中書門下屬于申訴機構,只進行法律審,實際上是五級三審制。對于應當受理而不受理,或者不應當受理而受理的,司法官將被追究責任。二是,對司法官員的回避作了規(guī)定。如《元史•刑法》則記載,“諸職官聽訟者,事關有服之親,并婚姻之家,及曾受業(yè)之師與所仇嫌之人,應回避而不回避者,各以其所犯坐之。有輒從法官臨決尊長者,雖會赦,仍解職降敘。”三是,對刑訊措施使用的嚴格限制。中國古代法律對刑訊的適用對象、強度、工具等通常都有規(guī)定。一般而言,刑訊只能用在具有一定證據(jù)、被告人絕不招供以及嚴重犯罪的案件中。《唐律疏議•斷獄》規(guī)定,“拷訊不能超過三次,總數(shù)不能超過二百板,對于杖罪以下和犯笞罪十板以上者需要拷訊,不能超過其所犯杖、笞罪所處刑的笞打、杖打的數(shù)目。如果拷訊超過三次,以及在三次以外,或用別的刑訊方法,如用繩索捆吊,用棍棒拷打,司法官應負的刑事責任是處以杖刑一百。如果拷囚超過數(shù)量,并因此致使囚犯死亡的,司法官則應處以徒刑二年。”
四是,雖然如前所述,“情理入法”是中國的司法傳統(tǒng),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官必須援引法律而不得直接引用倫理規(guī)范,如《唐律疏議•斷獄》明確規(guī)定:“諸斷罪,皆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五是,為當事人保留了申訴的權利。“《睡虎地秦墓竹簡》載:‘以乞鞠及為人乞鞠者,獄已斷乃聽,且未斷猶聽也?獄斷乃聽之’。這說明,在秦朝官府即已允許當事人和他人在判決以后提出申訴,請求再審。而且,秦也確有因乞鞠而再審改判的實例。”我國古代在不同歷史時期,為當事人開放了“登聞鼓”、“上表”、“邀車駕”、“立肺石”等在特殊情況下的越訴措施。上述這些程序性規(guī)定,成為中國古代防止司法官員濫權的重要方面。此外,中國古代的司法活動受到司法機關以外力量的制約,主要表現(xiàn)在,一是,徒刑以上案件一般都要啟動復核程序。例如唐代大理寺做出的徒刑和流刑以上案件判決,必須經(jīng)過刑部的復核和批準才能執(zhí)行,對于死刑案件還必須經(jīng)過皇帝的多次復核。此外對于全國各地做出的流刑以上判決都必須經(jīng)過刑部的復核,如果刑部在復核中發(fā)現(xiàn)有疑案、錯案或者冤案,刑部可以將案件發(fā)回地方重審,對于死刑案件則發(fā)回大理寺重審。一般而言,刑部不負責具體的審判活動,但它對審判活動起到監(jiān)督的作用。二是,對重大疑難案件可以啟動合議審判程序。例如唐代的八座議事制度和三司會審制度都是其他力量參與到審判中,一方面干擾了司法審判的獨立性,另一方面也起到了限制司法擅權的客觀效果。三是,國家每年都會派出監(jiān)察官吏到各地“錄囚”。“錄囚,唐以后又稱慮囚,是皇帝或中央和地方長官巡視監(jiān)獄,對囚犯進行市錄,以平冤糾錯,糾正掩滯的一種法律制度。錄囚肇始于兩漢。通常,中央和地方長官的錄囚是定期進行的。”
甚至在相當一段時期內(nèi),皇帝也要親自錄囚。貞觀年間,唐太宗“每視朝,錄禁囚二百人,帝親自案問”。四是,中國古代監(jiān)察御史制度對各類公職人員各種行為有著寬泛的監(jiān)督權。監(jiān)察御史作為皇帝的耳目,一方面通過合議審判、錄囚理冤等活動制約審判活動,另一方面通過糾舉失職、彈劾違法、甚至是風聞奏事的職權成為古代專司公職違法的機構。五是,司法官員違法裁判將受嚴厲制裁。西周時期就有“五過之疵,即惟官、惟反、惟內(nèi)、惟貨、惟來,其罪惟均。”秦朝法律規(guī)定司法官犯“失刑”、“縱囚”、“不直”等都要負法律責任。漢承秦制,也有“出罪為故縱,入罪為故不直”的法律規(guī)定。司法官員還要對同職違法負有連帶責任。《唐律疏議》卷五十五“同職犯公坐”條規(guī)定:“諸同職犯公坐者,長官為一等,通判官為一等,判官為一等,主典為一等,各以所由為首。”也就是說,在同一官府所有參與具體辦案的官吏都必須在有關的判決文書上署名并發(fā)表意見,并根據(jù)自己在判決形成中的權力和作用的大小有比例地承擔連帶責任,這客觀上使司法官員之間相互監(jiān)督、相互糾正。
作者:姜小川易娟單位:中央黨校浙江省義烏市檢察院
- 上一篇:大學生法律文化素養(yǎng)的思考范文
- 下一篇:法律文化價值的研究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