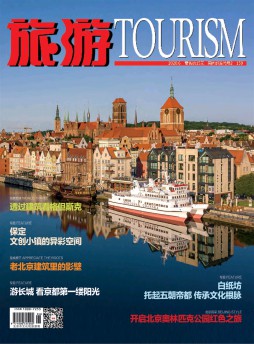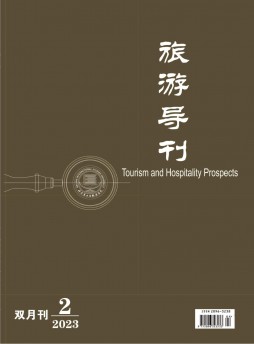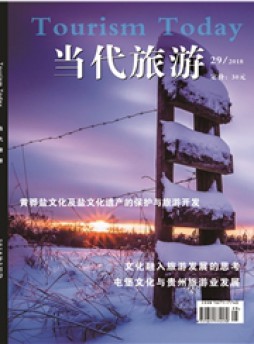旅游發展中文化保護和傳承問題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旅游發展中文化保護和傳承問題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在旅游發展全球化、現代化的潮流下,民族文化旅游開發究竟是對文化的保護,還是對文化的破壞?對此各方爭論不一。借助西方文化人類學、旅游人類學的舞臺真實理論,從民族文化旅游主客雙方的心理角度出發,對“看什么”和“給看什么”進行剖析,探索民族文化旅游中文化表演的舞臺真實性問題,以期對民族文化旅游資源的開發與少數民族文化的保護和傳承有所裨益。
關鍵詞:民族文化旅游;文化真實性;舞臺真實
一、舞臺真實理論和民族文化旅游
(一)舞臺真實理論
在旅游業中,舞臺真實的實質就是對文化舞臺化、商品化展示過程中文化真實性的探討。舞臺真實最初來源于戈夫曼的表演理論。他認為人生是一場表演,社會是一個舞臺。并且將表演分為不自覺的表演和自覺的表演。戈夫曼把前一種表演稱之為“真誠的”表演,后一種表演稱之為“玩世不恭的”表演。此外他還提出“前臺”和“后臺”的觀點。“前臺”是指演員演出的地方及觀眾(當地和外來人)聚居的地方,“后臺”則是演員為娛樂表演做準備的地方。為了“前臺”表演的“真實性”和“可信度”,就有必要保持“后臺”的神秘或者封閉,不能向外來人隨便展示。這些觀點被麥坎內爾(MacCannell)引用到旅游業研究中,并在《舞臺真實》一文中提出旅游業中的舞臺真實理論。他認為現代真實生活的破壞導致人們對異地、他人“真實生活”的迷戀已成為公開的話題。旅游的意識被體驗真實的愿望所激發,游客也可能相信他正朝著這個方向出發,但是,通常在事實上,這是很難確認旅游的體驗是否真實的。這主要是因為在旅游業中,游客對“前臺”和“后臺”是很難區分的。
因為旅游業中的“前臺”往往被裝飾的頗像“后臺”或者是將“前臺”精心裝飾為附著“后臺”活動暗示的地方;即便是對向游客展示的“后臺”,也是被舞臺化的“后臺”。在旅游中所能呈現給游客的一幕幕場景不僅僅是真正生活的復制或翻版,而且這些上演的復制品對真實生活的揭露遠比真實生活本身揭露的東西要多得多,當然不管他們的演出是不自覺的表演還是自覺的表演。每一個可能被參觀的場景,都許諾和使游客信服他們展示的是當地真實的生活和文化。最后,他總結到:文化旅游產品被當作“真實”搬上舞臺,其目的就是為了更好的保護“后臺”,使東道地的傳統文化免遭破壞。
(二)民族文化旅游
在國內外許多民族地區,民族文化旅游對其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作用和影響是有目共睹的,民族文化旅游僅只是一種旅游方式。國內外學者都針對被觀光對象的文化特征、獨特性和少數民族來下定義。有的將民族旅游和文化旅游分開來談。如美國旅游人類學家史密斯(ValeneSmith)把旅游方式劃分為民族旅游、文化旅游、歷史旅游、生態旅游和娛樂旅游五大類;其中民族旅游主要是以地方“奇異”的和常是異域的民族風俗習慣為特色來招徠游客;而文化旅游則是以參觀和感受地方文化為主的旅游。筆者則認為民族旅游和文化旅游可統一為民族文化旅游來談,是因為民族文化旅游實質就是以民族特色為主的文化旅游,即以探尋少數民族的“奇風異俗”,體驗富于“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古老”文化的一種旅游方式。
(三)舞臺真實與民族文化旅游
就民族文化旅游中的舞臺真實現象而言,“舞臺”是指在旅游中所能向游客呈現的一幕幕場景,并非狹義的舞臺表演。而“真實”又是怎么理解的呢。這取決于游客的體驗,或者說是一個衡量游客感覺的標準;因為不同的游客對真實的理解完全不同。如被許多人類學家或民族學家譽為人類瑰寶的儺戲,而文化學者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一書中則說出:“憑心而論,演出極為不好看。許多研究者寫論文盛贊其藝術高超,我只能對之抱歉”。那么旅游人類學家是怎么看待“真實”的呢?科恩認為,所謂“真實性”并不等于原始,而是可以轉變的,因為不同的人對真實有不同的看法和認識,這些都取決于他們的文化水平,審美能力等。張曉萍學者又認為“真實”分為“客觀真實”和“象征真實”,“客觀真實”就是我們所說的真實文化和傳統,即原生文化,而“象征真實”則是在原生文化基礎上的再造真實。顯然,由于真實是在不斷變化著的,所以在民族文化旅游中對待舞臺真實的態度體現在不管是客觀的真實,還是再造的真實,甚至舞臺化的真實,只要游客在對“真實”的認識、體驗和追求上,真正達到身心愉悅,就表明了民族文化旅游中的舞臺真實是可行的。
二、民族文化旅游中舞臺真實的決定因素
(一)民族文化旅游舞臺真實的具體表現
愛德華.布魯納(Bruner)對肯尼亞瑪賽人的同一族群,三種場景的案例進行研究,應該對政府、旅游規劃者、旅游經營者及少數民族精英有所啟示。即利用差異化營銷方式,針對不同的游客,發展不同的旅游場景:一是針對外國游客私人辦的旅游點美亞,雇傭瑪賽人來再現他們19世紀的真實“非洲土風”;二是針對肯尼亞國民,政府辦的搏物館波馬司,通過職業化演員表演“肯尼亞傳統”;三是由旅游機構經營的具有混合格調的旅游營地,即通過好萊塢影片《獅子王》插曲的播放和《走出非洲》氣氛的營造,突出“西方人眼中的非洲”。事實上,在中國的民族文化旅游中,也存在這樣大同小異的例子;如杭州的宋城表演、河南的春秋飲食城、泰山的祭天表演等就是一種彷真表演,在完整真實的歷史空間里,再現已經消失的歷史;如新華白族旅游村是盛興集團圍繞“南昭”文化和白族民俗資源,對“中國民族手工藝品之鄉”云南鶴慶新華村投資,將其打造為東南亞最大的旅游產品集散地,手工業品交易中心,這就是商業化的迎合而形成的舞臺真實或者是再造真實。
(二)民族文化旅游中舞臺真實的決定因素
第一,游客:想看什么。就游客而言,對舞臺真實的探討,也就是在民族文化旅游中,游客追求什么樣的真實?他們是怎樣經歷或體驗真實的?當然,在研究旅游產品的真實性問題時,我們不應該局限于本體的真實,而是應該側重了解特定旅游環境中的人的主觀體驗,來檢驗有哪些因素能夠使他們感到旅游產品傳達的意義是真實的。這個問題一方面關系到旅游地民族形象,另一方面關系到游客本身。旅游地民族形象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個是本底感知形象,另一個是實地感知形象。本底感知形象是指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對于某一地區民族的總體認識。實地感知形象主要是指旅游者在游覽旅游地的過程中,通過對旅游地環境形體(硬件)的觀賞和對當地民俗民風、民情、居民素質的體驗所產生的對該民族的總體印象。這種印象對游客的旅游的體驗、旅游宣傳的效果以及民族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有著重大影響。而對游客的研究,則因為不同的游客對真實的理解完全不同;因此是一個極為復雜的問題。這主要取決于游客的可供自由支配的收入、文化背景、休閑時間以及身體狀況等。筆者就其體驗方式將游客分為大眾游客和“民族志”游客,對大眾游客而言,旅游的目的就是獲得一種娛樂,一種神情愉悅的心情。他們更多地在乎食、住、行的舒適和現代化;而對文化展示的真實,他們通常沒有耐心等待一個哪怕即將來臨的節日以感受真實的氛圍,寧愿“買”來一段時空錯位的“表演”,又要求表演很“真實”。只要不是很過分、很人為、很虛假,游客即便意識到所看的未必就是原汁原味的風情,也樂意接受并給予贊賞。如中華民俗村、云南民族村為什么會吸引那么多的游客,就在于此原因。而就少數“民族志”游客來說,他們更多地注重“參與體驗”的過程。因為他們大多都是具有一定文化層次的人,他們對“真實性”的要求比一般游客要多。他們要到東道地區的“后臺”而不是“前臺”去旅游,去工作;與當地人接觸,參與到當地人的生活和文化中去。況且他們有的知道什么是“真實”,什么是“偽真實”,正因為如此,才產生了對“舞臺真實”的爭議。
第二,當地的少數民族:給看什么。在民族文化旅游中,實際就是一個游客“他群”對旅游民族“我群”的觀察和認識,旅游民族他們是如何看待旅游業中自己的文化、文化的真實性?以及他們對展示的本民族文化有什么看法?如大多數游客較為反感的民族婚俗表演,旅游民族他們同樣也有自己的看法,吳曉萍在《淺析民族地區旅游可持續發展的某些限制性因素》一文中提到她在參觀貴州省某處旅游目的地的“苗族婚俗”項目時,走出那個苗寨公園,就聽見兩個苗族老人議論:“為什么不讓那些女游客和我們苗族男孩(去一起經歷咱們苗族婚禮)呢?”很顯然,游客在從他們神圣的婚俗文化取樂時,是否考慮過他們的體會?那么他們到底想給游客看些什么呢?
由于客觀原因,少數民族地區大多比較落后、偏僻和閉塞,他們的文化水平較低,對自己文化的包裝出售,除了極少數的少數民族精英參與外,其它幾乎無人問津。但是民族文化旅游所依賴的主要資源是少數民族傳統文化,而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又是少數民族千百年來傳承下來的,因此少數民族應當是自己文化的主人。政府、旅游規劃者、旅游經營者在將少數民族文化當商品出賣時,應考慮到要征求傳統文化的“主人”的意見。當然,作為少數民族自己因為旅游開發而將他們推向時代的前沿,既要抓經濟又要抓文化的傳承,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他們怎樣由“被動變遷”向“主動適應變遷”的方向過渡,因此就必須賦予他們提高文化水平,弘揚民族審美意識,樹立民族自信心及增強民族認同的價值。民族審美意識又關系到他們想給游客看些什么的問題,況且民族審美意識是增強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因此,表現和弘揚什么樣的民族審美意識就顯得特別重要了。不能簡單地說民族的就是好的,甚至走向極端,認為越是民族的就越好。如斗雞、裸浴和性所表現的“民族審美意識”就值得嚴肅思考。弘揚民族審美意識,實質就是吸其精華,去其糟粕,并在此基礎強化民族自我意識,促進了民族的吸納意識,激發民族參與意識的覺醒。而樹立民族自信心及增強民族認同價值就在于讓一個民族真正認識到了哪些是“我們的”,哪些是“他們的”;“我們的”是“他們的”所沒有的;“他們”來“我們”這里是因為“我們”有著“他們”最想要的東西。這在民族旅游開發中,是族群認知最為重要的一點。在民族文化旅游中,少數民族對舞臺文化的真實性也應表達自己的觀點,體現主人的身份。真實性意味著贊同和接受,不真實則意味著排斥和反對;因為它決定本民族文化的走向和命運,并會影響游客對舞臺真實的信任度。
三、建立民族文化旅游舞臺真實的措施
第一,對民族文化旅游資源進行普查與分類。在此法國的經驗很值得我們借鑒。20世紀60年代初,法國在現代化建設的高潮中,民族傳統文化受到了極大的沖擊和破壞。1964年,在文化部長馬爾羅的倡議下,法國進行了該國歷史上最重大的一次文化遺產“總普查”。當時的口號是“大到教堂,小到湯匙”,凡歷史遺存的有價值的文物,都要登記造冊。這次普查大大增強了全民對民族文化的自豪感,激發了人們的文化自尊和民族自尊,從而使法國文化遺產經受住沖擊,得到了全面和真正嚴格的保護。我們在民族文化旅游開發中,也應該對民族文化旅游資源進行普查與分類,摸清家底,有的放矢地開發,唯此才能做到對瀕臨失傳的民族文化進行搶救。
第二,對民族文化旅游資源進行篩選和定位。通過調查研究,知道哪些文化可以作為“公眾”文化向游人展示,哪些東西可以被當作是“地方色彩”而向游客推銷,但與此同時又不會給當地文化造成嚴重的破壞。也就是在民族文化旅游資源開發并搬上舞臺的并非是少數民族的所有文化,而是有所選擇,區別對待,對熱鬧狂歡的大眾儀式可直接開發,如:彝族的火把節、傣族的潑水節;對具有神圣文化內涵的宗教儀式就應該謹慎開發,如:婚俗、葬禮和佛寺開光。正如云南的仙人洞民族文化生態村,他們的做法就非常值得稱贊。主要是他們將傳統的祭祀活動,如:祭龍節、密枝節仍有村民按傳統方式舉行;而火把節、花臉節以及再創的旅游節、辣椒節等節日,它們本身就是熱鬧喜慶的節日,游客的參與會使節日氣氛更加熱烈。
第三,制定民族文化開發政策,建立民族文化保護機構。政府的積極參與和有效管理是開發和保護好民族文化旅游資源的重要力量。因此,政府應該制定民族文化旅游政策,建立指導監督機構,使得舞臺表演更趨向真實或者是舞臺真實,確保民族文化的可持續發展,對瀕臨失傳的民族文化進行搶救和傳承。如云南的東巴文化傳承面臨的困境。
第四,大力發展民族文化旅游,注重民族社區的參與。社區民眾是民族文化資源的主人,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應當是民族旅游業的股東之一,在民族文化旅游開發時,真實性被看作是衡量社區控制和動員居民支持并參與活動成功的標準,因此只有強調民族社區的參與,才能為舞臺表演的真實性創造條件,才能為游客體驗當地居民的真實生活搭建平臺,更重要的是才能實現社區民眾分享旅游利益的最大化;只有在民族利益受益時,社區民眾才能做到自我管理、自我發展、自我控制本民族的旅游業發展。
第五,重點開發前臺,注重保護后臺。前臺是為民族文化旅游所設計的專門旅游區,其目的是既能滿足游客對民族文化旅游的需求,又能保護好后臺,盡量避免對居民生活環境的干擾,使傳統文化根基免遭破壞。前臺的設計理念是“真實化、民族化、地方化”,如傳統民居建筑形式盡量做到“外部民族化,內部現代化”;旅游產品應體現鮮明的民族特色;在前臺從事旅游的人,著裝和禮儀一律遵循民族的;民族美食應體現地方特色,民族歌舞、民族文化藝術應充分展示民族特色,具有深刻的文化內涵。
這樣的前臺設計最終就是體現一個舞臺化的后臺,使游客可以體會到“原汁原味”的真實。但是在民族文化旅游中,由于受全球經濟一體化、文化一體化的沖擊下,旅游區的前臺變得越來越現代化,民族的影子只是依稀可見;這對于尋求真實、體驗原始的現代人來說,旅游吸引力也就不大;如西雙版納的曼春滿、大理的古城。
參考文獻:
[1]瓦倫·L·史密斯.東道主與游客——旅游人類學研究[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2.
[2]白楊.旅游真實與游客[J].桂林旅游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6,(03).
[3]丁健,彭華.民族旅游開發的影響因素及開發模式[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02).
[4]周星.旅游產業與少數民族的文化展示[A].橫山廣子主編.有關中國的民族文化及國家的人類學研究[M].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2001.
[5]張曉萍.文化旅游資源開發的人類學透視[J].思想戰線,2002,(01).
[6]楊昌雄.民族審美意識與民族旅游經濟[J].河池師專學報,1998,(03).
[7]彭兆榮.“東道主”與“游客”:一種現代性悖論的危險——旅游人類學的一種詮釋[J].思想戰線,2002,(06).
[8]馬曉京.西部地區民族旅游開發與民族文化保護[J].社會科學家,20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