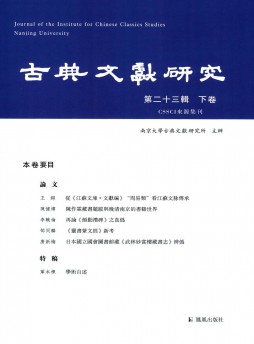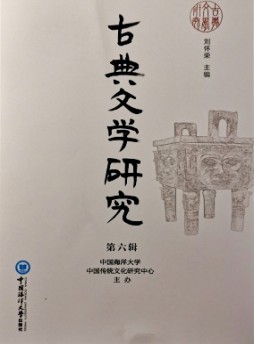古典精神分析社會文化論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古典精神分析社會文化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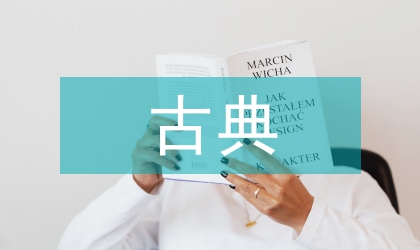
一、精神分析客體關(guān)系理論的早期確立與發(fā)展
古典精神分析理論在經(jīng)過社會文化學(xué)派的修正與發(fā)展后,開始將關(guān)注點從個體內(nèi)部轉(zhuǎn)向外部。社會文化學(xué)派對古典精神分析的修正與發(fā)展已經(jīng)初見其客觀關(guān)系取向發(fā)展的萌芽,社會文化學(xué)派將個體心理的發(fā)展視作是內(nèi)部驅(qū)力與外部社會環(huán)境張力的結(jié)果,這顯然已經(jīng)承認(rèn)主體之外的客體意義。在這種新的主客體關(guān)系中,本能驅(qū)力讓位給“自我及其諸多對象之間實際的關(guān)系聯(lián)結(jié)”,“自我”被“自體”替代是這一傾向的主要特征。克萊因是精神分析客體關(guān)系理論發(fā)展的主要推動者,在精神分析的發(fā)展史上,克萊因敏銳地發(fā)覺到弗洛伊德理論中所包含的客體關(guān)系的思想萌芽,開創(chuàng)性地提出客體關(guān)系是兒童心理發(fā)展基礎(chǔ)的觀點,改變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強(qiáng)調(diào)內(nèi)部本能驅(qū)力是心理結(jié)構(gòu)形成和發(fā)展的第一要因的觀點[11]。克萊因的理論涉及了本能和客體關(guān)系兩方面,她認(rèn)為生與死的本能驅(qū)動著兒童的心理活動,但這些本能受客體關(guān)系(通常是兒童的父母)的影響而發(fā)揮作用,她還認(rèn)為嬰兒在早期由于本能與客觀世界的沖突會發(fā)展出“精神分裂樣狀態(tài)”和“抑郁狀態(tài)”兩種消極心理傾向,它們是形成兒童人格障礙的基礎(chǔ)。克萊因的一些追隨者拋棄了本能而轉(zhuǎn)向環(huán)境,進(jìn)一步發(fā)展了客體關(guān)系理論,使之成為英國精神分析的核心理論。拜恩、溫尼科特、科赫特和費爾貝恩是將克萊因的理論發(fā)展到新水平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中,拜恩1970年在美國建立了“克萊因方向的分析者(Klein-orientatedanalysts)”小組,使克萊因的精神分析觀點得以在北美產(chǎn)生影響力。拜恩對精神分析客體關(guān)系理論發(fā)展的主要貢獻(xiàn)在于:(1)提出母親(作為客體)的“容納功能”,即通過母親的存在、行為和情感修正或強(qiáng)化兒童的沖動在人格發(fā)展中的作用;(2)強(qiáng)調(diào)環(huán)境以及內(nèi)部與外部(客觀環(huán)境)對兒童心理發(fā)展的影響。拜恩的理論觀點在某種程度上被認(rèn)為是“親克萊因主義”,基本上是對克萊因理論的延續(xù)和擴(kuò)展[12]。
相比而言,溫尼科特應(yīng)算是“折中的克萊因主義”者,他在借鑒了弗洛伊德、克萊因的觀點之后,結(jié)合自己的臨床經(jīng)驗,提出了客體關(guān)系理論,強(qiáng)調(diào)兒童心理發(fā)展與客觀環(huán)境處于連續(xù)不斷的反饋之中,關(guān)注個體與他人心理分離的體驗以及與他人融合的體驗之間的相互轉(zhuǎn)化。溫尼科特的理論存在的一個顯著的特性是,強(qiáng)調(diào)母親作為客體在母嬰關(guān)系中對兒童心理影響的重要性。他提出“夠好的母親(good-enoughmother)”這一概念,母親對嬰兒的保護(hù),使嬰兒將“母親”看作為一個整體的概念,并通過母親對自己的身體的照顧感受到自己是一個人,同時嬰兒通過各種方式明白他與母親不是一個統(tǒng)一體,而是與母親相互分離的[13]。所以溫尼科特認(rèn)為,兒童的成長常常是與母親自身的獨立性相一致的。溫尼科特相信,心理分析家可以通過創(chuàng)設(shè)“控制環(huán)境”重新體驗兒童與客體對象(母親)的沖突,在這種客體關(guān)系中使兒童產(chǎn)生積極移情,從而彌合母親與兒童的關(guān)系,實現(xiàn)對兒童的心理干預(yù)。盡管科赫特作為自體心理學(xué)的創(chuàng)始人,算不上是客體關(guān)系學(xué)派的代表人物,但科赫特的自體心理學(xué)也強(qiáng)調(diào)母親作為客體與兒童自體的重要性。他在臨床經(jīng)驗的基礎(chǔ)上,提出了被稱為“自體心理學(xué)”的客體關(guān)系論[14]。古典精神分析理論認(rèn)為自戀人格障礙,產(chǎn)生于迫切的驅(qū)力與反對驅(qū)力防御之間的內(nèi)心沖突,而在科赫特的自體心理學(xué)中,強(qiáng)調(diào)其根源來自于與看護(hù)者(通常為母親)之間令人不愉快的人際關(guān)系,由此產(chǎn)生不充分的自體感覺才是自戀人格產(chǎn)生的根源。事實上,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承認(rèn),在科赫特自體心理學(xué)理論的發(fā)展中,有關(guān)自我的對象既不是對象也不是自身,而是關(guān)系的主觀性。主體間性的概念促進(jìn)了自體心理學(xué)發(fā)展成一個完整的關(guān)系體系。從這種觀點來看,治療師越來越把自體對象與分析家的關(guān)系看作是促進(jìn)自體發(fā)展和改善的手段。因此,科赫特的自體心理學(xué)認(rèn)為,客體關(guān)系將關(guān)注點從機(jī)體功能擴(kuò)大到社會功能。將克萊因客體關(guān)系理論發(fā)展到極致的當(dāng)屬愛爾蘭人費爾貝恩,他在融合了克萊因、弗洛伊德等人的觀點后,拋棄了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理論中的驅(qū)力和本能概念,而是將客體關(guān)系作為其理論的核心,用客體尋求代替了快樂尋求,用現(xiàn)實原則代替了快樂原則,排除了與生物學(xué)特征相關(guān)的性本能、能量、驅(qū)力等概念,實現(xiàn)了由驅(qū)力模式向客體關(guān)系模式的徹底轉(zhuǎn)變[15]。因而,費爾貝恩的客體關(guān)系模式也被認(rèn)為是最為激進(jìn)的“純粹的”客體關(guān)系理論。
可見,以克萊因為代表的客體關(guān)系理論,是古典精神分析客體關(guān)系取向發(fā)展的早期形式。由于這些研究者并不完全反對古典精神分析的某些理論和概念,接受了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理論中的大部分基本概念和理論框架,仍被看作是古典精神分析的分支之一。但是,與古典精神分析關(guān)注自我的內(nèi)部沖突與指向不同,客體關(guān)系理論傾向于將客體(通常是母親)及客體關(guān)系(通常是母親與兒童的關(guān)系)置于理論和臨床研究的中心位置,將其看作是決定個體人格發(fā)展的重要影響因素,認(rèn)為人格心理的發(fā)展與變化依賴于客體關(guān)系的內(nèi)化(強(qiáng)調(diào)母親的作用),而與本能欲望、性沖動和原始驅(qū)力并沒有多大關(guān)系,這是精神分析心理學(xué)發(fā)展道路上的重大轉(zhuǎn)折,這些工作也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對心理驅(qū)力與動機(jī)的解讀。
二、精神分析客體關(guān)系理論的當(dāng)展
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有時也被稱為“心理動力學(xué)”,主要是指建立在物理學(xué)原理基礎(chǔ)之上的心理學(xué)。利用機(jī)械物理學(xué)以及本能和驅(qū)力的機(jī)械生物學(xué),弗洛伊德描述了作用于人的內(nèi)部驅(qū)力,而不是把這些方面看作環(huán)境對個體的作用或者個體與環(huán)境的交互作用。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弗洛伊德的心理動力學(xué)是一種“元心理學(xué)”[16]。在經(jīng)過幾次修正與發(fā)展后,古典精神分析理論的基礎(chǔ)面臨著嚴(yán)峻的挑戰(zhàn),這主要是由于古典精神分析已經(jīng)不能滿足現(xiàn)實應(yīng)用中的期望。以羅伊•謝弗為代表的精神分析主義者,最終對古典精神分析進(jìn)行了幾乎徹底的修正,使古典精神分析理論內(nèi)核發(fā)生了根本性改變。當(dāng)代精神分析客體關(guān)系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謝弗、斯彭斯、吉爾、魏斯與桑普森等。謝弗認(rèn)為古典精神分析采用了物理學(xué)和生物學(xué)的語言(如能量、動力、本能、驅(qū)力等),而摒棄了原本應(yīng)該是精神分析基礎(chǔ)的選擇性和意向性。這些從物理學(xué)和生物學(xué)中借用的語言妨礙了對主體本身的強(qiáng)調(diào),而主體性應(yīng)該是精神分析理論的核心。所以,弗洛伊德為了將物理機(jī)制轉(zhuǎn)換成可被理解的意義,不得不把他的結(jié)構(gòu)擬人化,將個體說成是一個獨立的實體。謝弗指出,這種擬人化的主要缺點是失去了有意義的行為,并使人類的行為失去了責(zé)任。他堅持認(rèn)為精神分析必須把心理動力學(xué)從其理論中排除出去,并把動作返還給人們。因而,謝弗在保留了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理論的某些重要概念(如伊底)的基礎(chǔ)上,確立了新的客體關(guān)系理論。謝弗認(rèn)為,要更好地吸收對社會文化和環(huán)境在人的心理發(fā)展中的作用的理解,有必要提出一個新的精神分析語言系統(tǒng),這種系統(tǒng)應(yīng)該強(qiáng)調(diào)動作語言[17]。在他的語言動作理論中,通過運用動詞或副詞,避免使用名詞和形容詞來描繪所有事件。因此,他刪除了像潛意識、伊底、驅(qū)力、沖動和心理能量這樣的名詞。但謝弗卻保留了伊底這樣的概念,他認(rèn)為伊底是引起性或攻擊行為的基礎(chǔ),由于伊底的非理性、不可調(diào)和性、不受控制性和徹底的自我中心性,更有可能與某些生理過程相聯(lián)系。可見,謝弗對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的語言系統(tǒng)做了較大修正,但他仍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古典精神分析的生物學(xué)傾向。
在謝弗的動作語言理論中,始終強(qiáng)調(diào)動作本身才是精神分析的主題,而不是另外的什么導(dǎo)致動作的發(fā)生。謝弗所指的動作不僅指可見的動作,還包括不可見的思維、記憶、幻想、希望,甚至還包括沉默,并認(rèn)為人類的這些動作都是有意義的,具有某些意圖和目標(biāo)。與古典精神分析相比,對動作的強(qiáng)調(diào)為分析對象提供了選擇和意向的新途徑。如:在心理分析過程中,分析家和分析對象一起檢驗從嬰兒期開始的動作對個體現(xiàn)在的影響,在分析家與分析對象這種客體關(guān)系的對話中,將這種影響看作是個體與環(huán)境的共同產(chǎn)物。當(dāng)謝弗用新的語言系統(tǒng)取代心理決定論和物理學(xué)的解釋時,通常在解釋和描述之間存在的區(qū)別不再存在了,因為由動作詞匯進(jìn)行的描述便成了解釋。謝弗的理論對古典精神分析的發(fā)展還在于,他認(rèn)為精神分析應(yīng)與過去保持較少的關(guān)聯(lián),而與現(xiàn)在有更多的關(guān)聯(lián),精神分析的過程是一種敘事的過程,而不是對隱藏動機(jī)的揭示。這種精神分析的敘事學(xué)轉(zhuǎn)向,使精神分析的理論迎合了當(dāng)代科學(xué)哲學(xué)的發(fā)展。在這一主張上,謝弗與斯彭斯有著極為相似的觀點[18],他們都認(rèn)為,當(dāng)分析對象在精神分析過程中描述某些心理障礙(如強(qiáng)迫癥、神經(jīng)癥等)時,這些障礙的特征就在修正的敘事中得到改變,而語言構(gòu)成了敘事這樣的動作中的經(jīng)驗。謝弗認(rèn)為精神分析應(yīng)建構(gòu)分析對象的現(xiàn)在,而不是去重構(gòu)分析對象的過去,通過患者發(fā)現(xiàn)新的事實,而不是處理歷史事實,患者的狀況才會得到改善。古典精神分析則恰恰只注重重構(gòu)和改變過去的觀念而不是現(xiàn)在。盡管謝弗的語言動作理論對古典精神分析的影響很大,但他的“嚴(yán)格的現(xiàn)實主義觀點”排除掉了精神分析中很多有價值的東西,而且他的某些激進(jìn)的觀點仍值得商榷。如,他認(rèn)為精神分析應(yīng)只關(guān)心現(xiàn)在而不必注重過去,事實上,正是被壓抑的過去才是精神分析的核心,如果用現(xiàn)在的結(jié)構(gòu)取代過去的結(jié)構(gòu),那么精神分析也就剩不下什么了。對弗洛伊德心理動力學(xué)的元心理學(xué)進(jìn)行更大的修正與發(fā)展的還包括魏斯和桑普森,他們共同提出了“潛意識計劃”,將精神分析作為一種治療心理障礙的主要方法,對弗洛伊德的心理動力決定論持否定態(tài)度,并決定徹底拋棄作為決定力量的伊底。在人本主義“自我實現(xiàn)”理論的影響下,他們提出病人的能力是他們自己的治療過程的動力的觀點。
他們的方法主要包括四種假設(shè):(1)病人有改變潛意識目標(biāo)的意愿;(2)阻礙達(dá)到目標(biāo)的“致病信念”是心理障礙的原因;(3)病人用來接受或反對分析家有關(guān)信念的檢驗;(4)是病人而不是分析家一直被看作導(dǎo)致改變的原因,分析家的任務(wù)就是幫助病人證明痛苦的信念不成立,并獲得安全感。作為一種方法,他們強(qiáng)調(diào)病人“致病信念”的根源,潛意識中的害羞、內(nèi)疚、恐懼都來自于真實的經(jīng)驗,而不是源自于生物驅(qū)力和伊底的能量。盡管早期精神分析的客體關(guān)系理論都強(qiáng)調(diào)客體關(guān)系(尤其是母嬰關(guān)系)的重要性,但魏斯和桑普森卻重新強(qiáng)調(diào)記憶在“致病信念”改變中的重要性。在這一點上,他們與謝弗與斯彭斯關(guān)注現(xiàn)在而忽略過去的觀點并不一致。魏斯和桑普森認(rèn)為,病人癥狀改善的關(guān)鍵在于分析家能順利通過病人的檢驗,通過檢驗之后,病人會獲得安全感,能夠?qū)⒇?fù)性記憶從壓抑中釋放出來,將過去與現(xiàn)在進(jìn)行整合。這種觀點幾乎放棄了弗洛伊德心理動力理論中所有的核心內(nèi)容,只保留了童年期創(chuàng)傷的壓抑,對古典精神分析進(jìn)行了較大的發(fā)展,除了從壓抑的強(qiáng)調(diào)上能看到古典精神分析的影響外,其他的觀點更像是人本主義心理學(xué)的心理治療觀。隨著后現(xiàn)代哲學(xué)的發(fā)展,在精神分析心理學(xué)之外,一個與精神分析客體關(guān)系理論密切相關(guān)的取向即精神分析的詮釋學(xué)傾向正快速發(fā)展。盡管弗洛伊德認(rèn)為精神分析應(yīng)該屬于自然科學(xué)的分支,羅伯特•斯蒂爾卻明確指出精神分析是一門詮釋學(xué)學(xué)科,精神分析的目標(biāo)不是通過潛意識挖掘分析對象的心理沖突,而是通過對話來解釋分析對象(客體)言語的意義。斯蒂爾認(rèn)為,詮釋學(xué)的核心觀點應(yīng)該是理解存在于語言、意義、歷史和反思中的事實。在對詮釋學(xué)的特征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xué)說的特征進(jìn)行比較的基礎(chǔ)上,斯蒂爾提出:“弗洛伊德的全部工作創(chuàng)立了一種詮釋學(xué)研究,在諸如弗洛伊德的《圖騰與禁忌》、《文明及其缺憾》和《摩西與一神教》等作品中,存在大量關(guān)于理解、語言、方法、歷史以及反思的闡述與現(xiàn)代詮釋學(xué)極為相似”。法國20世紀(jì)思想家利科也曾明確表示過,精神分析是一門解釋性的藝術(shù),它所關(guān)心的是通過解釋表面現(xiàn)象而發(fā)現(xiàn)隱藏在它背后的東西,由此在分析者和分析對象之間創(chuàng)造一種被分享的理解。綜上所述,精神分析的詮釋學(xué)傾向主張精神分析不處理那些可以說明的事實,而是處理那些只有通過理解才可以得到的意義,把分析對象的夢、愿望、聯(lián)想等看作是其創(chuàng)作的“文本”,借助詮釋尋求意義,以此達(dá)成對患者的治療。在弗洛伊德之后,盡管精神分析經(jīng)歷了多次修正和發(fā)展,但古典精神分析一些最本質(zhì)的核心概念仍被保留了下來,雖然精神分析的詮釋學(xué)祛除了古典精神分析最核心的本能驅(qū)力和伊底等生物學(xué)概念,但并沒有顛覆潛意識的核心地位,使?jié)撘庾R過程意識化仍然是精神分析詮釋學(xué)傾向的根本目的,主體與客體的語言對話和分析仍然是最主要的手段,主體對客體的理解與詮釋過程仍然是達(dá)到治愈的基本途徑。
三、結(jié)語
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作為一種理論體系和治療方法,在他百年之后的發(fā)展中已經(jīng)很難找到其原始特征,在歷經(jīng)幾次大的學(xué)派裂變和理論發(fā)展之后,當(dāng)代精神分析理論和方法改變了古典精神分析的大部分本質(zhì)特征,遠(yuǎn)離了它的生物學(xué)和物理學(xué)假設(shè)。精神分析的多次裂變既帶來了其元心理學(xué)的分裂,也帶來了新精神分析的發(fā)展,無論修正與發(fā)展的程度如何,始終無法完全根除弗洛伊德的影響(要么保留內(nèi)驅(qū)力,要么保留潛意識)。但是,無論是早期阿德勒等與弗洛伊德分道揚鑣建立各自的理論體系,霍尼等社會文化學(xué)派對精神分析的外部指向的確認(rèn),克萊因等客體關(guān)系理論將精神分析確認(rèn)為一種關(guān)系取向,謝弗代替弗洛伊德元心理學(xué)的動作語言,還是斯蒂爾等將精神分析與詮釋學(xué)的融合傾向,他們似乎都達(dá)成了一個共識,即精神分析已經(jīng)從驅(qū)力與沖突的內(nèi)部指向,轉(zhuǎn)為強(qiáng)調(diào)促使個體心靈愈合的外部客體及其關(guān)系的解釋。當(dāng)代精神分析的客體關(guān)系取向,已經(jīng)成為順應(yīng)當(dāng)代社會文化與科學(xué)哲學(xué)發(fā)展趨勢的一股潮流。在這種傾向的指引下,還會有一批跟隨者繼續(xù)對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理論和當(dāng)代的精神分析的客體關(guān)系理論進(jìn)行修正和發(fā)展,并不斷滿足社會和時代治愈人類心靈的要求。
作者:姜永志單位:內(nèi)蒙古民族大學(xué)教育科學(xué)學(xué)院/心理健康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