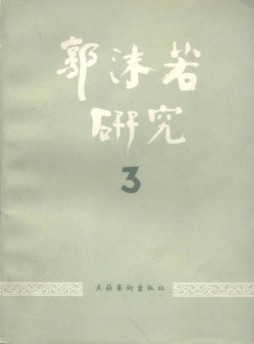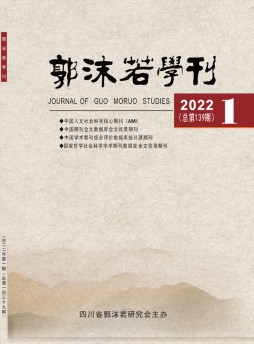郭沫若墨學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郭沫若墨學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學術背景
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郭沫若以其戰士的勇氣和詩人的激情在史學、文學甚至哲學等諸多領域都留下了獨特的印記。特別是在史學方面,他關于中國社會分期和性質的大膽論斷影響深遠,以致我們有時甚至因此而忽略了他在史學方面的其它成就。
討論郭沫若的學術研究,特別是諸子學研究,不應忽視他幼年時所受的教育。郭沫若幼年接受的是傳統的舊式教育,飽讀了《四書》、《五經》,并且學習了《爾雅》、《說文》、《群經音韻譜》等書,為以后的學術研究奠定了良好的文字基礎。他接觸諸子學比較早,大約是在他十
三、四歲時,從讀莊子開始的,他被《莊子》那恣肆的文風所吸引,也為其形而上的思想而陶醉。其后,他又讀了《道德經》、《墨子》、《管子》、《韓非子》等先秦諸子著作,甚至還抄錄過一些諸子文章中的警粹性的句子。他自己說:“這些雖然說不上是研究,但也總可以說是我后來從事研究工作的受胎時期了。”
郭沫若與墨學的真正機緣可以從20世紀二十年代算起。墨學是近代顯學,就郭沫若的文化氣質來說,他幾乎不可能放過時代思潮中任何一個在當時社會具有廣泛影響的學術文化現象,在甲骨文研究上他是這樣,在諸子學研究上他也是如此,特別是在墨學研究上他更是如此。早在20世紀二十年代初,梁啟超出版《墨子學案》一書,給墨學以較高的地位和評價,郭沫若就以其敏銳的學術視角寫了篇具有論爭性質的文章《讀梁任公〈墨子新社會之組織法〉》,發表了不同的觀點和聲音。四十年代,他又在《青銅時代》、《十批判書》等論著中進一步闡述了自己關于墨學的看法,表達了獨特的學術觀點。
二、墨學研究述要
墨學研究是郭沫若學術生涯中最具爭議性的問題之一。自他的第一篇墨學文章《讀梁任公〈墨子新社會之組織法〉》到四十年代的有關墨學的論文,對墨學的看法上已經有很大不同。他后來談到自己在20世紀二十年代對墨學的看法時說:“對于墨子我從前也曾謳歌過他,認為他是任俠之源。《墨經》中的關于形學和光學的一些文句,我也很知道費些心思去考察它們,就和當時對于科學思想僅據一知半解的學者們的通習一樣,隱隱引以為夸耀,覺得聲光電化之學在我們中國古人也是有過的了。”不過,后來,郭沫若對墨家的認識有了很大的轉變,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成書于1929年,其中也論及墨學,指出墨家宗教是“反革命”。四十年代,他對墨學的看法更加系統化,否定的態度也更明確:“我認為他純全是一位宗教家,而且是站在王公大人立場的人。前后看法的完全相反,在我是有客觀根據的,我并沒有什么‘偏惡’或‘偏愛’的念頭。我的方法是把古代社會的發展清算了,探得了各家學說的立場和根源,以及各家之間的相互關系,然后再定他們的評價。”郭沫若的墨學研究的重點篇章在四十年表,我這里所要論及他的墨學研究以四十年代的研究為準。
20世紀四十年代,郭沫若出版了《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等在當時學術界頗具影響的著作,其中有些篇章對《墨子》思想作了深入大膽的研究和評判,特別是在《墨子的思想》、《孔墨的批判》、《名辨思潮的批判》、《先秦天道觀之進展》等論文中較為全面地闡述了自己對墨學的有關看法和基本觀點。
墨子的生平缺乏足夠的歷史資料,歷來的研究者只能從非常有限的資料中推斷,由于史料的運用各不相同,因而結果也不相同。作為一個重視考證的歷史學家,郭沫若對墨子的生平考證也表現出一定的興趣。他認為,由于史料有限,墨子的家世不祥,《元和姓纂》以為墨子是“孤竹君之后”毫無根據。他基本贊同文史學家錢穆的看法,從文字演化的角度來考證墨子的身世:“墨”本刑徒之稱,而且“墨子兼愛,摩頂放踵”,以為“摩頂者摩突其頂。蓋效奴作髡鉗,所以便事。放踵則不履不綦,出無車乘”。從而認為或者墨子的先人是職司刺墨的賤吏,后世以為氏。總之墨子和老子、孔子比較起來,出身當得是微賤的。老子為周守藏史,孔子的先人是宋國的貴族,他們都是當時的上流人物,故他們的陳義甚高,而墨子則迥然不同,只是一味的保守。墨子的出生稍晚于孔子,作為孔子的反對命題而出現。郭沫若不僅考證了墨子的身世,而且試圖從其出身來探尋其思想的根源。
郭沫若的墨學研究是以他稱之為《墨經》作基本材料的。有必要指出,他所說的《墨經》并不是我們通常認為的《經》上下、《經說》上下及《大取》、《小取》,而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反映墨家十項主張的那些篇文章,包括《兼愛》、《非攻》、《尚賢》、《尚同》、《天志》、《明鬼》、《節用》、《節葬》、《非樂》、《非命》那一組文章。他認為,討論墨子的思想,不應超越這些文章的范圍。
在眾所周知的墨子十項主張中,究竟哪些是其思想的根本觀念,研究者們意見不盡相同。郭沫若明確指出:墨子有“天志”以為他的法儀,這是他一切學術思想的一根脊梁。抽掉了這條脊梁,墨子便不能成為墨子。墨子的“天志”,是天老爺之意志,也就是“天下之明法”,也是他的規矩,就如沒有規矩不能成其為輪匠一樣。墨子信仰上帝,更信仰鬼神,上帝是宇宙中的全能全智的最高主宰,鬼神要次一等,是上帝的輔佐。上帝鬼神都是有情欲意識的,能生人,能殺人,能賞人,能罰人。這上帝鬼神的存在是絕對的,不容許懷疑。郭沫若批評了那些認為墨子的“天志”是“神道設教”的理論,認為“神道設教”是儒家的做法。由此他指出,墨子是一位宗教家。其根本思想是天志、明鬼。他是把殷、周的傳統思想復活了。他是肯定了一位人格的天,自然也肯定了鬼神。墨子的兼愛、尚賢、非攻、節用等等學說都是以這天鬼為規矩而倡導出來的。
墨子雖然是宗教家,但并沒能夠創立一個宗教。郭沫若說:
墨子生在二千四五百年前,以他的精神和主張盡可以成立一個中國獨特的宗教,而在戰國年間的墨家學派也的確有過這樣的趨勢的,如等于教主的所謂“巨子”之衣缽傳授即其一例。然而結果沒有形成,后來反讓儒家和道家來奪了他的席,而儒家也并不成其為宗教,道也僅是印度教的拙劣的翻版。這在研究中國古代史上倒確實可以成為一個問題。為什么在奴隸制解體以后中國不能產生一個獨自的宗教呢?在這兒我的看法是,中國的地理條件有很大的關系。各個世界大宗教都產生在熱帶國家。那些地方的貴族們一樣受著自然界的壓迫,故爾容易在幻想中去討生活,在生前想求得一種法悅以忘卻現世的辛苦;在死后自己升上天堂,把敵對者打進地獄里去。中國是溫帶國家,天堂何如現世的宮殿?地獄何如現世的監牢?故爾中國貴族最質實,無須乎再有升天入地的必要了。因此中國的統治者早就知道歡迎比較更現實的工具,而冷落了那種虛無飄渺的東西。這,怕就是固有宗教雖是具體而微,而終究未能完成的根本原因吧?
郭沫若從地理環境分析了墨子沒有能夠創立宗教的原因,不免有些牽強。因為宗教的起源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有著復雜社會歷史根源,環境因素遠非一個重要的成因。從宗教的起源看,創立宗教的大多是被壓迫者,他們以宗教這種特有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愿望,以求得一種精神的慰藉。前面已經說過,“天志”只不過是墨家兼愛的工具,兼愛才是的根本觀念。
對于一般研究者認為墨學根本觀念的“兼愛”,郭沫若認為在墨子思想體系中起核心作用,與非攻一起構成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兼愛”是從積極的方面來說的,“非攻”是從消極的方面來說的,“非攻”只是“兼愛”另一種說法。不過,他對墨子的“兼愛”思想也持否定態度,認為其“最大的矛盾是承認著一切既成秩序的差別對立而要叫人去‘兼’”,名義上談“兼愛”,實際上是“偏愛”。他說:
《墨子》的“兼愛”主張頗是動人,也頗具特色。本來儒家道家都主張愛與慈,但沒有墨子的“兼”。大約墨子在這兒是有點競賽心理的:你愛吧,唉,我還要比你愛得更廣些!這樣把愛推廣到無限大,其實也就是把愛沖淡到沒有了。所以墨子一方面主張“兼愛”,一方面又主張“去愛”,大約在他的內心中或者下意識中,是把“兼愛”作為“去愛”的手段把?……他的最大矛盾是承認著一切既成秩序的差別對立而要叫別人去“兼”。……既承認著這一切的差別而叫人“兼愛”,豈不是叫多數的不安樂者去愛那少數的安樂者!而少數的安樂者也不妨做一點愛的施予而受著大多數人的愛了。請問這所謂“兼愛”豈不就是偏愛!
郭沫若把墨子看成既有秩序的維護者,一方面要維護既有的秩序,另一方面又要“兼愛”,是不可能的。這里有郭沫若立論的一個根本依據:那就是在他看來,孔子是支持亂黨的,墨子是反對亂黨的,而“亂黨”代表新興階級的利益。墨子既然是維護既定秩序的,又怎么去“兼愛”呢?出于同樣的理由,他認為墨子的“非攻”實際上也是從維護既定秩序出發的,名為“非攻”,實際上是“美攻”。因為墨子是承認著私有財產,把私產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并且承認著國家的對立的。由此他得出結論,墨子的“非攻”只是在替侵略者制造和平攻勢的煙幕而已。他進一步指出:
兼愛的結果便不會攻亂賊竊,不兼愛呢便會有攻亂賊竊;反對攻亂賊竊便是反對不兼愛,故爾“非攻”只是“兼愛”的另一種說法而已。因而在本質上,“非攻”也依然是對于所有權的尊重。……故“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攘殺其牲牷,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器重”,這比殺人越貨是更加不義了。“勁殺其萬民”與“攘殺其牲牷”并列,而與“攘人犬豕雞豚者”,“取人牛馬者”同等,故人民依然還是所有物;而攻人之國實等于侵犯最大的私有權而已。這就是兼愛與非攻說的核心,尊重私有財產權并保衛私有財產權。故他這一套學所并不重在愛人,而是重在利己,不是由人道主義的演繹,而是向法治刑政的歸納。……攻是侵犯私有權,非攻是反對侵犯私有權,因而非攻本身就是戰爭。
郭沫若從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出發,以當時的生產資料私有制來分析墨學的“兼愛”、“非攻”說,指出墨家的兼愛、非攻實際上是維護財產私有制,因而兼愛、非攻不是從人道主義出發,而實際上是利己。有必要指出,墨家不否認“利”,主張“兼相愛,交相利”,從這個角度說,兼愛、非攻既是利人,又是利己。但并不是如同楊朱那樣“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的利己一樣的利己。
與上述論斷相聯系,郭沫若對“尚同”也持否定的觀點,認為墨子的“尚同”是要建立絕對的君主專制,是不許人民有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甚至行動的自由。是為了“一同天下之視聽,尤須獎勵告密與厲行連坐”。他說:
以貴者智者統一天下的思慮,便是墨子的政治思想。所謂“一同天下之義”,“上之所示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上同而下不比”,不許你有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甚至行動的自由。要“美善在上而怨仇在下,安樂在君而憂戚在臣”,“君有難則死,出亡則從”,簡直是一派極端專制的奴隸道德!
他還在另一篇文章中說:
以王的意志統一天下的意志,以王的是非統一天下的是非。當然王之上也還有天,王也得上同于天。但,天是什么呢?天不過是王的影子。故結果是王的意志就是天的意志,王的是非就是天的是非。
郭沫若看到了墨子尚同有其不完善的地方,但他把這種不完善的地方顯然夸大了。墨子的尚同,并非是要“以貴者智者統一天下的思慮”,而是與尚賢密切相關的。在墨子看來,統治者應該是賢人,而不是世襲的貴族。有賢則舉之,無能則下之。這實際上是反對貴族階層的世襲統治,當然不是主張絕對的專制。而且,墨子還有“天志”,作為其尚同的“規矩”和后援。后期墨家把墨子的“尚同”論進一步完善,說:“君,臣萌通約也”。即是統治者是從民眾中產生的,與民眾有一種契約的關系。這是一種政治理想。
至于墨子的“非命”,郭沫若認為是一種宗教式的皈依,“正因為他尊天明鬼所以他才‘非命’。他是不愿在上帝鬼神的權威之外還要認定有什么必然性或偶然性的支配。在他看來上帝鬼神是有生殺予奪之權的,王公大人也是有生殺予奪之權的,王公大人便是人間世的上帝鬼神的。”。他還指出,墨子的“非命”與其宗教思想是矛盾的,他說:“宿命論固然應當反對,墨子學說里面似乎也以這一項為最有光輝。但奇妙的是和他的學說系統和不調和”。“宿命論是和宗教迷信不可分的,而倡導非命的墨子卻是尊天明鬼的人,這不是一個奇事嗎?”確實,郭沫若揭示了《墨子》思想中“天志”與“非命”的矛盾,這與他的立論前提有根本的關系,他首先給墨子定論為宗教家。還是梁啟超在這點上說得好,墨子強調“力行”,所以非命,天的意志就是叫人“非命”。以“天志”為宗教的郭沫若當然看不到這一點,而且,在他看來,墨子既然代表“王公大人”的利益,非命就很奇怪了。
至于“節用”與“節葬”,郭沫若認為是一套消極的經濟政策,和老百姓的生活并沒有直接的關系。因為老百姓的用是節無可節,葬也是節無可節的。因而,他的整套學說都是以“王公大人”為對象的,“王公大人”的不合理的消費如果節省一些,當然也可以節省一些民力。此外,“節用”與“節葬”的另一個目的,是在反對儒家的禮。他還說:
一味地以不費為原則,以合適用為標準,而因陋就簡,那只是阻擾進化的契機。墨子的專門強調節用,出節用之外沒有任何積極的增加生產的辦法,這不僅證明他的經濟思想的貧困,像“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于瓴缶”的民間音樂,也在所反對之例,簡直是不知精神文化為何物的一種狂信徒了。
郭沫若從社會生產發展與消費的關系角度指出節用、節葬的弊端,這有一定的合理性。不過,墨家的節用、節葬的經濟政策正是針對“王公大人”提出來的,是當時社會“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的反映,因此不能夠全部否定。
郭沫若對墨子思想中只有一點稍加肯定,那就是墨家的救世的精神,他說:“墨子正是一位特異人格的所有者,他誠心救世是毫無疑問的。雖然他在救世的方法上有問題,但他那‘摩頂放踵,枯槁不舍’的精神,弟子們的‘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態度,是充分足以感動人的。就是這樣被人感佩,所以他的思想真像一股風一樣,一時之間布滿了天下,雖然被冷落了二千年,就到現在也依然有人極端的服膺。”但就是這一點肯定,他的贊賞態度也非常有限,他隨后就說:“人是感情的動物,頭腦愈簡單,愈是容易受暗示,受宣傳,因而墨家的殉道精神,在我看來,倒并不是怎樣值得夸耀的什么光榮的傳統”。他還說,“墨子本人是一位特殊的人物,那是毫無問題,他存心救世,而且非常急迫,我也并不想否認,但他的方法卻是錯了。莊子的批評,我覺得最為公允”。“盡管他的人格怎樣特異,心理的動機是怎樣純潔,但他的思想有充分反動性,卻是無法否認的。在原始神教已經動搖的時候,而他要尊崇鬼神上帝。在民貴君輕的思想已經醞釀著的時候,而他要‘一同天下之義’。不承認進化,不合乎人情,偏執到了極端,保守到了極端,這樣的思想還不可以認為反動,我真不知道要怎樣才可以認為反動”。
墨學由盛到衰乃至中絕,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郭沫若也作了自己的考察,他指出:“墨子的思想從歷史的演進上看來,實在是一種反動。他的立論根據異常薄弱。但他的學術一出卻是風靡一時,不久便與儒家和道家的楊朱三分天下。揆其所以然的原故,大約即由于他的持論不高,便于俗受。本來殷、周二代都是以宗教思想為傳統的,尤其是周代乃利用宗教思想為統治的工具,宗教思想是浸潤于民間的。”至于墨學衰落,郭沫若以為:第一是由于墨家后學多數逃入儒家道家而失掉了墨子的精神,第二是由于墨家后學過分接近了王公大人而失掉了人民大眾的基礎。此外,它的所以不傳是因墨子后學溺于變而流于文,取消了自己的宗教特質。郭沫若的分析與近代學人的研究幾乎都不一樣。這是他墨學研究所謂的“人民本位”立場的必然結果。
三、《墨經》研究
郭沫若是走在時代浪潮前沿的學者,他當然不可能忽視墨學中很有價值的《墨經》部分。在《墨子的思想》和《孔墨的批判》中,沒有關于《墨經》研究的文字。但是在《十批判書》的另一篇文章《名辨思潮的批判》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研究《墨經》的。顧名思義,《名辯思潮批判》是考察研究先秦名辯思潮。郭沫若注意到《墨經》六篇與《墨子》一書其它篇章的表達形式及成書時間、內容均不相同,其中包含著邏輯學的內容,因而他沒有把《墨經》研究放在《墨子的思想》和《孔墨的批判》中,而是與先秦名辯學一起研究。他以《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為材料,考察墨家的“辯”。
郭沫若認為,他在《墨經》研究中有一大發現,而又被一般的研究者所忽視,那就是六篇文章中的主張不一致,甚至是完全對立的,《經上》、《說上》與《經下》、《說下》幾乎可以說是觀點對立的兩派。他從《莊子?天下篇》記載墨家后學“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奇偶不仵之辭相應”出發,指出“相訾”即是相反駁,“相應”即是相和同,墨家后學派別對立是公認的事實。觀點是需要材料來支撐的,郭沫若證明自己觀點的材料是先秦哲學史上十分著名的“堅白之辯”與“同異之辯”。眾所周知,墨家后學參與了先秦一些重要哲學命題的辯論并且在辯論中觀點分明,這是所有研究者公認的事實。郭沫若所說的被大家忽視的并不是這些,而是墨家后學內部在這兩個問題上觀點也不相同,甚至相反。具體說,在堅白論這個論爭的焦點上,“《經上》派和《經下》派的見解是完全相反。《經上》派主張盈堅白,《經下》派則主張離堅白”。《經上》派主張“堅白不相外也”,與公孫龍堅白相離的觀點相反。而《經下》則說:“一,偏棄之。謂而固是也,說在因(否)。可偏去而二,說在見與俱、一與
二、廣與修。”《說下》“二與一亡,不與一在,偏去。……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廣修,堅白。”郭沫若認為這是“離堅白”的觀點,與公孫龍的觀點完全一致。由此他得出結論,《經上》派與公孫龍派觀點對立,而《經下》派與公孫龍派觀點一致。為什么在墨家后學內部會有這樣觀點分明的兩派,郭沫若的解釋是就像《墨子》一書中不少篇章有上中下三篇一樣,是墨家不同派別的觀點,而后人在纂輯成書時一并收錄。同時,郭沫若認為《經上》派與《經下》派在“同異”的觀點上也不相同,《經上》派的同異觀是根據常識來的,《經下》派在同異觀上則承受惠施的主張,有時和公孫龍的見解也十分接近。《經上》派把同異均分為“重體合類”四種,又列出“同異交得”,都不外是常識的歸納。《經下》派則主張“物盡異”,“物盡同”,同異有大小。與惠施的“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是完全合拍的。,不過,他指出,《經上》派與《經下》派在同異觀上的對立不如堅白論明顯。《墨經》中另外兩篇《大取》、《小取》的見解與《經上》派接近,只是時代的先后不同。《大取》、《小取》的年代應該在后。由此,他得出結論,《經下》派受惠施、公孫龍的影響極深,與《經上》派實不相同。《經下》派是“離堅白,合同異”,《經上》派是“盈堅白,別同異”。既然《墨經》六篇中反映了涇渭分明的兩派的觀點,為什么又同屬于墨家呢?郭沫若給出的解釋是:《經上》、《經下》與《大取》、《小取》亦有相同之點。他們同樣承認辯的價值。《經上》:“辯,爭彼也;辯勝,當也。”《經下》:“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
郭沫若之所以得出《墨經》分為《經上》派和《經下》派,源于他對《墨經》的解讀,特別是他對《經下》一段文字的解讀。《經下》有這樣一段文字:“一,偏棄之。謂而固是也,說在因。不可偏去而二,說在見與不見、俱一與
二、廣與修。”郭沫若認為,這段文字反映了《經下》派“離堅白”的觀點。我認為,無論在這段文字的斷句和理解上,郭沫若的觀點均值得推敲。首先,他把“不可偏去而二”的“不”字與上文連讀,把“說在見與不見、俱一與
二、廣與修”讀為“說在見與俱、一與
二、廣與修”,導致對原文的理解錯誤。其次,這段文字實際上包含了三條經文,而不是郭沫若認為的一條內容。其中最關鍵的一條經文“不可偏去而二,說在見與不見、俱一與
二、廣與修”。《經說》應該是“不。見、不見離,
一、二不相盈,廣、修;堅、白相盈”。而不是郭沫若認為的“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廣修,堅白”。這條“經”與“說”正好說明了“堅白相盈”,而不是“堅白相離”,與公孫龍的“離堅白”大相徑庭。《經下》另一條“撫堅得白,必相盈也”,也證明了《經下》持堅白相盈的觀點。《經上》與《經下》在堅、白關系上并無根本的沖突。當然,我也并不想否認,墨家后學在一些具體問題的觀點上有差異,只不過是對一些問題的理解不同罷了,而與公孫龍及其他辯者在堅白、同異關系上卻有著根本的沖突。因而,郭沫若在這個問題的看法不可取。
事實上,郭沫若對《墨經》的誤讀不止于此,他對《墨經》中有關知識論的解讀也存在著根本的錯誤。《經下》有這樣一條:“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經說下》:“知,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惟以五路知,久不當。以目見,若以火見。”這是郭沫若的校讀。他由此認為“這是說感官的知識不能得到真知識,而可以獲得真知識的主動者在感官之外,但這主動者為誰,卻沒有說出。這和公孫龍的見解相近”。這樣的解釋與《墨經》的原意大相徑庭。前期墨家重視感性認識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墨家后學把這種知識論發揚光大,并且強調,只靠感性認識還不夠,還需要理性認識,才能認識事物的本質。這是墨家在知識論上的一大貢獻,郭沫若卻由于對《墨經》的誤讀而導致相反的觀點,從而得出墨家否認感性認識作用的結論,這是非常錯誤的。
郭沫若對《墨經》的研究不止于此,《墨經》中包含了大量的邏輯思想,許多研究者都很重視,郭沫若也作了一定的努力,并且試圖把墨家邏輯與印度因明相比較,指出墨家的類、理、故有些像印度因明學的三支宗、因、喻,但他沒有繼續下去,只是淺嘗即止。
四、墨學研究特點
20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思想文化界,爆發了著名的關于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和社會史問題的論戰,郭沫若是后一問題論戰的主將,在那場論戰中,郭沫若寫了著名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指導,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特征作了詳盡的考察和闡述。同時也表明,郭沫若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來指導自己的學術研究。那時的中國,處于紛亂動蕩之中,傳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不僅僅是一種思想文化思潮,更多的是一種政治斗爭的指導思想,或者說是意識形態的武器,因而對馬克思主義缺乏理性的考察和全面深入的研究,用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政治斗爭的武器取得了驕人的戰績,但作為學術研究的指導思想和方法論,雖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績,卻不可避免地帶有片面性。特別是對于郭沫若來說,有政治斗爭的熱情,又急于用世,其學術研究的時代性和局限性就表現得非常明顯,特別是那些非考證性的學術研究。郭沫若的墨學研究表現出下述特點:
其一,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為指導。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1954年新版引言》中說:“掌握正確的科學的歷史觀點非常必要,這是先決的問題。”說明他對學術研究的理論指導是非常重視的。用什么樣的理論指導自己的學術研究,這是個學術研究的關鍵問題之一,郭沫若在回顧自己學習和研究的經歷時,深有感觸地說:“辯證唯物論給了我精神上的啟蒙,我從學習著使用這個鑰匙,才認真把人生和學問的無門關參破了,我才認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學問的意義。”他比較系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開始于一九二四年,這就是通過翻譯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來鉆研馬克思主義。這部二十萬字的著作的翻譯,使他具有了初步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形成了他思想的“一個轉換時期”。在亡命日本的十年中,他深入鉆研思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著作,并明確以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方法”“為向導”來研究我國古代社會。他對當時學術界的流行的學術研究方法很不以為然,說:“談‘國故’的夫子們喲!你們除飽讀戴東原、王念孫、章學誠之外,也應該知道還有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沒有辯證唯物論的觀念,連‘國故’都不好讓你們輕談’。”因而,他在《跨著東海》一文中談自己的中國古代思想研究時說:“我主要是想運用辯證唯物論來研究中國思想的發展,中國社會的發展。自然也就是中國歷史的發展。反過來說,我也正是想就中國的思想,中國的社會,中國的歷史,來考驗辯證唯物論的適應度。”1930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標志著郭沫若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唯物史觀來指導自己學術研究的真正開始。其后,他又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唯物史觀為指導,對中國傳統文化作比較全面的省察,《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即是其產物。
郭沫若的墨學研究主要是在20世紀四十年代,當時他已經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因而,他在墨學研究中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這主要表現在他試圖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出發,不把先秦墨家思想學說看著一個孤立的現象,而是“以一個史學家的立場來闡明各家學說的真相”。在研究先秦墨家之前,他已經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社會、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作了系統的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礎上,對先秦的哲學思想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先秦天道觀之進展》把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作為一個系統來研究,墨子的思想成為其中的環節之一。墨子非儒,郭沫若指出是由于他們在天道觀上不一樣,他說:“老子和孔子在根本上都是泛神論者,而在肯定人格神的宗教家看來,便都是無神論者。故爾到了宗教家的墨子他們便一樣的非毀了起來。”他用唯物史觀來研究墨學的另一表現是以一種新的社會價值觀、歷史觀,即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價值觀去評判墨家思想學說,給墨家思想學說以新的評判,指出墨家學說的在歷史上的地位。
有必要指出,郭沫若這一時期對先秦諸子的研究,在于通過對意識形態的研究,為馬克思主義史學服務。他把意識形態的變化和社會性質的變革結合在一起。他說:“我對于古代社會的面貌更加明了之后,我的興趣便逐漸轉移到意識形態的清算上來了”,目的是要闡述“古代社會的機構和它的轉變,以及轉變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郭沫若的出發點是為馬克思主義史學服務的。可另一方面,使他的墨學研究意識形態化,學術價值受到了限制,他對墨家思想學說所下的許多結論經不住推敲,其學術價值打了折扣。
其二,在墨學研究中以“人民為本位”。郭沫若的墨學評判有個標準,那就是看墨學是否合乎人民的利益,即“人民本位”的立場。他在《十批判書?后記》中說:“批評古人,我想一定要同法官斷獄一樣,須得十分周詳,然后才不致有所冤枉。法官是依據法律來判決是非曲直的,我呢,是依據道理。道理是什么呢?便是以人民為本位的這種思想。合乎這種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惡。”所謂的“人民本位”,就是以當時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為本位。在對先秦諸子學說的評判中,就是要看他的學說和主張是為人民著想還是為王公大人著想。他認為,“孔子是袒護亂黨,而墨子是反對亂黨的人!這不是把兩人的根本立場和所以對立的原故,表示的非常明白嗎?亂黨是什幺?在當時都要算是比較能夠代表民意的新興勢力。”因而,他得出“孔、孟之徒是以人民為本位的,墨子之徒是以帝王為本位的,老、莊之徒是以個人為本位的”。因為“墨子之徒以帝王為本位”,他對墨家的思想學說基本持否定態度。指出其不科學、不民主、反人性、反進化。
必須指出,郭沫若既是一位文化人,又是一位直接從事政治活動的活動家。在一個社會動蕩、戰爭頻仍而政治形勢又變化多端的時代,他評判古人,難免受到他所在的政治環境的影響和制約。他的政治活動影響著他的學術研究,并使其學術研究深深打上了意識形態的烙印。這種急于用世為政治而學術的心理,使他的學術文章時而表現出一種對社會現實的影射。他對《墨子》“尚同”的批判實際上表現了他對當時政權專制的反抗。他的墨學研究中充斥了許多政治批判的用語:諸如反對亂黨、忠于主上、人民利益等等。
也由于政治斗爭對學術的影響,郭沫若的墨學研究矛盾之處不少。他一方面認為墨子出身微賤,另一方面又說墨子代表“王公大人”的立場,為什么出身微賤的墨子要代表“王公大人”的立場呢?郭沫若沒有能夠給出令人信服的解答。此其一。其二,郭沫若墨學研究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唯物史觀為指導,唯物史觀強調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那么,墨家思想學說是戰國時代的產物,郭沫若在研究時卻常常以自己所在的時代的政治斗爭的需要來評判,又背離了唯物史觀。這又是一個難以解決的矛盾。而且,這是郭沫若墨學研究中最根本的矛盾。
其三,從儒墨對立的角度來研究墨學。在郭沫若的《先秦天道觀之進展》一文中,他就注意探究先秦各家思想的邏輯聯系,特別是在天道觀上的聯系。他指出在天道觀上,孔子是泛神論,而墨子肯定人格神,故墨子批評儒家學說。在《孔墨的批判中》,他把儒家思想與墨家思想作比較研究,不僅指出他們在政治立場、宗教思想、社會經濟思想上的對立,而且指出了儒墨對立的思想根源。他肯定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先進性、民主性,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墨家思想具有保守性、落后性、專制性,代表王公大人的利益。進而指出,墨子是作為孔子的反對命題而出現。從比較的角度來探討儒墨的關系,從學術方法上來講這是一個進步,因為一方面這是把不同的思想學所作為一個整體的系統來考察,從而探索思想發展的規律性。另一方面,也擴大了學術研究的范圍。但是,郭沫若在儒墨的比較研究中有讀多牽強附會之處,上文已經指出,他不是從學術發展的自身規律來綜合考察儒墨的關系,而是受政治斗爭和意識形態的限制來考察儒墨的對立,這是不可取的。
【注釋】
1《后記——我怎樣寫〈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十批判書》第489頁。東方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
2《后記——我怎樣寫〈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十批判書》第488頁。
3同上,第493頁。
4《青銅時代》。《郭沫若全集?歷史編》(一)第362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
5《墨子的思想》。《郭沫若全集?歷史編》(一)第464頁。
6《青銅時代》。《郭沫若全集?歷史編》(一)第361頁。
7《十批判書》第111-112頁。
8《青銅時代》。《郭沫若全集?歷史編》(一)第471頁。
9《墨子的思想》。《郭沫若全集?歷史編》(一)第472頁。
10同上,第472、473頁。
11《十批判書》第115-116頁。
12《十批判書》第113頁。
13《墨子的思想》。《郭沫若全集?歷史編》(一)第466頁。
14《十批判書》第112頁。
15《墨子的思想》。《郭沫若全集?歷史編》(一)第475頁。
16《孔墨的批判》。《十批判書》的123頁。
17《孔墨的批判》。《十批判書》的117、118頁。
18《墨子的思想》。《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469頁。
19《墨子的思想》。《郭沫若全集?歷史編》(一)第476頁。
20同上,第477頁。
21同上,第484頁。
22《青銅時代》。《郭沫若全集?歷史編》(一)第362頁。
23《墨子的思想》。《郭沫若全集?歷史編》(一)第477頁。
24《十批判書》第295頁。
25參見《十批判書》第299頁。
26《十批判書》第302頁。
27《郭沫若全集·歷史編》(一)第4頁。
28《我怎樣寫〈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十批判書》第489頁。
29《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歷史編》(一)第9頁。
30《先秦天道觀之進展》。《郭沫若全集·歷史編》(一)第359頁。
31《孔墨的批判》。《十批判書》第78頁。
32《青銅時代·后記》。《郭沫若全集?歷史編》(一)第6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