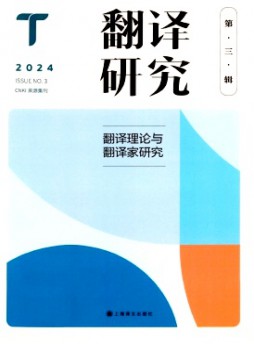翻譯實踐中再創的方式與體現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翻譯實踐中再創的方式與體現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翻譯是一門藝術,是一種再創造。正如法國文學社會學家Escarpit認為的那樣:“翻譯總是一種創造性叛逆。”著名教育家,翻譯家賀麟也曾說過,“翻譯為創造之始,創造為翻譯之成,翻譯中有創造,創造中有翻譯”。創造可以賦予原作以新的面貌、新的活力、新的生命,使其以新的形式與姿態面對新的文化與讀者。從美學角度而言,創造美可以說是翻譯藝術的本質特征。
縱觀中西方翻譯標準,以奈達、泰特勒為代表的西方譯者重“對等”或“等效”,以嚴復為代表的中國譯者重“信”,究其本質都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忠實于原文或原作者。但是,絕對地忠實原文,對原文亦步亦趨,非但不能將原文的意義和神韻客觀地傳達給讀者,反而會導致譯作貌離神散,不忠于原作的本質,辜負了讀者的審美期待。翻譯的再創造就是以看似不忠的手段,在新的文化語境和接受空間里對原文進行再創造,使原文的意義獲得再生,達到另一層次的忠實。
再者,不同的語言文字在發音、詞形、修辭、文體、思維習慣、文化背景、審美觀念方面相異甚遠,字、詞、句之間常無現成的對譯法可循。這就使得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需要像梁啟超所說的那樣,傷筋動骨地對原文“進行大膽的創造”,不僅傳達出原作的思想內容,而且還要再現原作的藝術意境,保留原作的美學價值,使之達到爐火純青、出神入化的境界,甚至營造出“出于藍而勝于藍”的效果,處處彰顯出美學的光芒。
創造性廣泛存在于文學翻譯中,一是讓目的語讀者較為容易地接受源語特有的文化方式和思維模式。ForrestGump這部經典影片被創造性地譯為“阿甘正傳”,而不是“弗雷斯特·甘普”。譯名借用了魯迅的《阿Q正傳》點出這部電影是傳記題材,既照顧了原片名,又點出了主人公的姓氏,堪稱中西文化合璧的經典。二是向目的語讀者介紹源語,包括源語的語言和文化知識。
在文學翻譯實踐中,創造有兩種不同的方式。
一、主觀性創造
主觀性創造即主動地創造,是指在脫離原語言形式的基礎上,按譯入語的音、形、義結合規律重新創作,從而準確甚至張揚地傳達原文的意美、音美、形美。《音樂之聲》中的歌曲“Doe-Ray-Me”部分歌詞如下:
Doe,adeer,afemaledeer/Ray,adropofgoldensun/Me,anameIcallmyself/Far,alonglongwaytorun/Sew,aneedlepullingthread/La,anotetofollowsew/Tea,adrinkwithjamandbread/Thatwillbringusbacktodoe
原譯:多,一頭鹿,一頭母鹿/來,一縷金色陽光/米,我這樣稱呼我自己/發,一條長長的路/索,一根穿線的針/拉,跟在索后面的音階/西,伴著果醬和面包來杯飲料/又將我們帶回了多改譯:朵,美麗的花朵/來,大家都快來/密,你們來猜秘密/發,猜中我把獎發/索,大家用心思索/拉,快點猜莫拖拉/體,怎樣練好身體/做茁壯成長的花朵
從歌詞的翻譯來看,原譯基本上是死譯原文的字詞,不能傳遞原文的妙處;而且從審美角度出發,原文是有諧音的,如此翻譯后韻味全無。改譯精巧構思,大膽拋棄了原文的字面意思,根據關鍵詞改造了表達結構。這才真正地忠實于原文的功能和目的,較完美地體現了意美、音美、形美,具有一定的寓意。
雙關語是翻譯中的一個難點,其在音、形、意上與漢語的不對等會影響到它的可譯性,要想在結構、表現形式、文化內涵完全不同的語言中找到類似的相關詞有很大的難度。例如,“—Whyistheriversorich?—Becauseithastwobanks.”如果翻譯為“—河流為什么很富有?—因為它有兩個河岸。”中國的讀者肯定會感到莫名其妙。如若翻譯為“—河流為什么很富有?—因為它年年有余(魚)啊!”,如此譯文甚為精妙,其所采用的諧音雙關表面上看似和原文格格不入,但在修辭效果上卻是一致的。
二、被動性創造
翻譯中的另一種創造則是因為兩種語言在轉換過程中有些無法逾越的困難,屬“不得已而為之”,是力求表達原意的基礎上,加入變通,即被動的創造。
田園詩人陶淵明《飲酒》中家喻戶曉的詩句:“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許淵沖的譯文堪稱經典:“Secludedheartmakessecludedplace.”寥寥數語,只一個“secluded”就使得整個詩句富于禪意,既創造出了相似的文本,又體現出了陶淵明的個性。
《紅樓夢》中有這樣一句話:“如今便趕著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個‘金蟬脫殼’的法子”。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先生譯為:“Well,it’stoolatetohidenow.Imusttrytoavoidsuspi-cionbythrowingoffthescent.”譯文中的“throwingoffthescent”使得“金蟬脫殼”更加傳神,流暢自然。
唐朝詩人元稹《行宮》中寫道:“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美國詩歌界漢詩英譯泰斗WitterBynner譯為:“Inthefadedoldimperialpalaces/Peoniesarered,butnoonecomestoseethem/Theladies-in-waitinghavegrownwhite-haired/DebatingthepompsofEmperorHsuan-tsung.”從表現手法來看,原詩是以樂景寫哀。詩句所要表現的是凄涼哀怒的心境,但卻著意描繪紅艷的宮花。Bynner不但譯出了宮花的“紅”,而且加上了peonies(牡丹),真是畫龍點睛之筆。末尾的“thepomp”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切合原意。
翻譯是一種創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譯不是原作的翻版,而是原作的再生,甚至還可以超過原作,將三流的原作譯為一流的名著。詩人惠特曼就認為弗雷里格拉(Freiligrath)翻譯的德語版《草葉集》遠遠地勝過他自己的原作。的確,創造性翻譯為解決許多文化差異上的矛盾和問題開啟了一種新的思維導向。然而,這種創造性絕對不能毫無止境、不經思索的亂用。余光中就認為翻譯是一種“有限的創作”,是表達技巧的創造。譯者當以忠實為本,避免“壞譯”、“誤譯”或“錯譯”。此外,譯者還需不斷提高自己的審美觀,提高對原文的審美判斷,從而提升自身創造性的審美品質,這樣譯出的文字才具有生命力,甚至流芳百世。